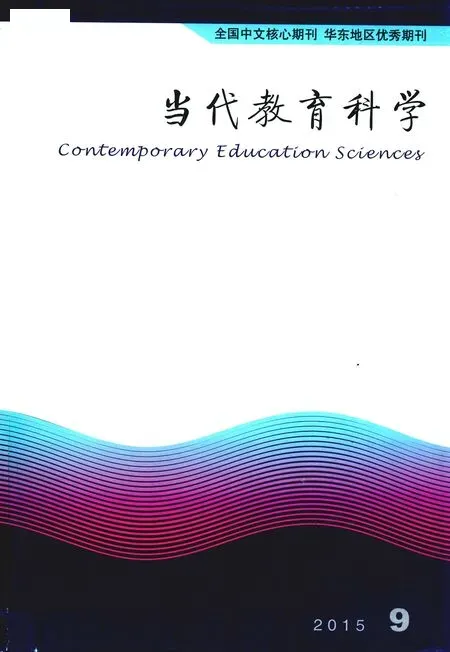后現(xiàn)代知識邏輯下的學(xué)術(shù)自由
●徐海波
后現(xiàn)代知識邏輯下的學(xué)術(shù)自由
●徐海波
學(xué)術(shù)自由是知識生產(chǎn)和科學(xué)研究的保障,學(xué)術(shù)自由有著知識層面的邏輯。作為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學(xué)術(shù)自由最初衍生于自治的知識。然而,后現(xiàn)代的知識觀至少在三個方面對學(xué)術(shù)自由產(chǎn)生了影響:知識自身邏輯的覆變;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轉(zhuǎn)向;知識生產(chǎn)場域的位移。在后現(xiàn)代知識邏輯下,學(xué)術(shù)自由面臨著合法性的重構(gòu)和外延的擴展,需要一種知識生產(chǎn)和應(yīng)用場域中學(xué)術(shù)自由的呼吁。
后現(xiàn)代;知識;學(xué)術(shù)自由
中世紀以降,大學(xué)在不斷遷移復(fù)制地過程中受到來自社會各方、意識形態(tài)以及民族文化的影響,其自身形態(tài)發(fā)生了分化。可以說,“任何類型的大學(xué)都是遺傳和環(huán)境矛盾作用的產(chǎn)物。”[1]學(xué)術(shù)自由同樣如此,其內(nèi)涵、理念及其制度隨著歷史的前行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學(xué)術(shù)自由賴以存在的知識論基礎(chǔ)卻一直延續(xù),這也是學(xué)術(shù)自由理念延綿不斷的原因之所在。知識的邏輯不斷發(fā)生變化,真理多元化,知識自反化。“不論是經(jīng)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一切都已經(jīng)去合法化的時代。”[2]學(xué)術(shù)自由的合法性基礎(chǔ)受到了人們的質(zhì)疑。而隨著知識的實用化,知識生產(chǎn)模式發(fā)生了轉(zhuǎn)向,知識生產(chǎn)場域也發(fā)生了偏移,我們只有從學(xué)術(shù)自由與知識論邏輯的哲學(xué)層面深思其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在知識自反與真理多元的后現(xiàn)代情境中,正視知識發(fā)生的變化,才能探明學(xué)術(shù)自由所受的挑戰(zhàn),辨清學(xué)術(shù)自由的未來。
一、學(xué)術(shù)自由的知識邏輯
在西方,學(xué)術(shù)自由理念幾乎貫穿整個歐洲思想史。作為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學(xué)術(shù)自由最先衍生于自治的知識。有學(xué)者認為,“學(xué)術(shù)自由的基礎(chǔ)是中世紀歐洲大學(xué)奠定的。”[3]此說法不無道理,然而這種論調(diào)卻忽視了作為觀念形態(tài)的學(xué)術(shù)自由。約翰·S·布魯貝克在探討學(xué)術(shù)自由的合理性時開篇明義地講道,“學(xué)術(shù)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個支點:認識的、政治的、道德的。”[4]他拋出了這樣一個論題: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還是真理是行使自由的先決條件。布魯貝克支持前者,認為學(xué)術(shù)自由的基礎(chǔ)是真理并不是先決完成的,而是在不斷地變化和完善。這種論述恰恰強調(diào)了其哲學(xué)知識論的本質(zhì)主義和基礎(chǔ)主義:真理一元,知識自治。事實上,關(guān)于真理的追求問題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蘇格拉底曾經(jīng)與智者學(xué)派有過爭執(zhí)。針對智者學(xué)派的相對主義,蘇格拉底認為有絕對真理,不會因人而異。柏拉圖同樣認為有絕對真理,那就是“善”的理念(不只是倫理或道德意義上的善,指宇宙的本質(zhì))。“亞里士多德常說許多聽過柏拉圖關(guān)于善的講演的人都有這樣的經(jīng)驗,每個人都以為他將被告知的善是財富、健康、權(quán)力這些驚人的樂事,但柏拉圖說的卻是數(shù)學(xué)、數(shù)、幾何和天文學(xué),并導(dǎo)向說明善是‘一’。”[5]古希臘的哲學(xué)家們并沒有形成實在的、具象的知識,而是傾向于對宇宙本源的認知,對道德和善的探討,但卻為后世奠定了追求真理的方法論:知識與真理的契合,具象與邏輯的統(tǒng)一。處于混沌狀態(tài)的知識其形態(tài)必然是統(tǒng)一性、整體性的,也是自治的。它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抽象的真理被哲學(xué)家們拿來懷疑和自由的討論,也就形成了觀念形態(tài)的學(xué)術(shù)自由。古希臘為后人定下了基調(diào):學(xué)術(shù)自由是探求真理的自由,這也構(gòu)成了學(xué)術(shù)自由的知識論基礎(chǔ)。當(dāng)時,哲學(xué)家和知識分子們探求真知的方式大多是講授和辯論,學(xué)術(shù)自由和廣義上思想、言論的自由無異。中世紀承古希臘、羅馬之遺風(fēng),其知識自治的形態(tài)并未發(fā)生太多的變化。但是,此時卻產(chǎn)生了對真理邏輯和學(xué)術(shù)自由造成巨大影響的兩種機構(gòu):教會和大學(xué)。隨著大學(xué)的產(chǎn)生,知識生產(chǎn)的場所和知識分子的活動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大學(xué)成為了知識分子籍以進行學(xué)術(shù)活動和抵制外界力量的制度性場所,而知識也隨之被封閉在大學(xué)中了。學(xué)者們不再像古希臘時期分散而游蕩,而是聚集在大學(xué)之中。知識生產(chǎn)和傳授也在大學(xué)這一唯一的場所中進行。世俗社會中再也不會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大眾哲學(xué)家了。與此同時,教會作為一種既扶助又控制大學(xué)的機構(gòu),不斷與大學(xué)進行博弈。受到教會的影響,中世紀的知識邏輯處于神學(xué)的一元框架之下,宗教知識成為地位最高的知識,統(tǒng)治了大學(xué)里的其他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學(xué)不越過不可碰觸的底線(宗教神學(xué)的合法性和正確性),教會便不會
侵犯師生的知識行為,學(xué)術(shù)自由可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大學(xué)也在教會和政府之間的博弈中漁翁得利。大學(xué)教師在有限度的范圍內(nèi)逐步爭取到教與學(xué)的自由。“除了哲學(xué)和神學(xué),其他學(xué)科的學(xué)術(shù)自由是普遍存在的。法學(xué)、醫(yī)學(xué)、文法和數(shù)學(xué)老師通常可以依據(jù)自己的意愿自由授課和辯論。”[6]中世紀大學(xué)的產(chǎn)生將學(xué)術(shù)自由與思想和言論自由區(qū)別開來,其知識論基礎(chǔ)發(fā)生了從道德知識觀到宗教知識觀的轉(zhuǎn)向。
現(xiàn)代大學(xué)的理念通過啟蒙運動和民族國家的興起而產(chǎn)生,“這種理念產(chǎn)生于那個時代流行的文化形式:文化的統(tǒng)一與文化價值的普遍性。19世紀堅信的重要信念是真理的可能性和知識的精神使命。”[7]大學(xué)從世界主義走向民族主義,教會對大學(xué)的控制已經(jīng)式微,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權(quán)體系也尚未建立,知識可以被自由的使用和流動。由于教會、神學(xué)對大學(xué)及知識的精神統(tǒng)治和道德制約逐漸消退,人們亟需一種新的真理取代物,那就是康德所說的理性。康德以理性的名義為學(xué)術(shù)自由和哲學(xué)系進行辯護,認為“哲學(xué)系必須被認為是自由的,只處于理性而不是政府的立法規(guī)范之下,因為它必須為它所要接受或承認的學(xué)說的真理負責(zé)。”[8]康德的二元論和接下來的哲學(xué)家們所形成的理性主義直接影響了德國的文化大學(xué),進而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不同于神學(xué)在精神上對于其他知識的外在統(tǒng)治和制約,理性是知識內(nèi)在的普遍統(tǒng)一原則。哲學(xué)取代神學(xué)成為當(dāng)時大學(xué)中的顯學(xué)。這種內(nèi)生的知識邏輯為學(xué)術(shù)自由提供了最強有力的佐證:知識本身即為目的。學(xué)術(shù)自由得以制度化。理性取代了信仰,唯理論接替唯實論。真理不再是已知的東西,而是需要人們?nèi)ヌ剿鳌⑷グl(fā)現(xiàn),教育的職責(zé)是培養(yǎng)學(xué)生發(fā)現(xiàn)真理的能力。而只有通過學(xué)術(shù)自由才能進行真理的探索。大學(xué)自此也就多了一項“嶄新”的職能:科研。這意味著一種新的知識模式:知識不再是簡單的傳遞和流動,而是進行更新和再生產(chǎn)。系科成為大學(xué)中重要的組織結(jié)構(gòu),是知識進行組織化生產(chǎn)的主要場域。大學(xué)完成了從與宗教的契約關(guān)系到與國家的契約關(guān)系的轉(zhuǎn)向。知識的形態(tài)向應(yīng)用性傾斜:由自治的、自由的知識變成實用的、組織化的知識。當(dāng)然,在德國古典大學(xué),“所謂的科學(xué)研究還只是‘純科學(xué)’的研究,當(dāng)時所謂的國家也只是一種文化共同體,尚非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因此,當(dāng)時的大學(xué)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并不突出,學(xué)術(shù)自由仍然沿襲中世紀大學(xué)的制度邏輯與治理系統(tǒng),被認為是學(xué)者行會自身的事情。國家既無干預(yù)的必要,也無介入的理由”。[9]
隨著現(xiàn)代性的進程,整個西方世界遭到科學(xué)和理性的“祛魅”。知識的實用性更加明顯,大學(xué)不再是紐曼眼中的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職業(yè)化的專門知識逐漸取得支配性地位。大學(xué)并沒有在民族國家的膨脹和功利主義中自保,專制國家?guī)缀跬耆刂屏酥R生產(chǎn),學(xué)術(shù)自由必然受到侵犯。這在廣泛參與政治活動的美國大學(xué)尤為明顯。無論是麥卡錫主義還是“冷戰(zhàn)”運動,都對學(xué)者及其學(xué)術(shù)活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另一個對學(xué)術(shù)自由產(chǎn)生影響的知識論是價值中立:大學(xué)在進行科研和學(xué)術(shù)活動時不應(yīng)表現(xiàn)出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見解。“一名科學(xué)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jié)之時。”[10]價值中立的原則并非限制學(xué)者的自由和活動,恰恰相反,它在學(xué)院和世俗領(lǐng)域之間劃分了一個平衡的界限,變相地保障了學(xué)者們的學(xué)術(shù)自由。然而,在實踐層面上,學(xué)院與世俗領(lǐng)域之間不斷密切地交往,科學(xué)知識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關(guān)鍵要素,大學(xué)也逐漸成為社會中的軸心機構(gòu)。知識具有了權(quán)力和財富的意蘊,大學(xué)中不斷增多的系科、專業(yè)反映了社會的需要。為了追求成績,爭創(chuàng)一流,學(xué)術(shù)泰勒主義和學(xué)術(shù)資本主義橫行,大學(xué)成為一種類企業(yè)學(xué)術(shù)共同體。而深具實用主義傳統(tǒng)的美國成為這種一流大學(xué)的溫床。大學(xué)可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卻不能在經(jīng)濟上保持自主。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xué),更多地要建立與企業(yè)和國家之間的契約關(guān)系。后現(xiàn)代的知識狀態(tài)發(fā)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對學(xué)術(shù)自由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二、覆變、轉(zhuǎn)向與位移:后現(xiàn)代知識狀態(tài)
晚近各種科學(xué)和技術(shù)的發(fā)展沖擊著知識的領(lǐng)域,也產(chǎn)生了后現(xiàn)代知識觀,其中首沖的是對真理的否定,對知識本質(zhì)的再定義。哈貝馬斯在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最終盲動性地對一切宏大敘事和元話語進行了去合法化。而70年代在法國興起的后現(xiàn)代運動也激進地對現(xiàn)代性中的敘事性思考方式和抽象本質(zhì)的意義進行解構(gòu)和否定,這不僅僅包括真理、理性、正義等作為現(xiàn)代社會知識體系架構(gòu)的根基,還包含著體系內(nèi)部所形成的文化和生產(chǎn)方式。然而,激進地推行反基礎(chǔ)主義和相對主義,勢必導(dǎo)致一種文化的虛無化和民主的無政府狀態(tài),這必然不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家們想要看到的結(jié)果。事實上,無論是德里達還是利奧塔,都試圖將現(xiàn)代性納入到后現(xiàn)代的范疇之中,“后現(xiàn)代主義最終演變成一種文化分裂的哲學(xué),并不是現(xiàn)代性的毀滅,而是在承認差異的基礎(chǔ)上重建意義的新的可能性。”[11]后現(xiàn)代知識觀對學(xué)術(shù)自由造成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內(nèi)部邏輯的覆變、生產(chǎn)模式的轉(zhuǎn)向和生產(chǎn)場域的偏移。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是具有解放能力的,其內(nèi)在價值在于可以被組織化并成為社會基礎(chǔ)。后工業(yè)社會則通過商業(yè)化和工具化來分化知識,知識
與文本無異,知識的應(yīng)用成為知識價值之所在。伴隨著知識的廣泛傳播與應(yīng)用,其自身越來越關(guān)注如何去適應(yīng)和競爭,而喪失了對社會的責(zé)任和意義,知識生產(chǎn)模式轉(zhuǎn)而成為一種應(yīng)用的、跨學(xué)科的和績效管理的模式。大學(xué)和知識的先天血緣關(guān)系開始消弭,面臨著一種身份認同的危機,知識生產(chǎn)場域發(fā)生位移。學(xué)術(shù)自由作為大學(xué)中追求知識的基本理念,不得不面臨著合法性危機與重新解構(gòu)的必要性。
(一)知識內(nèi)部邏輯的覆變
知識社會學(xué)將知識從純粹的哲學(xué)認知推向了社會領(lǐng)域,否定了知識的自治性和真理的一元性,對現(xiàn)代性所建構(gòu)的知識與社會規(guī)范相分離的、形而上的、神圣而高貴的特性進行了顛覆。這成為現(xiàn)代性通向后現(xiàn)代性的推動力。在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家眼中,現(xiàn)代社會中的“立法者”所壟斷的真理的確定性遭到質(zhì)疑,理性思想的傳播旨在建立和鞏固一個有序的社會。理性與知識并沒有起到啟蒙民眾的作用,而是教化和規(guī)訓(xùn)。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知識與權(quán)力的共生關(guān)系——一種由知識分子與國家統(tǒng)治者所玩弄的語言游戲。“‘知識/權(quán)力’關(guān)系顯現(xiàn)為一種無限的自我生長的機制,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它就不再依賴最初的動機,它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使自身得以進一步延續(xù)并發(fā)展壯大的條件。”[12]知識被工具化,它既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后現(xiàn)代批判的對象是真理一元而非真理,批判的是現(xiàn)代性中被知識分子和統(tǒng)治者所壟斷的真理的確定性和普遍性。由于不確定性所導(dǎo)致的恐懼,人們求諸于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對不確定性進行了解釋和闡述,掌握并壟斷了知識運行機制和驗證方法,成為真理和知識的代言人,這就是知識擁有者的權(quán)力。這也就成為國家取代宗教實行牧人式權(quán)力的手段。故在后現(xiàn)代情境中,人們發(fā)出一種異質(zhì)性、多元性的吁請。德里達的解構(gòu)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察視角:知識等同于文本。真理成為一種話語權(quán)。利奧塔則順延了知識性質(zhì)在流通和應(yīng)用層面上的變化,認為在知識社會和經(jīng)濟全球化的情境下,“知識的本質(zhì)不改變,就無法生存下去,只有將知識轉(zhuǎn)化為批量的資訊信息,才能通過各種新的媒體,使知識成為可操作和運用的資料。甚或可以預(yù)言,在知識構(gòu)成體系內(nèi)部,任何不能轉(zhuǎn)化輸送的事物,都將被淘汰。”[13]在這種邏輯下,知識不再是自治的而是一種自反性的存在,知識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人們更多地看到了知識的價值性和工具化。在過去,知識指向于實在的客體比如人、自然和社會的世界,而現(xiàn)在知識越來越按自身行事,直到社會完全地科學(xué)化。由于科學(xué)知識變得越來越必需,非壟斷化和解神秘化出現(xiàn)了,知識越來越面臨自身產(chǎn)生的問題,知識不僅僅解決問題也成為了問題的產(chǎn)生者。由于知識不再是普遍的、客觀的,也就不能成為全人類的“公共財富”,而是個人的利益和手段,那么現(xiàn)代知識中的“價值中立”原則也自然不再成立。后現(xiàn)代知識觀中的知識是價值有涉的。無論是人文知識還是科學(xué)知識,任何知識的生產(chǎn)、應(yīng)用都滲透著利益取向和價值偏向。
自反性的知識觀所引發(fā)的震蕩是全面的,學(xué)術(shù)自由必然在列。由于科學(xué)的全面凱旋,理性和真理已經(jīng)失去了合法性基礎(chǔ),不再是知識的終極意義。“科學(xué)已經(jīng)從服務(wù)于真理的活動轉(zhuǎn)為沒有真理的活動。”[14]真理變得多元,每個人或組織都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追求自己的“真理”,學(xué)術(shù)自由的合法性基礎(chǔ)——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面臨著挑戰(zhàn)。知識的價值有涉性否定了一直以來對學(xué)術(shù)自由起到保障作用的中立原則。學(xué)術(shù)自由逐漸被架空,成為一種虛無縹緲的、自反的存在,喪失了直接的指涉物。傳統(tǒng)上學(xué)術(shù)自由所指涉的學(xué)者免于外界干涉的內(nèi)涵便顯得不夠用了。后現(xiàn)代的復(fù)雜性增加了學(xué)術(shù)自由合法性重構(gòu)的難度,我們無法再從大學(xué)中知識自治的角度去探討學(xué)術(shù)自由。
(二)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轉(zhuǎn)向
在知識社會中,更廣泛范圍和更深內(nèi)涵的知識應(yīng)用成為可能。知識應(yīng)用的重要性更甚于知識生產(chǎn),知識生產(chǎn)更多地是知識在應(yīng)用的情境中進行再創(chuàng)造,科學(xué)研究和知識生產(chǎn)趨向于實用性的目的和價值,并將承擔(dān)更多的社會責(zé)任而呈現(xiàn)出自反性的特征,也就是由知識生產(chǎn)模式1到知識生產(chǎn)模式2的轉(zhuǎn)向。在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模式1中,知識主要在組織化的學(xué)科中通過標準化的認知活動而生產(chǎn)出來,而在知識生產(chǎn)模式2中,知識則在一個更廣闊的、跨學(xué)科的社會和經(jīng)濟情境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知識生產(chǎn)模式2有幾個特征:問題導(dǎo)向的、跨(超)學(xué)科的、異質(zhì)的和自反的。模式2所描述的是一種“社會彌散的知識生產(chǎn)體系”。[15]首先,知識生產(chǎn)不再以學(xué)科為中心,而是以應(yīng)用情境中的實際問題為中心,知識生產(chǎn)向全社會彌散,不再以學(xué)科中的個人興趣為導(dǎo)向,而是以實際應(yīng)用為導(dǎo)向。其次,由于問題的復(fù)雜性和應(yīng)用的可行性,知識生產(chǎn)是跨(超)學(xué)科的,然而跨學(xué)科之后還是學(xué)科,實際上也就并非在學(xué)科中進行。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力量如教授、學(xué)術(shù)團體、大學(xué)系科不再是知識生產(chǎn)的動力和權(quán)威,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職業(yè)中的行業(yè)規(guī)范和文化精神式微,短期的學(xué)術(shù)團體更受歡迎,它們因問題產(chǎn)生而產(chǎn)生,問題完成而解散,動態(tài)而靈活地進行協(xié)作、互動。再次,知識生產(chǎn)的異質(zhì)性表現(xiàn)在知識生產(chǎn)機構(gòu)和交流方式的多樣化。由于問題的突發(fā)性和效率的要求,知識生產(chǎn)場所可以直接在應(yīng)
用場域中選擇。不同學(xué)科的個人則是短暫性地進入組織進行學(xué)術(shù)活動,而溝通方式也隨著網(wǎng)絡(luò)和信息化的發(fā)展而變得多樣化。最后,知識生產(chǎn)滲透著社會問責(zé),由于科學(xué)發(fā)展對社會環(huán)境會產(chǎn)生影響,越來越多的團體希望能夠參與到科學(xué)研究活動中來,以反思它所產(chǎn)生的問題。
雖然知識生產(chǎn)模式2遭到了學(xué)術(shù)界的批評和質(zhì)疑,吉本斯本人也傾向于將這種模式視為一種趨勢而非事實。然而,當(dāng)今知識生產(chǎn)中確實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上述的特征。比如,科學(xué)研究越來越多地摻雜著企業(yè)、政府甚至是全人類的利益,早期的以教授個人為中心的“小科學(xué)”被學(xué)術(shù)團體的“大科學(xué)”所取代,當(dāng)今社會或者自然領(lǐng)域中復(fù)雜性的問題已經(jīng)不能允許個人單獨進行科研活動。傳統(tǒng)的學(xué)科必然也會隨著新的問題的出現(xiàn)而不斷更新、再造。而由科學(xué)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和自然問題也都將矛頭對準科學(xué)研究本身。在這種情境下,科學(xué)研究將會有計劃、有選擇地進行,需要強調(diào)績效的管理和責(zé)任的反思。學(xué)術(shù)自由將被眾多利益相關(guān)者(如企業(yè)、政府、社會人士)共同決定和治理,而不再限于學(xué)術(shù)職業(yè)。知識生產(chǎn)的異質(zhì)性將學(xué)術(shù)自由引向一種權(quán)利關(guān)系,屈從于利益和實際問題,學(xué)術(shù)自由的保障將成為水中月、鏡中花。
(三)知識生產(chǎn)場域的位移
在現(xiàn)代社會中,大學(xué)一直作為知識生產(chǎn)的主要場所。然而,隨著知識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到來,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轉(zhuǎn)向,知識的生產(chǎn)和應(yīng)用不再處于分離狀態(tài)。大學(xué)中不斷增加的系科、跨學(xué)科已經(jīng)難以滿足知識社會的需求,系科的地位開始衰退,大學(xué)已經(jīng)失去了作為主要知識生產(chǎn)場所的地位。“在全球化和經(jīng)濟生產(chǎn)自反性方法應(yīng)用的狀況下,知識生產(chǎn)的場所正從大學(xué)轉(zhuǎn)向廣闊的非大學(xué)領(lǐng)域,如工業(yè)實驗室、研究中心,智囊團和咨詢機構(gòu)。后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不斷生產(chǎn)和傳播知識的‘知識社會’。”[16]由于大規(guī)模的知識生產(chǎn)和新管理主義的盛行,引發(fā)了大學(xué)、產(chǎn)業(yè)和政府的合作與競爭。一方面,企業(yè)與大學(xué)之間的交互增多,企業(yè)與大學(xué)合作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出于對研發(fā)成本、技術(shù)標準和不同研究領(lǐng)域的考慮,企業(yè)之間相互合作進行研發(fā)也成為可能。隨著科學(xué)研究不斷地進入社會領(lǐng)域,社會中的幾乎每個組織都在構(gòu)建自洽的文化或者理念,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yè)、跨國公司變得像一所大學(xué)。它們創(chuàng)辦培訓(xùn)機構(gòu)、實驗室和研究所,培養(yǎng)先進的企業(yè)文化和管理方式,在垂直的合作和水平的競爭中進行科學(xué)技術(shù)的創(chuàng)造和利用。然而,大學(xué)卻在丟失自己的理念。伴隨著經(jīng)濟和知識全球化的進程,大學(xué)在進入市場的過程中其自身角色發(fā)生了變化。大學(xué)正在逐步喪失文化公民身份,變成一種類企業(yè)共同體。學(xué)術(shù)資本主義和績效管理制度在大學(xué)風(fēng)行。甚至有學(xué)者認為,“大學(xué)不只是像一個企業(yè);它就是一個企業(yè)。一流大學(xué)的學(xué)生不只是像顧客;他們就是顧客。”[17]可以斷言,隨著這種趨勢的明朗化,學(xué)科與產(chǎn)業(yè)、大學(xué)與企業(yè)、科學(xué)家與知識從業(yè)者的差異將會變得愈來愈小。
由于大學(xué)與企業(yè)角色的變化,大學(xué)不再被視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機構(gòu)。大學(xué)越來越與企業(yè)其他組織同等對待,大學(xué)和企業(yè)、政府之間的交互愈發(fā)頻繁,其內(nèi)部的專業(yè)人士越來越具有其他職業(yè)從業(yè)者的特征,而不再被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職業(yè)規(guī)范所羈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異質(zhì)的知識生產(chǎn)活動中,當(dāng)學(xué)者被招納入一個新的組織環(huán)境中時,學(xué)術(shù)價值觀勢必處于劣勢。在大學(xué)外部學(xué)術(shù)自由并不是制度化的存在,也不會作為一種必需的理念規(guī)范。學(xué)術(shù)自由向來產(chǎn)生于大學(xué)內(nèi)部,與大學(xué)自治互為犄角。而當(dāng)今,無論是大學(xué)內(nèi)部,還是社會中的知識生產(chǎn)場域,都面臨著學(xué)術(shù)自由消退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應(yīng)該將學(xué)術(shù)自由與大學(xué)的血緣關(guān)系割斷,轉(zhuǎn)而從學(xué)術(shù)自由與知識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中出發(fā),或許可以為學(xué)術(shù)自由更廣泛地進入實踐領(lǐng)域找到理由。
三、學(xué)術(shù)自由的重構(gòu)與擴展
后現(xiàn)代知識觀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宏大的知識范疇與社會情境相關(guān)聯(lián)的敘事方式,徹底改變了人們對知識的先驗性認識。然而事實上,后現(xiàn)代是以現(xiàn)代的高度發(fā)展為基礎(chǔ)的,與其說后現(xiàn)代是對現(xiàn)代的顛覆,不如說是超越。后現(xiàn)代知識觀并非推翻現(xiàn)代世界所建立的高度理性化、科學(xué)化的知識帝國,而是在此基礎(chǔ)上重構(gòu)知識體系,以求適應(yīng)變化,規(guī)避風(fēng)險。知識生產(chǎn)模式2完全可以和模式1并存,而大學(xué)也不可能被其他知識生產(chǎn)機構(gòu)所取代。知識的自身邏輯、生產(chǎn)模式和生產(chǎn)場域都是建構(gòu)在現(xiàn)代性的成年的基礎(chǔ)上所發(fā)生的轉(zhuǎn)向,而它所帶來的影響也并非顛覆性的,而是反思性的,是在自身高度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的反思。學(xué)術(shù)自由所受到的影響概莫能外。在普遍發(fā)生嬗變的知識社會中,學(xué)術(shù)自由不做出改變就很難生存下去,只有重構(gòu)學(xué)術(shù)自由的合法性,擴展學(xué)術(shù)自由外延,才能滿足知識生產(chǎn)和科學(xué)研究的需要。
(一)合法性的重構(gòu)
事實上,學(xué)術(shù)自由一直以來與大學(xué)、追求真理聯(lián)系在一起。大學(xué)是追求客觀真理和正義的地方,而學(xué)術(shù)自由則是追求真理的保障。后現(xiàn)代知識邏輯的嬗變,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學(xué)術(shù)自由的合法性。“在邏輯上,真理多元化是學(xué)術(shù)自由的基礎(chǔ),真理一元化
限制學(xué)術(shù)自由好像是對的,但現(xiàn)實中未必如此。”[18]在后現(xiàn)代知識邏輯下,學(xué)術(shù)自由更加應(yīng)該得到強調(diào)和重視。隨著真理多元化知識不斷進入社會,高等教育開始喪失了對知識的壟斷權(quán),我們不應(yīng)再從機構(gòu)層面上狹隘地探討學(xué)術(shù)自由,而應(yīng)該從個體和知識的層面上保障學(xué)術(shù)自由。追求真理成為每個人的事情,每個人的可能。價值有涉的知識使人們可以站在任何立場考慮問題,知識不再有等級之分,而只是領(lǐng)域之別。“無論在什么地方,一旦有人將自己的個人存在和學(xué)術(shù)存在融為一體,學(xué)術(shù)自由就會證明自己的價值。他們將變成一個時代的代表精神,在這個時代里,恰恰是他們對于歷史力量的意識使他們從對自己時代的或明或暗的依賴中超脫出去。”[19]學(xué)術(shù)自由歸根結(jié)底是人的自由,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那么,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說,學(xué)術(shù)自由已經(jīng)完全脫離大學(xué)了呢?實不盡然。正如大學(xué)逐漸從知識工廠變?yōu)榻煌膱鏊瑢W(xué)術(shù)自由也將在大學(xué)里面最集中地顯現(xiàn),以大學(xué)為根基。即便是后現(xiàn)代哲學(xué)家德里達在談及學(xué)術(shù)自由的時候也是“無條件”地肯定了大學(xué)基于探索真理的獨立和自由,而真理的本質(zhì)也應(yīng)該是無任何先決條件的。后現(xiàn)代并不批判真理,而是真理一元。可見,“‘真理’并不是能用后現(xiàn)代語言就可以消解掉的,盡管提出來的問題可能與各種權(quán)力相關(guān)的,但提問的方式是絕對自由的。”[20]因為現(xiàn)代已經(jīng)被包含于后現(xiàn)代,現(xiàn)代意義上的真理成為后現(xiàn)代真理的一種。在這種異質(zhì)性的邏輯下,與其說學(xué)術(shù)自由喪失了合法性,不如說學(xué)術(shù)自由擴展了外延,延伸為一種知識社會中對知識和人的普遍理念。
(二)外延的擴展
隨著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轉(zhuǎn)向和知識生產(chǎn)場域的位移,在機構(gòu)層面上我們不能再將學(xué)術(shù)自由僅僅局限于大學(xué),而應(yīng)擴展到所有知識生產(chǎn)場域。學(xué)術(shù)自由不僅僅是一項權(quán)利,也具有了責(zé)任的意蘊。知識生產(chǎn)場域的擴大,必然使得大學(xué)里的學(xué)者走向社會與企業(yè)合作,或者干脆變身知識從業(yè)者。受到利益的侵蝕和價值的導(dǎo)向,學(xué)術(shù)精神不得不屈從于企業(yè)精神,文化不得不屈從于金錢。社會不斷處于科學(xué)所制造的問題的危險之中,知識的反思性難以制度性地保障。不會存在任何法律或者制度來約束社會(尤其是企業(yè))中的學(xué)術(shù)活動。學(xué)術(shù)自由至少應(yīng)該是規(guī)避風(fēng)險、反思知識的一個途徑。正如希爾斯所言,“學(xué)術(shù)自由的理由源于一種特殊的價值,即作為一種利益的人類生活中真理的價值,它既有自身的利益,也能導(dǎo)致其他的利益。”[21]這里我們就應(yīng)該看到學(xué)術(shù)自由自身存在的兩面性:做什么的自由和不做什么的自由。學(xué)術(shù)自由向來不是完整的,而是有限的。傳統(tǒng)大學(xué)中追求知識的都是出于個人興趣的學(xué)者,學(xué)術(shù)自由自然由學(xué)者自身去考量,這依賴于學(xué)者的價值中立和無立場。隨著問題導(dǎo)向的知識生產(chǎn)的出現(xiàn),其他知識生產(chǎn)場域并沒有內(nèi)化在知識追求中的學(xué)術(shù)自由,也就沒有不做什么的自由。要知道隱性的、內(nèi)部的對學(xué)術(shù)自由的侵犯要比顯性地侵犯危險得多,自由和限度是相生相克的兩個事物,自由的一個內(nèi)在原則就是作為主體的個人所希望的限制不存在,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由的邊界。沒有絕對意義的自由,對自由的限制是為了獲得更大范圍的自由。強調(diào)學(xué)術(shù)自由,也就是在強調(diào)知識生產(chǎn)所應(yīng)該受到的限制。新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需要在更廣范圍、更多場域中呼喚學(xué)術(shù)自由。
[1][英]阿什比,E.科技發(fā)達時代的大學(xué)教育[M].滕大生,滕大春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2][7][11][16][英]杰勒德·德蘭迪.知識社會中的大學(xué)[M].黃建如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163,32,160,127.
[3]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卷8)[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728.
[4][美]約翰·S·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xué)[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6.
[5]周采.柏拉圖的未成文學(xué)說與書寫批判及其教育意義[J].清華大學(xué)教育研究,2011,(1).
[6][美]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學(xué)的興起[M].王建妮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44.
[8][德]伊曼努爾·康德.論教育學(xué)[M].趙鵬,何兆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9.
[9]王建華.學(xué)術(shù)自由的緣起、變遷與挑戰(zhàn)[J].清華大學(xué)教育研究,2008,(4).
[10][德]馬克思·韋伯.學(xué)術(shù)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M].馮克利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38.
[12][英]齊格蒙·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與知識分子[M].洪濤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
[13][法]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xiàn)代狀況:關(guān)于知識的報告[M].島子譯.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7:35.
[14][德]烏爾里希·貝克.風(fēng)險社會[M].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205.
[15][英]邁克爾·吉本斯.知識生產(chǎn)的新模式:當(dāng)代社會科學(xué)與研究的動力學(xué)[M].陳洪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10.
[17][加]比爾·雷丁斯.廢墟中的大學(xué)[M].郭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21.
[18]王建華.學(xué)術(shù)自由的緣起、變遷與挑戰(zhàn)[J].清華大學(xué)教育研究,2008,(4).
[19][德]卡爾·雅斯貝爾斯.大學(xué)之理念[M].邱立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5.
[20]林杰.西方知識論傳統(tǒng)與學(xué)術(shù)自由[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0:228.
[21][美]愛德華·希爾斯.學(xué)術(shù)的秩序[M].李家永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310.
(責(zé)任編輯:劉丙元)
徐海波/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科學(xué)學(xué)院教育史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從事外國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