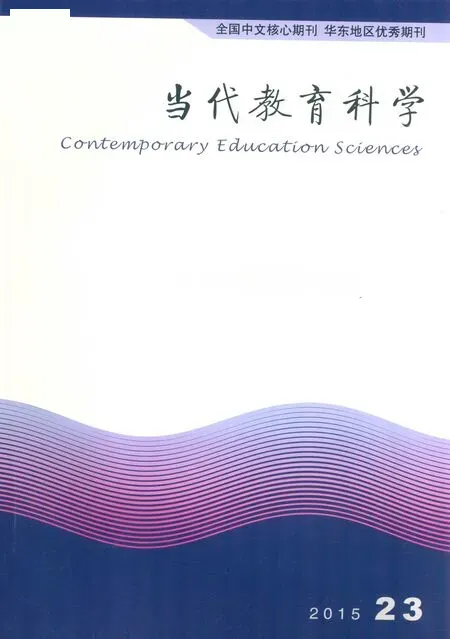高校社會服務倫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其超越*
●李天源 薄存旭
高校社會服務倫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及其超越*
●李天源 薄存旭
當前,社會中存在多種不良因素,導致高校社會服務倫理面臨諸多現實困境:對導引精神的偏執動搖著社會服務倫理的取向;對預期目標的盲視拓深著社會服務倫理的偏差;對服務對象的偏好影響著社會服務倫理的基調。因此,確定良好倫理秩序,不但有利于呼喚高校文化自覺,解除高校功利性發展困境,而且還可以合理確定高校社會服務的角色,并正視教育服務的能力限度。
高校;社會服務;倫理取向
當前社會中存在著多種因素導致高校社會服務活動失去了對本有倫理精神的堅守。因此,明晰高校社會服務面臨的現實困境,了解其超越訴求,對于確定合理的倫理標準、引導合乎倫理的行為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高校社會服務倫理面臨的現實困境
高校社會服務活動本應秉持的倫理精神和具體價值標準在當前中國社會中遇到了諸多阻礙因素,對此,我們可以從其導引精神、預期目標、服務對象和自身屬性等方面加以審視。
(一)對功利的追逐動搖著社會服務的倫理根基
高校社會服務所需面對的第一道倫理難題即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崇高精神訴求與現實利益間的沖突。無可回避的問題是,當前功利主義幾乎充斥著高校社會服務的一切領域,大多數服務活動更注重經濟利益的實現,偏離了學術性與社會價值。我國高校社會服務活動正是在利益的驅使下發展起來的,大多數高校的社會服務并不是根據自身實際條件開展的,而是取決于社會服務所帶來的效益回報,這對高校正常教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都產生了不小的沖擊。高校社會服務不但已脫離原有的對學術自由、獨立精神與促進社會進步的追求,異化為新的牟利手段,而且喪失了原有的思想與文化精神家園身份,[1]最終臣服于經濟等外部利益。
(二)對預期目標的盲視導致社會服務的倫理偏差
自威斯康星大學確定了高校社會服務的辦學職能后,世界其他國家的高等院校紛紛仿效這一辦學模式,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校學術成果的轉化速度,使服務對象在經濟等方面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高校社會服務到底應以什么作為行動依據?應該遵守哪些道德原則、規則或法則?哈佛大學原校長博克在其《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一書中,重新反思了高校的社會責任。他憂心忡忡地看到,社會服務活動不但深刻影響到了高校的學術自由,而且對學校自治與國家要求、大學目的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時代性挑戰。[2]當前,中國高等教育界對高校走出象牙塔,走進企事業機構進行服務的呼聲不斷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高等院校辦學模式的變革,但一旦論及到上述倫理問題,我們很顯然無法給出清晰的答案。
當前中國大陸高校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將社會服務確定為基本辦學職能之一,至于社會服務活動能給自身和服務對象帶來何種影響,這個多不在其考慮范圍之內,因為它們往往出于政治、經濟利益需求,而忽略社會服務本身的風險問題。因此,很多高校的社會服務活動具有較強的盲目性與隨意性,并且對后發不良結果也往往缺乏應對意識和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相關人員和機構并不把服務倫理納入到評價服務活動的標準中,由此使服務倫理陷入混亂之中。
(三)對服務對象的偏好影響著社會服務的倫理取向
高校社會服務活動對象的擇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相關人員、機構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進而影響著社會服務活動的倫理取向。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遵循著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的發展模式在當前社會遇到了效益和倫理方面的雙重否定,社會弱勢群體必須得到良好的關照,即使一向秉持個體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也為此展開了不懈努力,比如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論點就是差異補償原則和機會均等原則。因此,作為社會現實批判者和未來引領者的高校,在其社會服務活動中自然應當秉承這一原則。
當前,由于功利主義大行其道,追求整體經濟數字成為評判高校社會服務活動的基本指標,因此,中國高校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在政治權力上處于強勢地位的政府,在經濟地位上處于強勢的產業界,在社會地位上處于優勢的學習者,而處于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卻未能很好地享受到這一資源。這一現實在很大程度上使服務者與服務對象之間應該秉承的良性關系因經濟、政治利益而遭到人為分割,影響著當前高校社會服務活動的倫理取向。
二、高校社會服務倫理困境的超越
高校社會服務活動的倫理價值追求雖然在現實中遭遇了諸種不利影響,但時代發展則要求高校必須超越這一困境,這不但是高校歷史使命使然,也是高校自身健康發展的必然訴求。
(一)呼喚高校的文化自覺
根據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所謂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3]文化自覺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4]
大學擔當反思社會和引領社會的使命,是一個民族自身的精神存在的證明。在我們今天這個由世俗化原則所規定的時代中,對于一個民族的精神存在的最大威脅恰恰來自大學自身的現代性狀況。被現代性狀況所壓抑著的東西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覺,而守護民族文化自覺的最后陣地原本就是大學。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大學在它的現代性趨向中所包含的根本困境。[5]高校社會服務的首要目標并不是為社會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而是對自我文化進行充分覺醒,勇敢承擔起為生民立命的社會責任。
(二)解除高校功利性發展困境
以功利主義為行為導引,高校在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時往往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為了獲取經濟、政治利益,很多服務活動僅僅以滿足服務客體的眼前利益為目標取向,這就使高校社會服務的社會意義大大降低,這不但使高校深陷唯利是圖的漩窩之中,而且丟棄了自身的文化品性,遮蔽了高校承擔社會責任的應然渠道和途徑。因此,對高校社會服務倫理進行深度反思,審慎對待高校社會服務的后果,在科技理性、管理技術主義大行其道的洪流中,思慮行為之善惡,匡正高校社會服務活動的價值取向,糾正行為偏差,為高校社會服務活動尋求到有效的倫理價值依據,是當今高校健康發展并真正履行自己社會責任的必然訴求。
(三)合理確定高校社會服務角色
角色是“處于一定社會地位的個體,依據社會客觀期望,借助自己的主觀能力適應社會環境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6]由此可見,高校社會服務所承擔的角色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社會的期望,其二是自身的主觀意識和能力。能否選擇恰當的角色并能有效扮演這一角色,需要兩方面相互結合,無論只顧及其中的哪一方,都是難以有效承擔起其職責的。從現實來看,當前高校在確定自身職責時更多的是顧及社會期望和要求,并沒有很好地審查自身的條件和能力,因此,在扮演相應角色時,經常發生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唯外界要求是從;二是在無法達到自身原定目標和社會需求時,社會服務活動或是流于形式,或是退回原有的教學和科研職責。這無論是對于自身獨立性的保持而言,還是對于社會責任的承擔來說,都是不利的。究其原因,我們可以發現,高校服務活動的倫理出發點偏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此,高校對自身社會服務角色定位的混亂現實,要求必須對其倫理規則加以厘定。
(四)正視教育服務能力限度
高校社會服務的“正功能并不是無限的,而是有一定的限度”。[7]當盲目樂觀加大對高校的投入并開展更多合作時,產業界發現他們并不能完全如愿地從投入或合作中取得預期的高額利潤回報;而高校自身也并沒有在社會服務中獲得那么多讓人振奮的預期結果。這是因為,產業界以是否有足夠的利潤來判斷合作項目的價值與意義,關注的是應用性,而高校則在很大程度上以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和社會進步意義來判斷合作項目的價值與意義。因此,高校社會服務活動必須在兩者之間尋求合適的默契度。[8]從中國高校辦學的現狀來看,學校在設備、師資和財力等資源上都是比較匱乏的,以現有資源維持基本的教學和科研對于許多高校而言都顯得有些吃力,再要求高校師生走出校園為社會提供服務,這就是一件更為艱巨的事情。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為改變現狀而追逐短期利益,各種違背服務倫理的行為自然就會經常出現。從這一思路來講,高校現實能力的限度要求我們必須正視服務倫理,但是反轉這條思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如果我們能夠確定了合理的服務倫理標準,那么就可以較好地認清教育服務社會的能力限度,使政府機構、產業界、高校管理者以及高校師生清晰地認識到服務活動的功效,并以合理的態度和方式理性對待之。
[1][8]薄存旭.高校社會服務倫理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6-7,14.
[2][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現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J].徐小洲、陳軍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5.
[3]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4]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J].思想戰線,2004,(2).
[5]王德峰.通識教育與中國大學的文化自覺[J].新華文摘,2009,(7).
[6]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行為研究[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61.
[7]張人杰.教育與社會變遷的關系的理論之質疑——兼論教育的負功能[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2,(3).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從功利主義到公共責任:我國當代學校改革的價值范式轉換研究”(課題批號:CFA120127)階段性成果。
李天源/內蒙古大學滿洲里學院講師 薄存旭/臨沂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劉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