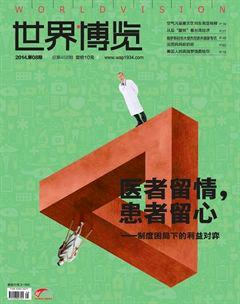懷念香港舊時繁華
牛篠剛
到一個地方旅游,無非是去發現那里的優點。但漸漸地,去發現缺點也成了旅游的重要內容,雖然有時是被動的。我去香港,通行證上毫不含糊地注明了行程性質:個人旅游。定位是準確的,但我還是想強調自己是去會友,我不大愿意有一個“大陸游客”的身份。
周圍的人都勸我最好不去。關于香港,近來全是負面消息。這個中國的特區,似乎正在發酵一種城市情緒:排外。不,是排大陸人。據說港人的不滿或不屑,已經寫在服務行業人員的臉上了。朋友的勸阻同樣以情緒結束:犯賤啊?給人“送錢”還叫人罵。
在國際上是“中國人”,在特區香港,我們則被進一步細分定位,叫“大陸人”或“陸客”。大陸人到香港干什么呢?買房子,據說炒高了房價;生孩子,據說港人的福利大鍋里伸進來許多筷子勺子;買奶粉,據說香港幼兒都得憑票供應了;破壞那里百年來英國人訓練出來的文明習慣,比如不排隊,橫穿馬路,小孩在公共場所小便、進食、大嗓門吵鬧。我的列舉不全面,種種不堪都在那首《蝗蟲歌》中。
陸客確實不堪嗎?
我1994年到珠海工作,僅在1996年年底去了澳門。香港雖然相距僅36海里(合67多公里),但一直以來感覺并不容易于出國。還有,那里確實不吸引我。
我們從中港城下船出境,一開始“大陸”味道濃烈:普通話的喧嘩,滿眼都是與國內無區別的服飾和旅行包;步行去地鐵站,走出幾百米,忽然間就消散難尋了。一路走,沒有人圍上來對我們唱歌;問路,回答者都匆忙,但也文明、耐心。我懷疑是妻子的廣東話的效果——她是廣東人,又在一家澳門老板手下做事,早已學得一口港澳味的好鳥語。
其實只需步行三五分鐘,香港之所以是香港而不是內地繁華城市,就能感受得到。不過,我已是中年人,我懷疑自己的閱歷和心境會讓視聽遲鈍,從而將感受性降格,于是詢問不滿五歲的女兒,“香港和珠海哪里不一樣啊?”她立即答道,“我發現有很多外國人。”她是對的,所謂“國際化”確實是第一感。又走了一會,她悄悄對我說,“爸爸,我發現很多女人打扮得很奇怪。”這就有點讓我驚奇了。她所說的,是包著頭巾的伊斯蘭馬來或印尼女子。“奇怪”這一判斷,以及她的謹慎語調,在我看來都有豐富的意味。之后我也開始留意這些“奇怪”的人,才發現她們的頭巾分粉、紅、黑三種,應當各有內涵。以前確實沒有發現。
我在街頭行走,近乎苛刻地觀察,目的僅在于驗證陸客的不堪。確實存在,但都是輕微得不值得一提的“不文明”。要知道,中國人出門在外,其實都帶著身處異鄉時的謹小慎微,這是掩飾不住的。相反的是,在我的有色眼鏡中,“表叔們”還都差強人意,倒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換的港人,讓我嘴角露出壞笑——“中國式過馬路”的,其實更多的是土著。不奇怪,為三餐奔忙的快節奏都市人,不逾矩就沒法生存;在步行街,一家經營日本電器的小店門口,有一個店員兩次走出來倚在墻角抽煙。我就坐在離他十米外的長椅上等購物的妻子,而“此場所禁止吸煙”的警示語隨處可見。
每家藥店門外都是小山般堆積的洋奶粉,也不見有陸客蠅爭血般涌過去。讓洋奶粉短缺的,固然是大陸的市場需求,但從事掮客生意賺點小錢的,恐怕更多的還是能自由往來兩地的港人吧;一家牛腩小店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們站著排隊,就在我們身旁,店門口臨時搭的一張圓桌上,幾個香港底層勞動者在抽煙,在旁若無人地聊天說笑。而鄰座的西裝男子沒有嫌厭之色,更別說起身制止了。
地鐵有點舊,但確實很干凈。不過,唯一一個手持面包咬嚼吞咽的是香港男子。30歲不到,混血,略有白人血統。那是在尖東站,他跳進車廂的動作嚇了我妻子一跳,她一直拿肘捅我,示意我別漏了這一令人瞠目的細節;香港似乎開車不禁鳴,所以經常聽到催促前面的車、提醒過路行人的喇叭聲。有一輛車好像要小小地逆行一下,它在等紅燈,堵住了后面的車,而后面要左轉正常行駛的車的喇叭聲一點不客氣。
只不過我在旅游,又事不關己,所以聽不出有太多的氣急敗壞或狂躁憤怒;在么地道,有五六個南亞男子頻頻攔截過往的白種男子,簡單地聊和撩,優雅地塞小卡片。不知道他們為哪種生意攬客,但我立即就想到了內地賣毛片的和給桑拿房拉客的小弟。當然,他們的衣衫整潔得多。警車開過時,他們會坦蕩地停止動作,看來雙方都心照不宣;哦,警察,剛走出碼頭就碰到了四個,步巡警,腰間掛著“點38”,只是,隊形那叫一個隨意。最重要的是,有三個人穿著春秋外套(其中兩個敞著懷),另一個大肚腩的,居然穿的是襯衫。我盯著與我擦肩而過佩槍的一位看了一眼,他有點吃驚,似乎想跟我“聊聊”,但最終還是一扭頭,追隨大部隊前進了。這副潦草畫面,在珠海街頭出現的可能性都相當低。
“蝗蟲歌”內在的憤悶
留意生活中的細節,一直是我刻意訓練的一種能力。以上記錄下來的,跟“蝗蟲歌”放大似地列舉的大陸人的不文明程度,其實在伯仲之間。我并不是在找平衡,并不是強調“人之所有我亦有”的普世哲理。它們確實是我對香港的印象,但寫下來或許不太厚道。特別是我可能隱隱抱著對“負面信息”進行反駁的小小沖動。
我當然愿意發現并存留美好的記憶。有,有不少。就算我將以上記錄放大一百倍,也難以改變香港繁榮、整潔、規矩的固有面貌,也難以改變港人文明、禮貌、友善的整體氣質。我承認,沒能邂逅街頭“唱歌班”,沒能撞上舉著米字旗游行的人群,使我有小小的居心不良的不滿足。
從政治設計而論,17年前,港澳被賦予特區的意義,我以為,僅僅在于讓其帶動廣東、繼而全國走向經濟的富裕,它應當不包含讓香港以其整潔、規矩、文明、禮貌反哺大陸的良好用心。很簡單,北京的政治家,不會認為香港原有的政體優越,起碼不會承認這一優越很重要。在他們看來,只需50年,也許根本不需要這么久,只要大陸的經濟與香港持平,政體差異乃至文明禮貌等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對香港人來說,“制度50年不變”則很重要。他們可信賴的,唯有制度文明而已。至于50年之后,那是孫子輩的事。endprint
但是,僅僅16年之后,大陸人就來香港撒錢了!仿佛乾坤倒轉了一樣。或者,就像16年間人民幣和港幣的匯率掉了個一樣。
“蝗蟲歌”內在的憤悶和訴求,絕不僅僅緣于陸客的不文明讓人不堪,讓人難以容忍。那都是表象,是一種更容易煽惑群體非理性情緒的簡單而又直截的由頭。這里容不得含糊了,包括那些政治訴求,比如要求普選,比如拒絕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宣教等等,其實都是枝葉而非根由。很簡單,歌的結尾,著落在“港英的繁華光景,再沒有保證”這一句。沒法證明他們留戀的是“港英政體”,因為那個政體的“特首”,別說普選了,連選委會都不需要,直接由英皇任命。說到意識形態,“祖國和人民”是,“皇家香港警察”也是。并且,我們這些共和觀念一百余年的大陸人,完全有理由認為那是另一種更糟糕的意識形態。
但香港確曾繁華過,這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繁華,會寫在人們的臉上言談舉止上精氣神上,在珠海的20年間,我印象深刻。還有,在其毗鄰的深圳、珠海,不管是行政氣質還是市民言行,即所謂的文明化,確實來自與香港的交流,來自港澳卓有成效的反哺。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本來,我曾對回歸的港澳寄予厚望,被西風重度熏染過的這哥倆,還可以、且應該繼續擴大氣場,讓更多的國人感覺得到。
無力的言說
但是,眨眼之間,乾坤倒轉了。
不需要深刻的解釋。就是經濟的反轉,讓港人優越感喪夫,然后方寸大亂,然后對前途茫然。“繁華”的喪失,其實又只是相對而言的黯淡。——想當年,大陸人在香港產子即獲居留權,基本法曾不想承認,但香港人以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堅持了這一做法。現在,港人放棄普世文明,讓人理解但更讓人遺憾。
我現在有點后悔。我應該在16年前香港依舊繁華時去看看。
在回歸之前及其后不久,香港能提供給國人的正能量,顯然不僅僅是影視名星雞零狗碎,不僅僅是投資客、金庸、港產片和燈紅酒綠。在國家敘事中,比如保釣,比如反擊菲律賓,比如賑濟內地災民等等,香港人發出的聲音響亮又而有力。但現在呢?有一些人在政協插科打諢,有一些明星在到處撈金,如是而已。總之,香港的言說越來越無力。
當然,還有幾場游行、抗議。但深究下去,港人的躁動,其實仍是整個國家民眾躁動情緒的一個區域性表述。它不比內地的某處更狹隘,但也不比內地更高明。它是一種正常的情緒,在整個亞洲經濟體上,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后,在財大氣粗、文明落伍、叫人不爽的大陸人面前,港人沉不住氣完全正常。
蝗蟲、黃蟲、黃禍,對這些詞進行考據,便不難推演出其言說立場和情感取向。3月20日,我回到珠海兩天,末代港督彭定康訪港。內部的政治博弈我們不得而知,在娛樂層面,倒是看到了二三十個人,舉著米字殖民旗,對其誠摯地表達歡迎,甚至還喊出了希望回歸英國統治的口號。向前走很迷茫,走回頭路,也是群體思維之一種。
看著他們的七葷八素,我突然就想到在香港時的一件事:我入住的是一家五星級酒店。午睡時,一位朋友在總臺打電話到我房間。我大為震驚:我并沒有告訴他房間號。我沒有問原因,我現在只能猜測,因為這位朋友是一個年高德卲講英語的白種人。——我這是小人忖度嗎?不一定吧。因為,晚上,我又在房間內接了服務臺打來的電話,她說有一位中國朋友來找,問我是否愿意接聽。這是五星級酒店應當有的服務。但為什么要讓白人例外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