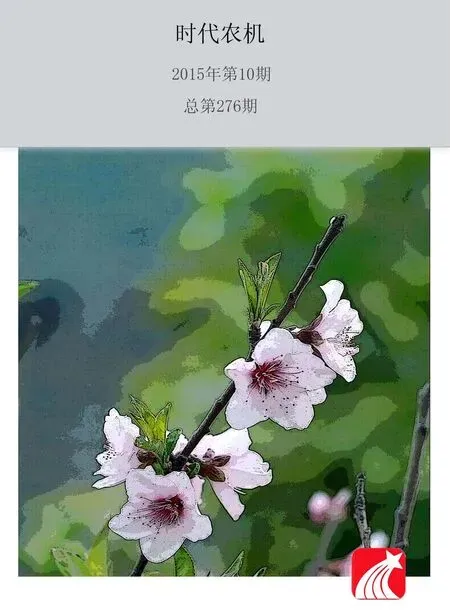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失地農民就業模式探索
姚 康,邊曉蓉,張 韻
(成都理工大學 旅游與城鄉規劃學院,四川 成都 610059)
自20世紀90年代起,由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農用土地轉為非農用地,全國每年至少有300萬農民成為失地農民。對于失地農民來講,城鎮化的內涵必然體現為農民的就業城鎮化、戶口城鎮化和生活城鎮化,這是惠及他們的利益所在。但我國城市化還存在失地農民失去了土地后也就失去了生存基礎的現象,用完僅有的失地補償費后,只能伸手向政府求援。因此,在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失地農民善后問題是城鎮化發展的核心所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
1 失地農民就業安置觀察
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之后,他們就失去了原本的工作條件,由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民轉變為從事其他產業的工人。相對于戶籍身份的轉變,職業身份才是農民賴以生存的保障條件。戶籍身份和職業身份兩者密不可分,如果只有戶籍身份轉變,而不能從根本上為失地農民帶來有效收入,是不徹底的,因而職業的轉變,即改變失地農民就業現狀才是處理問題的關鍵。
如果只是暫時把他們安排到鄉鎮或是村鎮企業,沒有考慮到失地農民本身的特點和適應性,他們可能再次面臨失業。因而這也只是暫時緩解這種矛盾,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反面可能使這種矛盾和利益沖突得到積累,造成更多更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種方式只能稱之為安置,而不是失地農民的轉化,這既有損于失地農民的利益,對于城市化進程也是有害無利的。因而對待失地農民的職業轉化和就業問題要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以及城市和農民的可持續性發展,這種轉化不是一個短期行為,是一個具有長期效果的工程。
在對待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時,不應該把就業僅僅作為一種安置,也不能把安置作為一種補償。失地農民轉變為城市人口應該是一種戶籍身份和職業身份的轉換,是對他們生活的雙重保障;而對城市化的主體而言,這種職業的轉換,也是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一個重要步驟,解決了失地農民的職業轉換,就可以使他們與城市實現共同發展。作為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安排就業和促進就業不是一次性就結束了這種責任關系,因為失地農民的職業轉換是一次繼續社會化的過程,是放棄原有的生產方式,學習新知識,適應新社會的過程。
2 失地農民就業安置模式分析
目前國家對農民的失地補償或就業安置已經出現若干個固定模式。其一,一次性貨幣補償的模式,這是最直接的補償方式,許多農民拿到一大筆補償款后不知所措,不正確引導還會帶來社會問題,因此模式不具備可持續發展性。其二,用土地換取社會保障的模式,只是將一次性補償變成了分期,沒有實質轉變。其三,失地農民轉入第二、三產業的模式,既可以有新的工作,也可以享受土地升值帶來的增產,還減輕了政府負擔;但是因為失地農民自身素質不一,是否能擔任相應的工作還是未知。其四,土地股份合作模式,在集團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將征用的土地折為股指,通過失地農民入股的形式,獲取增長效益。其五,自主創業模式,政府引導,促進創業,改變原有的生產方式,但是很大程度上受創業環境和自身素質的限制。
3 失地農民就業安置對策
只有將農民本身的優勢條件合理運用并規避自身不足,才能促進合理就業,解決失地農民后顧之憂。
(1)充分利用優勢技能。農民是對一種職業的稱呼,有著自己獨有的職業技能,即使農業生產實現全程機械化,但是還許多環節及工序仍要具有專業技能的人員手工完成,這種狀況使農民本身就具有勞動競爭力。作為第一產業,農業在我國具重要的地位,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是永遠消失不了農民職業。將農民職業化之后,人們或許不再“自由”的選擇自己的工作地點,而隨工作四處奔走。因此,政府應主導城市農業產業園區的規劃建設,以大量吸收失地農民就業。
(2)強化職業技能培訓。作為職業轉換,相應的職業技能培訓必須配備,在進行占地補償的同時進行有效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失地農民職業素質,增強適應轉變的能力。政府的經濟規劃導向、地方特色潛力產業、甚至招商引資的選擇等,都應考慮的職業培訓和就在安置,以保障農民失地不失業。同時要利用當地大中專院校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條件,組織開展失地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工作。
(3)互聯網就業途徑。互聯網的普及可以說是就業模式一次質的轉變。互聯網擇業從本質上打破了勞動市場的二元結構(城市—農村)壁壘,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職業搜尋方式由傳統求職向網絡求職的轉變,降低了求職成本、加大了搜尋密度,從而提高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匹配效率。而互聯網本身就具有職業特性,從互聯網金融到從互聯網交易形式中受益的快遞業,都昭示著其廣大的遠景。顯然這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就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