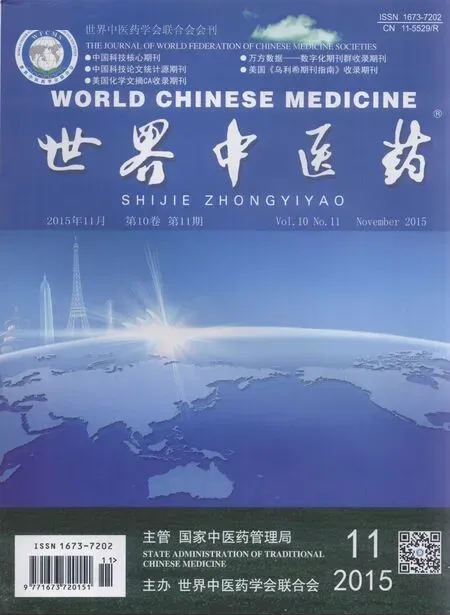相火、命門理論對肝臟象理論發展的影響
李 丹 李成衛 王慶國
(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中醫臨床基礎系,北京,100029)
相火、命門理論對肝臟象理論發展的影響
李 丹 李成衛 王慶國
(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中醫臨床基礎系,北京,100029)
命門一詞首見于《黃帝內經》,后世經過不斷的理論創新將其逐漸發展成為命門學說。從命門到命門學說的發展過程中,歷來各家一直將爭論的焦點放在命門與腎的關系上,文章通過從3個歷史時期考察得出命門與相火理論的出現對肝臟象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命門;相火;肝
命門與相火的理論問題一直是中醫理論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歷來對此理論問題的探討都是以腎為中心的,而筆者經過考察發現命門與相火理論的出現對肝臟象理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命門及相火的探討對于肝臟象理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1 《黃帝內經》《難經》時期相火、命門分論,與肝理論無關
《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中有兩篇提到了“命門”。《靈樞·根結》篇“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靈樞·衛氣》篇“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1]由此可見,《內經》一書中命門指的是眼睛。“相火”一詞《內經》中亦有記載,《素問·天元紀大論》:“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關于七篇大論的成書年代一直有所爭議,學界一般認為其成書是晚于《內經》的。而在內容方面,七篇大論亦同《內經》的理論系統相差甚遠,如張燦玾[2]認為其與《內經》并非一種學術體系。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相火一詞與《內經》中“命門”一詞無理論一致性,故不討論二者之間的關系。
《難經》第三十六難:“臟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腎有一也。”后世解釋說,此難“提出左為腎,右為命門,以說明腎有兩枚,這里所說的左右,并不是指人體的具體部位,中醫藏象學說的五臟及其功能,都不能作為西醫解剖部位的五臟去理解……故腎與命門應該從腎臟包括腎陰一腎陽兩方面的功能去認識。”[3]其實不然,此處原文很顯然是在討論臟腑的數目問題。《內經》對于臟腑的數目有諸多不同的說法,有五臟說、六臟說、五腑說、六腑說、七腑說,而且在臟腑系統的數目上來說亦有五臟五腑說、五臟六腑說、六臟六腑說[4]。《難經》此處是對《內經》理論系統的不一致性的質問,并且繼續提出質疑:臟都是單一的一個,為何腎臟卻有兩個?為了理論的完整性及一致性,《難經》把另一個腎稱為“命門”,并且賦予“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后面第三十九難繼續討論臟腑的數目問題:“曰:經言腑有五,臟有六者,何也?然。六腑者,正有五腑也。五臟亦有六臟者,謂腎有兩臟也。其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臟有六也。腑有五者,何也?然:五臟各一腑,三焦亦是一腑,然不屬于五臟,故言腑有五焉。”命門一詞在《內經》《難經》二書中皆是指實體性的臟或器官,而相火沒有在運氣七篇之外的篇章論及,二者與肝亦沒有聯系。
2 宋金元時期,命門是相火,肝內寄相火、為疏泄動力
2.1 命門是右腎、屬相火 金代醫家劉完素提出右腎屬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門”。劉完素的“火熱論”對后世醫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其在《素問玄機原病式》火類中將命門與相火聯系在了一起,以解決“水虛而寒”的情況。從五行理論上論水虛應為發熱,所以出現寒的情況,他解釋為“所以或言腎虛而下部冷者,非謂腎水虛也,所謂‘腎有兩枚’……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小心也……然右腎命門小心,為手厥陰包絡之臟,故與手少陽三焦合為表里,神脈同出,見手右尺也。二經俱是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門爾。故《仙經》曰∶‘心為君火,腎為相火。’是言右腎屬火,而不屬水也。是以右腎火氣虛,則為病寒也。”認為右腎手厥陰包絡之臟,都是相火,“相行君命,故曰命門”。
李東垣提出陰火論。《內外傷辨惑論》中,他認為火仍然是為心所主的,相火是下焦胞絡之火,為元氣之賊,而陰火雖起于下焦但是其系系于心。“火”類疾病的發生在于“元氣虛心不主令相火代令陰乘位”。李東垣的陰火論與劉完素的火熱論,相同之處在于,二者均是闡釋心臟之外的臟腑出現火病的原因;不同之處在于,河間是解釋水虛而寒,東垣是解釋土衰而熱。
劉完素與李東垣所論之火,都沒有與肝有直接的聯系。但是,無論火熱論還是陰火論,“火”開始在“心”之外臟腑而存在,與下焦胞絡及腎聯系在一起。同時,命門、相火的不斷出現,正是中醫肝臟理論巨大變化的標志。
2.2 肝內寄相火、為腎精的疏泄動力 元代朱震亨將《太極圖說》引入醫學,創立相火說,提出“肝腎之陰悉具相火”。《格致余論·相火論》“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唯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肝腎之陰悉具相火。”朱震亨“太極,動而生陽”定義陽的屬性為動。火分為君火、相火。心所主君火為不動之火,肝腎所主相火為主動的火。相火出于龍雷為木之氣即出于肝,出于海為水之氣即出于腎。與河間、東垣不同之處在于丹溪不再認為相火是病理的火,他引據《內經》病機十九條言火有五,說五臟六腑皆有相火,為此相火便成為了人體生理上所必須不可缺少的火。
故對男子精液而言,封藏、靜守的由腎完成,排除、疏泄由肝中相火完成。故《格致余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
元代之前,肝主疏泄說并不存在[5]。元代朱震亨第一次將肝與疏泄聯系在一起。《格致余論》云:“(肝腎)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于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6]。從理論結構分析,朱震亨肝“司疏泄”說中,疏泄的對象是男子的精液,疏泄的動力是相火。丹溪弟子戴思恭更為詳細的闡釋了肝中相火對男子精液的疏泄作用。《推求師意·夢遺》:“腎屬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然厥陰主筋,故諸筋皆通于厥陰。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疏泄……陽強者,非臟真之陽強,乃肝臟所寄之相火強耳。”[7]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肝的疏泄作用只是被用作對生殖之精的推動。當代肝主疏泄理論,是肝氣藉由疏泄氣機來疏泄氣血、情志、消化等功能,疏泄的對象要比男子精液廣泛得多,而動力是肝氣、是氣機,已經不再是肝中的相火。后世醫家多將肝主疏泄理論追溯至此。但將疏泄上升為肝的功能、并提出為肝所主的是明代薛己,其代表作《內科摘要》中說“丹溪先生云: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二臟俱有相火”。他將朱震亨的肝“司疏泄”改為了“肝主疏泄”。肝主疏泄說從無到有,與“相火”“命門”等學說的發展關系密切。
這一時期,肝臟象理論的內容,主要是肝為厥陰風木、內寄相火,并延續到明清時期。肝主疏泄理論并非核心理論。也是從丹溪開始,有了“肝有余”之論。在《金匱鉤玄》小兒科中有“小兒肝病多,及大人亦然。肝只是有余;腎只是不足”之論,究其原因他認為是“小兒十六歲前,稟純陽氣,為熱多也……肝則有余,腎尚不足,肝病亦多也。”此論發展至明初成為了肝常有余、肝無補法之說。
3 明清時期,以命門為核心的人體模式與“肝氣、肝風、肝火,三者同出異名”
明代命門學說以孫一奎、張介賓、趙獻可為代表,以理學易理為理論架構基礎,醫易結合,對臟象理論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明早期的虞摶(1438—1517)延續金元時期醫家的五運六氣說,采用五行制化論闡釋相火。他認為天地間惟火有二,君火與相火,君火是心所主而相火卻是全身五臟六腑皆有,并說相火游行于天地上下氣交之中合而為五運六氣而人身的相火則游行于腔內、肓膜之間。其后,命門部位、形質醫家有不同的認識。孫一奎認為“腎間動氣”[8],李梃認為“命門即右腎,本身有象如絲,上連心包,下尾侶,附廣腸之右,通二陰之間,前與膀胱下溲尿之處相并而出,男子以藏精,女子以受胎。”虞摶認為“兩腎總是命門”,張景岳認為“右腎為命門,男子命門藏精,女子系胞,即子宮命門說”,趙獻可認為“命門在兩腎之間。”
張景岳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命門學說,并且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以命門為中心的人體模式。其所論的天地宇宙模式是:“無極—太極—陰陽—四象—五行”,而陰陽由太極的動靜所劃分,認為“天地只此動靜,動靜便是陰陽,陰陽便是太極,此外更無余事。”而且太極之中又有太極,“太極分開,只是兩個陰陽,陰氣流行則為陽,陽氣凝聚則為陰,消長進退,千變萬化,做出天地間無限事來,以故無往而非陰陽,亦無往而非太極”[9],從而得出太極就是理這個結論“夫太極者,理而已矣”。他將天地之理推理運用到人體中,將命門定義為先天子宮精室,是人生命之“初”,即人體“無極”,其論人身形未生成即由父母之精室子宮而合成。而腎臟有兩枚正好為《坎》外之偶,而命門一者則為《坎》中之奇。所以命門以一統二,總主兩腎,兩腎都屬于命門是為“命門者,為水大之府,為陰陽之宅,為精氣之海,為死生之竇。若命門虧損,則五臟六腑皆失所恃,而陰陽病變無所不至。”為此,張景岳認為的人體模式則為:“太初(父母之精)—命門—陰陽氣血”,以命門統人身陰陽氣血。延續這個思路,后世醫家以先天為水火、后天為氣血,先天水火在命門,后天氣血在臟腑的人體模式逐漸形成。
在這個以命門為核心、臟腑化生氣血的人體模式中,相火及肝臟象理論得到了新的發展。如元代朱震亨將火分為君火、相火,主動的相火成為生命不可缺少的動力,并且在前人腎虛而起火的理論下加上了肝為龍雷之火;肝內寄相火、主推動,而錢乙論小兒生理時有肝氣有余論,張元素有“腎為肝之母,故云肝無補法,補腎即所以補肝也”的說法,到明代中后期,“肝無補法”的觀點流行,瀉肝法的濫用。張景岳《質疑錄》論肝無補法:“肝之所賴以養者,血也。肝血虛,則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氣逆也。肝氣逆,則氣實,為有余;有余則瀉,舉世盡曰伐肝,故謂肝無補法。不知肝氣有余不可補,補則氣滯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補也。”并提出滋水涵木的治補肝方法。
同時,宋以后肝為厥陰風木、內寄相火說,逐漸被肝化生氣血,肝氣郁、有余化火、火動生風的新理論替代。如王泰林《西溪書屋夜話錄》:“肝氣、肝風、肝火,三者同出異名”,“然內風多從火出,氣有余便是火。”在氣、風、火的病機演變中,肝氣郁滯、有余便是火,火動而生風。三者的演變不再采用厥陰風木及相火說,而且,作為在宋元時期肝氣本身的厥陰風木以及推動生命活動的生理的相火,此時已經變成病因病機、病理因素。此說對后世肝理論發展的影響重大,其在臨床的廣泛應用,當代肝主疏泄理論的構建提供了扎實的實踐基礎。
4 結語
宋以后的相火、命門理論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學說。這個學說重塑了宋以后的人體觀。隨著相火、命門理論的成熟,人體模式與臟腑功能隨之發生改變,肝臟象理論的發展是這些改變中的一個。在宋明時期,肝臟象理論核心內容為肝為厥陰楓木、內寄相火;而朱震亨之后,肝中相火從疏泄男子精液到二便、水液及情志等不斷擴大,逐漸成為肝的重要功能。到清代,命門學說構建的命門含先天水火、臟腑生化后天氣血的人體模式逐步得到認可,肝則成為內有氣血陰陽的臟腑,“肝氣、肝風、肝火,三者同出異名”的理論,為當代肝主疏泄理論的形成提供了理論與臨床實踐的支撐。
[1]王玉興.黃帝內經靈樞三家注[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89,139.
[2]張燦玾.《素問》對運氣七大論淵源探討[J].中醫文獻雜志,2002(1):3-5.
[3]秦越人.黃帝八十一難經[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117.
[4]張效霞.臟腑真原[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19-25.
[5]張清怡.《臨證指南醫案》中“肝藏血主疏泄”的臟象理論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3.
[6]金元·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金元四大醫家全書[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688.
[7]明·戴思恭.推求師意.[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20.
[8]孫一奎.孫一奎醫學全書類經[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648.
[9]張景岳.類經脈[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1579,1593.
(2015-11-02收稿 責任編輯:洪志強)
The Effect of Life-gate Theory and Ministerial Fire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 Manifestations Doctrine
Li Dan, Li Chengwei, Wang Qingguo
(Bei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Beijing100029,China)
The term “life gate” derives from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and later scholars added more meanings and created life-gat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it. In this progress, focuses have been pu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gate and kidney. The article found out that these 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have great contribution on the doctrine of organ manifestations through looking into academic thoughts of three different ages.
Life gate; Ministerial fire; Liver
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資助項目(編號:2011CB505100)
李丹(1986—),女,四川眉山人,淄博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國醫堂門診部,研究方向:張仲景診治體系的歷史與臨床應用研究;肝藏血主疏泄的理論與歷史研究
李成衛(1971—),男,河北保定人,醫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張仲景診治體系的歷史與臨床應用研究;肝藏血主疏泄的理論與歷史研究,E-mail:lichengw@126.com
R256.4
A
10.3969/j.issn.1673-7202.2015.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