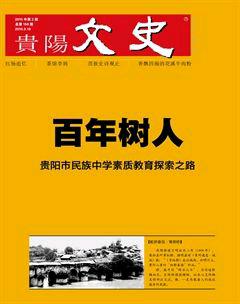那些像面包碎屑一樣的素質教育
楊甜甜

理論上來說,作為“90后”,我應該是全然籠罩在“素質教育”之下得到德、智、體、美全面培育發展的一員。可是提及此事,自身渾然不覺,脫口便反問一句“我接受過素質教育嗎?”再一聽身邊人的敘述,才恍然大悟“哦,好像有一點。”我把造成這一道迂回之路的原因歸結于——“應試教育”在記憶里太過根深蒂固。
從小學說起,那應該是一片沃土,“素質教育”的鮮花盛開。
記得那時正實行“減負”,低年級的時候連作業都沒有一點,回了家扔下書包就往外面跑。
語文、數學,是小學里最重的兩門課程,其他的還有什么自然、社會、思想政治,但是同學們最喜歡的還是周二的“第二課堂”吧。簡單來說,這就是一個生活課或者家政課。現在只模糊記著幾個主題:一次是做水果拼盤,一次是教我們如何查看生產日期和保質期,還有一次是教我們補襪子、縫扣子。
小學的活動特別多,大概是六年級最后一次參加“六一”兒童節。班主任安排班上兩名參加學校舞蹈隊的同學編舞,曲子選的是《還珠格格》里紅得發紫的“小燕子”唱的《撥浪鼓》。選了大約20個人參加。然后每天課間、放學時間,大家就在走廊、操場練習。從編舞到同學學會舞蹈動作,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完成,老師只是檢查我們的排練進度或者做些動作指導。而我至今還記得,這支舞蹈的第一個動作是我們低著頭蹲在地上,隨著“小燕子”的一聲“天晴朗,那花兒朵朵綻放”,雙手便做成一朵花朵的樣子慢慢升起。
到了初中,似乎素質教育的影子就開始淡化了。盡管學業壓力還沒有高中那么沉重,但是學校基本上沒什么這方面的教育動向。
然后是高中,最有指向性的應該是高二參加的為期5天的農訓和工訓,這兩項是輪流交替的。上一屆參加的是農訓,到我們這一屆就是工訓。然后在那里,我們學習了一系列實踐課程:用木板做飛機模型、打磨釘子、汽車駕駛、野外做飯……但就像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樣,這種走馬觀花式的體驗訓練,最終也只像寫在報告里的“在基地開展的定向越野、木工技能、汽車技能等實踐課程中,同學們認真刻苦訓練,學會了互相幫助,認識到團結的力量,鍛煉了自己堅強的意志。通過參加這次訓練,同學們在親手操作中進一步領會了理論知識,在提高實踐能力的同時鍛煉了堅持不懈、吃苦耐勞的精神”這段文字一樣,封進文件袋就睡著了。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學習的知識大抵是越來越難了。所謂“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卻好似只是停留在那個小小的“第二課堂”:老師一步一步教、我們一步一步學,教官一步一步教、我們一步一步學。鈴聲響了,我們下課;鈴聲又響了,我們上課。老師說“這個地方是考點”,我用記號筆勾出來,再在旁邊畫一個大大的五角星,然后讓它在我的腦海里越來越清晰。而那些我受過的“素質教育”,就像被我扔在身后的面包碎屑一樣,不知道什么時候就被一陣風吹散了,被一群鳥啄食了。
想說,什么時候“素質教育”才會是每所學校教育規劃里的那個大紅色的五角星呢?而不是面包的碎屑呢?
后記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梁啟超先生寫于百年前的《少年中國說》,今天讀起來依舊擲地有聲,也會在掩卷之后,無盡唏噓。
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學教育對于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發展中國家增長最快的群體就是年輕人,如果得不到必須的教育,他們就不能為我們和他們自己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中學生時期正處于“暴風驟雨”的青春期,又是能夠快速接受、吸納各種知識與思想的黃金期。不忽略真善美、不需要簡單的對錯認知,而是要有自己的判斷、要獨立、要善良……這些可以讓今天的青少年養成的能力和品行,可以影響他們一生,也能夠潛移默化他們的人生軌跡。
而曾經對于中學生的教育,就如一首詩中寫的:“我要他們背誦十字軍東征和赤壁之戰的年份,卻沒在每天他們咀嚼肉塊時告訴他們什么是死亡和戰爭。犯不完的錯記在黑板上,扣不完的分數塞滿作業本,不要奔跑,不準歌唱,除非已經開始評分。我用無數小小的規則困擾他們,無數小小的目標要去完成,讓他們練習整齊的向左向右轉,起立和蹲下,一面聲稱要讓他們變成比我更卓越的人。”(鴻鴻《先知的懺悔——給孩子的詩》節選)
如果全社會不去深思教育的本質何在,成長中的孩子學習的意義是什么,就會扼殺了生命成長中的無限可能。
取意“科甲挺秀”、期盼多出人才的甲秀樓,在南明河上已經屹立400多年,到今天我們依然期盼黔地人才輩出。對于人才的渴求,是期望未來美好最直接的訴求。
適合成長規律的青少年教育是培養人才的重要一環。不管是素質教育還是真正回歸到學習本質意義的教育,我們期望春風化雨、期望今天的孩子在明天會走得更加自信、更加堅實,走得更遠。
同時也期待魏林和她的同事們培育的求索之樹,結出更多、更豐碩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