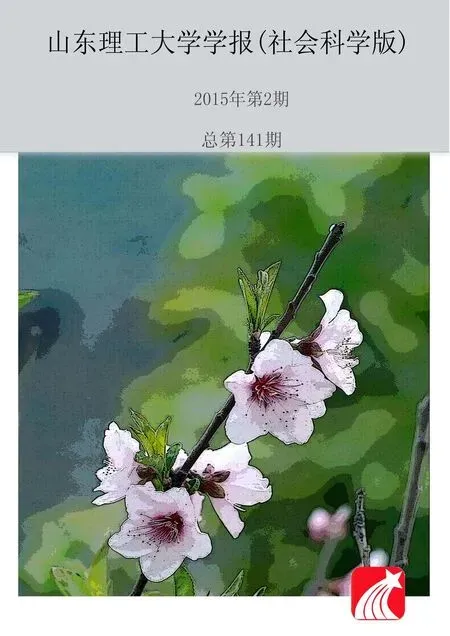法治視閾下地方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方案分析
封延會,馬東順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法治視閾下地方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方案分析
封延會,馬東順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2014年是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規劃的開局之年,各地密集出臺了地方版的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改革方案。方案中一些新的制度設計意在解決國企改革中的積弊,法治已然成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路徑,但地方國企改革方案又存在著法治思維不足的缺陷。彌補這些不足,將國有企業和國資管理改革納入法治的軌道具有重要意義。
地方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法治化
一、國有企業改革的法治化
國有企業與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始終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中心,這表明了國企改革影響深遠且高度復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企分類改革的方案,要求“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建立科學的分類標準,并以此推動不同類別國有企業的治理與考核機制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企業管理科學化和精細化的基礎。報告提出的國有企業類型化管理和監管為國有資產改革確定了基本框架,并將成為改革的新起點和下一階段改革的中心內容。
習近平同志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1]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縱觀我國三十多年國有企業改革進程,恰恰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的過程。這其中最缺乏的就是法律和制度的前瞻性設計。而在法治成為社會共同訴求的背景下,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和法治的保障中推進,必須加強國企和國有資產改革的“頂層設計”,特別是要有完備的法律支撐體系。
國有企業類型化改革是推動國企外部管理和內部治理的第一步。2014年以來,地方政府紛紛推出了本地國有企業改革的方案。本文搜集了全國二十一個省份發布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并對這些方案中涉及的分類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分類改革方案進行深入分析,探尋其中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
二、地方國企改革“錦標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2014年各地密集推出了地方國資改革版本。總體上看,外部改革主要從創新國資管理體制和引入多元資本推動混合所有制兩個層面展開;而內部則主要從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上推進。地方國企改革方案突出了對中央決定的落實,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資管理體制發展方向的定位,幾乎所有的省份在改革目標中均有類似的表述。這表明,在政府與企業關系這一宏觀問題上,將從調整現有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入手。
2002年,在基本完成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之后,黨的十六大提出建立“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資管理體制。2003年掛牌的國務院國資委成為新世紀以來這一體制的體現,也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導者。如同之前每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一樣,2003年之后國有企業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也伴有大量的爭議。如國有企業的巨額盈利與國資收益的上繳、國有資產的國進民退、國有企業負責人的選任等。國資委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上,行政色彩濃厚,行政紐帶強于產權紐帶。目前黨政系統常常把國資委當作國有企業的歸口管理部門和貫徹政府指令的“漏斗”,承擔了一些由政府交辦的與出資人職能沒有直接關系的事項。這些并不屬于出資人職能范圍內的事務,常常會推動國資委向著行政機構而不是出資人機構的方向移動。[2]如維護穩定、安全生產、節能減排等工作,國資委成為了政府向國有企業發號施令的“傳聲筒”,難以集中行使所有權職能,專注于實現出資人的商業目標。
強調“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新體制,顯然是對2008年《企業國有資產法》所確定的,國資委作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的回歸。地方政府的改革版本顯然也希望在此問題上有所突破。
(二)國有企業的分類改革
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是實現國有企業差異化管理的基礎,也是其他各方面改革的前提。如上文中的建立“管資產為主”的管理體制、推動混合所有制、國企高管的選擇和薪酬的確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分類考核機制、國有企業的信息公開等,都必須以科學的分類為基礎,制定不同的改革策略。從政企關系的角度看,國有企業是政府的延伸。明確國有企業作用的范圍、方式,同時也是確定政府邊界,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的過程。
通過梳理我們發現,除了湖北、山東和山西三個省份之外,其他省份都提出了分類改革的意見。承接中央提出的“公益性企業、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的表述,大多數省份確定的改革方案中也堅持了這樣的三分法或類似的表述。三類企業在目標和定位方面存在差異。以上海市的方案為例,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努力成為國際國內行業中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企業;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政府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城市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企業分類可動態調整。[3]
國企分類管理是公共產品理論的要求。國企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向社會提供私人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國家的任何支出都應當堅持并服從于這一目的。國家出資建立并運營國有企業是直接向社會提供基礎產品和普遍服務,而不僅是從事營利性的業務。其他還包括了促進就業、扶持貧困、基礎科技和研發甚至是戰爭資源的儲備等政策性的目標。從長遠來說,國有資產立法目標不是簡單地促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是如何增進全體國民利益的最大化。[4]
國企分類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必然選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我國的市場經濟進程更多體現了國家主導的特征。市場經濟發展的草根基礎并不扎實,因此政府通過建立國有企業(包括現在看來大量屬于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發展支柱產業,建立產業基礎,扶持并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彌補市場發育的不足,完善市場體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因此特定的市場發展狀況和階段性,決定了政府發揮作用的范圍要比成熟市場經濟更大。但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政府應當在市場中逐步退縮,將部分領域還給市場。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國有企業所處的行業領域、社會功能存在著不同,必須改變對國有企業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多元化的分類和管理機制。
(三)提出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
絕大多數省份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這是從國有企業內部進行的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多數省份的改革方案中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幾個重點方面都進行了展開,如上海市改革方案中幾乎復制了上述內容,并且在規范設置法人治理結構、推進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完善注重長效的激勵約束分配機制等三個方面展開。四川省改革方案也提出: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包括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規范董事會建設、建成以產權為紐帶的母子公司管理體制。全面完成企業內部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加大市場化選聘力度,依法落實董事會對經理層人員的決定權。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內容在于完善公司治理。短期來看首先要在高管的選擇方面進行突破。國有企業的行政化、國有企業高管的行政任命與行政級別問題長期困擾著國有企業的治理。另外如何在國企內部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也同樣被多數省份所強調。近年來我國查處的國有企業領域中的貪腐問題表明,由于缺乏監督,在一些國企內部幾乎形成了一個獨立王國。管理者的決策不僅偏離了企業作為營利性組織追求利益的目標,也偏離了國家對一名國有企業干部所提出的政治方面的要求。
(四)公司制改造和資產證券化
何為混合所有制?如何實現混合所有制?這是擺在國企改革面前的一個基本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混合所有制事實上是對國有企業進行深入的公司制改造。股份制改造既是落實混合所有制,同時也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組織基礎。因此絕大多數省份都將其作為改革的目標。如河北省提出“2020年所有的省屬國企百分之百是混合所有制企業”。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股份制伴隨著第一部《公司法》的頒布而開始。2008年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依然在延續這一進程,并規定了國家出資企業的改制。所謂企業改制是指:其一,國有獨資企業改為國有獨資公司;其二,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改為國有資本控股公司或者非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其三,國有資本控股公司改為非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可見企業改制正是一個公司化和股權多元化的概念。有的學者研究指出:全國90%以上的國有企業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已有52%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截至2012年底,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共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國有股權比例已超過53%。地方國有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681家,非國有股權比例已超過60%。[5]雖然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績,但股份制的深化依然非常迫切。從目前央企的產權結構來看,即便民營資本進入,更多的是在二級、三級,甚至四級公司的合作。對于市場呼吁的央企母公司層面的股權多元化仍未破題。在國資委監管的113戶央企中,母公司層面實現了股權多元化的央企僅為8戶,但是這8戶央企的多元股東也多為金融機構或產業基金或地方政府,都是國有性質的,沒有給民間資本撕開一個口子。[6]
股份制和資產管理的更有效形式是國有資產證券化。特別是對競爭性的國有企業,通過證券化,不僅能夠有效地對資產估值,還能夠便利地實現控股、參股或完全退出的市場操作,調整國有資產的結構和布局。同時證券市場的規則也能夠推動合理的公司治理機制的建立。因此從各地方的改革方案看,過半的省份都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多層次的證券市場,提高證券化率的目標。
三、地方國有企業改革法治分析
法治是一種動態的治理體系。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中進行。缺乏法律的規劃與指引,法律責任的追究機制不健全,法律的程序和監督機制不足,既是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的薄弱之處,也是過往改革弊端叢生、爭議不斷的根源。盡管地方國資改革的熱情令人澎湃,方案也不乏激動人心的熱點,但從法治的角度看,其中的問題也令人擔憂。
(一)法律的匱乏依然是國企與國資改革之殤
2008年,在啟動國企改革30年之際,作為規范企業國資管理的基礎性法律,《企業國有資產法》才得以通過。該法案更多的是對改革經驗的總結和對改革成果的固定,并試圖解決當時國資管理中的突出問題,如國有資產的流失,卻并未對今后的改革指明方向和路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企改革的論述體現為綱領性的文件,而地方版的改革計劃也只是從幾個大的方面和十幾個角度勾畫了國企改革的基本框架。更何況地方政府還普遍存在著“以文件落實文件”,對中央文件簡單復制的問題。這些文件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邊界不清,極易造成改革保守不前或者越界的問題。
目前在與國企改革有關的改革意見中,頂層設計方面有8個改革方案正在抓緊研究制定,此外還有34項具體措施。這些方案可能以“1+N”形式發布。[7]
(二)缺乏對國有企業改革環境和關聯領域的配套方案
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綜合系統工程,單兵突進不可能取得成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指出,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立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商業法律環境對于國有企業改革非常重要。如在實現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民營經濟所關注的平等地位、股權的保護與實現,甚至國企的溝通方式和效率問題、政策的不確定性問題等,都可能會造成民營經濟的躊躇不前。地方國有企業改革戰略更多局限于對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領域,而對“詩外”功夫卻著力不夠。
比如對于提高證券化率的問題。證券化水平的提高要依托于證券市場,雖然發展多層次的證券市場是我國證券市場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但能否容納天量的國有資產仍然存在不小的疑問。特別是考慮到國有企業的整體上市和現階段進行的證券發行制度改革,能否實現證券化率提升的目標仍然值得懷疑。如同金融市場一樣,“合成性謬誤”的問題也同樣存在:對單個省份來說,國資證券化是理性的選擇。但當多數的省份都將其作為政策選項的時候,證券市場本身的約束問題也就凸顯出來。
(三)完善分類改革方案中的重要法律問題
1.分類標準的完善。對國有企業的分類更多考慮功能和所處的領域,而對國有企業的規模缺乏考慮。20世紀90年代“抓大放小”的改革之后,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并未有實質性推動。國資委建立之后,中央和省級地方政府基本按照企業規模對特大型企業和大型企業行使出資人職責。現實中依然存在大量的中小型國有企業:截至2013年底,全國獨立核算的國有法人企業仍有15.5萬戶。[8]他們的改革舉措顯然與大型國企存在較大的差別。而這種差異在地方版的國企改革文件中較少涉及。
2.國有企業高管的權利與義務應當匹配。國有企業高管的選擇對于經營的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地方版改革文件中對此也著墨較多,主要從權利方面給予選聘者充分的信任和授權,強調要更多地從市場中選聘管理者,在考核和薪酬方面也體現市場化的要求,落實董事會選擇經理層等。但與之對應的責任方面的法律和規則卻相當缺乏。按照《公司法》的一般規則,董事和監事應當承擔對公司的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西方公司法中對此已經發展了一套成熟的規則,如“商業判斷規則”,來劃定管理層決策是否正當的邊界,以此作為高管違背信義義務承擔責任的基礎;同時普遍建立起了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保障高管的利益。而我國無論在公司法規則還是在配套的保險方面,都非常匱乏。權利與義務不匹配,有可能會加劇已經存在的“內部人控制”問題。
3.深化司法機關的參與。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之下,各地的改革方案并未考慮司法機關在國企改革中發揮必要的作用。根據筆者的檢索,“法院”一詞沒有出現在任何地方的改革版本中,司法部門也僅在企業負責人涉及犯罪的情況下才有介入的空間。這表明地方國企改革依然延續了行政主導的模式,方案設計缺乏法治思維。國企改革過程中涉及大量的私法事務(如落實混合所有制可能出現諸如契約、產權、股權保護等法律糾紛)和公共事務(如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這些都需要司法部門的介入。當前我國民訴法已經建立了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制度,可以考慮將其延伸到國資改革領域。
4.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強國有企業信息披露是其公共性質的必然要求。2005年經合組織(OECD)制定了專門針對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指引》(下文簡稱《指引》)。《指引》共六章,其中第五章規定了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問題,將其作為提高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主要方面之一。《指引》在信息披露方面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規則,覆蓋國有企業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年度報告、內部與外部審計、像上市公司一樣依照高質量的會計和審計標準,將明顯關系到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和普遍公眾的領域作為披露重點(包括公司目標與實現情況、所有權和選舉權結構、重大風險因素及應對措施、來自國家的承諾的財務支持、與相關實體的重大交易等)。[9]
然而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在地方版的國企改革方案中,僅廣東省在公司治理方面要求建立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上海市要求參照上市公司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體系。除此之外,其他省份對信息披露的要求則多是單方面的,如黑龍江省限于在混合所有制交易過程、勞動用工和預算方面;廣西則僅在收入分配方面;四川省只是在企業財務預算,以及國有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國有非上市公眾公司、國有上市公司加強信息披露管理。過半數的省份干脆沒有涉及此問題。
總之,國有企業改革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央尚未出臺國企改革的整體方案之前,地方政府當然可以對本地區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家出資企業進行改革規劃,但法治也應當伴隨著這一進程。方案的設計必須體現法治的思維和邏輯,在實體內容上體現改革的公平與公正,在程序設計方面也應正當;在立法先行與司法參與方面保持平衡;在國企內部制度安排中尊重商人自治的精神,在外部市場環境構建上應當公平合理、有效監管。
[1]習近平.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重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8/c_119558018.htm.
[2]企業研究所“中國企業改革30年研究”課題組(張文魁執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EB/OL].http://www.drc.gov.cn/xscg/20081204/182-224-33913.htm.
[3]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N].文匯報,2013-12-18.
[4]李曙光.國有資產立法需明確六大問題[J].中國改革,2008,(1).
[5]陳德勝,李洪俠.國有企業改革須分類推進[N].中國證券報,2014-10-08.
[6]張林山.三中全會后的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與建議[J].中國經貿導刊,2014,(9).
[7]劉麗靚.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接近完成,方案料以1+N形式發布[N].中國證券報,2014-12-03.
[8]韓潔,高立. 財政部首次對外公開全國國企“家底”[N].新華每日電訊,2014-07-29.
[9]OECD.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EB/OL]. http://www.oecd.org/corporate/ca/corporategovernanceofstate-ownedenterprises/34803211.pdf.
(責任編輯 李逢超)
An Analysis of th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lassified Reforming Scheme in the Legal Perspective
Feng Yanhui,Ma Dongshun
(LawSchool,ShandongUniversityofTechnology,Zibo255049,China)
2014 is the starting year of fully implemented the reform of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Localized reforming schemes concern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for short) & property mashroomed. Some new policies were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SOEs. Government by law has apparantly turned out to be a realistic path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capacity. There exist, however, in the reforming schemes of local SOEs, a lack of legal thought. To make up for all the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ring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property refroms into the legal path.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classified reforming; legalization
2015-01-1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青年項目“國有企業類型化改革與監管的法律體系重構”(14YJC820018);山東省科技廳軟科學項目“山東省國有企業類型化改革的法律保障機制研究”(2014RKB01574)。
封延會,男,河北鹿泉人,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馬東順,男,山東招遠人,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
F276.1
A
1672-0040(2015)02-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