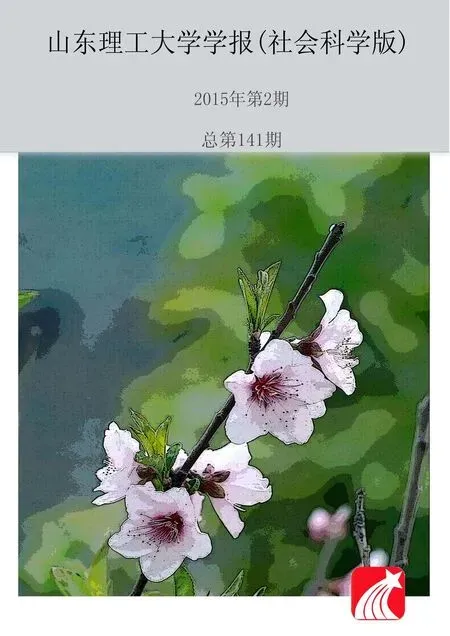民間法精神及在鄉村治理中的重塑
李美香,呂曉明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民間法精神及在鄉村治理中的重塑
李美香,呂曉明
(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山東淄博255049)
傳統民間法以和合精神為指導處理家庭、宗族、鄉黨等關系,強調和睦、合約與和諧,在秉承義務本位的同時也強調有限的權利義務對等,其與和諧社會和法治建設有一定的契合之處。民間法根植于活生生的鄉土生活,是鄉土社會自發性、地方性的資源,且因鄉民的內心確信而具有實效性,在建構鄉村秩序過程中能夠發揮國家法尚難起到的作用。基于此,在鄉村社會治理中,既要重視國家法對民間法有益內容的吸收,注意二者的協調;同時又要注意發揮民間法在解決糾紛、維護和形成和諧鄉村社會秩序中的作用。
國家法;民間法;和合精神;鄉村治理
作為一個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均衡的,同時在發展和轉型中的大國,中國的法律(此處指國家的制定法)雖然在整體上是統一和邏輯自洽的,但是中國的法治傳統卻與西方有諸多不盡相同之處。這種不同之處更多的體現在中國法治背景中隱含的本土資源更為豐富和復雜。立法中的“城市本位”忽略了鄉村實情及需求,移植來的理性建構的先進法律制度在獨具特色的國情中適用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在此背景下,作為法律文化之傳承的民間法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浸潤中國基層社會特別是鄉村社會的民間法對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產生諸多積極作用,其精神意旨與現代社會治理有暗合之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通過對民間法與國家法關系的梳理與定位,將對現代鄉村社會治理大有裨益。
一、傳統民間法的精神意旨與現代社會治理的暗合之處
傳統民間法在精神意旨上強調和合精神,提倡和睦、合約與和諧,對鄉村社會秩序的形成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傳統民間法在價值取向上以義務為本位,但也并不是只強調義務的履行,否認或不重視權利的享有,其也強調利益均衡基礎上有限度的權利義務對等,這與當代鄉村社會實情有切合之處。
(一)和合精神暗合和諧社會的目標取向
人際關系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基石。中華民族以和為貴,和合即和睦團結、親鄰友善、敬業樂群。說文解字曰:“和,相應也,從口。”“合,口也。從亼從口。三口相同是為合”。這表明人的行為恰到好處,合于道義;人與人彼此和好親近,形成和諧協調的人際關系。和合既是和諧社會的合理內核,也是傳統民間法的精神意旨。
首先,和合精神強調婚姻、家庭、宗族、鄉鄰等人際關系的和睦。以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放妻書(即古代的休書)為例,與我們通常理解的感情破裂的夫妻雙方水火不相容的婚姻關系不同,放妻書十分強調夫妻間的情愛與感情:如夫妻“恩深義重”“恩義深極”,婚姻中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在于“前世冤家,販(皈)目生嫌”。既如此,冤家宜解不宜結,二人應相互祝福,“相隔之后,更選重官雙職之夫”,“選聘高官之主,解冤釋結,更莫相憎”。[1]在宗族、鄉鄰關系方面也強調和睦友善。元代《鄭氏規范》要求族人“當以和對待鄉曲”;明代《蔣氏家訓》要求族人“和睦鄰里族黨”;[2]光緒年間的《項里錢氏宗族》提出和睦宗族的基本要求是“親親、老老、賢賢”和“矜幼弱、恤孤寡、周窘急、解紛競”。[3]此外,宗規族訓也強調對鄉親里黨體恤照顧、扶危救困。例如明代《鄭氏規范》第十九條規定:“凡遇兇荒事故,或有闕支,家長預為區劃,不使匱乏。”[4]349
其次,和合精神強調對民事合約的尊重。“民從私契、官不為理”說明國家法對民間契約的控管是有限的,這也為民事習慣法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同時也說明鄉村民眾已經具有了“私法自治”和“契約即法”的理念。例如《北涼承平八年翟紹遠買婢券》《高昌延昌二十八年趙顯曹夏田契》中均有“和同立券”“先和后券”或“兩和立契”等表述。[5]明清時期調整宗族內外部關系的族內合約、族外合約,少數民族地區的“榔規”“款約”“料話”等,也無不體現出民間法的“合約”精神。
再次,和合精神在糾紛處理方面主要體現為強調道德教化,以和解、調解的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沖突矛盾,重視社會關系的和諧。諸多家規族法均要求族人在發生糾紛時要以寬容、諒解的方式來化解矛盾,避免沖突擴大。《鄭氏規范》要求族人要“和待鄉曲,寧我容人,毋使人容我”。[2]廣西西林岑氏家族族法強調:“若與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始秉公斷。倘止戶婚田土閑氣小忿,無論屈在本族、屈在他姓,亦以延請族黨委屈調停和息。”[2]通過說“情”論“理”的調解,一方面可以維持宗族內部的和諧穩定;另一方面,依據民間法進行的傳統民間調解結果具有較強的有效性,規范義務人相互比較熟悉,監督相對容易,違規成本較高,這就使得其實際有效性增強。
(二)“有限度的權利義務對等”原則切合鄉村社會實情
傳統民間法以義務為本位,重視義務的分配與履行,其差序格局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6]29傳統民間法在強調義務本位的前提下,也重視權利義務的對等。當然因為對尊卑、貴賤等級秩序的強調,權利義務的對等是有限度的。這一原則并不一概體現于民間法的所有方面,而只零散地分散于婚姻、家庭、鄰里、宗族的個別方面。例如作為古代離婚基本條件與限制的“七出”“三不去”,在賦予丈夫及夫家離婚主動權的同時又對這種權利進行了一定的限制。“三不去”中的“前貧賤后富貴”也是強調因為妻子對家庭財產及地位的提升做出的貢獻,所以不準夫家休妻;“與更三年喪”也是強調妻子對夫家盡了孝道(基于古代人平均壽命較短這一客觀事實,古代已婚婦女相較于現代而言,更容易符合這一條件),所以不準夫家休妻。“三不去”也成為捍衛女性權利的有力武器。在財產繼承權方面,雖然各朝代對女子繼承權的規定不盡一致,但大都規定出嫁女原則上在娘家沒有繼承權,原因在于出嫁女在出嫁時已得到了一份嫁妝,從中國古代民法的觀點看,其繼承權已提前實現,同時由于出嫁女對父母沒有贍養義務,自然也不能繼承父母的遺產。在立嗣繼承方面,因為繼子(無論是立繼子還是命繼子)在被繼承人喪葬祭祀等方面盡了一定的義務,故其也有一定的繼承權。
二、轉型期民間法存在的合理性
國家法作為理性建構的產物,強調的是規范的邏輯性與統一性;民間法作為經驗的積累,強調的是法律文化的傳承性與區域性。無論作為何種形式存在的民間法,都是生活、生產智慧的總結與積累。立足于社會轉型期的現實國情和法律多元化的現狀,由于國家法自身的不足及缺陷,民間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一)民間法是鄉土社會自發性、地方性的資源
自發秩序是“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產物”,其形成依賴于生活經驗的總結和積累。作為自發秩序的民間法就是生活經驗的文化總結。[7]民間法作為一種生于民間的知識系統,是在鄉民長期生活、勞作、交往過程中生長出來的,具有自發性和豐富的地方色彩。[8]152民間法的理念也蘊涵于地方性知識當中,通過人們長期的生產、生活而逐漸產生并緩慢發展,它是日常生活的經驗總結,順應了鄉土社會鄉民們的生活、生產習慣和思想、行為模式。以財產繼承問題為例,按照我國《憲法》及《繼承法》規定的男女平等原則,出嫁女在財產繼承方面享有與男性繼承人同等的權利。然而這種規定在農村地區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執行。究其原因不在于出嫁女不知法懂法,而在于她們都在遵循一個民間潛在的“習慣”,一方面因為自己出嫁所以不能及時地照顧父母,對父母盡的贍養義務不足;另一方面如果自己將來有什么事,把房產留給叔伯兄弟后,尚可仰仗他們。人們選擇民間法來解決糾紛,既能維持良好的社會關系,又符合了鄉民們樸素而又理性的價值觀。
(二)民間法因鄉民的內心確信而具有實效性
民間法內生于社會,植根于現實社會需求的土壤中。從自身因素而言,雖然相較于國家法而言,民間法顯得較為粗糙,邏輯性、體系性不強,但仍具有規范性、權利義務性、權威性等法律的基本特征。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民間法能有效地分配爭執雙方的權利義務,調整和解決利益沖突。以山東省近年發生的多起“頂盆發喪應否獲繼承權”糾紛為例,法院并沒有局限于《繼承法》對法定繼承人范圍的界定,而是強調“頂盆發喪”是一種民間風俗,頂盆發喪者在喪事辦理過程中為死者盡了一定的義務,理應獲得相應的權利,其作為民間風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民間法在具有外在實效的同時,也是鄉民的內心確信,對鄉民的行為具有道德約束力,具備了內在的實效達致路徑。民間法的自發性、內在性特質,使其作為生活經驗的總結和積累,內化為人們的思考和行為習慣,而習慣難以通過外在的理性建構在短期內改變的,這也使得民間法具有了強勁的生命力。正如R·賽登所說:“這些規則盡管從來沒有被設計過,但保留它對每個人都有利。”[9]54
(三)國家法自身的缺陷
法治不僅僅是法律形式的合理化、法律程序的嚴密化和法律技術的精確化,如果將這樣的過程視為法治,只會形成“法律越來越多但是秩序越來越少的社會”。[10]356國家法的適用范圍是有限度的。基于理性的有限性,國家法難免出現漏洞和空白,而法律糾紛又不能以“法律未作規定”為由而拒絕解決,所以必須尋找填補法律漏洞和空白的其他法源,民間法或習慣法便成了各國立法和司法求助的對象。同時,法律的干預是有代價的,任何法律糾紛的解決都要考慮“正義的成本”問題,考慮在追求公平正義時需要耗費多少人力物力。[11]31如果能用較少的成本解決同樣的問題且執行效果更好,人們自然會作出自己所認為的更優的選擇。作為社會差異性和自主性產物的民間法,主要依靠鄉民的自覺遵守來維系其實效性,實施成本相對較小。因此,只要民間法能夠及時公正調整的事務,一般不需要國家法律的“出場”。
三、鄉村治理中民間法的重塑
我們應當承認,民間法內生于基層社會,其具有外在實效和內在實效的基礎是社會結構較為穩定、社會變遷緩慢、人員很少或較少流動。對于結構劇烈變遷、觀念急劇轉變的社會而言,民間法的實效性會大打折扣。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雖然國家法的范圍不斷擴大,但根植于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生產中的民間法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自身的運行邏輯,推進鄉村治理必須理性認識民間法,重塑民間法的地位和作用。
(一)理順民間法與國家法的關系
“在國家制定法與民間法發生沖突時,不能公式地強調以國家法同化民間法,而是應當尋求國家制定法與民間法的相互妥協和合作”。[12]61民間法與國家法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在鄉村建設中,二者應該相互結合,共同發揮作用。首先,國家法是實現鄉村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手段。盡管在中國鄉村社會與城市社會有著很大的區別,部分國家法在立法層面更多以城市社會作為出發點,對農村需求和利益考慮不夠,但隨著鄉村變遷和人員流動,人們的觀念也在逐漸發生轉變。民間法主要依靠道德、輿論來發揮作用,其確定性和強制力不夠。其次,民間法的調整范圍有限,主要局限于私法領域,對公法領域糾紛的解決以及運用民間法難以解決的糾紛還是需要國家法的出面。因此,要構建鄉村社會法律秩序,必須承認國家法的主導地位和作用。
民間法也是構建鄉村社會法律秩序不可缺少的因素。“幾十年來連續不斷的各項政治運動與社會變遷,伴隨著國家法制的強制推進和各種形式的社會動員,最多是使鄉土社會習慣法暫時蟄伏,實質上仍以種種私下變通的方式存續”。[13]民間法可以較好地彌補國家法的不足和缺陷,在解決糾紛時能夠提高效率、節約法律成本,同時又符合了鄉民樸素的法律意識,更易于為鄉民所認可和選擇適用。
(二)注重國家法對民間法的合理吸收
在法律制度的創制層面,需要合理劃分民間法和國家法的效力范圍,在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領域,因其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應由國家法予以規定,避免民間法的侵入和干預。而在婚姻、繼承、民事交往、民事糾紛處理等私法領域,國家法可以積極吸收民間法的內容,或者通過彈性法律條款對民間法的內容和效力予以認可。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鼓勵和幫助鄉村制定鄉規民約,把國家法不能覆蓋的生活領域納入民間法的范圍之中。
在發現民間法過程中,要注意民間法是否與國家法的基本法律精神相一致。田成有先生按照國家法的善惡之分,將民間法劃分為“優秀的民間法”與“糟糕的民間法”兩種,并指出“糟糕的民間法”最終會導致民間法被破壞,降低國家法的權威,使國家法在實施中被冷落、擱置和規避。[14]因此,在發現民間法過程中,必須秉承法律精神,遵守法律原則。如果民間法背離了國家法的基本精神,可能會導致民間法與國家法的對立、鄉村與國家的脫節,出現無法無天的局面。
(三)發揮民間法的糾紛解決功能
糾紛解決機制應該體現對人的關懷與尊重,以社會成員多層次、多樣性的社會需求為出發點。現代社會是多元的社會,由于利益的多元、社會關系的多元、價值觀的多元以及文化傳統的多元,決定了人們對公平和效率的理解和追求不同。因此,訴訟不能也不會是人們追求理想正義的唯一手段。法人類學和法社會學的研究成果表明,糾紛解決機制應根據社會的實際需要和風俗習慣來建立。現在,各國都十分重視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例如美國建立了多樣性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即所謂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日本在民事訴訟中建立了調停制度。我國的糾紛解決機制也不應一味強調訴訟的功能和作用,而應建立符合我國現實需要的多元糾紛解決體系。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要配合有關部門大力發展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擴大調解主體范圍、完善調解機制的要求。2013年,中央也重提“楓橋經驗”,要求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重視民間規則,重視群眾自身的生活實際。在鄉村社會中,鄉民的正義觀具有重“情”“理”“義”的特點,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往往在正當的利益之外,還要考慮天理人情和彼此的面子,考慮以后雙方交往的方便。基于此,鄉村社會更重視代替性的糾紛解決機制,即調解。通過調解解決糾紛,既能夠滿足鄉民們“省事”“省錢”“公正”的需要,同時又能兼顧鄉村社會人與人之間相互熟識、相互依賴的現實,避免人際關系的疏遠或破裂。
四、結語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正處于從“鄉土”走向“現代”的路上,但由于我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各地的現代化程度差距甚大,地緣文化因素廣泛多變,民間法還有其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合理性。傳統民間法價值取向、精神意旨與現代法治理念的有限契合,也為民間法在鄉村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提供了理論支持。在鄉村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護過程中,既要注重國家法和民間法的協調和溝通,又要為民間法的生長和發展提供可能。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構建和諧的多元化鄉土社會法律秩序,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1]張艷云.從敦煌《放妻書》看唐代婚姻中的和離制度[J].敦煌研究,1999,(2).
[2]陳延斌,張琳.宗規族訓的敦族睦鄰教化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J].齊魯學刊,2009,(6).
[3]付微明.習慣法精神及其對中國傳統鄉村治理的作用和影響[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8).
[4]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霍存福,劉曉林.契約本性與古代中國的契約自由、平等——中國古代契約語言與社會史的考察[J].甘肅社會科學,2010,(2).
[6]費孝通.鄉土中國[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
[7]于語和.論中國傳統民間法的根本特質[J].甘肅理論學刊,2014,(1).
[8]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9]Robert Sugden.TheEconomicsofRightsCooperationandWelfare[M]. Oxford Blackw,1986.
[10][美]羅伯特·C·埃爾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11]熊秉元.正義的成本[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12]朱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13]喻名峰.后鄉土社會法治秩序的構建[J].甘肅社會科學,2007,(1).
[14]田成有.鄉土社會中的國家法與民間法[J].開放時代,2001,(9).
(責任編輯 李逢超)
2014-10-05
李美香,女,山東青島人,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講師;呂曉明,女,山東淄博人,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DF0-052
A
1672-0040(2015)02-0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