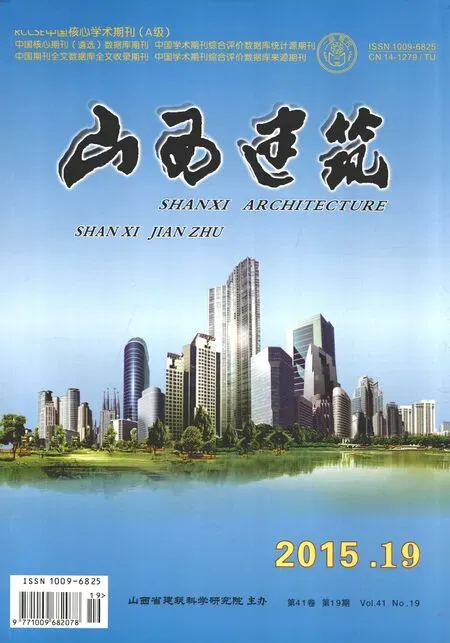從城鄉規劃的視角談城鄉環境正義問題
桂昆鵬
(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廣東廣州 510060)
長期以來,城鄉之間的經濟差距是黨和國家、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而對于城鄉之間越來越凸顯的生態環境方面的不平等關系缺乏關注。隨著生態文明成為國家戰略而得到高度重視,城市生態建設的投入也將加大,生態環境將會持續改善,但鄉村的生態環境變得越來越差,甚至成為城市環境改善的犧牲品。這種“城市環境趨向好轉,農村環境不斷惡化”的二元趨勢的逐漸凸顯反映了我國城鄉環境不正義的問題。
1 環境正義的內涵與研究進展
倫理學大辭典對環境正義的定義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所有人都應擁有平等地享受清潔環境的權利,二是環境享用的權利和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義務相統一[1]。這表明在社會中任何人或者群體均具有共享良好的自然環境與天然資源的權利,都不應當承擔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城市規劃中常常討論的綠地的均等化布局屬于前者,而鄰避現象(NIMBY,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的后院)則屬于后者。實際中所討論的環境正義大多集中于消極一面,這是由于環境正義運動直接起因于環境風險的不公平分配這一事實。1982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沃倫縣的500多名居民舉行游行示威,試圖阻止在阿夫頓社區附近建造多氯聯苯廢物填埋場而遭到逮捕[2]。由于華倫郡是北卡羅來納州最窮困的郡之一,加上當地居民以黑人居多,當時參與抗議的居民們認定,這個設施的選址與興建一定和當地的種族構成有關。人們指責這實際上是一種環境種族主義,并成立了許多基層環境正義組織展開活動。許多關注少數民族社區問題的機構和學者立刻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不少研究報告支持環境種族主義的結論,并推動了第一次全國有色人種環境峰會在華盛頓召開,并對美國的環境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與此同時,學者對環境正義的研究迅速擴展到了全球。日本學者飯島伸子也對漁民和半農半漁民群體遭受環境不平等現象進行了實證研究[3];印度學者古哈對貧窮國家和弱勢群體的環境保護予以了積極的探索[4],指出了環境正義是存在國家、地域、階層以及不同群體的差別的,強調了“窮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表達了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實現“環境正義”的呼聲。
我國對環境正義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臺灣地區比大陸地區稍早,這與我國臺灣地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環境正義運動有關。其中蘭嶼核廢料貯存廠的例子是臺灣地區環境正義問題的首要案例。有學者認為蘭嶼居民的構成以原住民為主,因此反核廢運動與原住民的社會處境有著高度的關聯,原住民社會經濟地位一般較低[5]。大陸地區的研究較為落后,目前學術刊物上有關環境正義的文章有增多的趨勢,大多是國外理論介紹和借鑒,還很不成系統,實證研究也比較缺乏,理論方面主要集中于哲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角度[6,7]。
2 城鄉規劃中的環境不正義的表現形式
環境不正義的現象廣泛存在于不同國家和種族之間,在當今中國,環境不正義的現象主要存在于不同經濟地位的利益群體之間,在區域尺度上反映為城鄉之間。作為城鄉空間資源分配手段,城鄉規劃是一只強有力的看得見的手,它從空間資源分配的角度,影響著生態、生產和生活空間布局和依存關系,也影響了城鄉環境正義。歸結起來,城市規劃中的城鄉之間的環境正義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表現形式。
2.1 鄉村環境衛生設施的缺乏
隨著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方式的變化,農村的污染日益加劇,相當數量的農村地區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以廣州南沙區為例,2013年對南沙區全區128條行政村開展的現狀摸查結果表明,由于農村居民人口分散,垃圾收集困難,雖然每個村幾乎都有垃圾收集站,覆蓋率較高,但運營狀況不好,農村的生活垃圾圍村依然存在。大部分區域沒有任何生活污水的收集和處理設施,現有的明溝排水系統亦已經年久失修或者堵塞,生活污水未經有效處理直接排放,大部分地區河、湖等水體普遍受到污染,飲用水水質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2.2 城市污染物和污染源向鄉村地區布局
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發布《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報告》,報告顯示,城市生活垃圾從1979年的2 508萬t增長至2012年的17 081萬t,增加了5.8倍。由于城市垃圾的排放量逐步增加,歷史欠賬太多,城市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依然嚴重滯后。許多城市,尤其是縣級城市和鄉鎮遠未建立起完善的垃圾處理體系,多數生活垃圾被運到郊區或者農村進行處理或者簡單堆放。“城內干干凈凈,城外垃圾成堆”成了許多地方的普遍現象,這種現象在一些地方的城鄉接合部尤為嚴重。同時,隨著近年來城市“退二進三”、轉型升級,城市技術落后、污染嚴重的工業企業向農村地區遷移,由于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一些村民在得到一些所謂的“實惠”后就認可了這些企業的存在,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極易造成農村地區的環境污染。
3 城鄉規劃中的環境不正義原因探析
3.1 城市規劃中公眾利益被等同于大多數人的利益
城市規劃是政府調控城市空間資源、指導城鄉發展與建設、維護社會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眾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但公共利益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概念,盡管為大多數國家的立法所認可,但至今卻沒有一個完整明確的定義和范圍,而且往往與價值判斷密切相關,隨著時間空間的轉換而有不同的內涵,因為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背景以及不同的個案有不同的解釋。不但立法上存在著解釋的困境,學術界也沒有統一的學說。在中國普遍“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多數就是對的”的集體權威[8],甚至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由而濫用公權力,從而忽視了少數的利益。從人口規模和人口密度的角度來看,相對于城市,鄉村就成了“少數”,因此在大多數人的良好生活環境面前,少數人的利益就容易被忽略。
3.2 鄰避設施規劃選址過程中最小抵抗路徑
政府決策者通過城市規劃手段來進行鄰避設施的選址,如污水處理廠、垃圾填埋場、垃圾焚燒發電站、高污染企業等,若政府將鄰避設施布局在離城市較近的地方,會遭遇極大的抵抗,導致無法實施。即便規劃通過,落地實施,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投訴和抵制,使得項目中斷或才建幾年就遭到拆除的命運。而鄉村地區的居民由于分布廣泛,影響人群相對較小,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成為鄰避設施選址的第一選擇。更為關鍵的是,鄉村地區信息獲取渠道少、權利意識不夠強、自發組織能力弱,對政府實施該類選址方案的抵抗力弱,并且更容易接受經濟補償而默許方案的實施。因此,政府、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權利博弈形成了最小抵抗路徑,鄰避設施規劃才能不至于夭折或毫無操作性。
4 規劃對策與建議
4.1 將城鄉環境正義理念貫穿城鄉規劃
在城鄉規劃中應當貫穿城鄉環境正義的理念,來考慮城鄉的內涵式發展。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在環境正義與城市增長之間,城市政府的偏好是追求經濟效益,我國經濟多年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形勢日益嚴峻,目前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若繼續堅持將經濟效益增長置于環境正義之上,將城市的環境改善建立在鄉村的污染基礎上,則建設生態文明將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只有上升到正義的認識高度,才能在建設生態文明、城鄉統籌上取得進步。
4.2 進一步促進城鄉統籌,共享城鄉環衛設施
在城鄉統籌的過程中,應當將城市與農村的環衛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通過統一規劃,統一安排,科學有序地開展城鄉環境衛生一體化工作,徹底解決農村環衛事業發展滯后、“垃圾圍村”、環境臟亂差的問題。具體而言,應當加大農村環衛設施的建設,將農村生活污水就近并入城市污水管網,城鄉垃圾收集系統應當覆蓋至農村地區。
4.3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消除鄉村地區的城市污染
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提高財政投入和建設水平,將城市對鄉村的客觀環境影響降到最低,從而有利于實現相對的環境正義。例如,隨著環保技術發展,現在的垃圾填埋場可以開發成公園、小球訓練中心等露天娛樂場所,實現以可持續的利用方式,在生態恢復基礎上消除污染、保護環境,讓地方生態與經濟價值再生。
4.4 大力推進鄉村規劃師制度,提高鄉村居民參與程度
在我國鄰避設施選址決策過程中,往往是政府決策和專家參與,選址周邊區域內的居民在之前并不知情,只是選址決定后才以網站公示的方式告知公眾,或由大政府決策后通知下一級政府。公眾是否參與、如何參與都不由自主,大部分情況下只能通過規劃調查、規劃公示等渠道被動參與。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決策思維使得城鄉環境正義無法得到提高。但提高廣大農民權利意識和參與深度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應當重視鄉村規劃師制度的建設,每年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優秀的規劃專業人才派駐到鄉鎮,代表鄉鎮政府履行規劃職能,為農民提供規劃資訊,并將農民和下一級政府的意愿通過規劃的語言反饋給上級政府,提高鄉村的規劃參與程度。
[1]朱貽庭.倫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2]王小文,王國聘.對美國環境正義的研究[J].環境保護,2007,378(16):62-64.
[3]飯島伸子.環境社會學[M].包智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4]拉瑪昌德拉·古哈.激進的美國環境保護主義和荒野保護[N].吳 蓓,譯.中國青年報,2001-02-06.
[5]紀駿杰.環境正義:環境社會學的規范性關懷[A].臺灣第一屆環境價值觀與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C].1996.
[6]馬 晶.環境正義的法哲學研究[D].吉林:吉林大學,2005.
[7]王歡歡.環境法正義價值之反思——以社會性別為視角[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6(5):86-90.
[8]張震東.正義及相關問題[D].臺北:中研院社科所,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