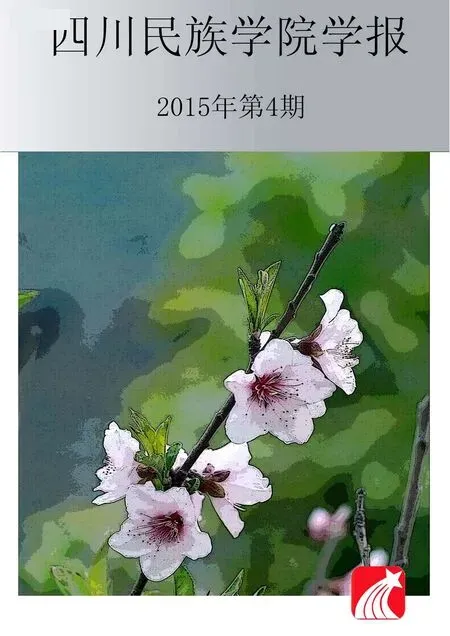對 “六寨苗”“跳花”文化的表現形式及其文化變遷的一點思考
周武畢
苗族是在中華歷史長河中文化淵源比較久遠的民族之一,支系龐雜,目前在國內主要分布于西南和中南的八個省市區。其中,人口分布最多的要數地處于西南邊陲的多民族省份貴州,而“六寨苗”就是主要分布于貴州黔西北地區的一個苗族支系。
“跳花”是“六寨苗”一個比較隆重的民族傳統節日。不僅融合了苗族傳統的語言與服飾特色,還飽含著以苗族傳統歌舞為表現形式的一種古老的民族婚戀交往方式。因此,對于當地的苗族同胞來說,“跳花”是他們文化傳承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對于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研究者來說,“跳花”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支系的文化表現形式,更多是它能體現出某一地區、某一民族的文化內涵及其文化變遷,對民族文化遺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六寨苗”的族源及“跳花”概況
(一)“六寨苗”的族源
據史料記載:“明朝洪武年間 (公元1371一1382年),朱元璋調南征北,其中有苗族6萬多人被逼迫參戰,戰后幸存者有12000余人,居于四川永寧 (苗語稱永寧為阿凱——今敘永縣)休養生息”[1]。到了清朝康熙三年 (公元1664年),水西、隴納等地發生了苗民起義,吳三桂從云南、貴州和廣西三省調集軍隊進行鎮壓,其中,有從敘永抽調的苗民幾千人,在平定了水西之后,吳三桂就命令這些苗民居住在大定 (今大方)的八堡、興隆一帶,并逐漸形成了阿龔寨(今菱角塘、大寨、青杠林、櫻桃)、青山寨 (含青山、板板橋、石板、法窩、大溝)、中寨(含中寨、五龍寨、三口塘)、仄垮寨 (今下寨、新房子)、燁匠寨 (上寨、新寨)和新開寨(今新開新寨),這六個自然村寨。而這些生活在這六個村寨的苗民最終被稱為“六寨苗”,成為苗族眾多支系的一支。
(二)關于“跳花”
“跳花”,又稱為跳場、跳廠、跳月、蘆笙會、跳花場等等,雖然名稱各有差異,但是內容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區別不大。關于跳花的起源有很多種傳說,對于跳花的記載也有很多,例如,清代方亨咸《苗俗紀聞》載:苗民“其婚也無媒約,男壯而無室者……登山四望,吹樹葉作呦呦聲,則知為馬郎至矣。未字之女,群往從之,任自相擇配”[2]。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古籍文獻對這一習俗有過記載,比如愛必達的《黔南識略》、李宗防的《黔記》、羅繞典的《黔南職方紀略》、貝青喬的《苗俗記》、徐家干的《苗疆見聞錄》等。可見,“跳花”在貴州一直都是深受苗族青年男女喜愛且兼具社會交際和娛樂功能的活動。“六寨苗”的“跳花”一般有春節跳花和端午跳花兩種,春節跳花一般從大年初一跳到初四,一般按照自然村寨、姓氏和家族來劃分花山點,“到了大年除夕的那天,姑娘們各自穿上節日的盛裝來到花山點,迎接小伙子們的到來”[2]。端午節的“跳花”則主要是在農歷五月五日這天,紀念苗族的始祖蚩尤而興起的。每到這一天,“六寨苗”的苗族同胞們就會相聚于花山點,進行節日的慶祝。
二、“六寨苗”“跳花”文化的表現形式
(一)解腰帶
在“六寨苗”春節的“跳花節”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解腰帶”,在這個活動期間,姑娘們一般都會戴上腰帶和“褂褂”(苗族的一種服飾),當遇到心儀的異性時,就會主動把腰帶或“褂褂”贈送給他,以此作為憑證,來表達自己對他的好感。如果男方對女方也中意,就會說“我拿回去玩幾天再還給你”,等到還腰帶或“褂褂”的時候男方就會托媒人去女方家里提親。而如果是小伙子看上了某個姑娘,也可以走到她的面前,去向她討腰帶或“褂褂”。如果姑娘對這個小伙子滿意,就會把腰帶給他,過一會再去向他討回,如果男方確定自己喜歡女方,就會向女方要求腰帶讓自己玩幾天再歸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寨苗”的跳花節上,姑娘可以把腰帶贈送給多個小伙子,然后從中挑選自己最為中意的一個,小伙子也可以接受多個姑娘的腰帶,不管喜不喜歡對方,這個時候就是出于一種禮貌和尊重。如果小伙子不喜歡那個姑娘,可以先把腰帶帶走,過幾天再主動把腰帶還給姑娘,如果姑娘不喜歡向自己討腰帶的那個小伙子,也可以拒絕送給他腰帶。同時腰帶除了是男女青年傳情達意的媒介之外,還是用來衡量女子是否心靈手巧的一個標準。
(二)蘆笙舞
對于在“六寨苗”的青年男子而言,跳花節上的一個重頭戲就是表演自己的蘆笙技藝,以此來吸引姑娘們的注意。他們會吹起蘆笙,伴隨著蘆笙跳起舞,盡情的展現自己。而那些能夠吹奏出悅耳的蘆笙,跳起優美的舞蹈的青年們,除了能夠收獲大家的贊美之外,還能夠俘獲姑娘們的芳心。
在“六寨苗”的跳花節上,吹奏蘆笙多與舞蹈相結合,蘆笙舞是苗族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般是圍成一個圓圈,由男子吹著蘆笙在前面,面朝圈里,橫身領舞前進,女子緊隨其后,面朝著前進方向,隨著音樂而舞,左右腳交替前進。通過這樣的文化表現形式,苗族的山歌、蘆笙和舞蹈才能能夠得到較好的傳承。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走進了學校學習文化知識,或者是走出了寨子去外面務工,唱歌跳舞的時間也就變得少了。特別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接觸到與本民族不相同的文化環境和內容后,對于自己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也會逐漸淡漠。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他們去學習本民族的歌曲和舞蹈,可能收效不大。這就是現代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給人們所帶來的影響,使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計方式都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也反應在了文化的變遷上。
(三)苗族服飾展示
在“六寨苗”的跳花節上,民族服飾展示是其中一個比較“亮眼”的內容。尤其是苗族的姑娘們及其父母親都會很重視這種展示自我的機會。姑娘們往往會在節日中梳洗打扮一番,穿上節日的盛裝,戴上精致的首飾,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跳花場上,人們可以從她們的服飾上看出姑娘們各自的刺繡手藝。換句話說,跳花節上不僅僅是苗族服飾的展示,其中更包含了競賽的成分。姑娘們通過本民族這種最精致華美的民族裝扮來“亮家底”,既有告慰祖宗的含義,也有通過這種方式擇偶的意圖。
三、“六寨苗”“跳花”的文化變遷
在市場經濟為主體,城市化進程高度發展的今天,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經受了不同文化形式和文化環境的影響和沖擊,就從“六寨苗” “跳花”這樣的民族傳統節日里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
(一)“跳花”主體的變化
跳花節雖然仍是“六寨苗”最為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但由于外出務工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每年參加跳花的人數也就相應地減少了。
(二)文化表現形式的變化
隨著“六寨苗”外出打工的人數的增多和時間的延長,很多年輕人都已經不再會演唱本民族的歌曲以及演奏本民族的樂器。同時,自己的民族服飾穿著習慣也會在外出務工中慢慢被舍棄,久而久之,這些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們就不再梳傳統的民族發型,不再穿著民族服飾,不再有時間做刺繡等手工藝,甚至不再參加世代相傳的“跳花”。
(三)婚戀方式的變化
傳統的“跳花”,除了是娛樂活動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戀愛交往。然而現在,“六寨苗”跳花節的這一功能正在逐漸的喪失。由于青年男女們大都外出務工,已經很少有人再參加“跳花”了,即使去跳了,在他們心中的“跳花”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神圣了。以前的老年人基本都是通過“跳花”、對歌認識結婚的,而對于“六寨苗”的年輕人來說,“跳花”只是一個娛樂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聊聊天,僅此而已,很少有人再像以前一樣想要在跳花節上去找尋伴侶了。
隨著信息網絡時代的來臨。“六寨苗”的年輕人們相互認識和了解的方式和途徑就豐富了許多,除了通過在外打工認識、朋友介紹之外,還多了手機聯系和網絡聊天等現代化的戀愛方式。不用通過跳花節的活動,他們也一樣可以認識異性,交到朋友。所以,他們對跳花節的依賴就很小,也就不再像以前老人們對待跳花節那么重視和依賴“跳花”這個曾經神圣而浪漫的活動了。
四、對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幾點建議
正如“跳花節”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化事項,其中包含了苗族的語言、服飾、歌舞等內容,民族傳統文化往往包涵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如果不對其進行保護的話,這些飽含著民族記憶的優秀文化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社會的發展而逐漸消失了。
(一)加強政府引導
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制度和保護條例來進行保護,將對文化的重視上升到法律的層面,通過法律來規范和管理。不僅如此,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政府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有了政府的重視,民眾才會受到鼓舞,增加對文化的重視,從而積極投入到對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中去。
(二)發揮文化持有者的積極性
文化的傳承并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更多的是要依靠本民族的精英分子,由掌握本民族優秀文化和傳統技藝的人才來進行傳承和發展,他們無疑是最有發言權的。可以通過成立一些類似于傳承人協會之類的民間團體,采取協會管理的模式,用行業自理的方式來進行傳承,與政府引導相結合,促進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
(三)注重學校教育的作用
學校教育在民族文化的傳承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增加對教育的投入,通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開設一些教授民族文化的課程,比如苗語,苗族蘆笙舞,苗族傳統蠟染等,來強化少數民族青少年對于自己文化的認識,建立一種文化自覺,讓他們從小就接觸到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建立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讓他們有熱情去主動學習自己民族的文化。
(四)傳承與發展相結合
文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在發展,相應地,文化也會做出一些適當的調整來適應社會的變遷,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下去。但是這種發展并不意味著以為的去迎合,而是要保持本民族傳統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不變,同時注入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喚起更多人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
五、結語
民族傳統節日是民族文化繼承和發揚的重要形式和內容。民族同胞利用傳統節日的活動形式定期進行文化的交流,才能讓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得以在民族群眾的生活中延續和傳承下來,而不至于淡化或消失。從“六寨苗”“跳花”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民族傳統文化表現形式正在慢慢消失。為了生存,很多年輕人都不得不離開家鄉外出打工,在打工的過程中就會逐漸的接觸到外界不同形式的文化,并逐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沖擊,也可以說是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結果。這其中,也有利與弊的辯證關系。有利的是,年輕人在外打工掙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水平。另外,他們會從外帶回一些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式,尤其是一些新的思想與觀念,都會對留在村寨里的人們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弊的方面來看,隨著外出打工人員的增多,留守在村寨里的能夠傳承本民族文化形態的人越來越少,弘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意識和觀念就越來越淡薄,民族傳統文化不能得到繼承和發揚,從而導致中國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逐漸消失和枯竭,影響深遠。
[1]大方縣民族宗教事務局.六寨苗族[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p2、p66
[2][清]方亨咸.苗俗紀聞,掃葉山房清末至民國間版,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