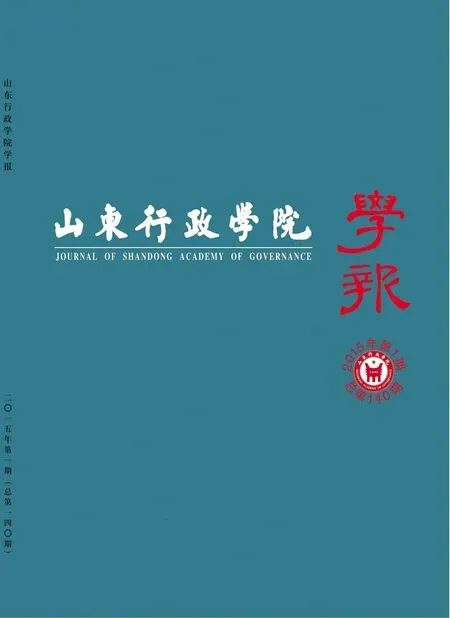墨家思想探析——以中國農村社會的價值重構為視角
張巖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
墨家思想探析
——以中國農村社會的價值重構為視角
張巖濤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
摘要:墨家學派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思想長河中熠熠生輝,“兼愛,非攻”的思想構成了墨家思想的理論核心,“尚同”、“尚賢”的思想構建了社會運行的良性機制,“節用”、“節葬”和“非樂”的思想對于當代社會倡儉節約的風尚的形成起到了理論支撐作用,“明鬼”、“天志”及“非命觀”孕育了中華民族虔誠的自然觀和奮斗不止的民族上進心與使命感。在現代化突飛猛進的今天,墨家思想對于轉型農村的建設和治理能夠起到價值重構、理念革新、人文回歸和公德重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墨家思想;兼愛;非攻;農村構建
一、引言
春秋末年,諸侯爭霸,戰事綿綿,各諸侯國處于激烈的動蕩之中,與此同時,學術思想領域也在孕育著一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戰爭。諸子論戰,思想擊撞,各學派都在紛紛探究經世治國之道和明理普世之學。墨家學派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大顯學也在歷史舞臺上發揮作用,以“兼愛,非攻”為理論核心的墨家學說理論豐富,具有濃郁的人文精神,兼愛非攻的普世哲學和愛好和平穩定的理想追求不僅彰顯了與儒學、道學的不同,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于當今社會轉型中的農村文化的構建和人文精神的培育更是起到一種價值標準的功能。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經濟、政治和文化高速發展的時期,城市化的潮流席卷了中國的各個角落,社會轉型時期的鄉村在城市化浪潮的面前表現出一種無措手足的現代性尷尬。中國農村在城市化的征途上引進了先進的技術、文明的理念和前沿的價值觀念,但是正是市場經濟和現代傳媒的滲透撕破了幾千年以來中國農村社會形成的穩定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現代性的生活邏輯尚未形成,而傳統的生活狀態已被摧毀得體無全膚。先進的理念還是在社會表層發揮著工具性作用,而未成為一種抽象的價值信仰體系,傳統的儒家思想在這種形勢的面前已經無法起到統領大局的作用,轉型中的中國農村建設陷入了一種精神空虛的困境。
墨家思想提倡“兼愛”、“非攻”,主張毫無等級的愛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對于當前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各種潛在問題和矛盾的化解以及社區情懷和集體記憶的建構起到一個很好的膠合作用;“尚賢”思想對于當前農村社區民主建設和社區管理的科學化具有重要的意義;“節用”等倡儉節約的思想不僅符合我國的憲法精神,更有利于維護和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公德。“明鬼”、“天志”等觀念也是重塑農民信仰和人文精神回歸的一個前提。
二、兼愛、非攻思想——引導價值重構
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向來一直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強大的穩定器和蓄水池而存在,因為農村有大片的農業土地和蘊含著無限生產力的農業人口,信息流動的緩慢性和文化的單一性、同質性使得農民思想和觀念更趨向于單純質樸,更有利于為社會的現代化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大環境,以及為現代化建設積累物質條件和社會財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農村再也不是費孝通老先生眼中的鄉土中國那樣,“捆綁在土地上的鄉下人”,由于現代傳媒、市場經濟的進入和對鄉土社會的滲透“感染”,中國農民的義利觀和價值觀逐漸出現異變,單純質樸的觀念被商業化的理性觀念所代替,傳統的人情關系開始變得更加理性化,衡量標準更加明晰,私的觀念占據了人們的思想觀念領地。農村社會逐漸呈現多元化發展模式,同質性減退,異質性增強,村民之間的熟悉程度降低,農村的“地方性共識”(1)的減弱也加劇了村莊內生秩序能力的喪失,村民對于村莊的主體感逐步喪失,越來越難以依靠內生的村莊秩序來維持世世代代在鄉村土地上生存的人們之間共同的價值理念和信仰,農村和農民、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農村社會正在從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鄉土中國向法理中國過渡。
中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人與人之間高度原子化和人情關系冷漠以及地方性共識的喪失,農民群體呈現機械化和無機化,團體行動力變弱。正是墨家所倡導的“兼愛”、“非攻”思想所預防和避免的,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包含著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指君臣、臣臣之間毫無等差的愛,消除階級、階層之間的隔閡,主張平等和愛。另一層意思是愛利相兼,即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墨子在體會到人的本性的基礎上主張在彼此獲利的基礎上去愛,在平等愛人的過程中彼此受益。農業社會商業化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農民從感性人和情感人向理性人和商業人轉變的過程中,勢必會發生傳統觀念和現代商業觀念的沖突,發生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潛在的社會矛盾,繼而會引起短時間的農民群體性精神焦慮和緊張,但是墨子主張在這種社會轉型和身份過渡的過程中注意平衡公和私、人情和利益的關系,做到義利共生共存,打破小農原有的宗族觀念,將分散或分裂的農村群體碎片用墨家的思想進行拼接粘合,用社會或集體本位來代替狹隘的宗族主義,倡導人人平等、兼愛,具體到市場活動中,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場誠信體系,呼吁誠信的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感,買賣雙方平等公平交易,使形成的“農業-商業”二元交易體系(2)在促進農民增收的過程中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同時也使得農民在和諧穩定的市場秩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之中彼此獲得收益,這也就是墨子所說的“兼相愛,交相利”。
三、尚同、尚賢——推動理念革新
墨家的尚同和尚賢的思想觀念相對于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具有鮮明的民主進步色彩,是由墨家的兼愛思想催生衍化而來,國家的治理,從下到上,從小集體到到大國家,從縣邑到中央,從諸侯到君王,都倡導賢人理政,即所謂“能者上”,任人唯賢,所謂“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尚賢中》)。從歷史的角度來縱觀,墨家尚賢的思想較儒家“尊尊君為首”的思想更具有進步性和理論性,更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更能與近現代的法制觀念相呼應,排除了世襲官制,賢人治國總比家族治國在理論上更具說服力和先進性。而尚同就是在尚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尚同思想的孕育和產生有其深厚的社會根源和文化根源,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諸侯割據、戰事頻頻的年代,國家四分五裂,而統一國家,統一政令是很多人的一種理想,人民希望建立一個君主一統的國家,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爭得社會地位,渴望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生活環境的迫切愿望。“這是當時墨學平民意識的集中體現,道出了平民要求參政的呼聲,是有進步意義的”[1]。其實,對于尚同的理解也可以解釋為人們否定個體化,推崇集體同一的一種價值觀和理想。不能說“尚同”是一種完美無缺的社會理想,這種思想容易發展成為君主高度專制制度,進而成為阻礙民主發展的因素,但是尚同尚一的觀念對于現代轉型過程中高度原子化的農民個體來說不失為一種值得的制度。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賀雪峰教授根據村干部個人的品行和治村能力將村級治理的形態分為四種類型,即好人型、強人型、惡人型和能人型。好人型治理是“從村干部的品性上來講的一般具有良好的人品和人緣,不愿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懲治村中任何一個村民,也缺乏讓一般村民畏懼的力量”,強人型治理是指“性格強悍之人治理村莊,這種人敢于與村中不良傾向作斗爭,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懼的健壯身體或暴烈個性”,但強人更容易向惡人轉化,所謂惡人治村,指的是“由惡人對村莊進行的治理,與強人不同的是惡人的私欲更重,撈取本來不多的村中公益或損害私益”,而大多數情況下,村民更期望能人治村,能人指的是“那些有特殊經營頭腦和一技之長的人,尤其是指那些已經發家致富的村民。為了不辜負村民對自己的熱望,這些能人也有參與村務的熱情。能人治村的好處有很多:第一,在個人已經富裕起來的情況下,他一般不會打村中公益的主意;第二,他有帶領村民致富的能力”[2]96-97村民的這種推崇能人治村的愿望與墨家的“尚賢”思想是一致的,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教育水平不是很高,村民素質也只是在中等水平線上下浮動,村務只能由品行優良和有政治主見、治村策略的人來治理。同時,村里又存在數個以宗族為單位的在數量上多于村干部但又少于普通百姓的大社員階層,這部分大社員大多是村內同姓宗族的代表人,有治村的才能,在品行和威信上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各自代表自己宗族的利益,往往對村主任或村支書的威望造成威脅。但是,在村民自治的過程中還是善于推舉一個最有才能的人和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來擔任村內的最高職務(3),帶領全體村民致富。這就是墨子所說的“賢人”。在賢人的統一領導下整個村莊的村民在一個相對團結的集體中共同生活,這可以說是墨家的尚同思想在現代村民自治之中的體現,也可以說是村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
四、節用、節葬和非樂——促進公德重塑
墨家的“節用”、“節葬”和“非樂”思想也是以其“兼愛”思想為基礎的,“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韗鞄、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古者圣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股鉗納之衣,輕又暖,夏服絺绤之衣,輕又清,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孟子·節用中》)這說明了節用就是人們的衣食住行只要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生產需要就可以了,一切以享受為目的消費都是奢侈和浪費,提倡大家反對鋪張浪費。節葬同理,反對過分夸張奢華的葬禮,主張葬禮從簡。非樂也是從節儉的角度來告誡統治者在解決人們溫飽問題之前,不應該把君主和貴族的淫樂放在首位,即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體現了在社會發展初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過程中的側重點的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4條規定:“國家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也說明了節用、節葬和非樂思想中所體現的節約思想不僅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和道德基礎,也是具有明確的憲法依據的。費孝通老先生在《江村經濟》中曾經提到過:“為滿足人們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種手段來獲得消費物資,但同時也規定并限制了人們的要求。它承認一定范圍內的要求是適當和必要的,超出這個范圍的要求是浪費和奢侈”[3]95,這準確地體現了墨家學派所稱的“節用”一詞的含義,“安于簡樸的生活是人們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費是要用懲罰來防止。孩子們飲食穿衣服挑肥揀瘦就會挨打或挨罵。在飯桌上孩子不應拒絕長輩夾到他碗里的食物。母親如果允許孩子任意挑食,人們就會批評她溺愛孩子。即使富裕的家長也不讓孩子穿好的、價格昂貴的衣服,因為這樣會使孩子嬌生慣養,造成麻煩。”[3]95這體現了中國農民家庭傳統的節儉觀念,中國農民將節儉教育從自家的孩子抓起,將節儉的理念融入到人一生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樹立和培養計劃之中。浪費,是村莊集體輿論所禁止和批判的,而節約不僅是一種美德,一種習慣,更是成為衡量一個人品性優良、一個家族榮辱興衰的重要標準。他指出“知足和節儉具有實際價值。一個收入全部用完毫無積蓄的人,如果遇到歉收年成就不得不去借債從而可能使他失去對自己土地的部分權利”[3]96,“在日常生活中炫耀富有并不會給人帶來好的名聲,相反卻可能招致歹徒的綁架,幾年前發生的王某案件便是一個例子”。[3]96這說明節儉在物質層面上也會給人們帶來實際的利益和價值,只有節儉,農民才會有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的能力,才會有生存主體感和安全感。可見墨家所提倡的節用也不是只著眼于品德養成的,也更具有其實用和功利主義的價值。勤儉節約的傳統習慣不斷向人們內心深處內化時,便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即所謂的農民的鄉土邏輯“中庸、平和、不出頭”[2]7。
但是,每逢婚姻喪禮場合,勤儉節約的觀念似乎就淡了。婚喪禮儀看起來僅僅是一種民俗活動,實則具有重要的精神價值意義,中國人通過這種婚喪之禮來獲得精神價值的體驗。費老說:“人們認為婚喪禮儀中的開支并不是個人的消費,而是履行社會義務。孝子必須為父母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墳墓。如前面已經提到,父母盡量為兒女的婚禮準備最好的彩禮與嫁妝,在可能的條件下,擺設最豐盛的宴席”[2]96。賀雪峰教授說:“一直以來,喪葬都是農村社會(也許是任何社會)中最為重大的儀式,是陰陽相交,是生離死別,是人生結算,是聯系親友的大事,甚至是人生的競賽。生養死葬,這個死葬實在太重要了。”[2]40自古至今,盡管墨家不斷地呼吁節葬,但是中華民族這個世界上最勤勞簡樸的古老民族卻實行鋪張浪費式的禮儀,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孝德情結,所謂儀式的本質就是婚葬儀式所包含的象征價值,與參與者投入儀式活動所獲得的主體感受有關。但是近幾年,隨著無神論思想的傳播和商品經濟思想的傳入,人們的思想觀念受到了現代化的洗禮,死,變得不再那么神秘;婚禮,也不再那么神圣。對于現代的喪葬禮儀,只不過是商品關系在人際關系領域的一種外化罷了,所有的儀式都成了活人之間的一種攀比和金錢競賽,所有的儀式都失去了其應有的魅力和神秘。當儀式活動失去了精神價值意義,徒具形式,變成農民進行社會性競爭的手段或喪失其嚴肅性而變成十分惡俗的活動時,都是儀式活動的一種異化,這種異化的儀式喪失了其本有的價值,成為純粹的鋪張浪費。這也是墨家所批判和反對的。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尤其是面對商品經濟和現代傳媒的沖擊,中國農民應該培養一種良好的消費觀念,辯證地看待儀式,注重儀式的精神價值,反對鋪張浪費和儀式的商品化,注重墨家提倡的“節葬”,來構建中國農民文明的儀式價值觀。
五、明鬼、天志和非命——呼喚信仰的回歸
“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閑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墨子·明鬼下》)。這一段話指出了墨家的明鬼和天志觀,墨家認為鬼神無處不在,鬼神控制和制約著人們的行為,人們的各種行為受到鬼神的監督,因此統治者應該順應民意,推行仁道,實際上這里的“鬼”只是墨家進行自我證成的一個工具,他希望通過鬼神對統治階級的制約和監督,來督促統治者大行天道,實施利民之政。中國古人一直都有一種樸素的鬼神觀,他們相信本體之外還存在一個超自我的神,這也是古代社會治理過程中規則之外的一種治理方式,這種鬼神之治比顯見的規則之治要有效得多。費孝通老先生在調查1980年代中國的農村時提到過:“節儉是受到鼓勵的。人們認為隨意扔掉未用盡的任何東西會觸犯老天爺,他的代表是灶神。甚至米飯變質發酸時,全家人還是盡量把飯吃完。”[3]96正是這種樸素的鬼神觀造就了中華民族自省、自制和自覺的民族意識,以及樸素的正義觀。有人說,中國是一個缺乏抽象信仰的民族,筆者并不是很同意這種觀點,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具有傳統的鬼神觀念,中國人對鬼神的各種祭拜儀式寄托的是中國人對生命的信仰和敬畏,就像西方人通過宗教來獲得精神上的救贖是一樣的。中國人那種樸素的鬼神信仰自五四以來被德先生和賽先生驅逐了,這種信仰被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簽。無神論的普及以及商品化大潮的沖擊使這種信仰逐漸銷聲匿跡,原本敬天畏地的中國農民經過現代化的洗禮,開始大言不慚“人定勝天”,最后是人戰勝了天,還是天報復了人,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農田因大量化學肥料的使用而板結,大量的毀林荒使得土地沙化,許多村莊變成了空殼村。同時,缺失了這種信仰,官不為官,民不像民,子不像子,父不類父。社會陷入一種潛在的危機之中,這種危機不僅僅是生態危機,更是社會倫理危機。面對人類從大自然中劫取的物質財富,面對著體無全膚的農莊和農田,農民會陷入深深的焦慮和精神空虛之中,又談何新農村建設?因此,呼喚農民群體信仰的回歸,重塑對天地的敬畏之情,這對于農民群體統一價值觀的形成和團體協調性的加強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
墨家的“非命”觀看似與其“明鬼”、“天志”觀念相互矛盾,其實他們是統一的,只不過非命觀是注重人本身的意念,明鬼和天志的觀念注重的是人外在的事物。墨子“非命”而尚“力”,更是一種對人的主體的自覺、克服命運安排的自覺,其基本精神是否定天命,追求真理,有著歷史的進步意義。從墨家“強力”的觀念出發,“非命”并不是否定天和鬼神,而是與其“天志”、“明鬼”觀念相結合,主觀上借“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在客觀上利用“鬼神”的宗教權威來曲折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轉型時期應當注重向農民宣傳不要屈從于命運、積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非命觀,這種觀念也有利于中國農民勤勞、艱苦奮斗性格的養成。
在現代化大潮洶涌澎湃,農村社會轉型的關節點上,農民的傳統價值觀念七零八落,現代觀念尚未形成,農民普遍陷入一種群體性焦慮和精神空虛之中,因此,應該從墨家兼愛、非攻的層次上來合理引導農民進行一種新的和諧觀念的重構,避免農民個體的過分原子化,注重群體活動的一致性,關注邊緣群體,推動賢人民主,重構敬天保民的傳統觀念,呼吁人性和信仰的回歸。
注釋:
(1)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在《新鄉土中國》中提到,地方性共識指的是由熟人社會的信息全對稱狀態而產生的公認一致的規矩。地方性共識包含價值與規范,是農民行為的釋義系統和規范系統,由其形塑的行為邏輯,稱之為鄉土邏輯。
(2)“農業-商業”二元交易體系,是指在農業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部分農民經商,而部分農民依舊務農,從而形成的農民收入來源呈現務農經商二元化的一種格局,是為充分利用大量的農村剩余閑散勞動力而出現的一種農民增收體系。
(3)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村都是實行村支書和村主任任職“一肩挑”制度,即村內支書和主任通常由一個人來擔任。
參考文獻:
[1]薛柏成.墨家思想的起源及歷史影響新探[D].吉林大學,2006.
[2]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世紀集團出版社,2007.
編輯:董蕾
哲學·文化
收稿日期:2014-10-20
DOI:10.3969/J.ISSN.2095-7238.2015.01.013
文章編號:2095-7238(2015)01-0078-05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D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