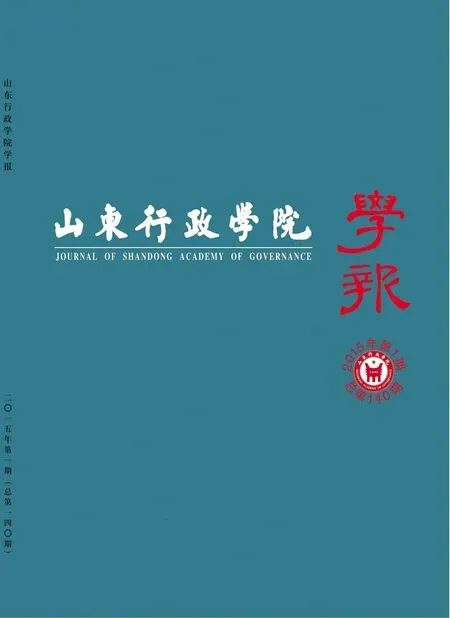基于人口流動趨勢的戶籍制度改革思考
俞云峰(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杭州311121)
?
基于人口流動趨勢的戶籍制度改革思考
俞云峰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杭州311121)
摘要:戶籍制度變遷的城市利益導向嚴重制約了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的進度。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跨省域遷移、舉家遷移與向大中城市集聚的趨向更加明顯,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要與人口的流動趨勢相適應,尊重各地實際資源承載能力,引導流動人口區域分布合理化,重點為長期在城市定居的外來人口落戶創造條件,同時加快配套制度等改革,調動各方推進戶籍改革的積極性。
關鍵詞:戶籍制度;人口流動;戶籍制度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形成我國第一波流動人口大潮,時至今日,不僅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各類人才在城市之間的流動也日趨頻繁。大量的流動人口具有明顯有別于戶籍人口的“半城市化”特征,在城市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特殊群體。截至2013年末,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接近53.7%,但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城鎮化水平不到36%,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80%以上的城鎮化率,也低于人均收入與我國接近的發展中國家60%的城鎮化率[1]。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間約17個百分點的差距對應著將近2.3億的龐大流動人口群體,因此,戶籍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升應重點關注和解決城市流動人口的戶籍遷移問題。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戶籍制度演變,其核心是服務于城市的發展與管理需要,以城市利益為其基本導向,并呈現出一貫的漸進式改革路徑依賴,缺乏系統的、全面的、徹底的改革[2]。戶籍改革至今沒有給予居民完全放開的戶籍遷移自由,由此從制度層面直接造成了龐大流動人口的事實。
戶籍制度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公民居住與流動的自由,實現公民身份的平等化[3]。人口的流動受到自身因素以及就業、收入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更受到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等基本性制度的制約。人口流動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下呈現出一定特征與規律,戶籍改革必然要遵循人口流動的客觀規律,探究近年來流動人口在城鄉之間的變化與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通過政策調整,合理引導人口流向,加快推進新一輪的戶籍制度改革。
一、我國人口流動的趨勢——人口普查數據的比較
對于本世紀以來人口流動的趨勢分析,本文借用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簡稱“六普”)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簡稱“五普”)進行比較。“六普”顯示,截止2010年末我國流動人口(即人戶分離,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不一致的人口)總數為26,093萬人,比“五普”時的14,439萬人增加了11,654萬人。十年增長近八成,遠大于總人口的增速。“五普”時流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11.6%,到“六普”時,這一比重增加至19.6%。相當于全國每5人中就有1人為“流動人口”。從地域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重慶、陜西、寧夏、青海等9省、直轄市流動人口增長超一倍。
(一)人口自西部省份向東部跨省流動趨勢明顯加強
2010年,全國跨省份流動人口8,587.63萬人,比2000年的4,241.85萬人增長102%;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跨省人口流入排名趨前的省份依然全部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其中廣東跨省流入人口最多,達2150萬,遙遙領先;超越千萬的還有浙江省,跨省流入1182萬人,其余依次是上海、江蘇、北京、福建、天津、山東;而跨省人口流出排名趨前的省份以中西部人口大省為主,依次是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廣西、貴州等。可見,人口流動維持了一貫由西向東的單向性(詳見表1)。

表1:2010年人口流動的主要省份排名
尤其是,和“五普”數據相比,這種由西向東單向流動的趨勢又有了明顯的強化。2010年,全國跨省流動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重平均為32.9%,即3個流動人口中,有2人是本省流動,1人是跨省流動。相比2000年平均29.38%的比重,10年增速僅12%,總體上變化并不明顯。但東部省份的跨省流入人口比例增速都大幅超過平均值,其中天津跨省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動人口比重十年間增長了79%,江蘇達45%、浙江38%,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分別為26%和22%,僅有廣東省增速為負(詳見表2)。這表明,東部沿海省份跨省流動人口的比重在持續快速的增長,而中西部省份則以本省流動人口的增長為主。
從具體省份看,跨省流入該省的人口占該省總流動人口比重超過平均數的省份有9個,依次是上海(70.8%)、北京(67.1%)、西藏(63.1%)、天津(60.4%)、浙江(59.4%)、廣東(58.4%)、新疆(41.9%)、江蘇(40.5%)、福建(39%)。其中上海、北京、西藏、天津、浙江五省這一比重超過50%,意味著該省份的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入人口已超過本省內部的流動人口數。這也反映了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化解流動人口戶籍的壓力有多大:上海近2300萬常住人口中,39%是跨省流入人口;北京1960萬常住人口中35%是跨省流入人口;天津23%、浙江21.7%、廣東20.6%的人口不具有居住省的城鄉戶籍。
(二)流動人口進一步向城市集中
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26,094萬,按“六普”統計的標準,流動人口的分布分城市、鎮、村三級登記,其中居住地在城市的有17,046萬人,鄉鎮5550萬人,村3497萬人,占全部流動人口比重分別為65.3%、21.3%、13.4%,大部分流動人口集中在城市。與2000年相比,城市流動人口比重增加了5.9%,鎮流動人口比重增加了2.1%,村流動人口比重下降了8%。這表明流動人口進一步向城市集中(圖1)。
對于一般小城鎮而言,2010年流動人口的比重總體上與2000年持平,十年間小城鎮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并沒有增強。結合具體省份來看,鎮流動人口總量居前的省份第一位是浙江,超過500萬人,這與省管縣體制下浙江小城鎮經濟增長速度遠超中型城市有關。其次是廣東、四川、江蘇、河南、山東、福建。這些省份普遍是人口數量大或是鄉鎮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從十年變化看,不

表2:2000-2010年跨省流動人口變動情況

圖1:流動人口分布情況對比
同省份間變化差別較大,小城鎮流動人口占流動人口比重同比減少的省份有四個:廣東(-13%)、天津(-9%)、江蘇(-0.7%)、浙江(-0.5%);而同比增長最快的省份有:江西(19%)、河南(15%)、青海(14%)、河北(13%)、湖南(12%)、山西(11%)、甘肅(11%)、陜西(10%)等。這表明,隨著國家振興中部戰略的實施和產業的梯度轉移,中部地區的小城鎮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吸引本地和外地勞動力的集聚作用明顯增強,而東部沿海省份流動人口向城市集中度增加,也說明全球金融危機后,這些省份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轉變后帶來的勞動力人口結構與空間布局的變化。
(三)在居住地長期定居的流動人口規模龐大
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2.6億,在居住地居住滿三年以上的人口達1.13億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43.46%,在居住地居住滿五年的人口達7267萬,占全部流動人口的28%。這表明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已經在城市長期工作生活并在固定城市定居。由于人口普查是按街道、鄉鎮為單位進行統計,“現居住地滿三年”指標僅能代表普查時在該街道(鎮)生活滿三年,并不代表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村人口進入城鎮生活的真實年份,由于外來務工者在城鎮間的流動性較大,其離鄉進城的平均年份要比普查顯示的年份多得多。這些長年居住在城市又無法在城市解決戶籍問題的流動人口成為城鄉之間的夾心階層,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是戶籍改革需要首先考慮的人群。
(四)“務工經商”引起人口遷移的比重有了明顯增長
根據2010年“六普”數據,在列出的八項最主要原因中,首要原因是“務工經商”,占45.1%;其次是“隨遷家屬”,占14.2%;隨后依次是“學習培訓”、“拆遷搬家”、“婚姻嫁娶”、“投親靠友”、“工作調動”與“寄掛戶口”。對比“五普”的數據,八項主要原因中最主要的兩項“務工經商”與“隨遷家屬”比重有了增長,其余六項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外出“務工經商”的比重增長最快,從2000年的30%增長到45%,十年增長15個百分點;“家屬隨遷”從12.8%增長到14.2%。
外出務工或經商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從鄉村到城鎮、從城市到城市遷移的最主要原因。本世紀近十年務工經商人口遷移的快速增長,進一步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完善,各類人才在城市之間、省份之間自由流動更趨頻繁,務工經商作為人口流動趨向的特征尤為明顯。“家屬隨遷”比重的提升也說明外出人員的家庭化流動是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發展趨勢。此外,近十年戶籍制度的逐步放松也使得“投親靠友”、“寄掛戶口”等遷移行為縮減明顯。

圖2:人口遷移原因“六普”與“五普”比較
二、由人口的流動趨勢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難點
以務工經商為代表的大量人口跨省流動、向城市流動、舉家遷移等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人口流動的主要特征。該特征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所在。
(一)人口過度集中致使大中城市戶籍改革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口流動呈現出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省份流動、由農村、小城鎮向大中城市流動的跨區域特征。而這種不斷加強的流動趨勢并非僅僅是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問題,也包括城鎮與城鎮之間的人口流向問題。從“六普”數據看,居住地與戶籍登記地在同一省份的流動人口中,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占46%,跨省流動的人口中,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也占到18.4%,特別是本省流動人口中城鎮戶籍比例近半,說明人口流動的重點除了由農村向城鎮的流向外,也包括從小城鎮向大中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無關戶籍性質的人口流向。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入壓力較大的區域,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及東部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面對的不僅是外來農村務工者,還有大量外來城鎮籍的工作人員的雙重落戶壓力。
就業機會、收入水平、教育質量、社會福利等諸多因素決定了大中城市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大中城市不僅吸引了農村外出的務工者,也集聚了大量的技術人員、經商人員、文藝工作者等等。大量人戶分離人口的存在一方面證明了中國戶籍遷移制度的苛刻,另一方面也凸顯大中城市戶籍改革之難。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單向流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尷尬處境同樣會出現在戶籍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在放寬大城市戶籍條件的改革中,“有序”似乎比“加快”更為重要。
相比于大中城市,小城鎮的戶籍吸引力則更具多樣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城鎮數量從1978年的2173座增加到20,113座[4]。其中大量的小城鎮缺乏明確的產業支撐,既不宜業亦不宜居。從結構上看,東部發達地區的小城鎮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中部省份的部分經濟強鎮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自身的集聚能力有所提升,此外的大多數小城鎮顯然難以擔當化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任。
(二)地方政府利益格局致使異地落戶改革難
流動人口在為流入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需要當地政府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測算,吸納一名戶籍人口需要地方財政負擔的費用約8萬元[4],巨額的開支讓地方政府望而卻步。戶籍異地遷移改革阻力大,其最主要的制度背景是現行的財政分權制度。戶籍人口享有的教育、醫療衛生、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開支均由地方財政開支,異地遷入人口增加的社會成本也完全要由當地的地方財力埋單。財政分權制度決定了地方政府必然要考慮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利益與其財政支出成本之間的對等問題,出于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只想要外來“勞力”而不想要“人口”。城市戶籍政策中的種種“嫌貧愛富”、“條件苛刻”,皆由當前的地方政府的社會角色所決定。
同樣出于地方自身利益的考量,相比較于異地遷入的外來人群,地方政府更愿意將有限的城鎮人口承載力為本地農民預留,但本地農民積極性并不高。無論是浙江嘉興的“兩分兩換”,還是江蘇“三集中、三置換”,效果都很一般。有的地方在學習效仿過程中演變為“趕農民上樓”、“拉農民進城”,甚至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總體上,要吸引本地農民脫離土地融入城市還存在制度層面的障礙。
(三)長期定居在城市的人群落戶難問題亟需解決
我國放寬人口流動限制已有三十余年,形成了大批在城鎮工作生活的流動人口,大量的流動人口為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時至今日,甚至他們的下一代生于城市、長于城市,也已成為城市的建設者。戶籍政策長期把這些流動人口置于城市邊緣,使其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被貼上外地人的標簽,造成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各種權益不平等,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也影響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因此,戶籍制度改革首先要重點解決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群,他們是戶籍改革中落戶需求最為迫切的、也是事實上的城市化人群,通過放寬戶籍,給予他們享有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勞動就業、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讓這些流動人口真正融入城市。
三、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分類推進戶籍改革,引導人口合理流動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指導思想,加快推進分類戶籍制度改革。改革需要考慮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資源與環境承載能力,創新人口管理方式,因地制宜、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要起到合理引導人口流向的作用,人口的流向是每個個體自身的理性選擇,無論大城市、中等城市還是小城鎮都應盡早出臺明確而清晰的戶籍政策與發展規劃,讓流動人口可以獲得明確的預期,根據自身的需求早做安排。不同城市的發展現狀與發展潛力各不相同,產業支撐能力、公共設施條件、生活環境質量、擁擠程度等各方面都會影響到人口的集聚,與之相適應的明確的分類戶籍制度改革導向,將能起到激勵和引導人口流向的作用。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戶籍限制逐步升級,從全面放開小城鎮落戶限制到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梯度性政策,有利于促進流動人口向宜業又宜居的中小城市或新興城市轉移,使各地區的城鎮分布、人口分布更趨合理。同時,要有重點地發展中小城市和中心強鎮,增強小城鎮產業承接能力,以就業帶動安居,逐步實現人口的均衡分布。
(二)創新大中城市戶籍管理,突出居住年限的重要性
對大城市而言,創新戶籍放寬的模式,科學地把控人口增長數量,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放寬落戶的政策,通常根據外來人口的社會貢獻等指標進行有順序的準入,如投資落戶、購房落戶、人才引進落戶等。這類戶籍政策利用有限的戶籍指標作為吸引投資、引進人才的附加福利,反映了戶籍改革中的“嫌貧愛富”,把普通外來勞動者拒之于戶籍大門外。因此,大中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應設立有序地吸納普通勞動者的制度安排,把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限或連續繳納社會保障金的年限作為一項重要條件,優先解決長期在城市就業、生活的外來人口的戶籍,使之逐步融入城市。
值得總結和進一步完善推廣的是廣州市試行的積分落戶政策。積分落戶模式的優點一是便于落實人口增長的規劃,明確地設定城市每年新增人口的數量指標,按照確定的數量指標公開、透明、有序地接納外來人口的戶籍遷入;二是有利于將各類落戶條件的指標量化,并使把居住年限作為重要指標的要求變得更具有操作性,通過調整居住年限指標的權重,使長期居住的普通勞動者更容易符合落戶要求;三是方便實行城市人口總量控制,使城市化速度處于可控區域,也便于中央從全國整體層面上對各大城市的人口城市化速度進行指標調控與監督。
(三)改革相應配套制度,提升地方政府戶籍改革積極性
地方政府是戶籍制度改革的主體,是具體戶籍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要充分激發地方政府的改革動力。
一是要創新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探索農民退出土地的機制,調動農民和地方政府的雙重積極性。現有的農村耕地承包制度與宅基地分配制度,造成大量長期進城定居的農村人口仍然保留農村戶籍,形成對城市與農村土地的雙重占用,一方面使農村土地閑置與浪費,另一方面又使城市建設用地和工業用地短缺。改革現有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對農業轉移人口在農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體土地等各類資產全面頒證賦權,做到所有權清晰、使用權完整[5],并與戶籍脫鉤;要允許宅基地在一定范圍的交易、過戶,抵押貸款,使農民能兌現退出宅基地的收益,獲得進城落戶的補充資金;同時,推進農村土地綜合利用,在調動農民進城積極性的同時也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二是建立跨地區的城市建設用地交易機制,由宅基地整理和復耕而增加的建設用地指標可以在全國地區間重新配置,有利于實現全國范圍耕地的占補平衡和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6];建設用地指標的區域間交易要與戶籍改革聯動,按城市的戶籍人口給予相應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權,把城市戶籍人口密度作為城市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審批的重要標準[7]。這一創新方式一方面可以改變地方政府推進土地城市化積極性高于人口城市化的現狀,有利于提升城市化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進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合理使用。
三是削弱城市發展中的行政級別限制,調動中小城市的發展積極性。城鎮的行政級別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審批權限、城鎮規模與建設用地指標等因素限制了部分勢頭良好的小城鎮的發展。東部地區一些縣級城市初具中等城市規模,一些中心鎮也具有發展成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潛力,要加快培育這些小城市的發展,從行政體制上打破現有行政級別的制約,賦予城鎮更多的自主權,強鎮可以擁有部分縣一級的職能與職權,強縣可以擁有部分省、市一級的行政審批權,充分調動地方政府推進城市化的積極性。通過強鎮擴權、強縣擴權,為小城鎮的進一步發展拓展空間。
參考文獻:
[1]新華社.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1-2020[N].人民日報,2014-03-17(009).
[2]趙文遠.新中國戶籍遷移制度史研究[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2:112.
[3]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等.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總體態勢與戰略取向[J].改革,2011(05):5-29.
[5]魏后凱.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措施[J].中國發展觀察,2013(03):15-17.
[6]陸銘.建設用地指標可交易:城鄉和區域統籌發展的突破口[J].國際經濟評論,2010(02):147.
[7]楚德江.就業地落戶: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現實選擇[J].中國行政管理,2013(03):40-43.
編輯:李磊
作者簡介:俞云峰(1975-),浙江海寧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區域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2BJY047);浙江省社科規劃重點研究基地課題(12JDKF01YB);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LQ13G030017)。
收稿日期:2014-10-26
DOI:10.3969/J. ISSN.2095-7238.2015.01.001
文章編號:2095-7238(2015)01-0001-06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D6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