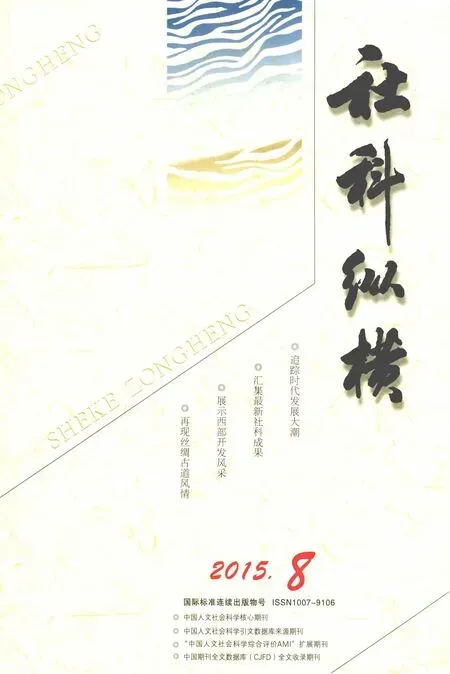移動互聯技術影響社會生活方式的新趨勢及應對
張麗紅
(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所 天津 300191)
中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已經有20多個年頭了。從最初的培養用戶、培育市場,到1997年以后上網人數的快速增長,再到如今網絡應用的高度普及,互聯網對大眾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也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推進。近幾年,移動互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化、移動化更是全面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大眾的社交方式、傳播方式、文化方式和消費方式等出現了一些新趨勢。把握住這些新趨勢,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使移動互聯技術更好地服務大眾是當務之急要做的。
一、移動互聯技術影響社會生活方式新趨勢
1.網絡社交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新型交往方式,但客觀上也加劇了現實的人際疏離
現代社會,隨著社會競爭的日趨激烈、人員流動的愈加頻繁以及人際信任狀況的不斷惡化,無論城市還是鄉村,人際交往變得越來越匱乏,身邊能宣泄的朋友越來越少。這樣的社會背景,給了網絡社交“橫空出世”的機會,網絡的超時空性、虛擬性、匿名性和網絡中地位的平等性,正好迎合了人們對人際交往的需要。它不僅能克服時間、距離的阻隔,還能將現實社會生活中的身份、年齡、性別、職業等影響人際交往的因素統統隱匿掉,ID代號成為每個人的標識。人們可以依興趣、愛好組成不同的群落,合則聚,不合立馬走人。人們通過互聯網交朋友似乎變得輕松容易,一些在現實社會中不善于人際交往的人,在網絡中也可能成為“交際達人”。因此,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社交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新型交往方式,它在拓展人際交際領域和擴大交際范圍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網絡社交并非完美,網絡社交迎合了人們交往快速、簡單和公平的需求,但客觀上也加劇了現實的人際疏離。在一項關于網絡新媒體對青年工作和生活狀態的影響調查中,當問及“自從接觸新媒體后,您認為自己社交活動、戶外活動的變化”時,認為沒什么變化的受訪者達到54.1%,同時,回答活動時間和活動頻率大大縮短的人占到了36.2%,還有9.7%選擇了能不參加的社交活動和戶外活動就不參加。統計結果表明,雖然有一半的被調查青年人感覺,他們的社交活動和戶外活動沒有受到影響,但是,依然有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感受到了網絡新媒體對他們現實交往的沖擊,更有近10%的人已因此變成了不適應現實生活交流的宅男宅女。在訪談中有人談到,我膩味了就會上網和網友聊天,聊得特別熱鬧,可是真的到了見了面,發現根本就沒有什么好聊的,特別的尷尬。[1]這種“微信近,隔壁遠”[2]的現象恐怕在許多年輕人身上都存在。更糟糕的是,以手機為載體的移動互聯網對父母子女之間親情溝通交流的沖擊。許多人沉溺于網絡,忽略了與親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羊年春節的“搶紅包”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質疑,也多是對這方面的深層憂慮。一些人為搶紅包甚至沒有和親人說上幾句稱心的話語,沒有來得及和爸媽嘮嘮知心嗑。因此,有人驚呼,搶紅包這個春節的“伴奏曲”蓋過了親情的“主題歌”,搶紅包正在毀掉春節。[3]
2.網狀發散結構的信息傳播方式實現了信息傳播形態的革命,但人們也不得不面對信息選擇的困擾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互聯網之父伯納斯先生在電腦屏幕上敲下這樣的文字:THIS IS FOR EVERYONE,即:這是每個人的。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網絡傳播降低了信息傳播準入的門檻,每一個普通大眾都可以以個體身份參與信息傳播,構成網絡節點。每一個網絡節點既可以是信息的發布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每一個用戶既是節點的實體,用戶以自己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激活每一個節點;同時又是節點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與其他節點的互動產生新的信息。[4]而手機等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更為網絡傳播“錦上添花”,人們可以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傳遞和接收信息。網絡環境下傳播節點數量巨大、紛繁復雜和動態多變的特點,造就了網絡傳播的網狀發散結構,這是對傳統媒體信息流動線性結構的巨大突破,實現了信息傳播形態的革命。
網狀發散結構的信息傳播方式離不開技術和人,技術實現了網絡自身的復雜建構,而人是技術的操控者。然而對于網絡這樣復雜的建構和建構中所包含的形形色色的內容,許多人都在反思:人是否還有能力或在多大程度上能進行自我操控。當前,電腦、互聯網、手機,數字化處理器等高速、高清、高容量信息傳輸工具的涌現,標明了現代社會的高信息化程度。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信息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過剩甚至泛濫的信息,將會使人們更加無所適從,不得不面對信息選擇的困擾。“有時選擇不但不能使人擺脫束縛,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貴,以至于走向反面,成為無法選擇的選擇。一句話,有朝一日,選擇將是超選擇的選擇,自由將成為太自由的不自由。”[5]
3.媒介新技術給文化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推動力量,但也催生了“速度文化”
人類的每一次科技進步,都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推動力量。媒介新技術憑借瞬息到達、即時互動的傳播能力,打破了國家和地域的時空界限,為文化的全球性傳播創造了條件,不同的文化傳播、不同的風俗習慣以及不同的價值觀念在網絡中交織、互容和碰撞,不僅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人們對于既有社會的習俗、傳統、社會關系和生活方式等的認知和評價。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媒介新技術所具有的文化影響是顯著的,它不僅沖擊文化中那些相對穩定、持久的意義結構,帶來特定價值、觀念及信仰的暫時性斷裂,而且還引發了既有社會網絡的分化和解體,促成新型意義結構的生成和鞏固。[6]
然而媒介新技術對文化的發展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推動文化整合發展的同時,也可能催生“速度文化”。數字化特征以及對模擬資源的處理,導致新媒介內容的碎片化,由此產生了媒介文化的拼貼化趨勢,即通過無規則地組合各種圖像、信息和符號,以為人們提供最淺表、感官化的體驗為要義。“抓眼球”是所有媒介傳播的首要任務,為了吸引高度分化和善變的目標人群,媒介不得不反復借用那些最能激發人們的好奇心、引發人們的興趣和吸引人們眼球的拼接方式,這又造成了媒介文化的同質化。媒介文化拼貼化與同質化的結果就是媒介內容的淺表化表現形式——“速度文化”或者說“快餐文化”。“速度文化”或“快餐文化”,帶來的表面現象是:信息數量高速增長,傳播活動日趨頻繁,文化主體更加活躍,文化內容更加豐富,文化取向更加多元。但實際上,對于社會文化整體來說,知識的增長速度并沒有明顯的加快,信息的社會影響力沒有增加反而有減弱的傾向。
4.網購作為一種新興的消費模式方興未艾,但網絡消費監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強調:全面推進“三網”融合,加快建設光纖網絡,大幅提升寬帶網絡速率,發展物流快遞,把以互聯網為載體、線上線下互動的新興消費搞得紅紅火火。實際上,這一政策正是為了迎合我國目前網購飛速發展的需要而提出的。2014年5月,國家郵政局發展與研究中心與德勤最新發布的聯合報告《中國快遞行業發展報告2014》指出,2008年我國網購人數為0.7億人,到2013年迅速增加到3.0億人,線上零售額在整個零售業中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1.3%提升至2013年的7.4%,網購滲透率也由24.9%提升至47.4%。網絡人數和網購頻次的不斷提升,使得中國網絡零售額迅速趕超美國,2013年達到1.84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世界第一網絡零售大國。據預測,未來五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仍將維持在30%以上。[7]因此,不容置疑的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便利、效率、節省的網絡消費作為一種新興的消費模式方興未艾,正在確確實實地改變著我們的消費方式。
誠然,網絡購物存在著諸多優勢,它可以滿足一些人低價買進高檔消費品的省錢愿望,可以給那些因工作繁忙而無暇去商店購物的人享受足不出戶購物的便捷,可以通過輕點鼠標讓來自全國各地的各類商品瞬間呈現在面前。但是,網絡購物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購物方式,由于我們還缺乏有效監管機制和措施,因此在網購輕松、便捷的背后,還存有諸多的不規范,如:宣傳與實物差距大、商品質量良莠不齊、物流配送問題頻出、貨款支付存在風險、售后服務爭議突出、欺詐行為屢禁不止、信息安全亟須加強等,急需出臺相關法律和法規予以規范,網絡消費監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應對措施
面對移動互聯技術影響社會生活方式的這些新趨勢,過分迎合和一味逃避都是不可取的。要在把握上述新趨勢的基礎上,從以下幾方面來著手:
1.加強網絡文化宣傳和引導
網絡上一切與觀念意識相關的文化活動,都會直接投射到社會文化和民眾的心靈深處,影響和重塑現實社會的價值觀。[8]在移動互聯時代,網絡空間已成為各種文化和各種社會思潮交流、交鋒、交融的平臺。要充分利用網絡傳播優勢,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使之成為弘揚先進文化、主流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平臺,成為傳播新知識、新思想的重要渠道。當前,要想占領網上思想輿論陣地,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就必須深入研究網絡輿論傳播的特點和規律,必須從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中汲取文化精華。唯有如此,才能唱響網絡文化的主旋律,避免網絡文化的“浮躁”和“短視”。
2.加強網絡倫理道德的教育
要教育和引導廣大網民,在網絡環境中自我約束、道德自律,而且這不是某一個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每一個網絡用戶的責任,不僅包括普通網民,也包括大V等意見領袖。信息網絡人際交往的匿名性和“去身份化”,對人們的心理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從某種程度上降低甚至剝奪了我們對現實生活的責任感,貶低了我們作為人的身份。責任感的缺乏,必然對我們的人際交往產生消極影響,引發現實的人際交往障礙。通過加強網絡倫理道德的教育與自我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網絡交往的健康發展。另外,加強在網下各類正式和非正式社會組織中人們之間的情感交流,努力使組織成員之間的關系由“同質、機械結合”向“異質、有機結合”方向轉變,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或降低網絡給人際交流帶來的“孤獨感”、“機械感”和“ 異化感”。[9]
3.凈化網絡空間
要通過技術、行政、法律等多種途徑,凈化網絡空間,有效遏制信息垃圾的生產和傳播。通過相關技術,層層設置關卡,對有害信息進行有效過濾,阻止其入網。管理部門應進一步完善相關的規章制度,進一步規范化網絡運作,敦促網站加強行業自律,堅持依法辦網、文明辦網,積極承擔應負的社會責任,對縱容網絡水軍、為網絡水軍活動提供方便的網站,進行嚴肅的處理,讓不良網絡信息失去生存的土壤。同時,要加快推進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化的法制化,立法執法,對信息犯罪進行嚴厲打擊。
4.加大網絡監管力度
要制定相關及配套的移動電子商務監管法規,對網絡交易市場的信息發布、準入資格、買賣細節、電子支付、各方責任等方面都進行明確的界定和規范。強化社會懲戒機制,凡是違法違規經營的電子商務者一經投訴、舉報并經監管、執法部門確認事實后,要在其主管部門的網站上公布,以便網民上網查詢或驗證,令其無可遁形。另外,還要對消費者加強教育,普及法律知識,增強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
[1]張麗紅.網絡新媒體對青年人工作、生活狀態的主要影響及建議[J].前沿,2014(5).
[2]余平.微信近,隔壁遠[N].中國青年報,2015-03-23(02版).
[3]評論:莫讓搶紅包毀掉春節[OE/0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2/id/1558087.shtml,2015-02-26.
[4]喻國明等著.微博:一種新傳播形態的考察——影響力模型和社會性應用[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3.
[5][美]阿爾溫·托夫勒著,任小明譯.未來的震蕩[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13.
[6]石義彬,熊慧.從幾個不同向度看媒介新技術的文化影響[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
[7]中國去年網購額1.84萬億元,超美國成世界第一[OE/0L].http://money.163.com/14/0527/10/9T8BG167002526O3.html,2014-05-27.
[8]黃桂清.論網絡在社會文化重塑中的作用[J].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2011(6).
[9]宋巨盛.互聯網對現代人際交往影響的社會學分析[J].江淮論壇,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