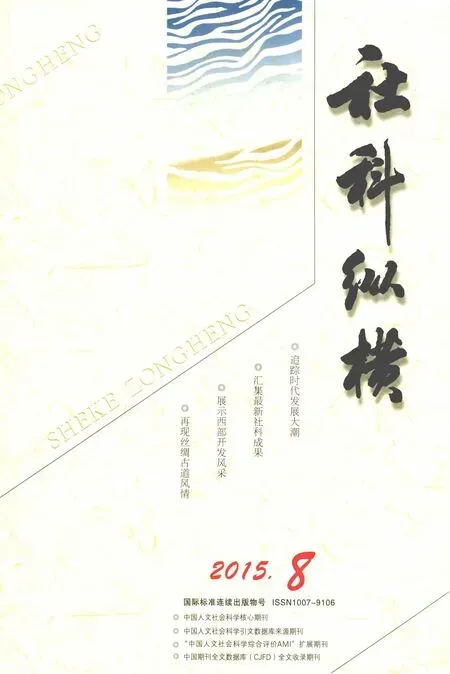晚清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
黃建剛
(蘭州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60)
用英國傳教士蘇慧廉的話: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就像三條腿的板凳,即教會、教育和醫療。[1](P180)實際上,在傳教過程中對中國教育、醫療事業做出的貢獻,遠遠超出傳教士的預料。
一、將西方醫學引入中國,給中國的醫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872年—1834年)到中國開始傳教。在廣州傳教期間,他和英國醫生列文斯頓目睹了中國人的衛生習慣堪憂,便開了一家診所給中國人治病。1820年,馬禮遜在澳門開設了一家中式診所,聘請中西醫師,以免費醫療服務的方式作為傳教的媒介。1827年增設一家眼科醫院。六年后,又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眼科醫生聘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醫師。
1873年,蘇格蘭傳教士麥金太爾牧師在山東行醫治病。為防治天花,他引進了牛痘接種技術,當時山東熱病、霍亂等流行病嚴重,李提摩太等傳教士免費向民眾發放奎寧藥、樟腦油,治療瘟疫等疾病。
當時中國的醫生們還沒有形成集體的力量醫治疾病和瘟疫,滿清政府在大規模的瘟疫面前尚且無能為力,國人對西方傳教士還充滿疑慮與不信任。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全然不顧個人安危,自籌資金用于中國的賑災。甚至傳教士們還將在其祖國募集到的資金、藥品運到中國,以賑災和治療民眾疾病。為幫助中國民眾擺脫瘟疫的折磨,有近百名傳教士因為感染瘟疫而獻出了生命。[2](P91)
在浙江溫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蘇慧廉,曾在英國接受過簡單的醫學訓練。他將隨身攜帶的奎寧、阿司匹林等藥物,為來聽道的中國民眾治療瘧疾、感冒等疾病。[3](P75)甚至他還利用自己淺顯的醫療知識幫助染上毒癮的中國人戒掉毒癮。1886年,在嘉會里巷的教堂里開辦戒煙所。前后兩年的戒煙所里,先后為三四百位中國癮君子戒掉毒癮。[3](P79)
蘇慧廉在溫州開張的城西診所,1892年就接待病人5624人,“日就診的病人在80—100人左右,病人大都是窮人、中途歇腳者、殘疾人、盲人”[4](P100)。到了1895年,城西診所已人滿為患。1897年,蘇慧廉用英國人約翰·定理和其他英國人的捐款建立了定理醫院。
美國內地會醫療傳教士稻惟德,1874年在紹興傳教,1880年在溫州開辦醫院及戒毒所。1882年轉到煙臺開辦芝罘醫院。甲午戰爭期間,倡議創辦紅十字會醫院,并因救治從威海衛來的傷兵有功,獲清廷“雙龍勛章”。1899年,稻惟德在診治病人時感染赤痢去世。
截至1900年,基督教醫藥傳教會在中國開設的醫院和診所有40多所。大部分為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小型診所,分布在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上海、江西、湖北、四川、北京、直隸。其中美國傳教士Peter Parker在廣州開設的眼科醫院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第一家西醫醫院。1858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John Glasgow Kerr開設的廣州博濟醫院最為著名。[3]
各教派傳教士在中國興辦的醫院,將西方的醫療技術、醫院制度、醫學教育引入中國。一改中醫分散的個體經營特點。更促使中國醫療教育及醫療服務體系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
二、投身賑災,盡力拯救災民
傳教同時,傳教士還在中國從事慈善事業。1876年-1877年中國北方大面積干旱,魯、晉兩省尤為嚴重。山東巡撫也無力解決饑民的糧荒。李提摩太拿出自己的積蓄給災民發放救濟金。并組織傳教士捐款賑災。
在荷蘭公使、英國駐煙臺領事、海關的幫助下,李提摩太將山東的災荒寫信發表在上海《申報》。隨后將收到的中國當地官員、士紳及外國人救濟金及時發放給災民。
1877年,李提摩太又到山西開展救災工作。災荒導致遍地都是餓死的饑民,此時陜西、河南官員還禁止向山西出售糧食,而山西當地官員還對傳教士的賑災救濟行為深表疑慮和戒心。李提摩太等傳教士毅然投入到賑濟災民的活動。李提摩太還向當時的山西巡撫提出救災的三項措施。[2](P117)
三、傳教士還在中國大力推行慈善事業
棄嬰現象也許是中國社會歷史悠久的骯臟現象。雖然充滿仁愛禮儀的國度里,從來沒有關于這方面的史料記載。但是在馬戛爾尼的日記里,卻披露了中國普遍存在的殘害嬰兒現象:在北京城里,每天步軍統領衙門都特備一車,在大街小巷里將已死的和遺棄嬰兒“納入車中拉入義冢埋之”。而西方傳教士則每天都等候在車旁:“遍察各嬰兒之尸,見其中尚有氣息者必抱歸灌救,救活則就教堂中撫養之,長而施以洗禮”。[4](P76)棄嬰現象在京城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同時,還有報道,解放前僅在上海,每年至少在街頭或垃圾箱里就可以找到一萬八千具童尸。遇到災荒年份里,食嬰現象更是普遍、嚴重。[5]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救濟常常限于鰥寡孤獨和殘疾貧困的民眾,而對女嬰、殘疾的兒童和因無錢治療患病的孩子更多的是遺棄。即使救濟,也大多是收養、提供食宿和施棺抬埋。
而傳教士在中國興辦的慈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許多嬰兒的生命。傳教士們不僅向中國傳輸醫療慈善精神,而且還在中國大力興辦慈善事業如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和聾啞學校。其中法國天主教集中在上海、天津、南昌;英國基督教在太原、長沙、四川、河南、湖北;美國傳教士在廣州、上海、寧波、煙臺。慈善機構不僅傳授宗教知識和必要的識字教育,還讓孩子們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如編織、刺繡、縫紉等。
李提摩太在青州府傳教賑災時,還用從外國人團體中募集的救濟金興辦了五個孤兒院,對遭受災難的孤兒進行基本的救助。他訂購了許多外國的機器,教、授孤兒基本的工商業技能。[2](P91)
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國興辦的慈善事業,是傳教過程中弘揚基督教的仁愛精神。這種慈善事業不僅僅是收養了一批中國的弱勢群體,還在于對這些弱勢群體進行相應的教育、傳授謀生的技藝,進而能夠自食其力。傳教士秉持“仁愛”精神的慈善事業不僅樹立了教會善人的形象,還改變了中國傳統“重養輕教”的慈善救濟理念,也轉變為“教養并重”。也促使更多的中國人從事新型的、西式的慈善事業。
四、傳播西方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
1870年,英國基督教浸禮派傳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在山東傳教時認識到:“驅逐中國人風水迷信的最好途徑就是向人們傳授自然科學知識,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2](P105)山西的災荒結束后,他不斷向中國的官員和學者介紹西方的科學成就、普及自然科學知識。推動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以避免饑荒再度發生。去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2](P139)。為了向中國民眾傳授西方科學知識,他縮減了所有個人性消費。自費購買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學、電學、化學、地理學、自然史、工程學、醫藥學及各類產業學書籍;各民族的歷史;亞洲文學;還有《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他還在歐洲購買了教學和科研儀器:望遠鏡、顯微鏡、分光鏡、手動發電機、各種化學電池、化學電流表、蓋斯勒管、電壓表、電流表、袖珍六分儀、小型無液晴雨表以及氧化氫、酒精、乙炔為燃料的幻燈機,附帶一套最新的天文學幻燈片,關于澳大利亞、非洲、美洲自然歷史的幻燈片,甚至還有關于茶、可可、橡膠和甘蔗的植物學知識的片子。通過上述書籍和儀器向中國官員和學者介紹了近代西方在化學、機械、蒸汽、電學、光學醫學和外科醫學上的技術成就以及歐洲在電報通信領域的巨大成就。[2](P140、P141-144)
早在1792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訪問大清時,就已向中國皇帝及官員展示了西方的槍炮。但是滿清官員對此偏執、麻木,竟然還高談“騎兵與大刀、長矛的優勢”。當時馬戛爾尼就預言:一旦洋兵長驅而來,中國必敗。1840年的鴉片戰爭,證明馬戛爾尼的預言是正確的。[4](P206)
在虎門銷煙前后,林則徐已經認識到一旦開戰,中國必敗。之后的有識之士開始悄悄地學習并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1863年,受曾國藩委派,容閎為籌建江南機器制造局赴美采購機器,所購100多種機器,成為第一個洋務企業——江南制造總局的主要設備。這個就讀于中國第一所教會學校——馬禮遜學校,也是第一個到美國耶魯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近代走向世界的先驅者”。容閎還參與了中國近代兵器工業的建設,如江南制造局、漢陽兵工廠。這些兵器工業也是后來中國能夠在抗日戰爭中堅持到最后勝利的物質保證。
隨后容閎積極建議“選派優秀青年出洋留學”,到美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與文化。
洋務運動是中國官吏中的有識之士企圖單純引進西方“堅船利炮”以抵御西方侵略的嘗試。但是我們應當清楚:在洋務運動中,西方傳教士也通過各種方式幫助中國軍事進步。例如: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年─1887年)受雇于江南制造局時期,為兵工廠翻譯大量的西方軍事資料。[6]
西方的思想啟蒙運動奠定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石。西方傳教士們也適時地向清政府官員及中國民眾宣傳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例如飽受爭議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時,就毫不保留地主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罷黜慈禧太后。但是傳教士的重點還是在傳教過程中向中國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成就。
五、帶來西方教育制度,催生中國的教育革命
1807年來到中國傳教的英國人基督教徒馬禮遜也是近代第一個在中國境內向中國人傳教的西方傳教士。他還是第一個在中國辦學校的傳教士。他采取了多種模式在中國傳教:文字、醫學、教育。但是他對宗教的熱情遠遠勝過政治熱情。1820年在馬六甲成立英華書院。[7]
1838年,耶魯大學選派畢業生塞繆爾·布朗(REV.Samuel R.Brown)作為第一個來中國的美國基督教教育傳教士,任馬禮遜學校的校長,兼任教師。最初的教育條件是非常艱苦的:沒有固定的教學計劃,學生人數少,“學校教育學生學習英文、中文,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和基督教教義,學制六年”。“學英文使他們學到許多有用的東西,如天文、代數、幾何等。學習中文,則整天《五經》、《四書》,讓人死啃書本,學生能夠讀書為的是將來升官發財,讀孔孟之書使人總是看著過去,學英文則讓人想未來,看當代社會,去發現世界”[8]。“剛開始辦學時,第一批學生是6名兒童。多數為無家可歸的兒童”馬禮遜學校的費用均由個人捐款支助。[9]馬禮遜學校學生最多時達42名,年齡最大的有16歲,最小的6歲。
1900年,山西巡撫毓賢在山西大肆迫害基督教傳教士超過千人。甚至對不足周歲的嬰兒也大肆屠殺。李提摩太反對以怨抱怨。他認為教案的發生是因為中國民眾的愚昧。他主張興辦學校,“以克服人們的無知和迷信。這種無知和迷信是導致對外國人屠殺的主要原因”。李提摩太用教案賠償款,籌建山西大學堂。這也就是后來的山西大學。
同樣蘇慧廉也在中國溫州開辦學校,后來應李提摩太邀請,前往山西大學任教務長。
從1818年第一所中文學校馬禮遜學校開始,到1912年,基督教興辦的學校達到3708所,在校小學生86241人,中學和大學533所,學生達31384人。[10]
馬禮遜學校是基督教在中國開辦第一所小學,從這里走到美國的容閎,是引進西方工業的先驅者。他帶到美國的第一批大清留美幼童中有:中國第一個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機器采礦業創始人吳仰曾;天津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南陽海軍寰泰艦艦長容尚謙……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還在上海成立翻譯部。主要將英文書籍翻譯成漢語,這也是為山西大學準備教材。學科涉及:植物學、礦物學、生理學、物理學、教學法等書籍,還包括日本東京學校的標準教材,兩冊算術、兩冊代數,《二十世紀普通天文圖集》。[2](P293)
最近幾十年來,國內的輿論界、文化界在評價教會在中國辦學動機時,總是斥之為:文化殖民、文化侵略。筆者認為這不僅是牽強附會,還是惡意歪曲。
首先,文化的傳播,既有本國向外國輸出,也有外國通過教育、學校等方式介紹進來。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們把西方在中國辦學,傳授西方文化視之為文化侵略,那么我們最近十幾年在國外開辦的孔子學院,在國外宣傳中國文化的行為,是不是也叫文化侵略?也叫文化殖民呢?
事實上,越是封閉、落后、愚昧的文化環境,越是難以接受先進文化。之所以視西方文化為猛獸,就是因為近代中國的文化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在西方文化面前,有些國人呈現出文化的極端狹隘、自以為是心理。
其次,明清兩朝政府、官員、民眾和知識分子對本民族文化毫無理由的自以為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的麻木、漠視,是導致中國遠離世界先進文明的重要原因。從馬戛爾尼開始,西方國家的官員不斷地給中國介紹西方的先進技術與文化,甚至在鴉片戰爭以后的很長時間里,英國、法國、美國的政府官員還在不斷要求滿清官員親赴西方,開拓視野。問題是承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仍然沒有使愚昧、麻木、自負的清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清醒。
恰恰是在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學校里,一些中國兒童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文化,并由此帶動了中國社會開始艱難地向西方文明靠攏。
所以應當正視西方在中國的教會學校,給中國社會進步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六、傳教士將中國文化推向西方
傳教士們不僅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還積極地把中國的文化介紹到西方。
馬禮遜于1815年編纂《英華字典》。1817年將《新約全書》翻譯成中文。[7]1824年,他回國休假時,將一萬多冊漢文書籍帶回英國。馬禮遜在倫敦出版了《中國雜記》向英國公眾介紹中國語言文學。英譯《論語》及朱熹集注。[11]
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中國傳教期間,不僅將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而且潛心研究中國文化。他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個印刷所——墨海書館。1838年,他在倫敦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國的現狀與傳教展望》,向歐洲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歷史與文明包括中國的禮儀、文化成就、語言文字、法律。
同樣蘇慧廉將自己在華期間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國與西方》《中國與英國》、《論語譯英》、《 中英佛學詞典》、《儒道釋三教》(法文版)在整理后分批次地在英國出版。蘇慧廉回國后,被牛津大學聘為漢學教授。
上述著作成為西方國家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文獻。
七、對歐洲文化及傳教士的敵視,導致對傳教士貢獻的歪曲
1500年到1600年的歐洲,是世界發生巨變的前夜。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將人們的視野從天堂移向人間,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使歐洲擺脫了基督教教條的束縛,新教徒們那顆“跳動的心”已經開始躁動不安,他們時刻準備把眼光投向歐洲外部。
這個時期的歐洲面臨兩個大問題:一個是對付宗教敵人——伊斯蘭教。奧斯曼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消滅了東羅馬帝國后,基督教世界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縮小。為了消除伊斯蘭教的威脅,他們需要到東方。因為在歐洲人看來,沒有信奉基督教的東方人,是被“上帝遺忘的人”(葡萄牙探險家亨利王子語)。歐洲人要擔負起“救贖”的責任,同時這或許是打擊伊斯蘭教時可團結的力量。
另一個是貿易的需要:奧斯曼帝國占領東羅馬帝國后,伊斯蘭教也控制了歐洲與東方的貿易。歐洲人的鐵器等工藝品不能順暢地沿著絲綢之路銷往中國、印度和東南亞。同樣歐洲如需要絲綢、茶葉、瓷器、胡椒、香料等東方特產,就必須經過中東,那得付出較高的代價。
這個時期的歐洲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而且航海技術足以保證歐洲人徜徉世界。
地理大發現、麥哲倫環球航海,使歐洲人第一次將全球融為一體。可以說,直到1800年以前,歐洲人要消滅“野蠻”的美洲土著人。他們要販賣黑人到美洲做苦役,建立他們的新家園。而唯獨到東方最初的動機是傳教和貿易,做“救贖”的功。1498年,印度卡利庫特港的統治者問到達該地的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想要什么時,他說:“基督教徒和香料”[12](P637)。達·伽馬的回答雖然無恥,但確實反映了當時歐洲人面向世界的動機和目的。
從早期的利瑪竇、湯若望前往中國傳教,再到馬戛爾尼到中國覲見乾隆皇帝時提出的在北京設立使館、提供荒島作為中轉貿易的要求及向中國展現歐洲的科技成就的情形看,當時英國對中國的態度并沒有惡意。歐洲當時的敵人或者說征服對象并不是中國。
事實上,清朝初期,中國對待基督教徒并不是仇視的。之所以形成清朝中后期及1950年以后對基督教徒的歪曲、敵視態度,蓋因:
1.宗教與文化上的差異
早在康熙年間,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已逾千人。中國的信徒也過萬人。但是此時的羅馬天主教要求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信徒放棄祭拜祖宗。這是1715年康熙皇帝禁止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國人對基督教產生反感的重要原因。
2.敗于“夷人”的民族憤怒
1875年,李提摩太在山東青州的遭遇很能說明一切:在大街上行走的中國人對他說:“英國是反叛我們的國家”。這位普通的中國人竟然認為,英國“在她成為中國的進貢國之前就屬于中國了”[2](P138)。即使乾隆皇帝給英國女王的回復也是“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4](P139)“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越境摻雜”。[4](P144)
將自己扮演成“天朝上國”、將外國到訪視為“萬邦來朝”的中國,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世界的巨大變化。更沒有意識到英國與中國傳統附屬國的本質不同。
中國從官吏到民間仍然視本國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外國,均視為“夷、狄、藩屬”,顯然是由于閉塞所致。
3.狹隘的民族自大狂
當年馬戛爾尼拒絕在見康熙皇帝時行中國的跪拜禮,同時也提出對等原則:馬戛爾尼稱若“中國大臣向英國皇帝皇后行三跪九叩之禮”,則“敝使即唯命是聽”[4](P92)。清政府不僅不同意,而且在日后滿清政府的記載卻成了:馬戛爾尼在皇上駕臨之際惶恐萬狀,“身不由己地雙膝跪下”。[13](P113)
不論蘇慧廉還是李提摩太,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始終面臨的問題是:中國人始終認為“碧眼赤須的歐洲人是怪物”。而歐洲青年“來教化他們這些孔圣人的后代?那真可笑之至!”。[1](P30)
所以在當時的中國,上至皇帝,下自官員,及至百姓在封閉的文化環境中,既有自以為是,隨意解釋自己都不了解的世界的一面,另一面也是儒家文化至上的優越感。
同時基督教的宗教理論,與儒家學說畢竟存在很大差異。
4.對基督教徒慈善事業的歪曲
中國社會的棄嬰,甚至在饑荒年代“食嬰”現象都是司空見慣的。同時儒家文化從來沒有善待過婦女,遺棄女嬰現象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絕跡。
但那時中國的這一劣跡,與基督教的傳統是不相容的。在中國人看來,歐洲人和中國人并不沾親帶故,憑什么收養中國的嬰兒?由于我們對基督教慈善理念的不理解。臆想之后,想當然地認為:洋人用中國嬰兒的內臟做西藥。編造并傳播的這些謠言的結果,必然導致洋教案的發生。
5.對基督教徒的奉獻精神無法理解
李提摩太為什么來中國傳教呢?他說:“在中國內地那英雄主義、自我奉獻的傳教計劃吸引我”[2](P11)。但是李提摩太時代的中國,并不是中國的隋唐時代。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人對歐洲更是產生了很深的敵視。他剛到煙臺,就得知天津慘案——法國領事和他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慘遭殺戮。[2](P20)可這依然沒有動搖他在中國傳道的決心。
同時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宗教信仰的狂熱時代,恰恰是對“鬼神、迷信”始終癡迷。在這樣一個封閉的、自以為是的文化環境里,這種沖突是必然的。
6.極左思潮作怪
1950年以后,在全面反西方的極左情緒下,我們排斥西方的文化、思想,更包括宗教。我們從教科書,到輿論媒體全然不顧歷史的事實,全面歪曲傳教士在中國的積極作用。這個局面在1978年后,才開始有所改變。
在當時落后、愚昧、自以為是、保守頑固的中國,是傳教士艱難地將新的文化、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帶到了中國。且其中許多新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新的制度、新的價值觀已在中國扎根,為中國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的文化力量。這是值得我們紀念和緬懷的。
中國晚清、近代日本的歷史事實證明:一個能夠走向現代化的優秀民族,不僅應當理智對待其他民族的文明,更應當對先進文明保持寬容、學習的心態。不應當是中體西用,而應當是:只要是先進的、符合當代文明發展潮流的思想文化,都不應排斥或歪曲。
[1]沈迦.尋找·蘇慧廉[M].新星出版社,2013.
[2][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晴四十五年[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91.
[3]任云蘭.傳教士與中國救濟理念的近代化[J].理論與現代化,2007(2).
[4][英]馬戛爾尼.乾隆英使覲見記[M].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76.
[5]張立.從晚清慈善事業的發展看傳教士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J].文教資料,2009:7.
[6]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進程[N].基督時報,2014-06-06.
[7]晏可佳.馬禮遜傳教事業的回顧與評價[Z].中國會議,2006-11-1.
[8]Chinese Repositoay:“ Morrison Edncation Society.vol.11P.339-340”
[9]仇華飛.馬禮遜教育會與馬禮遜學校的創辦[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2).
[10]任云蘭.傳教士與中國救濟理念的近代化[J].理論與現代化,2007(2).
[11]蘇精.馬禮遜史料舉隅[J].國際漢學,2007.
[12][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著.新全球史(下)[M].北京大學出版社.
[13]徐中約.中國近代史[M].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