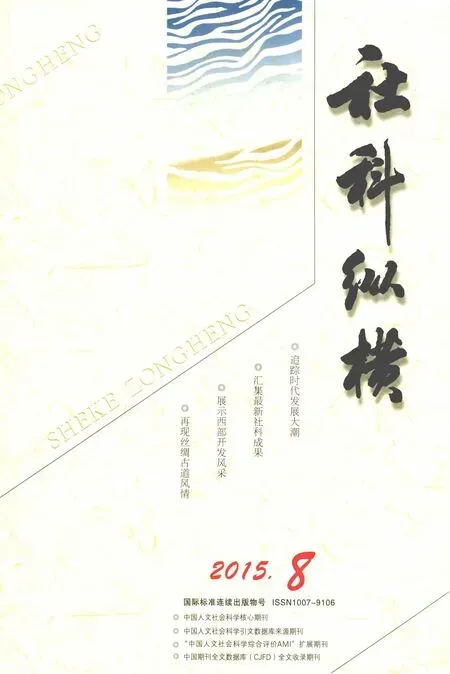宋代贅婿的財產繼承權利
石 璠
(東莞理工學院政法學院 廣東 東莞 523808)
中國古代的繼承,長期以來就將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連在一起,稱為“承繼”,承繼人的資格受到嚴格限制,基于“鬼神不享非類之祀”的觀念,只有同族之人才是正當的承繼者,與之相連的家產的繼承也被嚴格限制在族內。
贅婿一方面作為妻方之家庭成員,在家庭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贅婿作為異姓之人,缺少宗法血緣上的根據,其財產繼承權利一直以來都缺乏明確的法律保護。宋代最主要的傳世法典《宋刑統》中關于財產繼承的法條完全沒有提及贅婿,他的財產權依附于妻子。所幸這樣一種與實際生活需要相悖的情形,隨著宋代社會的發展逐步地得到了改善,法律對贅婿的財產繼承權利逐步地作出了規范,其財產繼承權的大小與其所贅居的家庭男丁狀況密切相關。
一、戶絕財產之繼承
在戶絕的情況下,因為繼承家產的男子缺席,贅婿的財產權利最有可能被顯現出來,有關贅婿的繼產問題也最早在戶絕的情況下被提及。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因各地對戶絕之家所遺財產的歸屬不斷地發生糾紛,有大臣上書要求朝廷立法解決,其提議被朝廷采納:
秘書丞知開封府司録參軍事張存言:伏睹元年七月敕,戶絕莊田檢覆估價,曉示見佃戶依價納錢,竭產買充永業,或見佃戶無力即問地鄰,地鄰不要方許無產業中等以下戶全戶收買勘會。今年春季后,來振東明諸縣申:戶絕狀雖已依敕,內有相承佃,時年深理合厘革者,并是亡人在日已是同居,戶絕后來供輸不闕,或耕墾增益或邱圓已成,無賴之徒因為告訴,久居之業頓至流離,官司止過莫能,獄訟滋彰逾甚,況孤貧之產所直無多,勸課之方其傷或大。欲乞應義男、接夫、入舍婿并戶絕親屬等,自景德元年以前曾與他人同居佃田,后來戶絕,至今供輸不闕者,許于官司陳首,勘會指實,除見女出嫁依元條外,余并給與見佃人,改立戶名為主,其已經檢估者,并依元敕施行。從之。[1](P5901-5902)
這時候,戶絕之家的贅婿只要是自景德元年(1004年)起到戶絕時止一直與妻家人同居佃田,并盡到了對妻之父母的贍養義務,即可以擁有對妻家財產的所有權了。這幾乎是宋代法律首次對贅婿財產權作出的規定,由此,贅婿的財產權被納入了法律的調整范圍,贅婿的無權地位得以改善。
但是,上述的法令對贅婿獲得家產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但要求贅婿“供輸不闕”,而且對贅婿的同居年限做了嚴格的限制,從景德元年到天圣元年,前后十九年的時間里,一直居于妻家的贅婿才是合格的權利人。而且,更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法令似乎只有溯及既往的功能,它只給與了景德及以前成為贅婿的男子財產權,而沒有承認景德以后成為贅婿的男子有這樣的財產權,這使得很大一部分贅婿被排除在外。這種情況到天圣四年(1026年)的時候得到了改善,國家制定了比較完整的關于戶絕財產的繼承法規:
今后戶絕之家如無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將資財莊宅物色,除殯喪營齋外三分與一分,如無出嫁女即給與出嫁親姑姊妹侄一分,余二分若亡人在日,親屬及入舍婿、義男、隨母男等自來同居營業佃蒔至戶絕人身亡及三年已上者,二分店宅財物莊田并給為主,如無出嫁姑姊妹侄,并全與同居之人。若同居未及三年及戶絕人孑然無同居者,并納官。莊田依今文均與近親,如無近親即均與從來佃蒔或分種之人承稅為主。若亡人遺囑證驗分明,依遺囑施行。[1](P 5902)
在有出嫁女或出嫁親姑姊妹侄時,在妻家居住三年以上的贅婿即可得到家產的三分之二,若無以上女性,他就可獲得全部的家產了,這是贅婿對妻家財產最大份額的權利了。此時,法律所給予的贅婿對戶絕之家的財產權更具有合理性,無論是對同居時間的要求上還是繼承財產的份額上。這種法律的變化主要考慮的仍然是贅婿對妻家所作的貢獻,給予同居三年者一定的財產,而不及三年的什么也得不到,即是這種思想的反映。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考慮到贅婿對妻家實際所作貢獻的大小,對那些經營妻家財產而使財產增值達到一定數額的贅婿,國家降低了其獲得妻家財產的同居三年以上的時間要求:
三省言:看詳元符戶令,戶絕之家,內外親同居記年不應得財產。如因藉其營運措置及一倍者,方計奏裁,假如有人萬貫家產,雖增及八九千貫文,猶不該奏,比之三二百貫財產增及一倍者事體不均。兼昨來元佑敕文但增置及一千貫者奏裁之法,今參酌重修雖不及一倍而及千貫者,并奏裁之。詔依仍先次施行。[1](P5904)
因此,即使贅婿在妻家戶絕之前,沒有在妻家居住三年以上,但是依靠他的經營使得妻家財產增值一倍或者千貫以上的,他有權通過法定審批程序獲得部分的財產。而到南宋的時候他似乎已經不需要經過特殊的批準手續即可獲得一定的財產了:
在法:諸贅婿以妻家財物營運,增置財產,至戶絕日,給贅婿三分。[2](P215-217)
法律發展到這里,贅婿對妻家財產的繼承權已經比較合理和有保障了,法律對權利的直接規定使得他成為了妻家財產的法定繼承人。但是,贅婿獲得上述的權利有一個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戶絕之人沒有留下關于其遺產處分的遺囑。如果戶絕之人留有遺囑,家產如何繼承將完全按照遺囑的要求進行了,此時,贅婿如果不是遺囑人選中的繼承人的話,他就無權對妻家財產作出要求。但存在希望的是,畢竟贅婿對妻家作出了貢獻,對妻之父母盡了贍養的義務,他也可能因被遺囑人喜愛而被選為繼承人,此時,他對妻家的財產繼承就要按照另外的方式進行了。
宋代法律自《宋刑統》開始即承認了戶絕人的遺囑權利,之后的法律都堅持了《宋刑統》的精神,戶絕條件下遺囑繼承的規則優先于法定繼承的規則適用。贅婿作為遺囑繼承人能夠繼承多少財產,除了取決于遺囑人所遺囑的份額外,還要受到宋代遺囑規則的限制。宋代的法律規定了遺囑繼承的最高額,繼承人不能超出這個限額獲得財產,即:其得遺囑之人,依現行成法,止合三分給一。[1](P5906)也就是說,通過遺囑的方式贅婿最多只能獲得三分之一的家產,這與他在戶絕條件下適用法定繼承時獲得的份額要少得多。但無論如何,這也是贅婿繼承妻家財產的一種途徑。
二、非戶絕財產之繼承
在父親死后有兒子存在,家庭處于非戶絕的情況下,贅婿的繼承權利以及繼承份額將因為與其并存的這個兒子是親生子還是養子而有所不同。
1.贅婿與親生子并存
一個家庭在父死有子的場合,兒子成為當然的繼承人,這是同居共財的家庭里繼承發生時最自然的結果。由于贅婿往往是在一個家庭無子時招入的,因此,子與贅婿并存的情形是不太典型的,法律最初也忽視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一直沒有規定贅婿在這種情況下的繼承權。雖然北宋的社會中,贅婿與子均分家產已經是川峽之民俗了,但法律對此未作承認,這使得贅婿此時在法律上完全處于無權的狀態。為消除這種不合理,遺囑在此時又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法律規定遺囑只在戶絕或無承分人的場合才發生,但是習慣上,亡人特別是父祖的遺囑權受到人們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乃至法官的判案過程中,非戶絕情形下父祖所立的遺囑并沒有因為家庭中有法定承分人而失去其效力。這種現實狀況的發生也是與中國古代家庭財產的共財性質相連的。在父子共財的家庭中,家長是整個家庭財產的所有者,他擁有對家產的處分權,對家產進行遺囑處分是他行使其處分權的表現。因此贅婿通過遺囑方式繼承財產成為可能。
這種遺囑繼承的方式也是贅婿在此時獲得繼承權的唯一途徑。因此有贅婿為獲得財產偽造岳父遺囑的案件發生,這時法官需要證明的只是遺囑的真偽,并不需要說明被訟之人有沒有繼承權:
縣吏死,子幼,贅婿偽為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3](P 9927)
在此案中對遺囑效力的否定就是對其繼承權的否定,郎簡只需要證明贅婿所持書契是偽造的就可以證明他沒有繼承權。
《清明集》中的另一個案件也同樣可以說明這一問題:
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遺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后財產合作三分,遺腹子得二分細乙娘得一份,如此分析,方合法意。李應龍為人子婿,妻家見有孤子,更不顧條法,不恤孤幼,輒將妻父膏腴田產,與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標撥,天下豈有女婿中分妻家財產之理哉?縣尉所引張乖崖三分與婿故事,即現行條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東尉,索上周丙戶下一宗田園干照并浮財帳目,將磽腴好惡匹配作三分,喚上合分人,當廳拈鬮。[2](P 277-278)
贅婿李應龍“妄作妻父、妻母標撥”的行為充分說明了贅婿此時沒有對妻家財產的法定繼承權,想要有所“占據”只有通過妻之父母的遺囑,遺囑是贅婿獲得妻家財產并為官方及妻方族人承認的必要條件。
但是,考慮到非戶絕情況下遺囑繼承的發生只是一種習慣的約定,雖然人們出于對遺囑人財產權的尊重往往會按照遺囑的要求處理遺產,但是,這種遺囑的效力畢竟沒有法律的保障,而且在這種遺囑的內容過分犧牲了親子的利益時,將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它的效力也可能受到置疑。所以,即使贅婿真的擁有了真實的岳父的遺囑,他能否據此獲得財產繼承權仍然是不肯定的,現實生活中也有因此而發生的爭議:
御史中丞張詠為工部侍郎,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托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于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馀三給婿,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4](P941)
此案中,贅婿確實持有真實的岳父之遺囑,但是,法官顯然認為這種遺囑是不合情理的,它使得法定的繼承人——親子的利益受到很大的侵害,因此,法官以主觀的推測否定了遺囑的字面意思,而以另外的方式處理了遺產。雖然,此案中的贅婿最終仍然繼承了十分之三的遺產,但是,法官這種改變遺囑內容的行為本身足以說明贅婿在這種非戶絕情形下依賴遺囑繼承家產的不穩定性。
當然,這種不穩定除了歸因于非戶絕情形下的遺囑缺乏法律根據外,還與宋代遺囑的一般效力相關。因為在提倡同居共財的儒家社會里,家產在家庭內穩定地世代相傳是人們的理想,法定的繼承方式給了家產流向一個穩定且可預測的方向,而遺囑繼承是家產在世代間流動的一個變數,人們因此對遺囑繼承總是懷著謹慎的態度。對有效遺囑的要求從“證驗分明”到“聽自陳,官給公憑”,越來越嚴,越來越規范化。即使是在正常的遺囑人得行遺囑的場合,法官在斷案過程中也不一定按照遺囑的處分方式裁判財產的歸屬,往往做一些調和,力求雙方的和睦和利益的均衡。而在很多最后依遺囑而判的案件中,法官也通常會給出大段的情理道德的說教,極力為這樣的處分行為找到道德的根據,法官不是從法律上確定,而是從情理上確定這種處分行為的有效性。這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了遺囑在處分財產時的局限。
所以,在一個有子招贅的家庭,繼承發生時,在法律上贅婿被排除在外,習慣上對亡人遺囑的尊重是贅婿在這樣的家庭獲得財產的唯一希望,但這顯然是不穩定的,再加上宋代遺囑效力本身的脆弱性,以及得立遺囑人在未立遺囑而亡的情況,贅婿借助遺囑來取得部分財產是不確定的,它只是一種可能性,出現任何一種差錯,這種可能性就會立即消失。
2.贅婿與養子并存
無子的家庭以招贅婿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缺乏問題,而以收養養子的方式來解決宗祧繼承問題,贅婿與養子并存的家庭是較為常見的。他們對家庭財產的權利劃分不同于贅婿與親生子那樣絕對,養子雖然承擔著延續宗之血脈的職責,但他本身也是家庭中的特殊成員,與親子比較是與贅婿一樣處于弱勢的人,他與贅婿之間的權利存在一種相抗衡的可能。尤其在父親死后立嗣的場合,贅婿可能獲得岳父的遺囑,并以此方式對財產提出要求,而養子此時對家產又有法定的繼承權,兩者矛盾不可避免。法律為解決這樣的矛盾不斷作出調整,因此有了“贅婿與養子均分”的法律出臺: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四月十九日,知涪州趙不倚言,契堪人戶陳訴,戶絕繼養,遺囑所得財產,雖各有定制,而所在理斷,間或偏于一端,是致詞訟繁劇。且如甲之妻,有所出一女,別無兒男。甲妻既亡,甲再娶后妻,撫養甲之女長成,招進舍贅婿。后來甲患危為無子,隧將應有財產遺囑與贅婿。甲既亡,甲妻卻取甲之嫡侄為養子,致甲之贅婿執甲遺囑與手疏,與所養子爭論甲之財產。其理斷官司,或有斷令所養子承全財產者,或有斷令贅婿依遺囑管系財產者。給事中黃祖舜等看祥,欲下有司審訂申明行下,庶幾州縣有似此公事,理斷歸一,亦少息詞訟之一端也。
詔:祖舜看祥,法所不載,均(今)【 分】給施行。[1](P5906)
需要注意的是,贅婿與養子均分的權利只在一千貫家產以內有效,超過一千貫的需要按另外的比例分割: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權知沅州李發言:近降指揮遺囑財產養子與贅婿均給不行誤。若財產滿一千五百貫其得遺囑之人依現行成法止合三分給一,難與養子均給,若養子贅婿各給七百五十貫即有礙遺囑財產條法。乞下有司更賜參訂。
戶部看詳:諸路州縣如有似此陳訴之人,若當來遺囑田產過于成法之數,除依條給付得遺囑人外,其余數目盡給養子,如財產數目不滿遺囑條法之數,合依近降指揮均給。從之。謂如遺囑財產不滿一千貫若后來有養子合行均給,若一千貫以上,給五百貫,一千五百貫以上,給三分之一,至三千貫止,余數盡給養子。[1](P5906)
如此一來,贅婿與養子的繼產矛盾就得以解決了,雖然限制了贅婿的繼產份額,但畢竟將這種均分的方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了,贅婿持遺囑而繼承財產就有了一份法律的保障了。但此時贅婿的繼承權仍然屬于遺囑繼承的范疇,贅婿與養子均分家產只發生在贅婿持有亡人遺囑的場合,這無疑又使贅婿的繼承權回到了上面關于遺囑效力的怪圈中。值得慶幸的是,或許是法律沒有執著于這一點,在以后的發展中作出了改變,也或許是法官在實際的司法操作中,沒有嚴格要求遺囑的存在,贅婿沒有遺囑而繼承了家產的案件在南宋法官的判詞中出現:
蔡氏兩房無子,楊夢登、李必勝,趙必怈分別為這兩房贅婿,后因為立嗣之事發生爭議,法官判決蔡氏以拈鬮的方式解決立嗣糾紛,隨后對其財產分割方式作出了這樣的處理:
合以一半與所立之子,以一半與所贅之婿,女乃其所親出,婿又贅居年深,稽之條令,皆合均分。[2](P205-206)
此時法官并沒有要求贅婿持有有效的遺囑,事實上也并不存在這樣的遺囑,而法官仍然采用了均分的處理方式,這至少可以說明,贅婿與養子均分家產已經不需要有遺囑的支持了,他已經從遺囑繼承人的身份變為法定繼承人了,其財產繼承權更為穩定。
另外一個贅婿沒有遺囑而可與子分割家產的情形發生在一個特殊的場合,即贅婿為保甲之時:
義子孫、舍居婿、隨母子孫、接腳夫等,現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4](P8009)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既不要求有遺囑,也不論其面對的是親子還是養子,贅婿都有分得與其相比一半家產的權利。這可以看作是贅婿的一種特殊的法定繼承權。
三、贅婿異居后權利的變化
贅婿之所以可以繼承一部分的妻家財產,是基于他居于妻家,在妻家勞動,對妻家作出了貢獻的事實,這種繼承權實際是對他的勞動的一種報酬。一旦他離開了妻家歸宗或者出外居住,他的這種基于同居而發生的繼承權就會喪失。宋代的一份判詞對此表現得非常充分:
劉傳卿有一男一女,女曰季五,男曰季六,季六取阿曹為婦,季五娘贅梁萬三為婿。傳卿死,季六死,季五娘又死,其家產業合聽阿曹主管,今阿曹不得為主,而梁萬三者乃欲奄而有之,天下豈有此理哉!使季五娘尚存,梁萬三贅居,猶不當典賣據有劉氏產業。季五娘已死,梁萬三久已出外居止,豈可典賣占據其產業乎?[2](P236-237)
這里,贅婿梁萬三出外居住已久,他對家產非但沒有繼承的權利,典賣處分的權利也是沒有的,其家產應由寡婦阿曹來管理。法官的這種處理很明顯地體現了贅婿可以繼承妻家財產的根據,即他的同居勞動的事實和對撫養贍養義務的履行。梁萬三出外久居就沒能夠盡到對妻家的義務,因此無權對財產提出要求。雖然寡婦與贅婿都是家庭中處于弱勢的人,但是,因為守志的寡婦代表著丈夫的人格,又有“夫亡妻為主”的法律支持,寡婦此時的財產權利就優于異居的贅婿了。
當然,如上所述,在贅婿為保甲的特殊場合,贅婿在與妻家異居之日可以分得一部分的財產,這可以看做是國家對于保甲贅婿為國家服務的一種補償吧。
四、結語
綜合來看,宋初法律對贅婿財產權利的漠視狀況經過不斷地發展得到了改善,到南宋時其繼承權已經較為合理了。但由于儒家“孝道”倫理和家族觀念的影響,拋棄本生父母,以異姓人身份居于另外一個家族的贅婿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仍然是當受鄙夷的一類人,因此,贅婿對妻家財產的繼承權利表現出明顯的受制約性和不穩定性。
1.受制約性。家族主義、義務本位是封建法律的精神所在,維護家族倫理秩序而不是保護個人權利是法律的宗旨,一切權利和自由只有在不超越家族利益的前提下才能獲得承認和保護。無論是戶絕還是非戶絕情形下,贅婿想要獲得對妻家財產的繼承權首要條件就是對妻家有所貢獻,要“居于妻家”、“對妻家之尊長供輸不闕,盡了贍養義務”,一旦贅婿離開妻家出外居住,就喪失了對妻家財產的繼承權。其財產繼承權利明顯受到家族利益的制約。
2.不穩定性。這主要表現在贅婿依遺囑繼承財產的情形下。對于同居共財的封建大家族來說,遺囑繼承的方式最有可能使得家族財產“外流”,因此,在強調家族利益的中國古代,對于遺囑繼承始終保持著謹慎的態度。贅婿能否依遺囑取得財產除了受到法律關于可否遺囑處分財產以及遺囑處分財產限額的約束之外,還要受到非法律的情理道德的約束,其所持遺囑的效力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其效果可能會因為法官主觀的情理道德的說教而大打折扣。
到了元代,贅婿的法律地位有了較大地提高,主要是法律關注的增多和相關制度的規范,相比宋代對贅婿財產繼承權利大多以臨時性的部門法規或者法官的解釋來貫徹,元代在最重要的法典中對贅婿的權利作出了明確。這種做法到明清時得到了繼承和發展,贅婿在法律上的地位穩定了下來。
[1]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
[2]不注撰者.名公書判清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