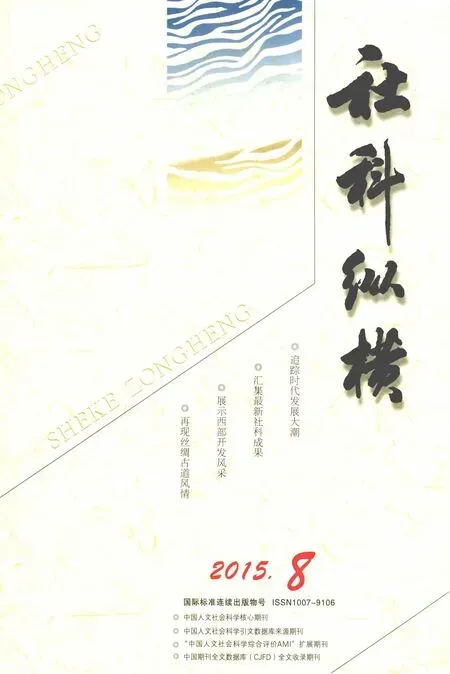論張秀亞小說中的女性書寫
王云芳
(天津社科院文學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張秀亞是臺灣著名作家,她雖是以散文知名,然而,其小說創作的成績同樣不可忽視。根據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的《張秀亞全集》收錄:除了未結集小說外,她總計創作了十部小說,包括兩部中篇小說,八部短篇小說集。數量上雖不像散文那樣卷帙浩繁,質量上卻同樣不可小覷,因為“較之寫詩與散文,我是懷了更嚴肅的心情執筆的。”[1]她的小說,承繼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女性書寫傳統,通過對女性持續不斷地關注,她在女性形象塑造、女性命運反思以及女性自我完成等層面的領悟逐漸深化,其文學實踐將女性書寫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一、日寇鐵蹄下的英雄女兒
文學史上,張秀亞多被冠之以臺灣著名作家,但去臺之前,她其實已是大陸很有名氣的后起之秀。早在20世紀30年代,年紀輕輕的張秀亞就憑借著出色的寫作天賦登上了文壇,不但在《益世報·文學周刊》、《大公報·小公園》 副刊、《武漢日報》“現代文藝”副刊、《國聞周報》上頻頻亮相,還受到凌叔華、沈從文、蕭乾等文學前輩的贊賞與扶持。1936年12月,張秀亞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在大龍河畔》,此時她還不到18歲。1940年,500行的長篇故事詩《水上琴聲》一發表即轟動了北平文壇。此外,她還相繼編輯過進步文學團體海風詩歌小品社的社刊《海風》、輔仁大學的校刊《輔仁文苑》。1943年她與同學結伴入蜀,接任重慶《益世報》社論委員和《語林》副刊編輯的工作。1948年冬,為了擺脫婚變的陰影,與兒女搭船遠去臺灣。這一時期,張秀亞的寫作才能在各個領域皆有突飛猛進的提高與出色表現,她勤奮搖筆,創作了不少詩歌、散文、評論,小說方面則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在大龍河畔》《柯羅佐女郎》,中篇小說《皈依》《幸福的源泉》。
從張秀亞早期的文學創作經歷來看,她寫作才能的成長期恰恰與中華民族的危亡時期相吻合。張秀亞遺傳了母親柔弱善感的氣質[2]然而,成長過程中社會現實的殘酷與沉重使得她無法依著性情沉迷于綺麗的夢幻,她說:“終于那俯拾都是美麗的國度,不能再停留了。夢,無法,再繼續著做。一些苦難,像巨靈的掌一樣,迎頭向我撲來。一些人的喊叫,哭聲逐漸在我耳邊高亢起來,我睜開了眼,我看見我的鄰人,我的朋友臉上刻畫著被損害的紋路,在我身邊走過,枯干樣削弱的軀體,拖著長長一條灰影。”[3]日本侵華戰爭開始以后,民族的苦難催促她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用手中的筆為自己的國家盡一份心力。由此,對于國族命運的思索與承擔,成為這一時期張秀亞小說中女性書寫的方向。
她筆下的女主人公,大都是英雄女兒的形象。小說《未完成的杰作》借法國教授萊昂的口吻塑造了露西的形象。露西是萊昂的戀人,高貴而素樸,柔韌又堅強。當德國法西斯占領祖國時,她沒有隨萊昂逃到異鄉過舒適的日子,為了救國,她放棄了愛情,勇敢地留下來做地下工作。根據文末所注,小說完成于1944年7月23日,故事講述的背景雖然是異國,但張秀亞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的創作意圖卻不言自明。小說《一個故事的索隱》則根據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刻畫了女革命者杜慈的形象。為了抗日救國,杜慈痛苦而又堅毅地選擇了犧牲個人的愛情,與日本追求者鈴木太郎虛與委蛇,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小說《動物園》則以諷刺與白描的手法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淪陷區敵偽統治下學校中的百丑圖:學生們不思進取,耽于享樂與攀比;教師們或者趨炎附勢,打壓進步學生的愛國熱情,或者滿足于追求個人的蠅頭小利茍且偷生;女眷們則偏愛制造流言,中傷異己……最終,滿懷愛國熱情的青年女教師文菁,目睹這一切丑惡現實,不堪同流合污,憤而離去。
這些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都是張秀亞的化身。她們氣質憂郁,喜歡身著一襲藍衫。富有才華,柔弱卻又堅韌,她們沒有多余的精力去思索女性自身的特殊命題,當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她們總是毫不猶豫地放棄對個人的堅守,而將小我的存在意義投入到大我中去,借用一篇小說中張秀亞的夫子自道:“翻開天文學,我們會驚異自己的渺小,只是微點與毫末,這小小的微點即使本身能夠快樂,可是多么卑微不足道,我們還是擁抱住一個偉大的理想,把自己的涓滴融入廣大的海洋吧!”[4]客觀地來看,她們其實都是生活中平凡的女性,然而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她們努力與男性共同承擔著國家民族的興亡大任,有時甚至比男性表現出更多的堅韌與決絕,她們超越自我、追求大義的精神使其像英雄一樣散發出耀眼的光輝。這些人物形象的形成與彼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雖然限于作者人生經歷的單純,她們還不夠血肉豐滿,人物個性上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復雜性,不過她們是張秀亞強烈的愛國情操的結晶,對于彼時中國人民的抗日來說,其存在無疑可以鼓舞士氣,堅定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信仰對張秀亞女性形象塑造的影響。大學時期,張秀亞就讀于北平輔仁大學。這是一所教會大學,在這里,張秀亞加入了天主教并終生信仰虔誠。寫作是作家與靈魂的對話方式,宗教信仰必然會影響到作家的文學創作。對張秀亞來說,最明顯的莫過于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宗教精神的烙印。例如中篇小說《皈依》講述主人公華和珍的有悲劇意味的愛情故事。華上大學時受到感召信仰了公教,飽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珍無法理解,兩人的思想軌跡漸行漸遠終至分手。然而,洪水滔天中華奮不顧身地挽救了珍的父親,其舍己救人的行為讓珍深受震撼,她亦追隨華的步伐接受了公教信仰。小說《幸福的源泉》則虛構了美侖、士琦與文菁之間的三角愛情故事。士琦是一個理智虔誠的公教教徒,他傾慕自信孤傲富有才華的文菁,然而,文菁不信仰宗教,二人思想上存在差異;美侖與士琦雖信仰相同,卻缺乏共同的審美觀念。她嫉妒文菁,陷入痛苦中。后來,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美侖意識到自己心胸的狹小,不再強求;文菁亦走進了公教的懷抱,與士琦共結連理。三人和好,心靈重歸平靜,找到了幸福的源泉。這兩篇小說,宗教氛圍濃厚,皆沒有脫離宗教文學的局限。為了傳達宗教精神,人物形象完全成了真善美的化身,有失真實。如果說此時的張秀亞尚未能將宗教領悟與文學創作水乳交融的話,那么在小說《北國一詩人》中張秀亞則大有進益。小說題記中,張秀亞寫道:“有些人是在輝煌的冠冕下尋找英雄,但真正的英雄卻隱蔽于黑暗中,走著無人行的崎嶇的路。鷓鴣,那呼喚春天的鳥雀,只令人聽到鳴聲,卻不肯向人炫耀翎羽。”[5]她在小說中塑造了女詩人P的形象。在一潭死水似的淪陷區,P堅持不懈地用詩句喚醒沉睡的靈魂;因為游行抗議,她上了敵人的黑名單,自己雖不能離開,卻積極鼓勵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邁向自由的世界。P就像魯迅一樣,盡己所能地“肩負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6]。小說中的P不再是張秀亞幻想中脫離現實的人物形象,她血肉豐滿,可以稱得上是耶穌的女性化身。綜觀這一時期張秀亞的女性書寫,大都著筆于抗日救亡的命題,洋溢著濃烈的愛國熱情,而宗教所倡導的犧牲精神,則成為女主人公放棄小我、成全大我,更加堅定地進行革命保衛祖國的動力與源泉。
二、癡心女子負心漢
在封建社會中,女子沒有直接從事社會生產的機會,她們被迫幽居于家庭之內,依附男子而生,幾千年來道德倫理規范所規定的所謂三從四德更從意識形態上強化了女性的從屬地位。男子有機會接觸更多的女性,可以三妻四妾,大部分的女子卻必須待在家庭之內,對丈夫保持忠貞。男子只是將愛情、家庭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對女子來說,丈夫家庭卻幾乎是生活的一切。這種不對等的關系模式造就了許多癡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典型的如陳世美與秦香蓮。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科學與民主的思潮遍及開來,女性也同男性一樣,走出家長專制的封建家庭,追求個性解放與婚姻自由。然而,社會變遷雖然為女性獨立提供了很多機會,但女性的解放遠未完成。社會風俗、傳統觀念使得許多女性心理上仍然是個依附者,張秀亞的小說塑造了很多這種心理上處于過渡期的女性形象。
去臺前后,炮火連天中,張秀亞遭受了國破、家亡、人散的三重悲哀,尤其是婚姻情感的破裂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傷害。雖然她努力地自勉:“痛苦侵蝕了我的身體健康,我應該轉而利用它來滋養我的文學生命。”[7]也用生活的苦酒,造就了大量的文學佳釀,然而過往愛情、婚姻生活的情感體驗,凝聚在這一時期的女性書寫中,使其小說形成了癡心女子負心漢的潛在模式。如《誤會》和《鸚鵡》均以不同的敘事視角書寫了婚姻中丈夫出軌的題材。女主人公為了維持家庭完整,放棄自我追求,犧牲良多,無奈仍無法喚回丈夫出走的心。小說《幻想》則講述了表姐菁和雕塑師羅里的愛情故事。世事變幻,陰差陽錯,二人終于錯過。菁以為羅里如此癡情,定會在她離去后黯然銷魂禹禹獨行。還為此創作了一幅《白骨赤心》的畫作。誰料想,羅里后來不但結婚,且為了追求新歡拋棄了結婚五年的妻子。《幻影》的情節設置巧妙,作者不動聲色地戳破了愛情的肥皂泡。那所謂的癡情男人原來只存在于女性的幻想中,真相是這個薄幸之徒既不忠于愛情,也沒有盡到做丈夫的責任。小說《娥姐》則塑造了一位癡情的女性形象娥姐,她質樸能干,為了愛人減去發辮、學習文字、甚至不惜損害身體健康,然而,男主人公為都市生活的虛榮所誘惑,到底還是辜負了她。
總體說來,這些女主人公多是為了家庭,全心全意地奉獻一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然而她們卻總是遭遇到背叛,癡心女子負心漢的處境使其在情感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淵,彷徨、無助而又絕望。表面上,偶然的遇人不淑造就了她們悲慘的命運,實質上,在傳統文化觀念熏陶下,她們放棄了女性個人的獨立與成長,將自身存在的意義建立在男子身上才是其悲劇的根源所在。
這些小說大都彌漫著淡淡的憂傷,天鵝的哀鳴之聲曲折地傳達出張秀亞內心的悲憤與痛楚。張秀亞出身于一個傳統家庭。小時候父親在外為官養家糊口,母親在家奉養雙親,撫育兒女。母親傳統文化的修養很高,她教授張秀亞唐詩元曲,為其心靈培育文學幼苗。上大學后,張秀亞又信仰了天主教,恩師英千里夫婦互敬互助的家庭為其婚姻生活提供了想象的典范。婚后,為了家庭和諧,她放棄自己喜愛的文學創作有三年之久。只是幫助丈夫,忙于家庭瑣屑。無論是原生家庭中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還是宗教文化的信仰,都注定了張秀亞并不是一個背叛傳統的人。盡管她廣泛閱讀了中國現代女作家如冰心、廬隱、凌淑華等人的作品,但她的女性自覺并非生而有之,更確切地說來,倒是情感受創后的覺醒。因此,這一時期,與她的前輩作家們的同類題材相較,張秀亞小說中的女性書寫鮮少諷刺與反思的筆觸,憂郁的基調下隱藏的是對傳統女性情感的共鳴以及其命運的同情。
三、肩負起命運的重擔
張秀亞是一個個性堅強的人,對于過往的情感遭際,她說:“生活曾經把我的杯子里裝滿了苦酒,我并未拒絕,卻一飲而盡,涓滴未留。如果我曾是個怯懦的人,由那時起,我已是個勇敢地人。我不再怨嗟,這就是人生。”[1]如果說,去臺初期張秀亞尚沉浸在婚變的情感糾結中痛苦不堪,其女性書寫由于偏于情感抒發而不夠深入,那么,在迷惘絕望的奔突前行中,她不抱怨,不逃避,心甘情愿地肩負起命運的重擔,反倒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在苦難的荊棘中開辟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生活中,張秀亞輾轉于講臺、桌臺、灶臺之間,辛辛苦苦地撫育一雙兒女長大成人;寫作上,痛定思痛之后,她慢慢跳出了過往小說創作中的潛在模式,以平凡世界中的蕓蕓眾生取代了小我的喜怒哀樂,她說“我觀察,我思索,我潸然淚下”,并期冀能“獨立蒼茫,以蘆管之筆蘸著心靈之泉,默默的寫著人性中永恒的那一點”。[1]
秉持了宏闊冷靜的觀察視角,張秀亞對女性命運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她刺破了愛情綺麗虛幻的外衣,借助愛情主題的探討,向讀者揭示出人性中的弱點。小說《春晚》其實可以看作是小說《娥姐》的續篇。如果說《娥姐》中,男主人公尚因為沒有珍惜娥姐的感情而表現出懺悔之意的話,那么《春晚》中,張秀亞則若無其事地刻畫出了其人性中的無恥與貪婪。男主人公一次次以愛情為誘餌騙取簡真小姐的同情與幫助,又總是因為貪戀財產而另娶他人。當簡真小姐徹底醒悟時,她才發現生活當真不曾為她留下什么,連同那溫馨的回憶也沒有了。掩扉自悲春晼晚,燈前猶自夢依稀。張秀亞的筆觸冷靜含蓄,余音裊裊中哀悼著簡真小姐逝去的青春,留給讀者無盡的惆悵與思索。小說《洄瀾》則以男主人公的口吻追述一場輾轉三地、斷斷續續持續了十年的愛情故事。這份情感,脫去了張秀亞早年作品中圣潔的想象,與其說是愛情,倒不如說是一個中年男子漫漫人生中的艷遇。因為“如果把這愛加以化定量分析,那是十分之五的占有欲,十分之三的好奇心,再加十分之二的憐惜。比起我來,她是那么年輕,那么較弱,那么美,那么無知。”[8]這愛情中哪里還有靈魂交流的成分呢?男人只是用征服、輕蔑的眼光打量著女人,像獵人一般對那雙可愛的素手充滿性幻想。當女主人公流露出自己的主見、思想時,男人立刻便產生挫敗感,惱羞成怒地放棄了。小說《白夜》則描寫了老教授一個晚上的心理活動。面對年輕的妻子,面對逝去的青春、夢想與生命力,他思潮翻涌、感慨良多。老教授拋棄發妻再娶,乃是期望用年輕妻子青春的氣息治愈他行將老去的感覺,希望“這光輝,照射上他那幽黯的巖壁一般乏味的生活”,然而,他的活力沒有復現,妻子卻在幽居的瑣屑家務中耗盡了往日的生機,一日日萎縮下去。一個陌生年輕人的來信,打破了沉悶的空氣。老教授開始思索,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他一直在索取光和熱,卻從未給予。當他醒悟到這點時,他要求妻子離開他,去過幸福的生活。妻子深受感動,開始發現,原來丈夫也是需要關愛的。這些小說,運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也許它們缺乏傳統的傳奇小說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但在人性的描摹與刻畫上,我們不得不說張秀亞是成功的。借助愛情的主題,她以幽微的筆觸探入男性、女性的內心深處,千頭萬緒細加剪裁,在人們熟視無睹之處發掘出了陌生的風景。
同時,對于以往塑造過的家庭主婦形象,張秀亞亦有了進一步認識,其書寫開始流露出明顯的性別反思的自覺性。五四運動以后,隨著社會風氣的自由與開化,許多女性擺脫了封建倫理道德的重壓,她們自由戀愛,步入婚姻,依靠男性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然而,這是一個現代女性應該追尋的方向嗎?張秀亞的思索由此深入下去。小說《晴陰》中塑造了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主婦形象——如茀。結婚以后,丈夫事業成功,忙于應酬。如茀沒有自己的興趣,生活重心完全圍繞著丈夫。雖然衣食無憂,但人越來越懶散倦怠,生命在平庸到可憎的日子中消磨著,日漸僵化。有時候,她也厭倦了這樣的日子,想追求有意義的生活,可是又缺乏耐心、毅力與突破的勇氣。更可怕的是,周遭的社會環境、傳統觀念都不鼓勵女性的自我實現。小說《不相遇的星球》中,家庭主婦央將全部的情感與精力都奉獻給丈夫后卻迷失了自我。她感覺到精神空虛,沒有存在感,試圖做什么來彌補,但很快被周遭反對的聲音所淹沒。那些聲音諷刺著她“身在福中不知福”,讓她安于被豢養的狀態。這些小說中,張秀亞詳盡地描摹女性無所事事、慵懶倦怠、生命力日益萎縮的生活狀態,揭示出了現代女性在自我實現中的障礙:一方面,幾千年來所謂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仍在無形中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的怠惰使其滿足于男性所提供的優渥的物質生活,滿足于寄生的生活狀態。她們看似獲得了解放,其實不過是現代模式下家庭牢籠中的金絲鳥,對自己的悲劇狀態一無所知。
縱觀張秀亞的文學創作軌跡,其女性書寫呈現出逐步深入的趨勢。一方面,她積極投身到社會變革中,以獨特的女性形象為國家和民族的興亡盡了一份心力;另一方面,在上世紀50、60年代臺灣反共文學流行的時代背景下,她又堅守個人的審美追求,抒發女性獨特的情感體驗,自覺地反思歷史進程中女性命運的形成,為后來的創作者脫離政治樊籠埋下了藝術審美的種子;她堅忍不拔地用苦難澆灌自己的文學創作,以不斷進益、著作等身的文學成就向讀者詮釋了一個現代女性覺醒以及獨立的艱辛歷程,她的文學實踐對當下的女性書寫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1]張秀亞.感情的花朵前記.張秀亞全集(第 11卷)[M].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73—75.
[2]張秀亞.作者自傳.皈依.張秀亞全集(第 10 卷)[M].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165.
[3]張秀亞.自序.在大龍河畔[J].天津海風出版社,1936(12):4—5.
[4]張秀亞.未完成的杰作.張秀亞全集(第 10卷)[M].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3):354.
[5]張秀亞.北國一詩人.張秀亞全集(第 10卷)[M].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3):365.
[6]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23.
[7]張秀亞.尋夢草前記.張秀亞全集(第 10卷)[M].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3):400.
[8]張秀亞.洄瀾.張秀亞全集(第 11卷)[M].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200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