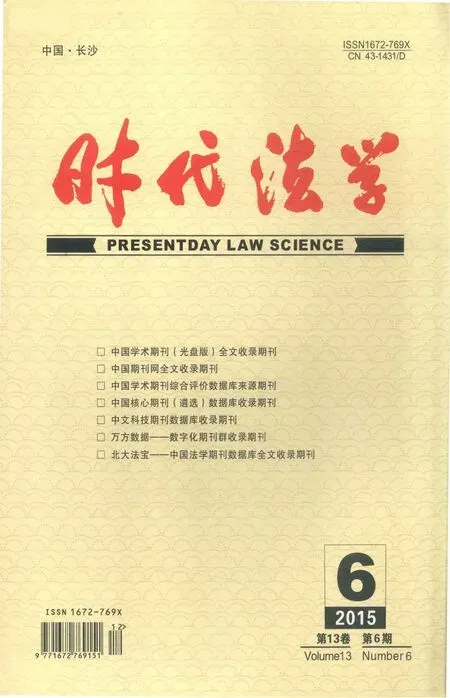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國(guó)際法思考*
王虎華,蔣圣力
(華東政法大學(xué)國(guó)際法學(xué)院,上海 200042)
自1946年通過(guò)第一項(xiàng)決議起至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在漫長(zhǎng)的40余年的時(shí)間里僅通過(guò)了659項(xiàng)決議。自從針對(duì)“伊拉克—科威特間局勢(shì)”通過(guò)的第660號(hào)決議起至1999年,安理會(huì)通過(guò)的決議的數(shù)量則達(dá)到了624項(xiàng)(第660號(hào)決議-第1284號(hào)決議);并且,在進(jìn)入21世紀(jì)之后,截至于2015年10月9日通過(guò)的最新一項(xiàng)第2241號(hào)決議,上述數(shù)量在十余年間又增長(zhǎng)了957項(xiàng)〔1〕資料來(lái)源:http://www.un.org/zh/sc/documents/resolutions/,訪問(wèn)時(shí)間:2015年10月10日。。由此可見,自冷戰(zhàn)結(jié)束以來(lái),安理會(huì)通過(guò)其作出的大量決議在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中發(fā)揮了越來(lái)越重要的作用。而隨著聯(lián)合國(guó)安全理事會(huì)在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中發(fā)揮的作用不斷提升,安理會(huì)是否得以在其決議中創(chuàng)設(shè)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并且適用于一般情形下的全體成員國(guó)問(wèn)題,倘若有權(quán)作出上述所謂的“造法性決議”,那么該決議具有何種法律效力等問(wèn)題,一直為國(guó)內(nèi)外學(xué)界所廣泛關(guān)注〔2〕英國(guó)Routledge出版社于2014年最新出版的一冊(cè)“國(guó)際組織系列叢書”(“Routledge Global Institution Series”)以《作為國(guó)際造法者的安理會(huì)》(“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作為書名,收錄了多位西方知名學(xué)者、政治分析人士和國(guó)際律師的文章。該書著重評(píng)價(jià)了安理會(huì)作為國(guó)際造法者、通過(guò)制定規(guī)則在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中所取得的成效。。西方學(xué)者的主流觀點(diǎn)認(rèn)為,安理會(huì)決議的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僅限于根據(jù)特定情勢(shì)向特定國(guó)家施加義務(wù),而不應(yīng)當(dāng)具有創(chuàng)設(shè)被普遍遵守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的功能〔3〕See Matthew Happold,“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73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no.3(2003):600.。對(duì)此,在我國(guó)亦有學(xué)者提出,安理會(huì)造法性決議的合法性將至少在對(duì)威脅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shì)的認(rèn)定的中立性、安理會(huì)職能范圍擴(kuò)張的法定性、決議通過(guò)程序的公正性和與人權(quán)保護(hù)之間的沖突等方面受到質(zhì)疑〔4〕陳亞蕓.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決議司法審查機(jī)制的構(gòu)建——以國(guó)際法院司法審查為研究視角[A].武大國(guó)際法評(píng)論(第十四卷第一期)[C].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1.134-139.。然而,在實(shí)踐中,基于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問(wèn)題的日益復(fù)雜,尤其是在“9·11事件”發(fā)生之后,安理會(huì)接連通過(guò)的多項(xiàng)在既存國(guó)際法之外實(shí)質(zhì)地增加了全體成員國(guó)法律義務(wù)的決議,卻不僅基本上為各成員國(guó)所接受,同時(shí)亦切實(shí)地對(duì)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起到了促進(jìn)的作用。是故,筆者認(rèn)為,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認(rèn)識(shí)不能僅僅基于理論或?qū)嵺`簡(jiǎn)單地做出結(jié)論,而應(yīng)當(dāng)在首先明確了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情形的基礎(chǔ)上,對(duì)據(jù)以支持其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的法律依據(jù)、客觀需要以及使其與國(guó)際法治相抵觸的不足、缺陷等進(jìn)行全面考察,據(jù)此才能評(píng)價(jià)安理會(huì)既有的決議造法實(shí)踐和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行為本身。
一、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情形
首先,安理會(huì)決議的性質(zhì)由特定性發(fā)展為普遍性。傳統(tǒng)觀點(diǎn)認(rèn)為,由于安理會(huì)的職能一般僅限于保護(hù)特定成員國(guó)免受暴力的國(guó)際沖突或者國(guó)內(nèi)叛亂等情勢(shì)的侵害,以及處置涉及特定國(guó)家對(duì)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問(wèn)題,因此,其決議的內(nèi)容亦應(yīng)當(dāng)以針對(duì)特定國(guó)家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為限,即在性質(zhì)上應(yīng)當(dāng)是具有特定性的“國(guó)別的決議”(“country-specific resolution”)〔5〕See Vesselin Popovski,“The Legislative Ro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s Thematic Resolutions,”in Vesselin Popovski and Trudy Fraser(eds.)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4),3.。然而,倘若要求決議的性質(zhì)必須固守以國(guó)別為標(biāo)準(zhǔn)的特定性,那么,安理會(huì)在應(yīng)對(duì)那些并不直接產(chǎn)生威脅或者威脅的后果并不發(fā)生在特定國(guó)家的領(lǐng)土范圍內(nèi)的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問(wèn)題時(shí),其所發(fā)揮的作用便必然將受到影響和限制。對(duì)此,有學(xué)者即指出,針對(duì)特定成員國(guó)采取制裁或者干涉措施的決議并未能夠廣泛地阻止核武器在全球的擴(kuò)散,而對(duì)非國(guó)家方式的恐怖主義、海盜行為或者氣候變化采取通常以特定國(guó)家為對(duì)象的武裝干涉或者經(jīng)濟(jì)制裁措施亦顯然是不切實(shí)際的〔6〕See Trudy Fraser,“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in Vesselin Popovski and Trudy Fraser(eds.)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4),290-291.。事實(shí)上,安理會(huì)在堅(jiān)持通過(guò)前述特定性的“國(guó)別的決議”處置有關(guān)特定國(guó)家的威脅的同時(shí),其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亦開始向包括恐怖主義、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kuò)散、兒童士兵征募、非法武器走私等在內(nèi)的諸多對(duì)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造成了全面威脅的問(wèn)題轉(zhuǎn)移,并且為應(yīng)對(duì)上述問(wèn)題而通過(guò)了一系列以全體成員國(guó)為對(duì)象的、向全體成員國(guó)施加義務(wù)的“普遍性決議”(“thematic resolution”)。1999年,安理會(huì)通過(guò)的關(guān)于保護(hù)武裝沖突中的兒童的第1261號(hào)決議、關(guān)于保護(hù)武裝沖突中的平民的第1265號(hào)決議以及關(guān)于消除國(guó)際恐怖主義的第1269號(hào)決議,可認(rèn)為是安理會(huì)決議的性質(zhì)由特定性發(fā)展為普遍性的發(fā)端。例如,第1269號(hào)決議規(guī)定,全體成員國(guó)應(yīng)當(dāng)“通過(guò)雙邊和多邊協(xié)議、安排開展合作,防范和打擊恐怖主義行為,保護(hù)本國(guó)國(guó)民和外國(guó)人免受恐怖主義襲擊,對(duì)實(shí)施了恐怖主義行為的罪犯進(jìn)行審判,并且通過(guò)一切合法手段預(yù)防和抵制本國(guó)境內(nèi)的任何準(zhǔn)備或者資助恐怖主義的行為”〔7〕聯(lián)合國(guó)安全理事會(huì)第1269(1999)號(hào)決議[EB/OL].[2015-10-10].http://www.un.org/zh/sc/documents/resolutions/99/s1269.htm.。同樣地,2001年和2004年,安理會(huì)分別通過(guò)的關(guān)于國(guó)際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第1373號(hào)決議和關(guān)于防止核生化武器擴(kuò)散的第1540號(hào)決議,被普遍認(rèn)為是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典型。因?yàn)椋怖頃?huì)“一反常態(tài)地”針對(duì)的是聯(lián)合國(guó)全體成員國(guó),而非某一或某些特定的國(guó)家,并且,其向各成員國(guó)施加的義務(wù)亦具有“一般針對(duì)性”,即規(guī)定了各成員國(guó)在一般情勢(shì)而非特定情勢(shì)下作為或不作為〔8〕王秀梅,李小玲.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的司法審查權(quán)芻議——以國(guó)際組織憲政為視角[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2).。可見,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就是其通過(guò)的決議是以全體成員國(guó)為對(duì)象的具有普遍的性質(zhì);而這類普遍性決議造法的具體表現(xiàn),則是其構(gòu)成了為之后的其他決議,尤其是前述具有特定性國(guó)別的決議所應(yīng)遵循的先例。具體而言,大量的特定性國(guó)別的決議的序言均明示了該決議所采取的措施或者對(duì)特定國(guó)家施加的義務(wù),是以在此之前被通過(guò)的普遍性決議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作為參照的〔9〕例如,安理會(huì)于2001年通過(guò)的兩項(xiàng)關(guān)于阿富汗局勢(shì)的第1378號(hào)決議和第1386號(hào)決議的序言均表明,該決議“支持根據(jù)《聯(lián)合國(guó)憲章》根除恐怖主義的國(guó)際努力,并重申2001年9月28日第1373(2001)號(hào)決議”。。
其次,安理會(huì)決議的內(nèi)容由執(zhí)行國(guó)際法發(fā)展為創(chuàng)設(shè)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有學(xué)者指出,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包括三種情形。其一,通過(guò)決議規(guī)定,國(guó)家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其本應(yīng)承擔(dān)的法律義務(wù),以強(qiáng)化國(guó)際條約中既有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其二,通過(guò)決議規(guī)定,國(guó)家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原本無(wú)須承擔(dān)的國(guó)際條約義務(wù),以使得涉及該國(guó)的威脅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問(wèn)題能夠得到更加有效地解決;其三,通過(guò)決議規(guī)定,創(chuàng)設(shè)一項(xiàng)在既有國(guó)際條約中均尚未作出規(guī)定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10〕See Vesselin Popovski,“The Legislative Ro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s Thematic Resolutions,”in Vesselin Popovski and Trudy Fraser(eds.)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4),5.。在聯(lián)合國(guó)成立之初,安理會(huì)即被視為是聯(lián)合國(guó)體系下的執(zhí)行機(jī)構(gòu),并且,其職能亦相應(yīng)地被確定為在既有國(guó)際法規(guī)則的范圍內(nèi),對(duì)各成員國(guó)的行為進(jìn)行監(jiān)督和規(guī)范〔11〕See Peter Calvolcoress,i“Peace,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dividual,”in G.R.Berridge and A.Jennings(eds)Diplomacy at the UN(London:Macmillan Press,1985),17.。同時(shí),無(wú)論是規(guī)定作為締約國(guó)的國(guó)家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國(guó)際條約義務(wù)的決議,還是將作為非締約國(guó)的國(guó)家納入某一國(guó)際條約,向其施加相應(yīng)的法律義務(wù)的決議〔12〕例如,在關(guān)于防核武器擴(kuò)散的朝鮮問(wèn)題的第1718號(hào)決議中,安理會(huì)即要求朝鮮必須撤回退出《不擴(kuò)散核武器條約》的宣告,并且繼續(xù)履行該條約規(guī)定的各項(xiàng)義務(wù)。,其所依據(jù)的亦仍然是既有的國(guó)際法原則和規(guī)則。因此,在以上前兩種情形中,安理會(huì)通過(guò)決議僅是在具體地履行執(zhí)行既有的國(guó)際法原則、規(guī)則的固有職能而已;而真正意義上的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則應(yīng)當(dāng)是前述第三種情形,即安理會(huì)通過(guò)決議在既有的國(guó)際法之外創(chuàng)設(shè)新的國(guó)際法原則和規(guī)則。具體而言,根據(jù)前述安理會(huì)第1373號(hào)決議中的規(guī)定,各成員國(guó)被禁止向恐怖主義提供任何形式的資助。對(duì)此,盡管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guó)際公約》第2條第1款亦作出了相同的規(guī)定,但由于截至安理會(huì)通過(guò)上述決議的2001年9月28日,僅有博茨瓦納、斯里蘭卡、英國(guó)和烏茲比克斯坦等四個(gè)國(guó)家就加入公約交存了批準(zhǔn)書,遠(yuǎn)未達(dá)到該公約規(guī)定的生效條件。可見,在安理會(huì)通過(guò)上述決議時(shí),該公約實(shí)則尚未生效,因此,上述安理會(huì)的決議,實(shí)際上并非是對(duì)一項(xiàng)已經(jīng)既有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的重申,而是創(chuàng)設(shè)了一項(xiàng)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13〕See Jan Wouters and Jed Odermatt,“Reflections on the Law-making Pow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in Vesselin Popovski and Trudy Fraser(eds.)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4),79.。同樣地,盡管在安理會(huì)通過(guò)前述第1540號(hào)決議之前,1968年《不擴(kuò)散核武器條約》、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和1993年《禁止化學(xué)武器公約》等一系列業(yè)已生效的國(guó)際條約均已對(duì)核生化武器擴(kuò)散作出了禁止性的規(guī)定,但由于其規(guī)定所禁止的核生化武器擴(kuò)散的范圍僅限于國(guó)家之間,而并未包括非國(guó)家行為者,因此,上述決議關(guān)于禁止向非國(guó)家行為者進(jìn)行核生化武器擴(kuò)散的規(guī)定,實(shí)則構(gòu)成了一項(xiàng)超出既有國(guó)際法的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
綜上,傳統(tǒng)意義上,安理會(huì)通過(guò)決議主要針對(duì)特定地區(qū)或特定國(guó)家的情勢(shì),而近年來(lái),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情表現(xiàn)為:安理會(huì)通過(guò)決議規(guī)定了全體成員國(guó)在一般情勢(shì)下均應(yīng)予履行的義務(wù),其性質(zhì)具有普遍性;并且,這些規(guī)定本身同時(shí)亦創(chuàng)設(shè)了既有國(guó)際法規(guī)則之外的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
二、安理會(huì)既有的決議造法實(shí)踐的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
針對(duì)諸如上述第1373號(hào)決議和第1540號(hào)決議等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有學(xué)者指出,安理會(huì)從未被設(shè)想過(guò)將成為一個(gè)獨(dú)立自足的國(guó)際造法者〔14〕See Georg Nolte,“The Limit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s Powers and its Fun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Some Reflections,”in M.Byers(ed.)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998]),321.;盡管其有權(quán)針對(duì)特定情勢(shì)重申或者適用既有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但卻并未被賦予創(chuàng)設(shè)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的權(quán)力〔15〕See Michael C.Wood,“The Interpret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 Law 77,(1998):78.。而筆者認(rèn)為,任一國(guó)際組織的職能范圍均直接取決于其建立該國(guó)際組織的組織約章對(duì)此作出的規(guī)定,因此,安理會(huì)作為聯(lián)合國(guó)的主要機(jī)關(guān),其是否有權(quán)通過(guò)決議進(jìn)行造法,以及上述有關(guān)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則應(yīng)當(dāng)以《聯(lián)合國(guó)憲章》中的規(guī)定作為認(rèn)定的依據(jù)。
首先,安理會(huì)既有的決議造法實(shí)踐基于“隱含的授權(quán)”而具有合法性。誠(chéng)然,《聯(lián)合國(guó)憲章》并未明確賦予安理會(huì)以決議造法的權(quán)力,但是,憲章亦未明確禁止安理會(huì)得以通過(guò)決議進(jìn)行造法,并且,除享有組織約章明文規(guī)定所賦予的權(quán)力外,國(guó)際組織及其機(jī)構(gòu)亦還享有必要的“暗含權(quán)力”,即基于該國(guó)際組織的宗旨和目的,而根據(jù)其組織約章所推論而得出的必要的權(quán)力〔16〕饒戈平.國(guó)際組織法[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255.。因此,從《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的規(guī)定來(lái)看,安理會(huì)實(shí)則是被默示地授予了決議造法的權(quán)力。具體而言,根據(jù)《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24條第1款、第2款的規(guī)定,安理會(huì)因履行其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能而被授予的特定權(quán)力,被具體規(guī)定在了憲章的第6章、第7章、第8章和第12章中。憲章第24條第1款規(guī)定:“為保證聯(lián)合國(guó)行動(dòng)迅速有效起見,各會(huì)員國(guó)同意將維持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zé)任,授予安全理事會(huì),并同意安全理事會(huì)于履行此項(xiàng)責(zé)任下之職務(wù)時(shí),即系代表各會(huì)員國(guó)”。可見,各會(huì)員國(guó)自身同意并自愿授權(quán),安理會(huì)為了維持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zé)任,代表各會(huì)員國(guó)行事。那么,安理會(huì)的行動(dòng)(包括決議造法),被視為是會(huì)員國(guó)自己的國(guó)家行為。由此,憲章對(duì)安理會(huì)為履行上述職能而通過(guò)決議進(jìn)行造法的“隱含的授權(quán)”,即主要體現(xiàn)在其第7章第39條和第41條的規(guī)定中。根據(jù)《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39條規(guī)定,除有權(quán)認(rèn)定一項(xiàng)行為是否構(gòu)成“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者侵略行為”外,安理會(huì)還得以通過(guò)兩種途徑履行其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能,包括提出建議或者采取憲章第41、42條規(guī)定的方式,即采取武力之外的方式或者在武力之外的方式力所不及的情況下采取武力方式。對(duì)此,盡管上述憲章第41條就何為“武力之外的方式”進(jìn)行了列舉,但由于該條文本使用的措辭是“包括”,即表明安理會(huì)有權(quán)采取的武力之外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所列舉的各項(xiàng)方式。因此,誠(chéng)如前南國(guó)際刑事法庭上訴分庭在其判決中指出的,《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41條實(shí)則僅是消極地規(guī)定了安理會(huì)不得在憲章第42條規(guī)定的情況外采取武力方式,而并未就安理會(huì)有權(quán)采取的武力之外的方式作出任何實(shí)質(zhì)性的限制。換言之,根據(jù)該條規(guī)定,安理會(huì)有權(quán)采取除武力方式外的其他任何方式以應(yīng)對(duì)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17〕Prosecutor v.Dusco Tadic',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IT-94-1-AR72,[1995].。因此,根據(jù)上述憲章第41條的規(guī)定,除了被動(dòng)地在事后對(duì)具體個(gè)案作出應(yīng)對(duì)或者對(duì)特定國(guó)家采取措施外,安理會(huì)還被默示地賦予了通過(guò)前瞻性的決議立法以履行其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能的權(quán)力〔18〕See Dapo Akande,Tim Murithi,Tarcisio Gazzini,Nikolaos Tsagourias and Enrico Milano,“Old Questions and New Challenges for the U.N.Security Council:the Ro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light of the Charter's Refor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vol.V(2007):28.。
事實(shí)上,不僅抽象的決議造法作為安理會(huì)有權(quán)采取的一項(xiàng)“武力之外的方式”得到了《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的“隱含的授權(quán)”,前述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情形所表現(xiàn)出的決議性質(zhì)的普遍性和決議內(nèi)容創(chuàng)設(shè)了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的特性,在憲章中亦同樣有相應(yīng)的依據(jù):一方面,由于根據(jù)憲章第41條的規(guī)定,安理會(huì)有權(quán)促請(qǐng)聯(lián)合國(guó)全體成員國(guó)執(zhí)行其關(guān)于采取武力之外的方式的決議,并且,該條規(guī)定亦未限制決議所針對(duì)的情勢(shì),因此,安理會(huì)采取決議造法的方式所通過(guò)的造法性決議便可以適用于一般情勢(shì)和全體成員國(guó)。另一方面,根據(jù)《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24條的規(guī)定,安理會(huì)在行使其為履行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職能而被賦予的特定權(quán)力時(shí),應(yīng)當(dāng)遵守聯(lián)合國(guó)的宗旨和原則。由此,從規(guī)定了聯(lián)合國(guó)宗旨和原則的憲章第1、2條的文本看,由于第1條第1款已經(jīng)明確規(guī)定〔19〕1945年《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1條第1款規(guī)定:“一、維持國(guó)際和平及安全;并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duì)于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guó)際法之原則,調(diào)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guó)際爭(zhēng)端或情勢(shì)。”這是聯(lián)合國(guó)的宗旨。,安理會(huì)僅在“調(diào)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guó)際爭(zhēng)端或情勢(shì)”時(shí)須依照正義和國(guó)際法原則行事,而在“防止且消除對(duì)于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時(shí)則不受這一約束〔20〕簡(jiǎn)基松.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行為之定性分析與完善建言[J].法學(xué),2009,(10).,從而使得當(dāng)安理會(huì)根據(jù)憲章第七章“對(duì)于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yīng)付辦法”中的條文規(guī)定作出一項(xiàng)決議時(shí),并無(wú)須對(duì)該項(xiàng)決議是否與既有的國(guó)際法原則相符合進(jìn)行考察〔21〕See Leland M.Goodrich et al,“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Commentary and Documen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267-269.。
因此,當(dāng)安理會(huì)根據(jù)憲章第41條的規(guī)定進(jìn)行決議造法時(shí),即便其在決議中創(chuàng)設(shè)了超出既存國(guó)際法的、與既有的國(guó)際法原則不相符合的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亦并不構(gòu)成對(duì)聯(lián)合國(guó)宗旨和原則的違反〔22〕此處,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對(duì)上述憲章第1條第1款規(guī)定的文本含義作不同的理解,即認(rèn)為安理會(huì)在“防止且消除對(duì)于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時(shí)同樣應(yīng)當(dāng)受到正義和國(guó)際法原則的約束,由于所謂的“國(guó)際法原則”并不等同于由國(guó)際條約、習(xí)慣國(guó)際法或者一般法律原則確立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因此,即便安理會(huì)在根據(jù)憲章第41條進(jìn)行決議造法時(shí)須依照國(guó)際法原則,亦并不意味著決議的內(nèi)容必須以既有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為限。。
其次,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實(shí)踐基于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客觀需要而具有正當(dāng)性。誠(chéng)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立法者應(yīng)當(dāng)將自己看作一個(gè)自然科學(xué)家。他不是在創(chuàng)造法律,不是在發(fā)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2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7.但凡立法均應(yīng)當(dāng)僅是對(duì)客觀實(shí)際的一種反映,是根據(jù)客觀需要將事物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表現(xiàn)在法律中,而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亦概莫能外。由此,在前述《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相關(guān)規(guī)定的“隱含的授權(quán)”為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提供了法律依據(jù)的同時(shí),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客觀需要亦為其正當(dāng)性提供了支持。
第一,正如1992年1月31日安理會(huì)主席聲明指出的,“國(guó)家間的戰(zhàn)爭(zhēng)和武裝沖突的消退并不能保障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人權(quán)和生態(tài)領(lǐng)域中的各項(xiàng)非軍事化的不穩(wěn)定因素已經(jīng)成為了對(duì)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新的威脅。聯(lián)合國(guó)全體成員國(guó)均應(yīng)當(dāng)通力合作,通過(guò)安理會(huì),對(duì)上述問(wèn)題予以最優(yōu)先的解決。”〔24〕Note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UN Document S/23500),31 January 1992.在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安理會(huì)所須應(yīng)對(duì)的是包括恐怖主義、核生化武器擴(kuò)散等在內(nèi)的非傳統(tǒng)的威脅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問(wèn)題。而由于如前訴述地,傳統(tǒng)的針對(duì)特定情勢(shì)的、以特定國(guó)家為對(duì)象的安理會(huì)決議并不適用于上述實(shí)施主體為非國(guó)家行為者或者威脅的后果并不發(fā)生在某一或某些特定的國(guó)家境內(nèi)的問(wèn)題,并且,基于既有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所采取的干涉或者制裁措施亦無(wú)法切實(shí)有效地解決上述問(wèn)題,因此,安理會(huì)在決議中創(chuàng)設(shè)超出既存國(guó)際法的、適用于一般情勢(shì)和全體成員國(guó)的新的國(guó)際法規(guī)則,是符合防止和消除當(dāng)前威脅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上述新問(wèn)題的客觀需要的。
第二,盡管如前所述地,針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在國(guó)內(nèi)外學(xué)界中均是持否定或者懷疑態(tài)度的學(xué)者占到多數(shù)。但在實(shí)踐中,聯(lián)合國(guó)各成員國(guó)對(duì)于安理會(huì)通過(guò)的各項(xiàng)造法性決議卻是在經(jīng)歷了最初的質(zhì)疑之后最終轉(zhuǎn)變?yōu)槠毡榈慕邮堋@纾谇笆龅?540號(hào)決議通過(guò)之初,德國(guó)就曾質(zhì)疑安理會(huì)作為一個(gè)代表性不足、無(wú)須自負(fù)其責(zé)并且不受任何司法約束的政治性機(jī)構(gòu),是否有權(quán)在決議中創(chuàng)設(shè)對(duì)整個(gè)國(guó)際社會(huì)具有深遠(yuǎn)意義的法律規(guī)則〔25〕Statement by Gunther Pleuger,Representative of Germany,to the United Nations,at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eform of the Security Council,U.N.。然而,在經(jīng)過(guò)了數(shù)年的實(shí)踐之后,誠(chéng)如第1540號(hào)決議委員會(huì)主席Jorge Urbina指出的,最初對(duì)于該決議的合法性以及決議委員會(huì)存在的必要性的質(zhì)疑已經(jīng)全部消除了,并且,該決議正在得到越來(lái)越多的聯(lián)合國(guó)成員國(guó)的理解和認(rèn)可〔26〕1540 Committee,Briefings by Chairman Ambassador Jorge Urbina,14 December 2009.。由此,聯(lián)合國(guó)各成員國(guó)對(duì)于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實(shí)踐情形的接受,實(shí)際上就是認(rèn)可了安理會(huì)為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而通過(guò)決議進(jìn)行造法的正當(dāng)性。
三、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與國(guó)際法基本制度相悖
應(yīng)當(dāng)指出,基于《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相關(guān)規(guī)定的“隱含的授權(quán)”和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的客觀需要,雖然使得前述安理會(huì)既有的決議造法實(shí)踐,安理會(huì)業(yè)已通過(guò)的造法性決議具備了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但卻并不意味著安理會(huì)可任意地通過(guò)決議進(jìn)行造法。事實(shí)上,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行為本身尚且存在諸多的不足和缺陷,并且有違國(guó)際法的基本制度。
眾所周知,國(guó)際社會(huì)并不存在凌駕于主權(quán)國(guó)家之上的立法機(jī)關(guān),因此,主權(quán)國(guó)家既是國(guó)際法的主體,同時(shí)亦是國(guó)際造法的主體,而普遍適用于各主權(quán)國(guó)家的國(guó)際法本身實(shí)則亦是由各國(guó)在共同同意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設(shè)而成的〔27〕[美]路易斯·亨金.國(guó)際法:政治與價(jià)值[M].張乃根等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36.。國(guó)際法是主權(quán)國(guó)家通過(guò)協(xié)議的方式形成的,這是國(guó)際條約;或者是通過(guò)國(guó)家的長(zhǎng)期實(shí)踐形成通例之證明而確立的,這是國(guó)際習(xí)慣。在國(guó)際法上,任何人、任何機(jī)構(gòu)均沒(méi)有國(guó)際造法的權(quán)力,并且,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亦顯然不符合國(guó)際造法的主體和程序要求。
其一,盡管《聯(lián)合國(guó)憲章》作為聯(lián)合國(guó)的組織約章可以被視為是對(duì)各成員國(guó)協(xié)調(diào)一致的國(guó)家意志的體現(xiàn)〔28〕黃瑤.國(guó)際組織決議的法律效力探源[J].政治與法律,2001,(5).,并且,憲章中的部分規(guī)定亦確實(shí)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作出了“隱含的授權(quán)”,但是,這至多是體現(xiàn)了聯(lián)合國(guó)各成員國(guó)所具有的執(zhí)行安理會(huì)造法性決議的意志,而并不能夠表明作為決議造法的主體的安理會(huì)即代表了上述各國(guó)在決議造法的過(guò)程中的意志。根據(jù)憲章第27條第3款的規(guī)定,安理會(huì)關(guān)于非程序性事項(xiàng)的決議,僅需包括五個(gè)常任理事國(guó)在內(nèi)的九個(gè)理事國(guó)同意即可通過(guò),而無(wú)須聽取其他聯(lián)合國(guó)成員國(guó)的意見,并且,即便與決議有利害關(guān)系的其他成員國(guó)得以參與安理會(huì)的討論,其亦仍然不享有對(duì)該決議的表決權(quán)〔29〕1945年《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31條、第32條。。因此,除安理會(huì)理事國(guó)外的其他聯(lián)合國(guó)成員國(guó)實(shí)則均僅是被動(dòng)地接受由安理會(huì)獨(dú)斷地通過(guò)的造法性決議,而并未能夠經(jīng)由安理會(huì)在決議造法的過(guò)程中主動(dòng)地表達(dá)其意志。因此,由于安理會(huì)并未能夠代表占多數(shù)的其他聯(lián)合國(guó)成員國(guó)的意志,并非適格的國(guó)際法造法主體,因此,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亦就無(wú)法符合國(guó)際造法的主體要求。
其二,就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而言,盡管《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28條至第32條已經(jīng)就安理會(huì)決議的通過(guò)程序作出了規(guī)定,但上述規(guī)定卻僅是廣泛地適用于任何性質(zhì)、任何內(nèi)容的安理會(huì)決議的通過(guò)程序的一般規(guī)則,而并非具體適用于造法性決議的通過(guò)程序的專門規(guī)則;并且,其在實(shí)踐中亦并未能夠起到有效地規(guī)范安理會(huì)決議的通過(guò)程序的作用。對(duì)此,有學(xué)者即指出,部分安理會(huì)決議實(shí)則是由少數(shù)理事國(guó)在安理會(huì)會(huì)議之外作出的,并且未做任何相關(guān)的記錄,從而使得決議通過(guò)程序的合法性令人堪憂〔30〕See Anthony Aust,“The Procedure and Practic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oday,”in R.J.Dupuy(ed.)Development of the Ro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Colloque,(1993),365.。此外,盡管在通過(guò)前述第1540號(hào)決議的過(guò)程中,安理會(huì)除由15個(gè)理事國(guó)進(jìn)行了持續(xù)數(shù)月的磋商外,還在磋商的最后階段舉行了兩次公開會(huì)議,邀請(qǐng)30個(gè)聯(lián)合國(guó)成員國(guó)共同與會(huì)進(jìn)行磋商,并且由此得到了國(guó)際社會(huì)對(duì)于該決議的通過(guò)程序的肯定〔31〕See Vesselin Popovski,“The Legislative Ro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s Thematic Resolutions,”in Vesselin Popovski and Trudy Fraser(eds.)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4),5.。但是,這終究亦只是安理會(huì)在個(gè)案中所采取的實(shí)踐做法,而并非可以直接適用于此后所有的安理會(huì)造法性決議的通過(guò)程序的具體規(guī)則。因此,基于具體的程序規(guī)則的缺失,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便同樣無(wú)法符合國(guó)際造法的程序要求。
四、國(guó)際法院缺乏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制約
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還缺乏國(guó)際法院通過(guò)司法審查對(duì)其加以必要的制約。誠(chéng)然,作為聯(lián)合國(guó)體系內(nèi)的首要司法機(jī)關(guān),國(guó)際法院一直被學(xué)界認(rèn)為是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進(jìn)行司法審查的最為恰當(dāng)?shù)闹黧w〔32〕See Jan Wouters and Jed Odermatt,“Reflections on the Law-making Pow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in Vesselin Popovski and Trudy Fraser(eds.)The Security Council as Global Legislato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14),85.;并且,在與安理會(huì)第748號(hào)決議相關(guān)的“洛克比空難案”中,多位國(guó)際法院法官亦在其單獨(dú)意見中表達(dá)了應(yīng)當(dāng)由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的權(quán)力進(jìn)行規(guī)范和限制的觀點(diǎn),例如,Judge Shahabuddeen即指出,倘若安理會(huì)的權(quán)力應(yīng)當(dāng)受到范圍的約束,那么,除了國(guó)家法院之外,便沒(méi)有其他機(jī)構(gòu)能夠?qū)Π怖頃?huì)的權(quán)力范圍作出界定了〔33〕ICJ Reports,Lockerbie(Provisional measures,Order of 14 April 1992):140-142.。然而,事實(shí)上,國(guó)際法院卻并不能夠?qū)嶋H地享有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的司法審查權(quán)。
其一,無(wú)論是《聯(lián)合國(guó)憲章》還是《國(guó)際法院規(guī)約》,均未就安理會(huì)與國(guó)際法院的關(guān)系問(wèn)題予以明確,并且,上述兩項(xiàng)國(guó)際法律文件亦均未明文賦予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進(jìn)行司法控制或者司法審查的權(quán)力。盡管有學(xué)者基于《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96條第1款的規(guī)定進(jìn)而提出,國(guó)際法院可以在被請(qǐng)求對(duì)一項(xiàng)安理會(huì)決議的法律效力作出咨詢意見時(shí),通過(guò)對(duì)該決議的合法性的認(rèn)定而間接地對(duì)其進(jìn)行司法審查〔34〕See Dapo Akande,“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Is there Room for Judicial Control of Decisions of the Political Org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6(1997):309,331.,但是,從該條款規(guī)定的文本含義看〔35〕《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guī)定:“大會(huì)或安全理事會(huì)對(duì)于任何法律問(wèn)題得請(qǐng)國(guó)際法院發(fā)表咨詢意見。”,國(guó)際法院只有在安理會(huì)提出相應(yīng)的請(qǐng)求的情況下方才得以被動(dòng)地作出咨詢意見,而并不能夠主動(dòng)地介入安理會(huì)正在處理的“任何法律問(wèn)題”。而自國(guó)際法院成立至今的70年間,安理會(huì)亦僅有一次地就納米比亞的國(guó)際地位問(wèn)題向國(guó)際法院提出過(guò)作出咨詢意見的請(qǐng)求〔36〕See D.W.Bowett,“Judi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n Hazel Fox(ed.)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1997),74.。由此,國(guó)際法院據(jù)以實(shí)現(xiàn)其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的司法審查權(quán)并無(wú)國(guó)際法依據(jù)。
其二,從國(guó)際法院實(shí)踐的角度看,盡管有學(xué)者提出,由于在國(guó)內(nèi)法實(shí)踐中,即便并無(wú)明確的憲法授權(quán),國(guó)內(nèi)高等法院亦同樣可以行使司法審查權(quán),因此,前述《聯(lián)合國(guó)憲章》和《國(guó)際法院規(guī)約》中的明文規(guī)定的缺失,并不影響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進(jìn)行司法審查〔37〕See José Alvarez,“Judging the Security Council,”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0(1996):81-99.,但是,實(shí)踐中,國(guó)際法院對(duì)其自身在并無(wú)法律依據(jù)的情況下,是否享有針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的司法審查權(quán)所持的態(tài)度,卻是更加接近于否定的——在“洛克比空難案”中,國(guó)際法院在最終的判決意見中指出,“法院并不享有否決或者排除安理會(huì)決議的權(quán)力……法院曾經(jīng)不止一次地否認(rèn)其享有司法審查權(quán)……從舊金山制憲會(huì)議達(dá)成的各項(xiàng)決定的宗旨看,憲章的起草者們并沒(méi)有賦予法院以司法審查的權(quán)力的意圖。”〔38〕ICJ Reports,Lockerbie(Summary of the Judgment,27 February 1998):21.同樣的觀點(diǎn)還出現(xiàn)在關(guān)于納米比亞的國(guó)際地位問(wèn)題的咨詢意見中,即“法院并不享有對(duì)聯(lián)合國(guó)機(jī)構(gòu)作出的決議進(jìn)行司法審查或者申訴的權(quán)力。”〔39〕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South West Africa)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1970),ICJ Advisory Opinion,(21 June 1971):16.而在“某些費(fèi)用案”的咨詢意見中,國(guó)際法院則更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在聯(lián)合國(guó)體系內(nèi)存在司法審查程序:“盡管在國(guó)內(nèi)法律體系中,通常存在特定的程序?qū)σ豁?xiàng)立法或者政府行為的合法性進(jìn)行認(rèn)定,但是,在聯(lián)合國(guó)框架下卻并不存在諸如上述的程序”〔40〕Certain Expen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Article 17,paragraph 2,of the Charter),ICJ Advisory Opinion,(29 July 1962):168.。可見,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進(jìn)行司法審查的實(shí)踐還遠(yuǎn)未形成。
誠(chéng)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唯有對(duì)現(xiàn)行《聯(lián)合國(guó)憲章》進(jìn)行修改,加入明文的授權(quán)規(guī)定,方才能夠使國(guó)際法院得以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進(jìn)行司法審查;但是,根據(jù)憲章第108條的規(guī)定〔41〕《聯(lián)合國(guó)憲章》第108條規(guī)定:“本憲章之修正案經(jīng)大會(huì)會(huì)員國(guó)三分之二表決并由聯(lián)合國(guó)會(huì)員國(guó)三分之二、包括安全理事會(huì)全體常任理事國(guó),各依其憲法程序批準(zhǔn)后,對(duì)于聯(lián)合國(guó)所有會(huì)員國(guó)發(fā)生效力。”,修改憲章所須滿足的條件相當(dāng)嚴(yán)格,尤其是其中關(guān)于必須經(jīng)安理會(huì)全體常任理事國(guó)同意的要求,在實(shí)踐中更是難以滿足,因此,通過(guò)修改憲章以實(shí)現(xiàn)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的司法審查權(quán)絕非易事〔42〕王秀梅,李小玲.國(guó)際法院對(duì)安理會(huì)的司法審查權(quán)芻議——以國(guó)際組織憲政為視角[J].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1,(2).,而這亦就使得國(guó)際法院目前并無(wú)法切實(shí)地通過(guò)司法審查對(duì)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加以制約。
五、結(jié)論
綜上所述,對(duì)業(yè)已被通過(guò)的造法性決議,即既有的決議造法實(shí)踐的合法性和正當(dāng)性的肯定,并不能夠使安理會(huì)便由此成為得以任意地通過(guò)決議進(jìn)行造法的所謂“國(guó)際造法者”。由于在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以保障國(guó)際法治的同時(shí),安理會(huì)自身亦應(yīng)當(dāng)服從于國(guó)際法治〔43〕趙健文.聯(lián)合國(guó)安理會(huì)在國(guó)際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J].吉林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51(4).,因此,在為安理會(huì)決議造法制定了明確的法律規(guī)范以使其能夠符合國(guó)際法治的要求之前,決議造法應(yīng)當(dāng)僅是安理會(huì)為維護(hù)國(guó)際和平與安全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并且應(yīng)當(dāng)受到嚴(yán)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