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以“仁政”為核心的治國(guó)思想解析*
王成 孫菱
(山東大學(xué),濟(jì)南 250100)
宋濂以“仁政”為核心的治國(guó)思想解析*
王成 孫菱
(山東大學(xué),濟(jì)南 250100)
宋濂治國(guó)思想的價(jià)值基礎(chǔ)是以民為本,他認(rèn)為君主之權(quán)來(lái)自民授,治國(guó)理政的著力點(diǎn)應(yīng)當(dāng)放在“安民”,在天下財(cái)富有限的情況下,富國(guó)應(yīng)當(dāng)為富民讓路,民富與君富、國(guó)富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在解決了富民、養(yǎng)民等民生問(wèn)題之后,必須對(duì)百姓進(jìn)行教化,教之以詩(shī)書(shū)禮儀。對(duì)百姓要施以仁政,推行德政,讓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國(guó)家各項(xiàng)政策安排;刑罰只是作為治國(guó)的輔助性手段而存在。官員是國(guó)家治理、為民服務(wù)的“公仆”。官與民是平等的,官員要學(xué)而為民。對(duì)于治國(guó)人才,宋濂主張要倍加愛(ài)惜,不拘一格加以任用。
宋濂;民本;仁治;設(shè)官為民;任賢以公
宋濂(1310-1381年),明代思想家、文學(xué)家。生于浙江金華一個(gè)貧寒家庭,字景濂,號(hào)“潛溪”,“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shū)卷,于學(xué)無(wú)所不通”①。元順帝曾詔命翰林院編修,宋濂固辭不就。至正十九年(1359年),應(yīng)朱元璋之召出任寧越府(后更名為金華府)五經(jīng)師,頗受朱元璋寵信。明朝建立后,尊為太子朱標(biāo)之師,累官至翰林院學(xué)士承旨、知制誥,《元史》撰修總裁。朱元璋贊之為“起草莽列侍從,為開(kāi)國(guó)文臣之首”②。后受牽于胡惟庸案,全家流放茂州(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病死于流放途中。宋濂在文學(xué)、哲學(xué)、政治等領(lǐng)域頗多建樹(shù),《明史》本傳說(shuō):大明“一代禮樂(lè)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宋濂治國(guó)思想的價(jià)值基礎(chǔ)是民本,核心是“仁政”,其理論主張主要見(jiàn)于《宋學(xué)士文集》、《宋文憲公全集》以及《明史》相關(guān)紀(jì)傳中。
一、仁以致治的治國(guó)主張
元朝末年,宋濂曾經(jīng)提出“君權(quán)民授”說(shuō),這在君權(quán)神授、君權(quán)至上的政治氛圍中頗顯難能可貴。貴就貴在,此說(shuō)不僅僅需要政治勇氣,更離不開(kāi)睿智的洞察與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動(dòng)力的深刻體悟。他認(rèn)為:“有民斯有國(guó),有國(guó)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dú)夫耳,可不畏哉!”③可見(jiàn)在宋濂的政治邏輯之中,先有黎民百姓而后才有國(guó)家,先有國(guó)家而后才有人君。人君之權(quán)來(lái)自黎民百姓,并非上天賜予。如果說(shuō)有天,那么,百姓就是人君的“天”。何人可為人君完全由百姓決定。百姓立之就是人君,棄之就是“獨(dú)夫”。人君要保其君位,就要以仁義治國(guó)。在宋濂奉命主修的《元史》中有這樣一段話很能代表宋濂以“仁義”治國(guó)的政治主張:“自古國(guó)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后為政者得以盡其愛(ài)民之術(shù),而良民興焉。班固有曰:‘漢興,與民休息,凡是簡(jiǎn)易,禁網(wǎng)疏闊,以寬厚清凈為天下先,故文景以后循吏輩出。’其言蓋識(shí)當(dāng)時(shí)之治體矣。”④其仁以致治的治國(guó)思想具體包括下述內(nèi)容:
第一,憫安斯民。宋濂繼承傳統(tǒng)民本思想,認(rèn)為“國(guó)以民為本”⑤,治國(guó)理政的著力點(diǎn)應(yīng)當(dāng)放在“安民”。“安民”的第一步是“得民”,要點(diǎn)則在得民心,順民意,體民情,“得天下以人心為本”⑥。得民心,政權(quán)的合法性就有了堅(jiān)固的基石;順民意,則和諧的治理局面自然生成;體民情,理政實(shí)踐就更加接洽地氣。元朝以民族壓迫、暴力威脅與摧殘為手段的治國(guó)實(shí)踐盡喪民心,即便擁有橫掃歐亞大陸的鐵騎,也阻止不了江山易手,元帝被迫退回漠北的歷史進(jìn)程。短短幾十年,元政權(quán)從勃興到灰飛煙滅,轉(zhuǎn)瞬即逝。這種政權(quán)的迅速易手,正是民眾之于社會(huì)前進(jìn)動(dòng)力的生動(dòng)體現(xiàn)。不過(guò),改朝換代不可避免地給百姓造成了不盡的災(zāi)難。面對(duì)元末明初的大規(guī)模征伐,面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給百姓造成的災(zāi)難,宋濂表現(xiàn)出深切的同情。應(yīng)該引起注意的是,宋濂對(duì)農(nóng)民的生存狀況關(guān)注度更高。宋濂敏銳地發(fā)現(xiàn),同為百姓,農(nóng)民這一群體在生產(chǎn)、生活方面承受的痛苦較之其他群體尤為刻骨,“民之至苦,莫甚于農(nóng)”。這種情況的存在,導(dǎo)致農(nóng)村最易成為官民矛盾激化、社會(huì)動(dòng)蕩的潛在危險(xiǎn)區(qū)域。古代的國(guó)家治理中,農(nóng)村恰恰是皇權(quán)不及或是國(guó)家治理的末梢之地,社會(huì)控制力的單薄與基層吏員的短視甚至借落實(shí)國(guó)家稅賦之名肆意攤派胡作非為,極易造成革命的火花在各種失去控制的勢(shì)力碰撞之中點(diǎn)燃。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shí),宋濂提出:“有國(guó)家者,宜思憫之,安之。”⑦他認(rèn)為:“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⑧這個(gè)“道”可保人君維持久遠(yuǎn)的統(tǒng)治,否則“無(wú)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⑨。一次,宋濂為朱元璋講解“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cái),有財(cái)此有用。德者本也,財(cái)者末也。外本內(nèi)末,爭(zhēng)民施奪。是故財(cái)聚則民散,財(cái)散則民聚。”⑩換言之,如果治國(guó)者耽于聚斂財(cái)富,則民心必失;藏富于民,則聚攏民心,國(guó)勢(shì)日隆。朱元璋深有所悟,說(shuō):“人者,國(guó)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guó)固。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cái),自然之理也。”(11)可見(jiàn)宋濂對(duì)朱元璋治國(guó)思想影響之深。
第二,富國(guó)先富民。宋濂是孔子富民思想的堅(jiān)定繼承者。孔子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12)充分肯定了百姓之于物質(zhì)生活需求的正當(dāng)性。孔子甚至深刻地指出:在追求物質(zhì)利益問(wèn)題上,君子和小人是別無(wú)二致的。他曾經(jīng)有過(guò)這樣幾段言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3);“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14)表達(dá)了孔子“求富”的強(qiáng)烈愿望。縱觀歷史,卻讓人頗感遺憾,歷朝歷代總是存在這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們一方面嘴里喊著以民為本,讓利于民、造福于民,讓百姓有恒產(chǎn)以有恒心,及至提出“愛(ài)民如子”。另一方面,這些人又固執(zhí)地認(rèn)為,富國(guó)與富民是一對(duì)矛盾。在天下財(cái)富總量有限的情況下,富民必然削弱富國(guó)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甚至狹隘地認(rèn)為,民富則國(guó)貧。還有些人不顧國(guó)家安危,私下里打著小算盤,在君主面前嘴里喊著民富國(guó)貧,萬(wàn)萬(wàn)不可落實(shí)民富的治國(guó)策略,似乎為君計(jì),背地里是擔(dān)心民富影響官富,民富“降低”了官員們的生活質(zhì)量,民富影響官員們肆意揮霍民脂民膏的敗國(guó)丑行。在治國(guó)精英集團(tuán)中,宋濂的看法迥異于民富必須為國(guó)富、官富讓路的聒噪。他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經(jīng)過(guò)元亡明興的長(zhǎng)年戰(zhàn)爭(zhēng),百姓的生存狀況已經(jīng)非常惡劣,為尋求生的希望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流亡各地。這不僅是百姓的苦難,更是治國(guó)者無(wú)能的體現(xiàn),是治國(guó)者的奇恥大辱。為迅速解民眾于倒懸,宋濂提出富民思想。他認(rèn)為國(guó)家治理中,國(guó)富須以民富為先,民富與君富、國(guó)富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天下得治,財(cái)富增加,民眾富裕,整個(gè)國(guó)家呈現(xiàn)良性運(yùn)行狀態(tài),怎么可能出現(xiàn)唯獨(dú)治國(guó)者貧窮的局面呢?“民富則君不至獨(dú)貧”(15)。就此先賢們已經(jīng)樹(shù)立了理論與實(shí)踐的榜樣,如孟子認(rèn)為十稅一即為王者之治。大漢王朝推行三十稅一,不僅君、國(guó)未貧,卻締造了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個(gè)真正意義上的大國(guó)盛世。及至今日,國(guó)人依然津津樂(lè)道于漢唐盛世。宋濂指出,人君在國(guó)家治理中居于主導(dǎo)地位,是萬(wàn)民之所依,民眾福祉實(shí)現(xiàn)的依賴性力量。作為國(guó)家治理主導(dǎo)者的人君如果借助手中權(quán)力追求獨(dú)富,暴斂財(cái)富,榨民過(guò)度是非常危險(xiǎn)的,“民貧則君何能獨(dú)富?”(16)況且,“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17)這樣的富是無(wú)道之富,曾經(jīng)受到孔子嚴(yán)厲的批判。正確的選擇是“捐利于民”,這是“興邦之要道”(18)。宋濂的富民思想很得朱元璋賞識(shí)。這位平民皇帝認(rèn)為,“大亂未平,民多轉(zhuǎn)徙”(19),苦不堪言。立國(guó)不久的王朝百?gòu)U待興,“軍國(guó)之費(fèi)所資不少,皆出于民”(20)。民眾已經(jīng)為立國(guó)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所以,進(jìn)入承平建設(shè)時(shí)期,能夠讓百姓“衣食給足”,“為治之先務(wù),立國(guó)之根本”。(21)反之,如果不能讓百姓安心于發(fā)展生產(chǎn)獲得富足的生活條件,“不得盡力田畝,則國(guó)家資用何所賴焉?”(22)朱元璋與宋濂君臣相似的富民主張,對(duì)于明朝前期實(shí)行恤民政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
第三,重教化民思想。孔子及其后世儒家與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政治家是主張以文教化百姓的。雖然堅(jiān)持孔子“愚民”說(shuō)的學(xué)者頗多,但總體講論據(jù)并不十分充分。即便是其強(qiáng)有力的證據(jù)——“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3)——也因標(biāo)點(diǎn)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分歧。且不說(shuō)孔子大興民間教育,有教無(wú)類,弟子三千(其中包括部分來(lái)自社會(huì)底層的人士,這些人是無(wú)可爭(zhēng)辯的“民”),其在衛(wèi)國(guó)與冉有的一段對(duì)話亦為明證:“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4)由此不難推斷,孔子是主張?jiān)跐M足了民眾基本生存條件之后予以教化的。深得儒家思想精髓、并以繼承儒家道統(tǒng)為己任的宋濂更是注重教化百姓的重要性。他指出:“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yǎng)與教而已,養(yǎng)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25)此說(shuō)與孔子和冉有對(duì)話中傳遞的富而后教思想顯然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在告誡治理天下國(guó)家者,要天下太平,確保國(guó)祚長(zhǎng)久,在解決了富民、養(yǎng)民等民生問(wèn)題之后,必須要“廣設(shè)學(xué)校”,對(duì)百姓進(jìn)行教化,教之以詩(shī)書(shū)禮儀。否則,僅僅停留在物質(zhì)層面的養(yǎng)而缺乏符合“道”之要求的教化,百姓最終會(huì)淪為暴民。暴民由于掌握了一定知識(shí),而又缺乏“道”的引導(dǎo),最容易做出破壞社會(huì)治理規(guī)則的舉動(dòng),走上邪路,這是國(guó)家動(dòng)蕩的開(kāi)始。要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必須使“海內(nèi)之民,皆能沾沐禮儀”(26),“以學(xué)校治民,則禍亂不興”。(27)在宋濂看來(lái),“政令能禁民為非”(28),但不能讓百姓明辨事理,心甘情愿地遠(yuǎn)離是非,自覺(jué)地免予為非作歹,亦即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wú)恥。”(29)宋濂指出:“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為非,人倫藉之以厚,風(fēng)俗因之可移,顧有出于政令之上者,豈細(xì)故也哉!”(30)教化的具體內(nèi)容則是倫理綱常,“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31)。同時(shí),宋濂主張通過(guò)《六經(jīng)》教育,幫助民眾樹(shù)立忠心不二,精忠報(bào)國(guó)的思想,“說(shuō)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shuō)事莫辨乎《書(shū)》,由吾心政之府也;說(shuō)志莫辨乎《詩(shī)》,由吾心統(tǒng)性情也;說(shuō)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shuō)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導(dǎo)民莫過(guò)乎《樂(lè)》,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wú)二心,《六經(jīng)》無(wú)二理”。(32)如此,“則邪說(shuō)不入”(33),百姓就可以遵禮樂(lè)道,發(fā)自內(nèi)心接受國(guó)家的制度安排了。
第四,德主刑輔的治理思想。儒家主張德治,卻不一概地反對(duì)法治與刑罰。孔子治理中都時(shí)的措施就是德主刑輔。只是由于孔子推行德治效果甚佳,其輔助手段——刑——幾乎沒(méi)有派上用場(chǎng)。宋濂主張?jiān)谥螄?guó)中推行德主刑輔的策略。他認(rèn)為二者功能各異,“德以懷之,刑以威之”。(34)意即對(duì)百姓施以仁政,廣布恩澤是帝王之道。推行德政,可以讓百姓心甘情愿地接受國(guó)家各項(xiàng)政策要求,自覺(jué)地將國(guó)家治理的要求轉(zhuǎn)化成自己行為約束的準(zhǔn)繩。刑罰是作為治國(guó)的輔助性手段而存在,旨在對(duì)某些冥頑不化者進(jìn)行威懾,使之改變既有的錯(cuò)誤思想與行為。由于刑罰工具更多的是借助暴力手段、甚至殘酷刑罰使百姓產(chǎn)生恐懼,從而不得不接受國(guó)家律令與規(guī)則。一旦條件具備,比如國(guó)家機(jī)器的反應(yīng)能力、控制能力下降、法治機(jī)器鞭長(zhǎng)莫及之時(shí)等等,他們就會(huì)掙脫刑與法的繩索羈絆,演變成破壞國(guó)家政治秩序的一支力量,甚或如火山突然噴發(fā),迅速摧毀既有王朝的根基,直至推動(dòng)改朝換代的發(fā)生。況且刑之愈嚴(yán),其反彈愈烈,破壞愈強(qiáng),對(duì)國(guó)家造成的沖擊就愈是難以估量。所以,治理國(guó)家應(yīng)該一手興德一手持法,德刑并舉。“刑罰非所先也”。(35)在宋濂的治國(guó)理念中,刑罰始終應(yīng)該放在次席。宋濂不厭其煩地指出:“鷙鳥(niǎo)之揚(yáng)揚(yáng),不如威鳳之翔翔;狻猊之疆疆,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wù)德則已,茍有德焉,又何僉壬之不革行哉!僉壬革行,正氣之復(fù),正道之行也。”(36)顯然,刑與法固然有其威嚴(yán)、威勢(shì),對(duì)民眾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威懾,但通過(guò)德治能夠使百姓真心向善,使國(guó)家長(zhǎng)治久安。他說(shuō):“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37)儒家所推崇的上古三代,正是將仁義作為基本國(guó)策,才經(jīng)歷了長(zhǎng)久的國(guó)祚,三代總計(jì)長(zhǎng)達(dá)1800多年,約占中國(guó)古代文明歷程的46%時(shí)長(zhǎng)。宋濂還將湯、紂這一對(duì)正反面典型放在一起進(jìn)行了對(duì)比,指出:“成湯務(wù)德,帝命式于九圍;紂為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身亡國(guó)破為萬(wàn)世笑,非不幸也,宜也。”(38)“務(wù)德”與“失道”兩種不同的治國(guó)路徑選擇在商王朝這個(gè)政治舞臺(tái)上分別進(jìn)行了實(shí)踐,結(jié)果是將兩個(gè)同樣具備非凡才能的人——湯、紂——妝扮成為截然不同的政治角色——圣王與暴君。宋濂的結(jié)論是“以一人治天下”乃是自古皆然的公理,“未聞以天下奉一人”。(39)顯然,宋濂心目中的理想執(zhí)政者是代表上天來(lái)治理天下的,并非上天設(shè)置天下來(lái)為執(zhí)政者服務(wù)。所以,“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40)。厲行仁政,贏得民心,國(guó)運(yùn)長(zhǎng)久;推行暴政,殘害黎民,必失天下。刑罰只能作為治國(guó)的輔助手段不可濫用。“法乃司命,懸于重輕,脫不獲于簡(jiǎn)孚,將枉物而傷生”。(41)一次,朱元璋要將背叛自己的侄子朱文正處死,宋濂勸說(shuō):“文正固當(dāng)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諸遠(yuǎn)地善矣。”(42)于是,朱元璋將朱文正軟禁于桐城,直至終老。這是宋濂德主刑輔治國(guó)思想在大明王朝的一次有益嘗試。
二、設(shè)官為民思想
宋濂出身清苦,對(duì)元代民族歧視政策下官民關(guān)系的扭曲設(shè)計(jì)有著深邃的思考,結(jié)合儒家仁政愛(ài)民學(xué)說(shuō),他提出了頗具特色的“設(shè)官為民”思想,具體內(nèi)容如下:
第一,民“主”官“仆”思想。宋濂認(rèn)為,國(guó)家設(shè)置官職,并非為了讓官員們獨(dú)享榮華富貴,而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民眾的福祉,“國(guó)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為民也”。(43)換言之,官員是國(guó)家治理、為民服務(wù)的“公仆”。戶部主事樊德新也有同樣的考慮,并進(jìn)行了詳細(xì)闡發(fā):“國(guó)之祿位,非以優(yōu)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yōu)細(xì)民耳。故祿者出于民,所以傭我之心力;位者出于上,所以使我自別于細(xì)民。夫位高于細(xì)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為尸位;受民之傭而無(wú)功以報(bào)之,則為茍祿。”(44)樊德新的這段話,一方面明確界定了官員在國(guó)家治理體系中的身份——受雇于民,“雇工”而已;另一方面規(guī)定了其職責(zé)所在——造福于民;同時(shí)說(shuō)明了俸祿的性質(zhì)——百姓雇傭官員提供的報(bào)酬。意即,國(guó)家設(shè)置官位并賦予相應(yīng)的俸祿,并不是對(duì)官員的優(yōu)待,而是為了讓他們更加盡心于民事。民作為官員的服務(wù)對(duì)象,在接受服務(wù)的同時(shí),通過(guò)為國(guó)家提供勞役賦稅的形式,補(bǔ)償官員付出的心智成本。其地位居于民之上,則是為了明確各自不同的身份。如果官員身份居于民之上卻沒(méi)有與之相匹配的德性,就是“尸位”;如果官員受雇于民而又不能造福于民、回饋于民,就是“茍祿”。宋濂對(duì)樊德新的這一思想頗為贊賞,將其收錄到自己的文章中,以期自鑒鑒人。因此,上述引文可以作為宋濂治國(guó)思想的表述。二人的思想都與朱元璋治國(guó)理民的要求相契合。朱元璋認(rèn)為,“設(shè)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致紛擾,無(wú)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45)可見(jiàn),在朱元璋君臣看來(lái),所謂俸祿與官職、官位沒(méi)有什么了不起,俸祿是普通百姓為雇傭官員為自己服務(wù)的合理對(duì)等的付出,官位是在國(guó)家治理體系中給官員的角色定位,有著明確的責(zé)權(quán)利界定,其權(quán)是履行為民服務(wù)的手段,而不是為一己謀私利的工具,更非國(guó)家最高執(zhí)政者為優(yōu)待官員而設(shè)。這樣,官與民的關(guān)系就非常清晰了:通俗地講,民與官員是雇主與雇工的關(guān)系,是“主”與“仆”的關(guān)系。“祿”是百姓提供的傭金,作為官員付出“心力”的報(bào)酬;“位”為名分,作為官員區(qū)別于百姓的象征符號(hào)。有了這樣明確的分工——“天子與宰相運(yùn)于內(nèi),四海之遠(yuǎn),兆民之繁”“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于下也”(46)——國(guó)家機(jī)器就可以高效運(yùn)轉(zhuǎn),以實(shí)現(xiàn)朱元璋這個(gè)平民皇帝造福黎民的宏偉愿望。如果官員居于高位卻不具有崇高的道德,不能盡心竭力以為民,如果官員拿了百姓的傭金而不能為百姓謀取福利,就是尸位素餐,應(yīng)該將之驅(qū)逐出官員隊(duì)伍,補(bǔ)充以能夠宣政化者。這種思想顯然把民視為天下之“主”,而官員不過(guò)是受雇于民的“仆”罷了。
第二,官民平等思想。有論者認(rèn)為,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的思想家、政治家天然主張官民的全方位不平等,就其思想而言,骨子里徹頭徹尾冥想著為統(tǒng)治階級(jí)服務(wù),時(shí)時(shí)處處體現(xiàn)出諂媚與對(duì)最高當(dāng)權(quán)者的奴才相,一級(jí)級(jí)向上看臉色行事,在充當(dāng)奴仆的同時(shí),還扮演著國(guó)家治理的棍棒與鞭子,或是精神麻醉劑。姑且不談此論對(duì)復(fù)雜政治現(xiàn)象的簡(jiǎn)單化處理和機(jī)械二分法以及對(duì)階級(jí)觀點(diǎn)的庸俗化應(yīng)用,僅就中國(guó)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群體出身于平民百姓者甚多,具有對(duì)民眾天然的樸素的仁愛(ài)情懷而言,其為民謀利,為民追求經(jīng)濟(jì)、政治上的平等權(quán)利的內(nèi)在訴求就是不容抹殺的。宋濂只是眾多主張官民平等的政治人物之一。宋濂認(rèn)為,官與民都是人,“彼,人也;我,亦人也”,差別只在于各自在國(guó)家治理活動(dòng)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既然從本質(zhì)上官民都是同樣的、平等的人,官與民都有“人心”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循此思路,官、民在國(guó)家治理中就應(yīng)該具有實(shí)質(zhì)上的平等的主體地位。官員之所以為官的根據(jù),不在于其出身高貴,是由女?huà)z娘娘“捏”出來(lái)的,僅僅就在于他們肩負(fù)著神圣職責(zé),是要救民于水火,造福于大眾的一個(gè)勞心群體。即如宋濂所言:“古之人仕也,欲安斯民也。”古人之所以出仕做官,內(nèi)在的動(dòng)因就是讓百姓安居樂(lè)業(yè)。孔子在魯國(guó)先為中都宰,又為司寇,如果不是胸懷崇高的政治追求,完全可以在任何一個(gè)官位上與當(dāng)權(quán)者同流合污以換取自己的榮華富貴。孔子最終選擇了一條充滿艱險(xiǎn)的探索之路,周游列國(guó)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是為尋得“良木”,使自己的治國(guó)理念能夠找到得以落實(shí)的政治環(huán)境,讓百姓們能夠在德治的雨露滋潤(rùn)下各安其位。孔子身前身后,這樣的官員燦若群星。僅在明代,就有大家熟知的宋濂、劉基、方孝孺、呂坤等等。當(dāng)他們看到百姓身處水深火熱之中,頓生惻隱之心,實(shí)為人之常情:“睹斯民遑遑于涂炭之中,其心惻然……厥身則同一身也。”(47)這一點(diǎn)與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48)均是基于人性善的基本假設(shè)所做出的必然判斷。誠(chéng)然,僅僅對(duì)百姓的苦難抱以同情還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孟子主張應(yīng)該將人性中所天然具有的仁義禮智發(fā)揮出來(lái),造福人群。宋濂則提出:“茍棄之而不救,則非人也;然欲救之,非仕不可也。”可見(jiàn),在宋濂看來(lái),做官不過(guò)是實(shí)現(xiàn)造福民眾理想的舟楫、坐騎、橋梁罷了,“譬之渡長(zhǎng)江之險(xiǎn)者,必藉舟楫之利;適千里之遠(yuǎn)者,必藉騏驥之力;行濟(jì)物之志者,必假祿爵之貴”,“如斯而已矣”(49)。換言之,如果一個(gè)人不能獲取國(guó)家治理中的相應(yīng)職位,他就不可能獲得相應(yīng)的職權(quán),不可能掌握相應(yīng)的資源,也不可能將自己造福民眾的愿望轉(zhuǎn)化成實(shí)際的治理行為。從而使理想與抱負(fù)只能淪為空中樓閣。意即,出仕做官是為造福百姓謀求施展政治追求的平臺(tái)。也有些人胸中并無(wú)此志。宋濂對(duì)此類人等進(jìn)行了批判,指出:如果入仕為官抱著追求個(gè)人飛黃騰達(dá)的心理,是非常可恥的事情,“以榮與名而仕,必賤丈夫也”。榮華富貴、高官厚祿對(duì)于高潔之士而言都是身外之物,“何有于我哉!何有于我哉!”(50)其鄙視為為官而為官的言辭堪稱辛辣,與民眾心心相連的情懷可謂蒼天可鑒。
第三,學(xué)而為民。《莊子·列御寇》記載了這樣一個(gè)故事:“朱泙漫學(xué)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wú)所用其巧。”意在說(shuō)明,無(wú)論掌握了多么高深的本領(lǐng),必須找到施展其技的舞臺(tái)。否則,不學(xué)無(wú)術(shù)固然需要批判,技成而無(wú)用武之地同樣是大大的問(wèn)題。宋濂認(rèn)為,官員要實(shí)現(xiàn)造福于民的治政目標(biāo),必須加強(qiáng)學(xué)習(xí),增益治世才能,“士不學(xué)則已,學(xué)則必期世用”。官員的學(xué)習(xí)必須有明確的目的性、針對(duì)性,并且要著力于經(jīng)世之學(xué),著力于掌握治理國(guó)家的具有強(qiáng)烈實(shí)踐性的學(xué)問(wèn)。同時(shí),這種學(xué)習(xí)不僅有知識(shí)的“輸入”,而且能夠以具體的治國(guó)理念、方針、策略、方式方法等進(jìn)行“輸出”,即學(xué)習(xí)的知識(shí)不僅可以而且要不吝于轉(zhuǎn)化成治理國(guó)家的具有實(shí)踐意義的操作手段。宋濂特別批評(píng)了那種致力于學(xué)習(xí),卻學(xué)不致用拒絕服務(wù)于國(guó)家治理,自命清高的做法。這類人甚至批判學(xué)得屠龍術(shù)貨于帝王家是“學(xué)者”的墮落,是對(duì)知識(shí)的玷污,或者在帝制條件下輔佐君主治理國(guó)家取得的成效,也被有些人質(zhì)疑為沽名釣譽(yù)、為了自己光耀門楣等等。照此邏輯,有人品者當(dāng)是耗費(fèi)大量社會(huì)資源,學(xué)富五車之后,卻又不造福于百姓,摒棄與國(guó)家合作實(shí)施善治,孤芳自賞者?宋濂說(shuō)這樣的人“有如大賈行廢舉術(shù),寶貨填溢市區(qū),乃振鐸號(hào)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51)宋濂的這種批評(píng)是很有針對(duì)性的,一針見(jiàn)血地抨擊了那些置國(guó)家、民眾利益而不顧,徒費(fèi)社會(huì)財(cái)富卻又無(wú)所作為者。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這些人不是超然世外的君子,而是只將目光關(guān)照于自己的自私自利之徒。試想,在帝制時(shí)代,帝王雖然獨(dú)攬?zhí)煜麓髾?quán),但國(guó)家治理離不開(kāi)一群群有志之士。百姓福祉的落實(shí)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為官者是不是能夠?qū)⑷收哂枰哉嬲芈鋵?shí)。難不成帝王當(dāng)政,有智識(shí)者紛紛避入深山,不聞天下之事,聽(tīng)任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就是“仁義”?坐等天下大同,就是對(duì)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帝王們?cè)诩姨煜碌恼伪尘跋拢蠖嘀铝τ趪?guó)運(yùn)長(zhǎng)久,主觀上希望國(guó)泰民安。有些成功了,成功的背后總是站著一群為國(guó)事、民事殫精竭慮的知識(shí)型、實(shí)干型官員。有些失敗了,這些失敗者背后恰恰缺少這樣一支官員隊(duì)伍。于是,宋濂告誡為官者,不要為榮華富貴所動(dòng),避免不學(xué)無(wú)術(shù)招搖撞騙,“士之患,常在乎內(nèi)虛而外玄,學(xué)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52)。這樣就可以利用自己學(xué)到的知識(shí)行益民、利民之政,“背私之謂公,當(dāng)理之謂法,行法當(dāng)理則不謬于是非,處事無(wú)私則允合于公正”(53),成為“承順以為恭,奔走而效勞”(54)的良吏。
三、任賢以公的思想
宋濂應(yīng)朱元璋之召時(shí)已經(jīng)五十一歲,之前懷才不遇的遭際令他對(duì)于治國(guó)理政與人才問(wèn)題有過(guò)深入思考,撮其要如下:
第一,治國(guó)理政倚人才。按照墨子的觀點(diǎn),君主的主要職責(zé)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55)。若要實(shí)現(xiàn)如此的治理目標(biāo),對(duì)于中國(guó)這樣自夏代以來(lái)即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的巨大型國(guó)家而言,君主不可能事必躬親,必須將賢德才俊選拔到治國(guó)的關(guān)鍵崗位上來(lái),借助大量股肱之士的智慧與才能,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善治。如《墨子》言:人才乃是“國(guó)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56)可見(jiàn),宋濂之前的思想家、政治家早已提出人才之于治國(guó)理政的不可或缺和珍貴性。宋濂面對(duì)的歷史變遷,一方面是元朝憑借金戈鐵馬迅速崛起,一度成為世界上地域最為廣大的強(qiáng)盛帝國(guó),另一方面又由于大力推行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政策,將大量無(wú)能之輩安插到國(guó)家的要害部門,未能獲得有智之士的輔佐,導(dǎo)致國(guó)祚苦短,急速?gòu)膸p峰衰敗北遁。親身感受其中的滄海桑田巨變,使得宋濂再一次深刻體會(huì)到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國(guó)家興衰決定于人才的治國(guó)主張,“國(guó)家之治在于得人”(57)。是說(shuō),能否獲得賢才,直接關(guān)系到國(guó)家的前途命運(yùn)。治國(guó)理政如果能夠獲得大批人才的支持,不僅是國(guó)家之幸,而且是天下之幸,百姓之幸。在賢才輔佐之下,國(guó)家就可以興旺,社會(huì)就可以安定,人民就可以安居樂(lè)業(yè),“使國(guó)家有得人之盛,而天下蒙至治之澤”(58)。反之“王公大人為政于國(guó)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59),國(guó)家必然衰微,社會(huì)必然混亂,人民必然陷入無(wú)邊的苦難之中。為了說(shuō)明個(gè)中道理,宋濂用了一種很形象的說(shuō)法,即治國(guó)實(shí)踐若用不得其人,未能適材適所,其情況比用豬代替牛去耕種還要糟糕,“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60)宋濂的意思是告誡那些有國(guó)者,治不得其賢,或是避長(zhǎng)用短,輕則貽害天下,重則亡國(guó)。他還以元朝在中原統(tǒng)治的崩塌為例做了進(jìn)一步說(shuō)明,認(rèn)為元朝政府任用的官員大多是庸碌且貪圖享樂(lè)的小人,像鄧弼文那樣文武全才的人卻不得其用,結(jié)果“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shù)千里,人影殆絕”,這完全是元朝各級(jí)政府用人不當(dāng)造成的,“使弼在,必當(dāng)有以自見(jiàn)。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發(fā)上沖也”。(61)
第二,惜才愛(ài)才治國(guó)之要。宋濂認(rèn)為,雖說(shuō)千里馬常有而伯樂(lè)不常有,國(guó)家治理的實(shí)踐卻表明,能夠擔(dān)當(dāng)治國(guó)大任的卓越人才自古以來(lái)始終是稀少的。在任何歷史條件下,普通人總是社會(huì)成員的大多數(shù),他們固然是國(guó)家賴以發(fā)展的基礎(chǔ)性力量,是根本,但是國(guó)家的發(fā)展終究離不開(kāi)一大批經(jīng)天緯地之才以匯聚民智與民力。宋濂指出:“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櫪,不培而自長(zhǎng);才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jiàn)”(62)。宋濂將普通人比作野草,將人才視作靈芝、瑞木,固然有強(qiáng)烈的歧視色彩,其要旨則在于說(shuō)明人才不僅具有珍貴性,而且其成才需要苛刻的環(huán)境條件,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隨時(shí)有可能出現(xiàn)變異或夭折,借以強(qiáng)調(diào)人才始終是國(guó)家治理之稀缺而難得的財(cái)富與資源。另外,即便朝堂上人才濟(jì)濟(jì),由于國(guó)家治理涉及面太廣,對(duì)于任何一個(gè)執(zhí)政者而言依然表現(xiàn)出人才資源的稀缺,故要倍加珍惜各類人才。典型者如漢武帝時(shí)期,人才匯聚可謂空前。即便如此,出使西域之類的政務(wù),依然需要面向社會(huì)廣征人才,這才有了張騫的脫穎而出。漢武帝時(shí)期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宋濂強(qiáng)烈主張,“國(guó)家盛時(shí),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shí)者,且猶愛(ài)之!”(63)無(wú)論是天下混亂與各路豪杰爭(zhēng)雄,還是平復(fù)動(dòng)亂,百?gòu)U待興的時(shí)候,抑或是恢復(fù)秩序,安撫百姓,發(fā)展生產(chǎn),爭(zhēng)取人才、任用人才都是急迫不已的事情。人才的這種稀缺難得性,要求執(zhí)政者要絕頂愛(ài)惜。殘酷的事實(shí)卻是,元朝社會(huì)后期天下混亂,大量人才玉碎,湮沒(méi)于塵。江河日下的政局又迫切呼喚人才加盟,其情勢(shì)更凸顯了人才的治國(guó)價(jià)值。進(jìn)入朱明之后的情況似乎更為糟糕:“今喪亂之余,斯道之不絕者如發(fā),則才之生于此時(shí)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ài)乎?”(64)面對(duì)元政府對(duì)人才的漠視與壓抑,面對(duì)天下黎民對(duì)治世人才的強(qiáng)烈呼喚,宋濂大聲疾呼:“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jiàn)者茍不愛(ài)之,非無(wú)目之人,必?zé)o識(shí)者也。是豈人情哉!”(65)他強(qiáng)烈呼吁執(zhí)政者不要讓人才總是感嘆“老將至矣”(66),或是“丹穴之鳳,五色褵褷,不高翔于千仞,乃戢翼而委蛇”(67),而是讓“奇雋之士”(68)“卓然有立,小或作州牧,大或聞國(guó)政,使德澤簡(jiǎn)在人心,聲聞流于后世,然后始無(wú)愧于斯名”(69),這是真正的惜才、愛(ài)才。
第三,不拘一格用人才。在用人方面,宋濂深受孔子人才思想的影響。他雖然沒(méi)有為人才的內(nèi)涵做過(guò)界定,但是從他擢用人才的實(shí)踐看,其對(duì)人才的認(rèn)定范圍非常廣泛。如洪武初年(1368年),泰和(今江西省屬縣)人陳謨應(yīng)朱元璋之召赴南京議“禮”。陳謨不僅長(zhǎng)于經(jīng)學(xué),而且精通經(jīng)世之學(xué)。宋濂認(rèn)為陳謨?nèi)瞬烹y得,建議明太祖留用陳謨,陳謨以疾辭歸。之后,陳謨又征為朝廷的考試官,在為國(guó)選拔人才的同時(shí),積極宣傳自己的理論主張,一時(shí)之間,從陳學(xué)者蔚為壯觀。洪武六年(1373年),宋濂向朱元璋推薦天界寺兩名僧人,證傳和愿證。朱元璋首先閱讀了他們的文章,認(rèn)為“議論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70)次日面見(jiàn)后,朱元璋對(duì)二人的學(xué)問(wèn)、文采均非常滿意,頗多賞賜,予以重用。次年(1374年),宋濂又向朱元璋推薦了郭傳(時(shí)為僧人)。宋濂認(rèn)為郭傳“學(xué)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jù)六經(jīng),異才也”(71)。朱元璋授郭傳翰林應(yīng)奉,后任湖廣布政司參政。為了更大量地為國(guó)家網(wǎng)羅人才,宋濂建議朱元璋打破既有人才選用的條條框框,用“鄉(xiāng)舉里選”的方法搜羅人才。雖然這種方法早在漢代已經(jīng)廣為應(yīng)用,并一度演化為漢代人才選拔的主要制度——察舉制,但最終在魏晉時(shí)期被九品中正制所取代。宋濂卻堅(jiān)持認(rèn)為“取士莫善于鄉(xiāng)舉里選”(72)。“鄉(xiāng)舉里選”的人才選用方式不僅可以在民間廣布朝廷恩澤,讓民間人士看到進(jìn)入國(guó)家管理體系的希望,增強(qiáng)政權(quán)的吸引力與親和力,而且可以使大量埋沒(méi)于民間的、無(wú)法通過(guò)科舉之途入仕的奇能異士有機(jī)會(huì)進(jìn)入國(guó)家治理系統(tǒng)施展才華。科舉終究側(cè)重選拔儒學(xué)之士,而治國(guó)則需要各類人才齊心協(xié)力方能取得良好效果。從田野間崛起,更易于體恤民間之苦,更易于站在民眾的角度為國(guó)家治理獻(xiàn)計(jì)獻(xiàn)策。何況,大量人才藏于民間不為國(guó)家所用,既是國(guó)家的損失,也有可能成為引起國(guó)家動(dòng)蕩的巨大隱患。朱元璋接受了宋濂的建議,在全國(guó)大舉推行察舉之策,使得洪武年間經(jīng)察舉入仕的人才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科舉入仕者。
通過(guò)前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宋濂基于“民本”的思考為大明王朝國(guó)家治理設(shè)計(jì)了符合“國(guó)情”的路徑。每一個(gè)角度、每一個(gè)層面都體現(xiàn)出宋濂對(duì)百姓疾苦、對(duì)國(guó)家長(zhǎng)治久安的深切關(guān)懷。其理論訴求在那時(shí)國(guó)家治理的政策措施中獲得了極好的體現(xiàn),為明王朝前100年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恢復(fù)發(fā)展并走向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宋濂治國(guó)思想的可貴之處,最根本的一點(diǎn)體現(xiàn)在明確告知執(zhí)政者權(quán)力來(lái)源于民眾,即“君權(quán)民授”,而不是什么“君權(quán)神授”、“奉天承運(yùn)”。如果說(shuō)有神、有天,那就是百姓。基于這樣的判斷,宋濂提出安民、富民、化民的主張,并告誡那些官員,雖然他們?cè)诟旧吓c民是平等的(都是人),但由于其擔(dān)當(dāng)了官員,故與民的關(guān)系就演化為“主仆”,為了更好地盡到“仆”之職責(zé),官員必須勤于學(xué)習(xí),增益才智。另外,宋濂主張選拔大量的人才為國(guó)所用,從而實(shí)現(xiàn)國(guó)泰民安的治理目標(biāo)。宋濂的這些主張雖然產(chǎn)生于600多年前,由于其揭示了國(guó)家治理的一般性規(guī)律,對(duì)于今日中國(guó)而言,可以作為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參考依據(jù),我們現(xiàn)在面臨著如何將“以人為本”貫徹到治國(guó)實(shí)踐中的考驗(yàn),這是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前提條件,也是建設(shè)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必須跨過(guò)的門檻。執(zhí)政者除了必須要在思想上確立“以人為本”的價(jià)值理念,還必須要設(shè)計(jì)出切實(shí)可行的路徑。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紀(jì)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huì)的講話中指出:“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可以為治國(guó)理政提供有益啟示”,為我們大膽借鑒古人治國(guó)理政思想為今所用指明了方向。
注釋:
①(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7頁(yè)。
②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宋濂全集》附錄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59頁(yè)。
③(明)宋濂:《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9頁(yè)。
④(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91,中華書(shū)局,1976年,第4355頁(yè)。
⑤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宋濂全集》附錄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55頁(yè)。
⑥(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5頁(yè)。
⑦(明)宋濂:《宋濂全集》,《翰苑別集》卷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24頁(yè)。
⑧(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66頁(yè)。
⑨(明)宋濂:《宋濂全集》,《芝園續(xù)集》卷5,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61頁(yè)。
⑩《禮記·大學(xué)》。
(11)《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49,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961頁(yè)。
(12)《論語(yǔ)·里仁》。
(13)《論語(yǔ)·里仁》。
(14)《論語(yǔ)·述而》。
(15)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53頁(yè)。
(16)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53頁(yè)。
(17)(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5頁(yè)。
(18)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53頁(yè)。
(19)《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19,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259頁(yè)。
(20)《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19,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259頁(yè)。
(21)《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19,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260頁(yè)。
(22)《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19,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259頁(yè)。
(23)《論語(yǔ)·泰伯》。
(24)《論語(yǔ)·子路》。
(25)(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5,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28頁(yè)。
(26)(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5,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29頁(yè)。
(27)(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6頁(yè)。
(28)(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后集》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2頁(yè)。
(29)《論語(yǔ)·為政》。
(30)(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后集》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2頁(yè)。
(31)(明)宋濂:《宋濂全集》,《芝園續(xù)集》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68頁(yè)。
(32)(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2頁(yè)。
(33)(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6頁(yè)。
(34)(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 1頁(yè)。
(35)(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6頁(yè)。
(36)(明)宋濂:《宋濂全集》,《翰苑續(xù)集》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86頁(yè)。
(37)(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6頁(yè)。
(38)(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頁(yè)。
(39)(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頁(yè)。
(40)(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頁(yè)。
(41)(明)宋濂:《宋濂全集》,《翰苑別集》卷6,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56頁(yè)。
(42)(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128,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3785頁(yè)。
(43)(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先生集輯補(b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74頁(yè)。
(44)(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7頁(yè)。
(45)《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6,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63頁(yè)。
(46)(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先生集輯補(b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74頁(yè)。
(47)(明)宋濂:《宋濂全集》,《龍門子凝道記中·憫世書(shū)》第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8頁(yè)。
(48)《孟子·公孫丑上》。
(49)(明)宋濂:《宋濂全集》,《龍門子凝道記·憫世書(shū)》第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8頁(yè)。
(50)(明)宋濂:《宋濂全集》,《龍門子凝道記·憫世書(shū)》第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8頁(yè)。
(51)(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后集》卷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56頁(yè)。
(52)(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77頁(yè)。
(53)(明)宋濂:《宋濂全集》,《芝園后集》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71頁(yè)。
(54)(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前集》卷10,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45頁(yè)。
(55)《墨子·兼愛(ài)下》。
(56)《墨子·尚賢上》。
(57)(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前集》卷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6頁(yè)。
(58)(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前集》卷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7頁(yè)。
(59)《墨子·尚賢上》。
(60)(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頁(yè)。
(61)(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后集》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2頁(yè)。
(62)(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5頁(yè)。
(63)(明)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6頁(yè)。
(64)(明)宋濂:《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6頁(yè)。
(65)(明)宋濂:《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5頁(yè)。
(66)(明)宋濂:《宋濂全集》附錄一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472頁(yè)
(67)(明)宋濂:《宋濂全集》,《翰苑別集》卷7,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93頁(yè)。
(68)(明)宋濂:《宋濂全集》,《潛溪前集》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頁(yè)。
(69)(明)宋濂:《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37頁(yè)。
(70)(明)宋濂:《宋濂全集》,《翰苑續(xù)集》卷8,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28頁(yè)。
(71)(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卷285,中華書(shū)局,1974年,第7334頁(yè)。
(72)《明實(shí)錄·明太祖實(shí)錄》卷106,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1968年,第1764頁(yè)。
On Song Lian's National Governance Thought:Benevolent as the Core-idea
Wang Cheng/Sun Ling
Song lian'sgovernance thoughtisbased on the valueofpeople-oriented thought.He thought that the power ofmonarch granted from people,and the focusofgovernance should be on giving people peace and wealth.Making country rich shouldmake people rich first which is correlated withmakingmonarch and country rich,and they complementeach other.After dealingwith people's livelihood problem such asmaking people rich and raising people,governors should teach people with'Book of Songs'and Etiquette;carry out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andmoral administration to people,make people voluntarily accept policies of government.Punishment is just an auxiliary of governingmethod.Officialsare people's'servants'tomanage and service the people.Officialsand people areequal,officialsshould learn for people.To the talents of governing,Song Lian advocated that governors should highly cherish them,appoint talents without overstressing qualifications.
Song Lian;People-oriented;Benevolent;Setup Official for People;AppointTalents for Public Interests
K825.6
A
1009-3176(2015)01-027-(9)
(責(zé)任編輯 譚力)
本文是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中國(guó)傳統(tǒng)政治文化與堅(jiān)持走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研究》(項(xiàng)目號(hào):13&ZD008)暨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中國(guó)傳統(tǒng)政治思想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價(jià)值重構(gòu)研究》(14AZZ005)的階段成果。
2014-9-12
王成男(1969-)山東大學(xué)政治學(xué)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教授歷史學(xué)博士
孫菱女(1989-)山東大學(xué)政治學(xué)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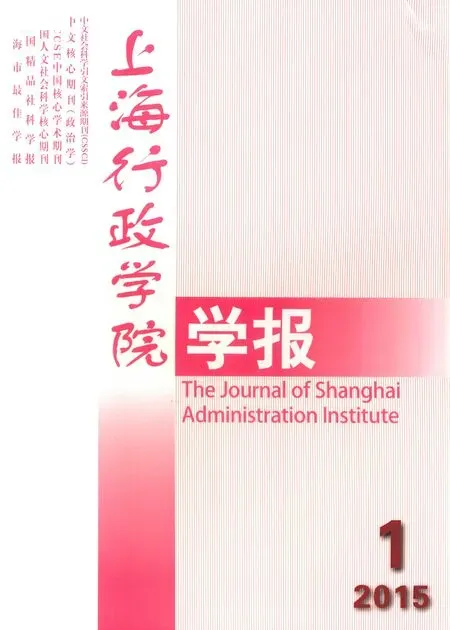 上海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1期
上海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1期
- 上海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基層綜合性應(yīng)急救援隊(duì)伍組建模式及管理機(jī)制研究*
- 中國(gu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演進(jìn)與城市化進(jìn)程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性研究*
- 人際關(guān)系的和諧與統(tǒng)一*
——《白虎通》的治理思想研究 - 產(chǎn)業(yè)升級(jí)的國(guó)際比較
- 前瞻性探究未來(lái)30年上海特大城市的治理
——“上海未來(lái)30年發(fā)展視野下的特大型城市治理”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 學(xué)術(shù)動(dòng)態(tài)兩則文化傳承與文化創(chuàng)新發(fā)展
——“文化·改革·發(fā)展”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綜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