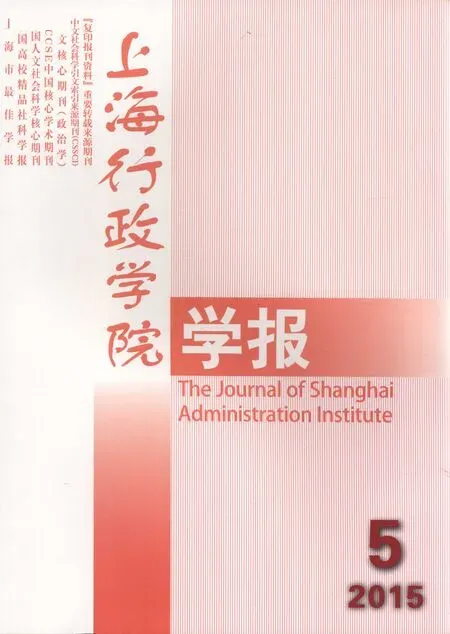20世紀初美國崛起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
楊魯慧 任綠勃
(1.山東大學,濟南 250100;2.武漢陽光凱迪新能源集團,武漢 430223)
20世紀初美國崛起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
楊魯慧1任綠勃2
(1.山東大學,濟南 250100;2.武漢陽光凱迪新能源集團,武漢 430223)
大國崛起必然要從區域走向世界,成長為世界大國并發揮領導國家的政治影響力,這是歷史上大國崛起所必經的發展邏輯。20世紀初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門羅主義的外交政策,是美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地區政治結構以及國內諸因素的必然產物,體系層次結構構建了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的變量要素。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為美國的崛起提供了戰略機遇期,并成為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動因。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妥善處理了美國的周邊關系與地區關系以及域外的大國關系,為美國崛起創造了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對美國的崛起具有重大影響作用,保障了美國在崛起過程中的國家利益和周邊安全;強化了美國在崛起中對拉美地區的影響力;保障了美國在地區乃至全球日漸增長的經濟利益及秩序。
美國崛起;門羅主義;外交政策;西奧多·羅斯福
20世紀初美國處于確立地區主導大國地位進而走向世界大國的重要戰略關鍵期。隨著經濟、軍事實力的迅速增長,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著眼于美國所面臨的國際和地區環境,對美國長期以來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門羅主義的本質內涵進行了拓展延伸,提出了著名的 “羅斯福推論”,從而把門羅主義的目標由地區防御型轉變為地區主導型發展戰略。“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為排除歐洲國家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而提出了‘門羅主義’。不過在歐洲勢力退出南美之后,‘門羅主義’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即美國開始在政治與經濟等領域對拉美不斷施加‘影響力’,最終使‘門羅主義’成為了‘美國霸權’的一個代名詞。”①
自19世紀美國門羅總統發表《門羅宣言》以來,門羅主義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門羅之后歷屆總統都通過繼承和豐富門羅主義外交政策來維護美國在西半球的利益。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為美國20世紀的大國崛起構建了一個良好的地區環境,同時維護和增進了美國不斷擴張的
國家利益,對美國的崛起產生了深刻影響。從世界大國崛起的發展定律看,它們都將面臨復雜而嚴峻的周邊安全環境,需要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雙邊關系、和地區的多邊關系以及與傳統大國的關系,由地區主導大國走向世界大國,最終完成大國崛起的歷史發展進程。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發掘過去,也就是理解當下。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面臨復雜而嚴峻的周邊安全環境,需要處理好周邊國家關系、地區多邊關系以及大國關系。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對于當今中國崛起具有重要的啟示借鑒意義。
一、體系層次結構: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分析架構
對于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而言,建構一種對外政策理論,將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和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結合起來,更好地去解釋國家對外政策的形成是一個很好的嘗試。與古典現實主義者一樣,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也將國家、政府、決策者等單元層次上的因素作為重要的關注對象,卻又比古典現實主義者更具備方法論的研究意識。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者繼承了結構現實主義關于國際政治體系結構是塑造國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的假設,并將它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在新古典現實主義那里,“外交政策理論首要的使命是對國際體系在國家行為實踐中所產生的影響作出回答,因為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將決定其所擁有何種一般性的特征。然而,要增進對國家理解和回應外部環境的認知則需要更進一步解析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結構等單元層次的變量在傳到體系性壓力中的作用。”②這樣以來,在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探索過程中,新古典現實主義采用內嵌式納入國內變量的理論構建方式,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外交政策理論分析框架。
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理論的理論路徑是:“肯定國際結構對外交政策大方向的決定性作用,但由于國內因素的影響,結構信號不能準確完整地傳達至決策者或者結構本身沒有給出應如何回應的確切信號,因此要理解外交政策,必須解釋哪些國內因素影響以及如何影響結構信號的傳達和回應。”③在其基本理論假設中,該學派指出,“對外政策是國際體系和國家兩個層次之內和兩個層次之間的復雜互動的結果。盡管國家的權力以及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決定性地影響國家的選擇,但是按照認知、價值觀等國內因素做出的選擇同樣能夠影響對外政策。”④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將國際體系和國內政治結合起來,分析國家內部結構如何對外在威脅和機遇進行過濾,國家領導人如何評估威脅、制定戰略、動員社會資源以支持這些戰略”⑤。
新古典現實主義明確指出,正是體系因素和國內因素的互動,推動了國家對外政策這一必然結果的產生,在這一基礎上界定其理論分析的三大變量關系,并對變量之間的關系做出了具體分析。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因素是自變量,國家對外政策是因變量,而國家單元因素則是干擾變量。國內因素不僅影響對外政策決策者對體系結構信息的認知和判斷,同時還影響著政府動員國內資源去應對體系結構壓力的能力。在處理國內變量與體系變量二者的關系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一直堅持國際體系結構因素的主導地位,國內變量對結構壓力起到加強、傳輸和削弱的作用,影響著國家對體系結構的反饋。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核心自變量可以概括為“經國內要素過濾后的相對實力結構”⑥,這才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形成變化的真正動因。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外交決策實際上是由國家領導人和政治精英做出的,因此決定外交政策選擇的不僅僅是國際政治結構即各個國家經濟、軍事、政治力量的對比,還有決策層對于這種結構的認知以及他們能夠動員國內資源去應對來自結構壓力的能力。因此,分析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形成,在了解國際政治結構的基礎上,還必須考察國家內部的觀念和政治結構等要素。
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國家層面的因素以內嵌的方式融入到國際政治體系結構之中,大大提高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論化程度。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代表主要有施韋勒的 “利益平衡理
論”、法利德·扎卡利亞的“政府中心型”現實主義、杰弗里·特里菲拉的“資源汲取模型”和柯慶生的“國內動員模型”等。施韋勒的“利益平衡論”認為,由于國家行為偏好和目標的不同,面對相似的體系結構壓力時對結構壓力的認知也會存在差異,因此也就會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扎卡利亞所提出的“政權中心型”現實主義認為,“如果社會資源可以被國家政權以更便捷的手段占有,政府可以擁有更加集中和統一的決策能力,那么國家的外交政策才可能對既有國際體系的變化做出更為直接的回應。”⑦特里菲拉的“資源汲取模型”則指出,國家政權從國內社會獲取和運用資源的能力對國家制定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響。柯慶生的“國內動員模型”則強調,“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變遷可能會迫使國家不得不采取相應的長遠戰略,而如果這一戰略與國內政治環境產生對立,決策者會為了確保長遠戰略的實施而進行國內政治動員,不過此舉也可能導致國家在某些領域所推行的對外政策會與既有的國際結構體系相背離。”⑧這些理論大都從對國內干擾性變量在外交政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入手,強調國內因素的重要性,彌補了結構現實主義在國家行為動因上的缺陷,全面客觀地解釋了國家在某一時期的具體對外政策的制定。
20世紀初美國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形成的變量因素主要是地區次體系層次的引入。國際體系是最大的分析結構體系,地區次體系內嵌于國際體系之中,是國際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地區次體系結構是由國際體系結構所決定的。但是,在具體的地區次體系中,介入大國在地區的力量存在由于受到地理因素、技術因素、介入國力量分配等因素干擾,事實上并不等同于介入國本身的全部實力。因此,地區次體系結構又是與國際體系結構有差別的。我們在分析國家的對外政策時,對結構層次變量進行了內部分層,也就是說地區政治結構內嵌在國際政治結構中,共同影響一國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國際體系結構是根基,決定著地區次體系結構;另一方面,地區次體系結構在地區層次上對國際體系結構做出的折射,是國際體系結構在地區層次的具體化。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框架,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是由國際體系和地區次體系結構和國內層次的諸多因素共同決定的,其中國際體系和地區次體系結構是自變量,國內因素是干擾變量,對自變量起著過濾作用。西奧多·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主要是由美國在20世紀初所面對的國際結構層次的壓力決定的。
二、崛起大國角色定位: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演進的動因
美國建國初一直奉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門羅主義正是沿襲了孤立主義思想原則的具體體現,是適應了19世紀初美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局勢而形成的。門羅主義是為了防衛西半球以阻止歐洲大國干涉而提出的,它實質是保護美國在美洲地區的利益。因此,它是美國在美洲地區對外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19世紀末美國經過與英國等歐洲列強的較量,事實上已經成為美洲地區的大國。1898年美國的世界強國地位經過美西戰爭的考驗得到了世界大國的承認。1900年,美國的鋼鐵產量幾乎相當于英德兩國的總和,海軍實力達到世界第6位。綜合國力特別是硬實力的提升,導致美國開始更加主動地去維持美洲地區的秩序,承擔地區主導國的責任,這推動了門羅主義在20世紀初由地區防御向地區主導的轉變。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時期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國內因素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以總統為核心的行政權力的擴大、羅斯福的現實主義觀念、壟斷利益集團對拓展海外市場的需求,都促使美國利用有利的國際和地區政治結構,確立和發揮地區主導作用。因此,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實際上是由國際體系結構、地區體系結構和國內諸多因素共同決定的。
第一,從國際體系層次上看,19世紀下半葉,工業發展和技術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現代化迅速改變了全球經濟和軍事力量對比,工業化的程度決定了20世紀初各個大國的發展和相對地位
的變化。這一時期,英國開始從它的霸主地位上滑落,而美國、德國等工業化較快的國家迅速崛起并大有趕超英國的勢頭,法國、俄國、日本、奧匈帝國則相對落后。因此從整體上看,國際體系呈現出多極的形態。
美國在這一多極體系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其外交決策的根本出發點。其一,英國實力的相對衰落。1900年英國雖然還具有超強的經濟實力,從包括財源、生產力、海外殖民地以及海軍力量等諸因素在內的綜合實力來看,英國是毋庸置疑的世界主導國,但是它的全球霸主地位已不如19世紀中期前的鼎盛時期。其二,美國實力的迅速增長。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初,世界各國的實力對比發生的最大變化是美國的崛起。美國先是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然后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打造了一支世界一流的海軍,使得其國家綜合實力迅速提升。而且美國的整體工業實力也得到迅速提升,逐漸超越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品生產國。“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占世界工業生產的第4位,1894年已經躍居第1位,產量等于歐洲各國生產總量的一半。”⑨“1890年美國的鋼產量達到了930萬噸,超過了英國和德國,居世界第一;到了1900年,美國的鋼產量達到1030萬噸,幾乎相當于英國的一倍。1900年美國占世界制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達到了23.6%,超過了英國的18.5%,成為世界第一。”⑩20世紀初,美國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化之后,就已經超過英國、法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有兩大海洋作為天然屏障,美國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發展海軍。國內經濟迅猛增長使得美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張,美國的經濟利益早已突破了西半球,這就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去保護日益擴展的海外貿易,同時強大的工業基礎也為建造軍艦提供了條件。 1893年美國的海軍實力已經上升到世界第7位。“到了1900年,美國海軍戰艦噸位達到了33.3萬噸,僅次于英法俄三國,位列世界第四。”?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和世界第四的海軍實力,美國20世紀初一躍成為世界一流國家。這不僅是美國崛起的重要基礎,也是制定大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
第二,從地區次體系層次上看,門羅主義外交政策作為一個地區政策還要受到美洲地區力量結構的影響。美洲地區結構是國際體系結構的一部分,是國際體系結構在美洲地區內的具體體現,它是由地區內的力量對比決定的。一個地區子系統主要由核心部分、邊緣部分和介入部分組成,三者的實力對比決定了地區次體系的結構。在美洲地區,核心部分是美國,邊緣部分是其他美洲國家,而介入部分則是英、德等歐洲大國。由于美洲其他國家都處在比較落后的狀態,美國早已是西半球最強大的國家,甚至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唯一與美國相抗衡的就是英國的勢力介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迅速崛起并實行海外擴張政策,開始對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發起挑戰,這導致了英德矛盾的激化,加速了英國從西半球的戰略撤退。英國不得不減少在美洲地區的力量存在,這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在地區結構中的優勢地位,英國從西半球的最終撤出,意味著美洲地區的政治格局已經轉化為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這種地區體系結構也決定了美國新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的出臺。
美國在美洲地區具有無與倫比的實力優勢。20世紀初,從大國對美洲的介入情況來看,主要是英、德、法三國。首先,我們從國際體系結構方面對這三個國家的實力對比進行分析。由于美洲地區的特殊地緣狀況,“巨大的水體極大地影響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因此軍事力量對比中主要看海軍力量對比。從海軍力量上看,“1900年英國的戰艦噸位106.5萬噸,居世界第一位,遠遠超過法國的49.9萬噸、美國的33.3萬噸和德國的28.5萬噸”?。英國海軍的實力幾乎相當于法、德、美三國戰艦噸位總和。因此,20世紀初英國的海軍實力仍然是世界第一,英國依舊擁有世界海上霸權。從經濟實力上看,美國則領先其他三個國家。綜合來看,美國比英國實力要弱,但要比德國和法國要強一些。因此,即便作為介入部分的英國、德國、法國傾其全力,占優勢的只有英國而已。再加之美國本身就是地區內的國家,占有地緣戰略的優勢,而其他國家則要跨越大西洋,這是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緣條件。“歐洲人不但要投入重要的資源以保護自己的國家免遭彼此攻擊,而且跨過大西洋向北美投送力量非常困難。”?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的大國沒有能力在美洲與美國進行抗衡。因此,美國作為
美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處于地區次體系的核心地位。
第三,從國家單元層次上看,外交政策的制定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國家單元層次,還是要由政府來制定實施。美國外交政策主要由行政部門來制定,行政部門的權力大小決定著其動員國內資源應對國際結構壓力的能力。因此,作為政府首腦和權力核心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便成為影響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形成的關鍵因素,他的個人政治、外交觀念和性格特質影響著他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抉擇。從國內政治權力結構的角度看,20世紀初美國政治權力結構呈現出中央權力不斷擴大的趨勢,即總統的權力不斷擴大,國會的權力日益削弱,權力逐漸向總統手中集中。西奧多·羅斯福改變了立法部門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支配地位,他堅持進步積極的和以行政部門為中心的政府理念,“通過行政權力的擴大,使總統在國家政策的制定中扮演一個更為直接的角色”?。總統在對外事務上的權力也得到相應的增強。羅斯福認為:“即便沒有得到國會的支持,總統在這些事務上也要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20世紀初美國國內政治結構呈現出總統代表的中央行政部門權力不斷擴大的趨勢,這一權力結構特征決定了美國外交決策較強的國內動員能力和總統作為決策核心的特征。
三、周邊與大國關系: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為美國崛起創造國際環境
西奧多·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在拉美地區處理域外大國關系、域內雙邊關系和多邊關系的重要戰略選擇:在處理與域外大國關系方面,美國積極阻止歐洲大國對美洲事務干涉,并抓住英國從美洲撤退時機確立自己在地區的領導地位;在域內雙邊外交方面,美國通過積極干預地區事務,發揮地區主導作用,維護了西半球的穩定;在域內多邊外交方面,美國通過倡導泛美會議的召開,以泛美會議為主要媒介倡導地區貿易互惠及和平解決爭端,促進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增強了美國在地區發揮主導作用,擴大美國的地區影響力。通過這三個層次的對外關系的處理,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為美國的大國崛起構建了一個美國主導下的相對和平、穩定、安全的地區環境。
第一,處理好拉美區域的雙邊關系,為大國崛起創造安全穩定環境。美國在1895-1896年的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后獲得西半球的優勢地位,門羅主義原則也得到英國的承認,至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時期美國在西半球的優勢地位就更加穩固。對此,美國并不滿足于排除歐洲大國對美洲事務的干涉,而是希望在地區內發揮主導作用,更好地保護美國在拉丁美洲日益擴張的經濟利益,同時確保拉丁美洲的安全和秩序。一個穩定、繁榮的西半球不僅可以避免歐洲大國的干涉,而且有利于美國在西半球經濟利益的快速增長,為美國的崛起再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在處理與美洲地區雙邊關系中,更注重的是美國必要時可以在西半球扮演“警察”角色。這表明美國開始主動承擔維持地區秩序的地區主導國責任,這是大國崛起過程中在地區事務上日漸成熟的標志。
掌握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為美國更好地發揮地區主導作用提供了重要條件。自美國獲得加利福尼亞領土從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以來,在中美地峽修建一條運河從而連接兩個大洋就成為美國的宏偉戰略目標。1914年8月巴拿馬運河開通是美國工程和技術力量的樣本,它改變的不僅是一個熱帶叢林小國,而且重新改寫了世界地緣政治經濟格局。開通巴拿馬運河不僅關系到美國國內市場的流通和經貿的繁榮,也關系到美國本土和周邊安全穩定問題,更是構筑了美國的大國崛起新時代。據美國《輿論》雜志的調查數據,“美國政府的這種強權做法在國內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大家都認為美國非常需要這條運河”?。美國前眾議員韋勒認為,即便是在100年后的今天,美國依然是巴拿馬運河最大的受益者,“當年西奧多·羅斯福所推動的3.75億美元 (相當于如今的80億美元)投資對美國的農民、工人、制造商和消費者所帶來的收益是巨大的。”?西奧多·羅斯福一直把獲
得巴拿馬運河控制權作為其總統任上的最大政績,這是為美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著眼,而且這一做法體現了他的宏大戰略性思維。“西奧多·羅斯福看到了這個既能促進世界貿易,又能增強我們海軍實力的絕好機會。”?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羅斯福竭力把持道德的底線,搶在別人之前一把抓住了扼制美國咽喉的海上要道,使其在崛起過程中吸取俄國在土耳其海峽受挫的教訓,避免了重蹈覆轍,為美國主導西半球創造了有利的地緣戰略優勢。
美西戰爭結束后,1899年古巴獲得美軍占領下的獨立。1906年,古巴發生了反對政府的暴動,此時古巴總統埃斯特拉達·帕爾馬請求美國援助。美國以此為契機通過對古巴政治動亂的干預,實現了其保衛美國“南大門”的安全和美國在古巴的經濟利益的目的。自1899年以來,革命和動亂一直困擾著多米尼加共和國。多米尼加政府由于無力解決國內困境也開始向美國政府尋求幫助,1904年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提出對外戰略新思維,美國要承擔美洲國際警察職責,以維持地區秩序免受域外大國干涉的“羅斯福推論”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隨后美國對多米尼加進行政治干涉并與其進行了談判。羅斯福宣稱,“美國的干涉將多米尼加人民從無休止革命騷亂的災禍中解放出來,并給他們提供了與古巴人民同樣的進步機會。”?多米尼加的債務危機是導致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最終成型的誘發性事件,羅斯福對這一事件的應對則是“羅斯福推論”的第一次具體實踐。美國對多米尼加債務危機的介入,再次向美洲各國展現了美國作為地區主導國積極維持地區穩定和秩序的大國形象,為美國在地區內贏得了稱贊和信任,擴大了美國的地區政治影響力。
第二,正確處理美國域內的多邊關系,積極推進地區合作協調機制建設,通過多邊外交的途徑來擴大美國的地區影響力。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塑造了美洲地區的安全環境,“泛美會議”成為這一時期美國在地區開展多邊外交的典型案例,這也標志著美國開始探索發揮地區主導大國作用的新路徑。1890年4月第一屆泛美會議閉幕,“盡管布萊恩的議程缺乏具體的成果,但卻暗示了美國強調商業與和平‘新外交’的主要方向。”?同時,這次會議為美國獲得美洲地區的領導權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多邊外交。1901年10月至1902年1月,第二屆泛美會議在墨西哥城召開,這次會議重組了美洲共和國商務局,擴大為美洲共和國國際事務局,由美國國務卿擔任理事會主席。改組和擴大的結果,使得美洲共和國國際事務局“成為一個超國家權力的政治組織”,?為美國擴大在地區的影響力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第三屆泛美會議于1906年7月在里約熱內盧召開。這次會議決定把美洲共和國國際事務局的工作由商業領域擴展到文化領域,從而擴大了這一機構的職能范圍和權限。這次會議比第二屆泛美會議又有了新的進展,無論是仲裁問題還是索取債務問題,都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決。歷屆泛美會議為西奧多·羅斯福促使拉美國家接受商貿互惠、和平解決地區爭端和強制仲裁等外交原則奠定了基礎條件,促進了美洲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從而使美國開始在地區多邊外交中發揮領導作用。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的美國政府開始謀求擴大自己在美洲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以確立自己在地區內的大國領導地位。
第三,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妥善處理與域外大國的關系。門羅主義主要是針對域外大國的干涉而提出的,多年來美國反對歐洲大國干涉美洲事務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在處理與歐洲大國關系時不僅繼續反對歐洲大國對西半球事務的干涉,而且進一步確立了美國在美洲地區領導大國的地位作用。此時美國在推行門羅主義外交政策時態度更加堅定與自信,在同歐洲大國的交涉中始終占據著優勢,并迫使歐洲的傳統大國做出了妥協讓步。具體表現為:
其一,取代英國成為西半球的主導國。英美關系自從美國獨立戰爭以來一直處于比較緊張的狀態,其間發生過1812年戰爭,這與英美在美洲地區長期的利益沖突有關。1895年委內瑞拉第一次危機時,英美兩國矛盾沖突甚至到了戰爭邊緣。但由于英國實力的衰落和廣泛的殖民地義務,導致英國在其他地區與其它歐洲列強矛盾重重,特別是日益崛起的德國不斷向英國全球霸主地位發起挑
戰,英國自顧不暇的處境令其不得不在美洲問題上讓步,默認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正如亨利·亞當斯所言:“德國作為灰色恐怖突然出現,嚇得英國人投入了美國的懷抱。”?1902年時任英國首相的貝爾福宣稱:“據我所知,門羅主義在這個國家沒有反對者。我們歡迎美國在西半球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美國也對英國的退讓做出了友好的回應。1905年,作為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為此給英國首相寫信指出:“你不必為兩個偉大的英語國家民族間的競爭夢魘所困擾,我從未考慮將英國作為戰爭對象,并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國在美洲的妥協退讓給美國領導西半球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機遇,美國可以名正言順地發揮地區主導國的作用。因此,“20世紀初英美重建友好,在美國外交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西奧多·羅斯福時期英國在美洲的戰略撤退主要體現在向美國做出的三次讓步——中美地峽運河控制權爭奪、阿拉斯加邊界爭端、北大西洋捕魚權問題的解決,這三次讓步使得美國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西半球的主導大國。
其二,阻止域外大國對美洲事務的干涉。在同域外大國的關系方面,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還體現為反對歐洲大國對美洲事務的干涉,美國憑借強大的地緣戰略優勢在與英、德、意等大國交涉時顯得更加自信和執著,這是前所未有的。1895年美國以調停國的身份成功地化解了委內瑞拉與英屬圭亞那之間的邊界危機(即“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從而借助這次調解行為將自己推向了拉美地區秩序維持國的地位。如果說19世紀末美國維持西半球秩序只是為了排除域外大國干涉美洲事務,而且僅是在美洲國家遭遇到歐洲大國干涉的前提下才會出面調節,其維持西半球秩序的行為還是被動的;那么20世紀初隨著美國自身實力的增長和西半球局勢的逆轉,美國的對外戰略逐漸變得更為主動和強勢,尤其是羅斯福對委內瑞拉的干涉使得歐洲大國試圖控制委內瑞拉的企圖落空,同時也保證了委內瑞拉的領土安全和主權完整。羅斯福堅信,“權力只有在愿意和準備用它時”?才能使歐洲大國全面理解門羅主義的含義所在。因此,美國在委內瑞拉債務危機上采取了十分強硬的態度,并最終迫使英國和德國接受美國的仲裁安排。美國憑借美洲地區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優勢迫使英德意三國撤軍、解除封鎖并接受美國的調停。由此可見,在美洲地區無論是傳統大國的英國還是正崛起的德國都沒有強大的實力及資源優勢來與美國抗衡,美國獨特的地緣戰略優勢進一步佐證,在這一地區的美國大國領導地位已非常穩定堅固、難以撼動。
四、大國利益與秩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對美國崛起的影響
西奧多·羅斯福是美國20世紀的第一位總統,在麥金萊通過美西戰爭于1898年把美國帶入世界強國的發展道路后,羅斯福則從美國當時所處的全球和地區國際政治結構入手,推行了新的地區主義政策。羅斯福的地區外交政策是建立在豐富發展與時俱進的門羅主義基礎之上的,通過確立美國的地區領導地位和構建國際秩序目標,進一步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為美國崛起創造了良好國際環境,推動美國在大國崛起道路上不斷前進。
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大國崛起必然伴隨著利益的擴張,只有對海外擴張利益的積極作為才能推動國家的不斷崛起。我們可把20世紀初美國的國家利益分為國家和周邊安全、地區政治影響力、海外經濟利益三種類型。國家與周邊安全是大國生存的攸關利益,地區政治影響力是崛起大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而海外經濟利益則是主導性大國的根本利益。西奧多·羅斯福通過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對美國這三方面的利益進行了進一步鞏固及深化維護,為美國的大國崛起帶來重要作用和影響。
首先,保障了美國在崛起過程中的國家利益和周邊安全。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利益和周邊安全關系到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政治環境,也是大國崛起最基本的基礎條件,更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美國周邊安全利益最大的威脅來自于歐洲列強的殖民和干涉。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
義外交政策以更積極和自信的姿態來應對來自歐洲大國的干涉威脅,并以地區主導國的身份干涉介入拉美地區事務以避免域外的歐洲大國滲透,展現了新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的戰略主動性。
美國在建國初只有大西洋沿岸的13個州,后來領土不斷擴張,領土的擴張使得美國的本土安全利益不斷發生變化。1848年美墨戰爭結束后,美國獲得了加利福尼亞,正式成為一個兩洋國家。東西兩側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作為天然的屏障,再加上海軍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國的本土長期處于一種比較安全的狀態。1903年11月,美國通過與獨立后的巴拿馬簽訂《海·約翰——比諾-瓦里亞條約》,租借了運河區,1904年巴拿馬運河開始動工,這為美國控制這一戰略樞紐,進而更好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和周邊安全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條件。從歷史角度看,1823年門羅總統發表門羅宣言是美國維護其西半球安全的開端,其后美國一直以門羅主義為借口反對歐洲大國對美洲事務的干涉和在西半球進行勢力擴張,迫使作為世界主導國的英國屢屢妥協,最終確立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作用和地位。此后,美國又通過1897年的美西戰爭把西班牙趕出了美洲。到了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時期,新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開始展現門羅主義的積極作為和戰略主動性,美國以主導國的姿態主動干涉拉美地區的國際事務,以避免域外的歐洲大國介入干涉。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使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半球的主導大國,阻止了歐洲大國在西半球的勢力擴張,堅定地捍衛了美國周邊地區的安全穩定,為美國的大國崛起創造了一個安全的地區環境。
其次,增強美國在地區的大國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的主張是:為了維持西半球的地區穩定,美國在必要時可以行使地區干預權利。美國依據這一原則調停了中美洲國家的糾紛,促進了美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同時增強了美國在地區的政治影響力。美國作為一個地區主導大國,開始在美洲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不僅維持了西半球各國的穩定,體現了一個地區主導大國的責任感,而且向地區各國展現出了一個地區主導大國的風采并得到地區各國的認可,這就增強了美國崛起的政治合法性和地區認同感。
1902年,美國參議院批準了保證美國在必要時有干涉古巴內政權力的《普拉特修正案》,不久古巴也將其寫入憲法和美古條約之中。1906年當古巴發生反政府暴亂時,古巴政府向美國求助,羅斯福依據《普拉特修正案》對古巴內政進行了干預,穩定了古巴的政治經濟秩序。1902年委內瑞拉因為國內混亂導致對外債務危機并招致英、德、意三國的軍事干涉,主權領土受到侵犯,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出面干預才迫使三國撤軍接受國際仲裁。此外,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美國還通過主導1901年、1906年的第二、三屆泛美會議及其常設機構開展多邊外交,努力倡導美洲各國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并依據這一原則調停了中美洲國家的糾紛,促進了美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同時強化了美國在地區的政治影響力。美國作為一個地區領導型大國,開始逐步在美洲國際事務中不斷塑造大國形象,履行大國責任。
再次,維護了美國的海外經濟利益。20世紀初由于美國國內壟斷企業資本不斷擴張,迫切要求擴大海外商品資本市場。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適應了這一要求,促進和維護美國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及海外權益,使得美國的地區商業投資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初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它不僅有利于美國經濟的繁榮,而且經濟的持續增長為美國的繼續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為美洲建立了一個相對開放的地區經濟政治新秩序,拉動了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也成為推動美國可持續崛起的內在動力。
西奧多·羅斯福時期的美國,一直推行確保拉丁美洲各國對美國經濟開放的政策,擴大并保護美國在拉丁美洲地區的投資和貿易市場。西奧多·羅斯福的門羅主義外交政策促進了美洲地區的經濟開放。在對美洲的投資方面,我們以美國對墨西哥的投資為例就足以說明:1897年,“美國在整個拉丁美洲的投資還不足3億美元”?;“190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對墨西哥的投資已經達到了5億美元;在1903—1910年間各種投資急劇飆升,到1910年,美國對墨西哥的投資增長到20億美元”?。
而在對美洲的貿易方面,美國比內戰以來任何時候發展都快。“1901年到1910年之間,美國出口美洲的總額由24100萬美元增長到47900萬美元。”?構建開放型的地區經濟秩序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的戰略目標。羅斯福門羅主義外交政策在美洲塑造了相對開放的地區經濟秩序,推動并維護了美國經濟繁榮和地區穩定,這也是美國成為崛起經濟大國的內在驅動力所在。
注釋:
①http://jjlife.joins.com/club/club_article.asp?mode=&ctg_id=&page=1&total_id=15332625.
②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1992,p.197.
③劉若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進展與困境》,《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2期。
④[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閻學通、陳寒溪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89頁。
⑤劉若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進展與困境》,《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2期。
⑥劉若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進展與困境》,《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2期。
⑦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p.93.
⑧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New Jerse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12.
⑨劉緒貽、楊生茂:《美國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頁。
⑩[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94—196頁。
?[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97—198頁。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頁。
?[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陳景彪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98頁。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頁。
?[美]斯蒂芬·斯科夫羅內克:《總統政治——從約翰·亞當斯到比爾·克林頓的領導藝術》,黃云、姚榮、李憲光譯,新華出版社,2003年,第280頁。
?[美]西德尼·M·米爾奇斯、邁克爾·尼爾森:《美國總統制——起源與發展(1776—2007)》,朱全紅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5頁。
?Thomas A.Bailey,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Y.:Meredith Corporation,1969,p.495.
?Jerry Weller,"After 100 years,US still the Panama Canal's biggest beneficiary",The Hill,August 14,2014,http://thehill.com/ blogs/congress-blog/economy-budget/214266-after-100-years-us-still-the-panama-canals-biggest.
?[美]路易斯·奧金克洛斯:《莽撞的麋鹿——西奧多·羅斯福傳》,饒濤、胡曉異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頁。
?[美]沃爾特·拉夫伯、理查德·波倫堡、南希·沃洛奇:《美國世紀——一個超級大國的崛起與興盛》,黃磷譯,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69頁。
?Mark T.Gilderhus,"The Monroe Doctrine: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36,no.1(March),2006, p.9.
?洪育沂:《拉美國際關系史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25頁。
?時殷弘:《國際政治——理論探究·歷史概觀·戰略思考》,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68頁。
?David Dimbleby and David Reynoles,An Ocean Apart,N.Y.:Random House Inc.,1988,p.38.
?黃正柏、梁軍:《從沖突到和解:近代英美關系考察》,《史學集刊》2006年第5期。
?李慶余:《美國外交史——從獨立戰爭至2004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第69頁。
?[美]埃德蒙·莫里斯:《美國崛起的舵手:西奧多·羅斯福》,匡吉等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第150頁。
?徐世澄主編:《美國與拉丁美洲關系簡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84頁。
?張爽:《美國崛起之政治經濟學分析(1865—1945)》,北京:時事出版社,2012年,第227頁。
?Th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 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536。轉引自張爽:《美國崛起之政治經濟學分析(1865—1945)》,北京:時事出版社,2012年,第215頁。
Monroe's Foreign Policy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Yang Luhui/Ren Lvbo
The rise of big country must go beyond region to the world and become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logic for all big countries.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the Monroe's foreign policy carried out by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is the result of US'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issues.The political ecology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rise of the States.Monroe's foreign policy deals proper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s and neighbor countries,and created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It secured the United States'economic profit and orders.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Monroe Doctrine;Foreign Policy;Theodore Roosevelt
D871.2
A
1009-3176(2015)05-071-(10)
(責任編輯 方卿)
2015-4-20
楊魯慧 女(1956-)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山東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任綠勃 男(1988-)湖北武漢陽光凱迪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