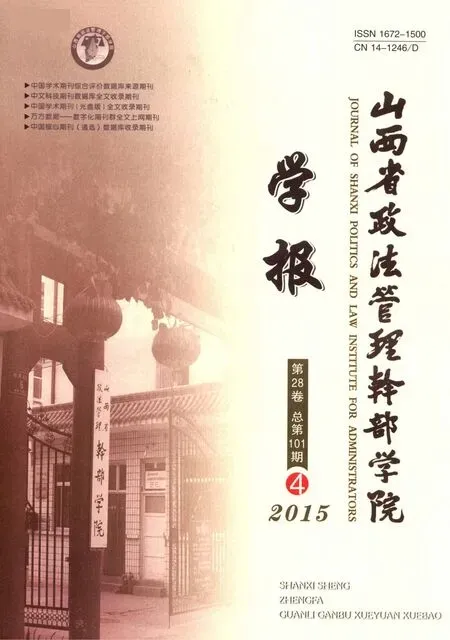未成年人刑罰適用問題探究
辛瀟瀟
(天津市寶坻區人民檢察院,天津301800)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嚴重性日益突出,甚至被列為環境污染與毒品犯罪之后的第三大社會公害。對此,法學理論界與司法部門從不同角度予以了高度關注,并在實踐中進行了大量有益的嘗試和探索。依據《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即《北京規則》)與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要求和相關規定,公檢法三部門分別就辦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標準及法律適用出臺了具體的解釋和規定,司法實務中體現了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核心內涵,然而不同方面的認識分歧仍然存在。在此,筆者擬就未成年人犯罪之刑罰的刑種適用與從量刑情節的適用談一些個人觀點,敬請各位同仁斧正。
一、無期徒刑的適用
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適用無期徒刑,理論界的否定觀點比較突出。其理由是:根據《刑法》第四十九條,未成年人不得適用死刑,因而其法定最高刑就是無期徒刑。但《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由于無期徒刑沒有上下浮動的任何幅度,從輕或者減輕不可能在無期徒刑的范圍內實現,所以在此前提下,如果體現從輕或者減輕的原則,只能不適用無期徒刑而以有期徒刑替代。這也是有些學者明確提出的觀點。[1]這一理由明顯違背邏輯規律,混淆了法定刑與宣告刑兩個概念。我國沒有針對未成年人的單獨刑法,任何人犯罪適用的都是同一部法典。以故意殺人罪為例,其基本犯的法定刑是死刑、無期徒刑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沒有任何法定、酌定的從輕、減輕情節時,應當宣告的刑罰也必須遵循這一順序。如果被告人未滿18周歲,按照法定刑宣判應當是死刑,引用第十七條第三款以后減輕為無期徒刑,這就是宣告刑。那么是否還有必要推翻這一法條適用的順序,在量刑之前首先引用第四十九條,直接降低為無期徒刑以后再引用第十七條第三款,對被告人的刑罰再一次予以從輕或者減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應當判處的死刑減輕宣告為無期徒刑,它同時已經符合了第四十九條的禁止性規范,沒有必要將這一量刑原則混淆為類同第十七條第三款的量刑制度。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適用無期徒刑。
二、罰金和沒收財產的適用
罰金刑主要是針對貪利性犯罪,目的是限制犯罪人再犯經濟類的刑種。實踐中,罰金的適用同樣眾說紛紜,而事實上,它確實優劣并存。
主張擴大適用罰金刑的理由是:第一,對未成年人適用罰金刑不違背我國刑法規定的罪責自負原則。雖然科以未成年犯罪人的罰金基本是由其監護人代繳,但監護人疏于管教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之一,因而他們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況且即便是成年人的犯罪,其罰金刑由其家人或親屬代為履行的亦不罕見,所以不能僅以未成年人無能力履行而單純認為它違反刑法原則。第二,有利于預防未成年人犯罪。貪利性是未成年犯罪的主要表現之一,因而對此類犯罪處以罰金,可以憑借貪利反而破財的報應方式,使其心理遭受更加沉重的打擊,預防再次犯罪。第三,以單處罰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可以有效防止未成年犯在監管場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第四,罰金刑具有經濟性、開放性、匿名性,因此對未成年犯科處罰金符合“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也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
但是,不能否認適用罰金刑也存在弊端:第一,罰金刑適用于沒有固定收入的未成年人,必然要由其監護人代為繳納,事實上是變相的株連。名義上接受處罰的未成年人不可能因繳納罰金而感受到刑罰的懲罰性質和威懾力,因而也就難于體現刑罰的社會功能。第二,類比其他刑罰,罰金刑不具有人身性,因而相同數額的罰金對于不同的人絕非同一概念。在經濟狀況相差極大的情況下,貧富之間的差距使承受者對等額罰金的感受必然異常懸殊。所以,這事實上導致了刑罰的不平等。第三,執行難。部分未成年人的貪利性犯罪不排除經濟困難的誘因,這種情況下罰金刑的科處很容易形成一紙空文,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法律的威嚴性。第四,可能形成刑與罰之間的轉移。罰金雖然作為附加刑,但是可以獨立適用。不能排除因此而導致部分法院將是否實際繳納罰金作為是否判處自由刑的標準,形成刑與罰互相替代的情況。這不僅使刑罰失去了應有的意義,而且可能本末倒置為偏移的社會理念。
綜上,筆者認為,對于罰金刑應當適度限制適用。既不能因其存在缺陷而有所偏廢,也不能由于其片面的積極效應而趨之若鶩。適用罰金刑,必須考慮以下三個因素:必要、適當、現實。更加有效的改革方案是易科制度的實行,即以無償的公益勞動代替罰金。對于年滿16周歲以上的未成年犯,可以根據不同情況科處其一定時間的無償公益勞動,這不僅能使刑罰罰當其罪、罰當其人,而且更能收到教育和改造的實際效果。英、美等國家以無薪社區服務作為一種處罰方式,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2]至于沒收財產,根據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參加工作時間有限,不可能積累過大的財產數額,因而科以這一刑罰也不會具有多大意義,筆者認為以不予適用為宜。
三、從重情節的掌握——兼析累犯的適用
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同時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是常見現象。由于《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必須適用,故這種情況下必然出現量刑情節的反向競合。司法實踐中并未對未成年人予以毫無節制的放縱。立法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寬容絕非終極目標,遏制和預防犯罪,防止重新犯罪才是真正目的。然而綜觀目前各種理論觀點的發展趨勢,似乎于各種犯罪的量刑和處罰,年齡都成了天平一側越來越重的砝碼——只因未滿18周歲,就可以受到各種相對優越的處遇。但是,從維護社會正義的角度出發,年齡也絕非應當是唯一的砝碼。僅以筆者曾經辦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來看,不少人的心理與生理成熟程度已經遠遠超越實際年齡,而其犯罪時的表現與逃避處罰的能力更加遠甚于一般成年人,心理素質實非“未成年”三字所能衡量。對于具有其他法定、酌定從重處罰情節的未成年犯,法律適用應當遵循這樣的次序,即確定基本刑罰之后適用從重情節,然后考慮第十七條第三款的幅度,但是最高限制應以第四十九條為原則。宣告刑罰允許高于同等罪責而無任何從重處罰情節的成年犯。
之所以對累犯特殊強調,不僅因為《刑法》總則第六十五條規定了應當從重處罰,而且第七十四條和第八十一條第二款還分別再次明確,“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不得假釋”。這標明了我國刑法對累犯的重視和懲罰力度。但累犯如何適用于未成年人,則同樣眾說紛紜,有學者主張對未成年人不以累犯論處。[3]筆者認為對未成年犯追求極度的寬容,那么社會的正義置于什么地位?被犯罪所侵害的受害人是否需要公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犯罪的未成年人,無論怎么犯罪、多少次犯罪,都會受到寬容的處罰,真的能使他們有所警覺,從而迷途知返,并有效地預防犯罪嗎?恐難盡人意。《刑法》第一條就明確其制定是“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第十七條第三款固然是因為未成年人自身的特點而設置的,但前提也不能排除其不懂法、不更事而特別賦予的社會包容。打個簡單的比方,父母訓誡犯錯誤的孩子,第一次總會寬容些,但同時也必然警告再犯要受到重責。而未成年人不適用累犯的論調則幾乎等同于這樣的說法:錯誤隨便犯吧,不滿18周歲永遠從寬。棍子總不舍得落下來,還會有人害怕嗎?其引申后果會呈現什么狀態,實在殊難逆料。所以,寬容不能無限地蛻變為縱容,不能僅僅因為“未成年”三字而一味地買好示惠。事實上,這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嘗不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那些執迷不悟者恐怕不會將此理解為社會的保護和接受,反而能把不滿18周歲作為變本加厲危害社會的本錢。
累犯于未成年人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未滿18周歲而第二次犯罪的,一定是累犯;未滿18周歲時曾經犯罪,成人以后再次犯罪的,也存在構成累犯的可能。因此,筆者主張對于未成年累犯的處罰應當有限度地適用第十七條第三款,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不是十分突出的犯罪可以適當從輕,但絕不能減輕于法定刑幅度之下;對于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8種犯罪,則應明確體現累犯的從重處罰后果。刑事立法和司法所維護的,應當是整個社會的利益和秩序,著眼點應當在于多數群體。在未成年人犯罪日益膨脹的高潮面前,不能由于未成年人需要保護就只重視寬容而失去理性,我們更需要重視伸張社會的正義。
[1]李文峰.對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適用無期徒刑[J].法律適用,2000(7).
[2]張孟東.未成年人適用罰金刑問題研究[J].鄭州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1).
[3]張 蓉.加強未成年人保護 完善我國累犯制度[J].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