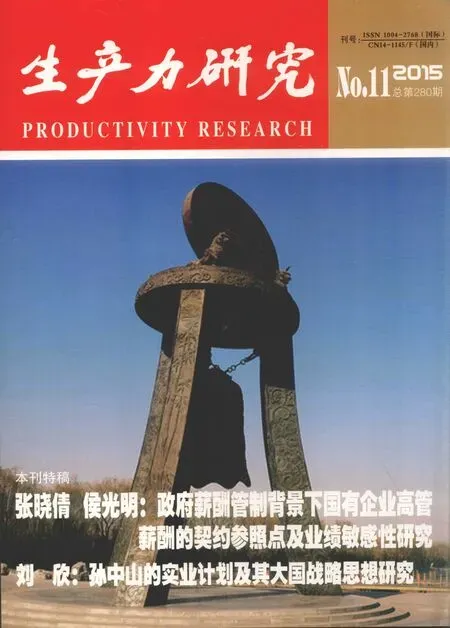論楊萬里薄賦節用、富民寧邦的經濟思想
陸雙祖,孫玉霞
(1.甘肅政法學院 人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2.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192)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南宋著名的詩人,杰出的理學家、政治家。楊萬里的青少年時期,時代氛圍極為特殊,與他同年誕生的南宋王朝被迫偏寄江南一隅,家仇國恨集于一身,救國圖存,收復中原成為時代最強音。當時,人們的政治熱情極為高漲,稍有民族氣節的宋人都投身于抗金救亡的行列。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楊萬里也將救亡圖存,收復中原作為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標。他走上仕途后就開始積極研究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原因,探尋富國強兵之道。
南宋王朝寄身江南,國土與北宋相比,雖然減少了將近一半,但是,農業生產最豐富的江、淮、湖、廣等地都屬南宋版圖。這些地區物產豐饒,商業發達,但據宋史記載:“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1]南宋王朝有肥田沃土,有大商巨賈,但國庫空虛、經濟拮據、費用僅為“粗給”,其民眾境況就可想而知。據史載,南宋初期“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絕如絲”[2],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楊萬里特殊的人生經歷,多年的州官、地方官生涯,加之兩度進京為官,使他對南宋的社會矛盾有全面深刻的認識。面對這種國貧民弱,內外交困,人心渙散的局面,楊萬里提出了“國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氣,國之命在民心”[3]1102“保國之大計在于結民心,結民心在于薄賦斂,薄賦斂在節財用”[3]1121的政治、經濟思想。
一
楊萬里繼承了儒家民為邦本的政治思想。他認為要救亡圖存,收復中原,首先要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的前提是社會安定,要使社會安定,則必須使民眾能休養生息、安居樂業。但當時的社會現實卻是民不聊生、人心渙散,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宋室南渡以后,統治者一方面利用政治權力大力侵占兼并土地。另一方面,以抗金為名,進行橫征暴斂。楊萬里在《千慮策·民政》[3]1425中例舉江西屯田者的境遇曰:“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原因在于“租重。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于官,不瘐死,不破家則不止”。可見,農民種地越多,耕作越勤懇,則離家破人亡越近。而商人的境遇與農民大體相當,其《得臨漳,陛辭第二劄子》[3]1106云:“綱運所過,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為名,冥搜細索,秋毫必征。”他在《轉對劄子》中對這種掠奪式的“冥搜細索,秋毫必征”有極為具體詳細的描述:
今之財賦,有地基茗課之征,有商賈關市之征,有鼓鑄榷酤之入,有鬻爵度僧之入……。而取于農民者,其目亦不少矣!民之輸粟于官者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也,今則以二斛輸一斛矣。民之輸帛于官者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也,今則正絹之外又有和買矣。民之鬻帛于官者謂之“和買”,舊之所謂“和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則無錢與鹽矣。無錢尚可也,無鹽尚可也,今又以絹估直,倍其直而折輸其錢矣。民之不役于官而輸其僦直者謂之“免役”,舊以稅為錢也,稅畝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歲增其額而不知所止矣。民之以軍興而暫佐師旅征行之費者,因其除軍帥謂之“經制使”也,于是有“經制”之錢。既而經制使之軍已罷,而“經制錢”之名遂為常賦矣。因其除軍帥謂之“總制使”也,于是有“總制”之錢。既而總制之軍已罷而“總制錢”又為常賦矣。彼其初也,吾民之賦止于粟之若干斛,帛之若干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數倍其錢之名矣;而又有“月椿”之錢,又有“板帳”之錢,不知幾倍于祖宗之舊,幾倍于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臣所知者也。至于蜀民之賦,其額外無名者,臣不得而知也。[3]1121
作為上書言事的公文——劄子,其內容應該是社會現實狀況的真實反映。從楊萬里此書可見:首先,南宋的稅賦征及領域“廣泛深入”,涉及的群體“全面周詳”。只要政治權力能關涉到的范圍就可征稅,只要能和民眾沾邊的物事就能征稅,只要執政者能“想到的”與民眾可以沾邊的物事都得征稅。其次,南宋沒有科學合理的賦稅制度,稅種稅額全由官吏隨意確定,以致稅賦名目繁多、五花八門。例如農民,其生產資料本為土地,生產行為就是耕作土地,而來自于土地的收入就是農作物。但是,他們不但要繳納來自土地的收成——糧食,還要繳納不是來自土地的收成——絹帛,更要繳納名目繁多的錢款。這些賦稅名目,有的屬于常賦,如“苗”“稅”等,而大部分則為“與時俱進”所產生的新賦 ,如“ 和 買 ”“ 免 役 錢 ”“ 經 制 使 ”“ 總 制 錢 ”“ 月 椿 錢 ”“ 板 帳錢”等。再次,政府任意向民眾重復征稅,社會危害極大。就如農民納“苗”輸粟,明明兩斛,卻合算一斛,明晃晃強迫農民繳納雙倍的“苗”稅,還要瞞天過海,自欺欺人地宣揚農民是按常規繳稅的。而納“稅”輸帛更與明搶沒有區別,所謂“和買”者,自然是一方愿買,一方愿賣。但南宋的“和買”卻是民眾最為沉重的負擔之一,因為朝廷雖言“買”卻不付費,實為重復征稅,而且沒有限度、沒有定時、沒有規則,只要朝廷或地方政府有意外開銷、或者缺絹少帛,就可以“和買”為名進行征收。正如楊萬里在《民政》中所言“始乎為市,終乎抑配,……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愿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于正租,實為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準衣’者,亦例為正租矣”。所以百姓和一些地方官吏往往聞“和”色變。就如楊萬里《與湖廣總領林郎中》[3]1759中所言:聞“和糴米二萬石,此聲一傳,民戶駭懼”。而《與淮西韓總領》[3]1760也曰:聞“收糴米七萬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恟懼,不知所出”。足見其危害之大。
《轉對劄子》作于光宗紹熙元年,此時,南宋建國已達六十四年,這應該是南宋一百五十年中政治最為清明,經濟最為繁榮興盛的時期。因為,此時雖然進入了光宗時代,但延續的政治經濟策略依然來自于孝宗朝。而宋孝宗是南宋歷史上最有抱負,最有作為,最為清明,最有仁政思想的皇帝。他多次詔令清除繁雜的稅種,蠲免民眾沉重的賦稅。但民眾依然要承擔如此繁雜沉重的稅賦,窺斑見豹,南宋的民眾在其他昏庸無道或軟弱無能的皇帝治下會負擔多少稅賦就可想而知。
二
楊萬里認為南宋對民眾的剝削壓榨除了征收名目繁多,數額巨大的賦稅以外,還包括各種不合理的經濟政策。南宋統治者雖然征收幾倍于前朝的賦稅,但總是倉廩空虛、入不敷出,于是就寅吃卯糧,頒布各種新的經濟政策如“和買”“預借”“改鈔”“會子”等,向百姓進行殺雞取卵、涸澤而漁式的經濟掠奪。一方面“預借民間來年之租”,以“預借”為名提前征收明年的賦稅。另一方面,又以“改鈔”為名,用今年的賦稅填補往年的虧空。如楊萬里在《上殿第二劄子》中所言:
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何為改鈔?縣以新鈔而輸之,州必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止有一政之財賦,今也不然,今歲所輸,往往改鈔以補去歲之虧,甚者或以補數歲之虧;後政所輸,往往改鈔以償前政之欠,甚者或以償累政之欠。是以歲歲有負,任任有逋。廣右以有此弊矣,江浙又甚焉,至有一縣必令償十馀萬緍之逋者。[3]1108
民眾當年繳納當年的稅賦,一任執政者征收一任的賦稅,如此清楚明白的事情,但南宋執政者卻“借來改去”,使其變得異常復雜。民眾不但不能因為去年預交了賦稅而今年免責,反而還要以填補“積欠”的名義,繳納去年,甚至前年,更甚至很多年前的賦稅。楊萬里認為此做法極為不合理,既為“積欠”,自然有積欠的緣由,“夫所謂積欠者,或以兇荒而減免,或以恩霈而蠲除,或窮民逋負而不可償,或貪吏奄有而不可校”。顯然,“積欠”所欠者,或者是因天災所減免,或者是因蒙恩所蠲免,或者是因百姓困無所出而作罷,或者是因官吏貪腐而無法計量,總之是有名無實,不可再取的。但“改鈔”之策卻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硬性地使有名無實之稅變為有名有實之稅。楊萬里認為,如此之策“是特其名存耳,以其名而責其實,從何出哉?不過驅縣令以虐取于民爾”。此論真是切中肯綮!他認為民力民財自有限度,這種超限度的榨取,無異于上層統治者驅趕下層官吏以暴政對民眾進行敲骨吸髓式的掠奪。
北宋時,海外貿易繁榮,隨著貨物的出口,銅錢大量外流,“邊關重車而出(流往遼境),海航飽載而歸(流往海外)”。[4]因此,在北宋晚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錢荒現象。宋室南渡以后,一方面,鑄幣能力下降,一般年鑄幣不過八萬貫,最多的年份也只有十六萬貫;另一方面,銅錢外流屢禁不止,錢幣依然大量流往海外。同時,國內有錢人囤積居奇,將銅錢窖藏起來,如楊萬里所言:“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官,權貴將相,皆殷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泄,泄而不流。”[3]986所以,錢荒問題比北宋更為嚴重。南宋政府為了解決錢荒,在杭州專門成立機構“行在會子務”,大量發行紙幣。紙幣名頭也很多,如“會子”“川引”“淮交”“湖會”等。這些紙幣多限定在特定的地區使用。理論上,紙幣與金屬錢幣可以按照規定的比例自由兌換。但因政府沒有足夠的錢幣作為兌換紙幣的本錢,而紙幣的印造卻與日俱增,這使紙幣越來越貶值。到后期,南宋政府竟不許民戶用紙幣繳納課稅。楊萬里在紙幣發行初期,就堅決反對此經濟政策。他認為解決錢荒,應以朝廷干預的方式促使錢幣流通,而不是大量印造紙幣自欺自人。其于淳熙十二年給宋高宗的《上壽皇論天變地震書》[3]983中就將此列為當時的十大急務或者說十大政治失誤之一。他指出一方面有錢人囤積錢幣,另一方面,國庫空虛,錢幣儲備匱乏,以致“至于百姓三軍之用,則為破楮券爾”。他進而發問“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顯然,其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明確指出那些持“楮券可以富國”之論者,無異于禍國殃民。而大量發行紙幣,自然是禍國殃民。
紹熙三年七八月份,朝廷欲將通行于兩淮的鐵錢會子在江南諸郡作為軍餉發行。當時,南宋為了防止銅錢外流,在長江以南地區使用銅錢,而在長江以北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等邊境地區使用鐵錢。而與錢幣相應,其紙幣“會子”也分為兩種,銅錢的代用紙幣叫“行在會子”,鐵錢的代用紙幣叫“新會子”。“會子”的發行,其主要目的是緩解金屬稀缺、鑄錢不足的壓力。會子在流通過程中,由于兌換不等價,通貨膨脹等因素,人們普遍重錢輕會子,收到會子,常常會盡快兌換為金屬錢幣以保值。現在朝廷詔令在使用銅錢的江南地區發行新會子,而且先作為軍餉使用。時為江東轉運副使的楊萬里認為此詔令漏洞百出、邏輯混亂、弊端顯而易見。他一方面拒絕接旨,另一方面,作著名的《乞罷江南州軍鐵錢會子奏議》,上書朝廷,陳述其弊。現將該奏議的核心內容擇錄如下:
蓋見錢之與會子,古者母子相權之遺意也。今之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鐵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今之新會子,鐵錢之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后錢、會相為用。會子之法曰:“會子并同見錢行使。”今新會子之法曰:“每貫并準鐵錢七百七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交子止許兩淮及沿江八郡界內公私流轉行使。”且會子所以流通者,與錢相為兌換也。今新會子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足,則明然為鐵錢之會子,而非銅錢之會子矣。淮上用鐵錢,用新會子矣。前有會子,斯有見錢可兌矣,是母子不相離也。江南禁鐵錢而行新會子,不知軍民持此會子而兌于市,欲兌銅錢乎?則非行在之會子,人必不與也;欲兌鐵錢乎?則無一鐵錢之可兌也。有會子而無錢可兌,是無母之子也,……江南官司以新會子發納左帑內帑,左帑內帑肯受乎?左帑內帑萬一不受,則百姓之輸官物,州縣亦不受矣。州縣不受,則是新會子公私無用,上下不受,而使鎮江、建康兩稅入納,雖入納百萬而行使不通,不知將何用也?若止欲用之于軍人之支遣,百姓之交易其肯受乎?萬一有受有不受之間,此喧爭之所從起,而紛紜之所從生也。[3]1134
楊萬里在此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地闡明了四個觀點:第一,在江南發行“新會子”缺乏配套的經濟政策。銅錢與鐵錢各自流通的地域不同,而且法律明文規定不能越界使用。會子僅為錢幣的代用券,它們依附于相應的錢幣,各自的兌換規則不同。當時,人們對銅錢、鐵錢與會子的價值認可度更不同。人們普遍貴銅錢輕鐵錢,貴錢幣輕會子。所以,楊萬里認為,在使用銅錢的地域發行鐵錢會子,即使可行,其兌換折算就是一大難題。第二,在江南發行“新會子”與當時的經濟法規相沖突。南宋法律規定,銅錢的代用券為行在會子,鐵錢的代用券為“新會子”。錢幣與相應的會子之間形成了“母”與“子”的對應關系。會子與相應的母錢之間可以互相兌換,但非“母”“子”之間不可以交替兌換。以此為據,楊萬里認為,在僅流通銅錢的江南地區,新會子作為鐵錢的代用券是無母錢可兌的。當其兌換不成金屬錢幣時,無異于廢紙一張。第三,江南發行新會子之決策缺乏可行性。楊萬里認為,錢幣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價值在于能夠流通,能夠等價交換。當時,無論朝廷還是個人,雖然普遍貴錢幣輕會子,但不能否認會子所具有的“錢”的屬性。朝廷發行會子,一方面在于減輕金屬錢幣供應不足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欲通過此策將民眾手中的金屬錢幣收歸國庫。但是,此破綻百出之策顯然無法實現其目的。楊萬里對此洞若觀火。因而,他向朝廷發問:假如江南各州縣以“新會子”作為國稅上繳國庫,國庫會收納嗎?顯然不會。國庫不收納,州縣衙司就會拒絕民眾以新會子為賦稅錢。州縣衙司不收納,民眾自然不認可其“錢幣”的性質,不會以其為等價交換物進行交易。那么,一種“公”與“私”都不認可的“錢”還會是錢嗎?顯然,朝廷制定此策缺乏嚴謹的論證。如果朝廷強行推行此策,純粹為擾民之舉。第四,錢幣的發行事關重大。楊萬里在《上壽皇論天變地震書》中曰:“古者足國裕民,為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3]986他認為“食”與“貨”是民之本、國之本。會子既為當時的通貨——銅錢、鐵錢的替代品,則其必然具備通貨的屬性,其價值只能在流通周轉中體現出來,并非如旌表、詔告張貼出去,其價值就已實現。而朝廷卻“令江南八州軍袞同流轉”,僅以新會子為江南駐軍的軍餉。這意味著,軍務部門則需要以其為資采購軍需,軍人需要以其為資養活家小。但是地方政府以及民眾都不認可其“錢”的性質,拒絕以其為質進行交易。在此情形下,駐軍與地方民眾的矛盾在所難免,社會動蕩因而會產生。更為嚴重的是,當新會子無法體現其“錢”的價值時,無異于廢紙一張。此時,戎戍官兵有被朝廷欺騙耍弄之感,對朝廷的怨恨情緒自然會滋生。如果因此引起軍人嘩變,后果不堪設想。因此,他懇請朝廷“此事必出圣斷,力賜寢罷江南八州行使鐵錢會子指揮,庶幾沿江軍民得以安靖”。綜上所述,楊萬里認為貨幣政策事關民眾的安寧,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全,頒布新政必須要慎之又慎。
三
楊萬里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攘外必先安內,富國必先寧邦,寧邦必先安民,安民必須使民眾能夠休養生息。他認為南宋的橫征暴斂在毀掉民眾生活的同時,在逼民為寇,毀掉國家的根基。因為“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其私,則不得不取于官。于是飲食衣服之用,資糧屝屨之用,補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3]1106民眾忍辱負重,只為能繁衍生息,當最低的需求——生存都沒有保障時,只能鋌而走險。因此,他從“保國”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保國之大計在于結民心,結民心在于薄賦斂,薄賦斂在節財用”的具體措施。
楊萬里曾曰:“能節用而后能愛人,能不傷財而后能不害民。”[3]992其認為國家費用有可節者,有不可節者,“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是不可節也。至百官之冗,百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不可求所以節之乎?”他主張節用應從上而下,最高統治者應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方可有效。其在《見執政書》[3]1019中曰:“清介廉潔之行,此豈非天下之所難?而貴富饒樂之事,此豈非天下之所利者耶?君子于所難者,有諸身而后可以責諸民。于所利者,無諸身而后可以譏諸民。”因此,他在《轉對劄子》[3]1123態度堅決地指出:“今竭東南之財而支天下之全費,見內帑之富而忘斯民之日貧……節財在陛下而已。”且引用韓琦語“欲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要求南宋朝廷沿用祖制,制定節用法令,取消皇室私藏,裁減內廷不急之需。然后裁節宮室、車服、祠祀之過制,清理百官、百吏、三軍之冗食,取消中外官賜之濫費。只有如此,“蓋用節而后財可積,財積而后國可足,國足而后賦可減,賦減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寧。”
南宋“重租”使得雖有肥田沃土,但卻無人耕種,尤其是兩淮等邊疆地區土地的撂荒情況更為嚴重。楊萬里建議朝廷制定切實可行的蠲免措施,授民以田,免費提供耕牛種子等,吸引民眾在邊疆進行屯田。這樣既可以掩敵耳目,以農為兵,如其所言:“農以兵食,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又可以發展邊疆的農業生產,節省國防開支。如其預期“不出十年,兩淮無余田而有余谷,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3]1429其次,楊萬里上書朝廷,建議“綱運所過,稅場不得苛留以檢稅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必議其罪”。[3]1107他認為只有通過嚴刑峻法,取消水旱兩路沿途設置的層層關卡和重重稅收,才能使“舟不住則漕運之至者甚速,稅不檢則商販之微者可附”。再次,楊萬里建議取消“和買 ”“ 改 鈔 ”“ 免 役 錢 ”“ 經 制 使 ”“ 總 制 錢 ”“ 月 椿 錢 ”“ 板 帳 錢 ”等害民傷民的經濟政策,使民眾能夠休養生息。同時,建議朝廷輕徭薄賦,還富于民,使民眾能夠安居樂業。
綜上所述,楊萬里認為“其政理者,其財給”[3]1038,只有朝廷施行仁政,肅清吏治,開源節流,輕徭薄賦,散富于民,使民眾能夠休養生息,安居樂業,如此才能締結民心;而民眾富足,民心齊聚,則國家自然會富強安定。楊萬里生活的時代距今已逾八百年,其社會形態,生產方式、人情世故等與今有很大區別。但是楊萬里所倡導的執政理念與我們今天所倡導的建設和諧社會、法治社會、全民奔小康的社會理念相一致。借古鑒今,其所提出的富國安邦的經濟思想對于我們發展當代社會經濟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1][元]脫脫,等撰.宋史·食貨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7:3438.
[2][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6.
[3][宋]楊萬里.楊萬里詩文集[M].王琦珍,整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4][元]脫脫,等撰.宋史·食貨志·錢幣篇[M].北京:中華書局,1977:3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