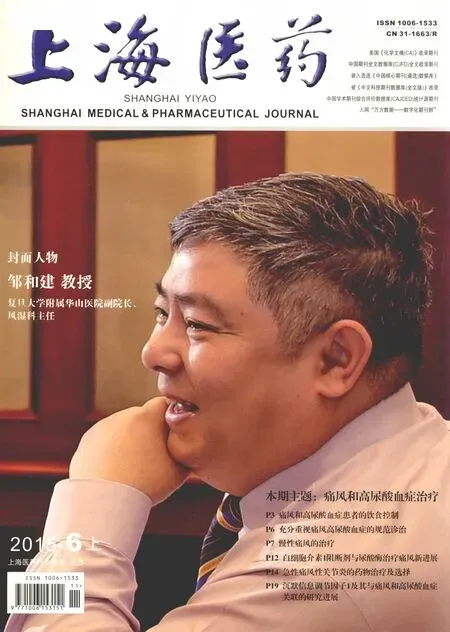慢性痛風的治療*
楊雪薛愉 鄒和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風濕科 上海 200040)
慢性痛風的治療*
楊雪**薛愉 鄒和建***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風濕科 上海 200040)
痛風發病率逐年增加且易反復發作,遷延不愈會發展成為慢性痛風。慢性痛風可累及多種器官并引起多種合并癥,從而對機體造成更大的危害。現有對痛風治療的研究報告大多以急性痛風發作為對象,而有關慢性痛風的治療研究不多。慢性痛風因有痛風病情反復發作的特點,更需要長期、持續和綜合的治療。本文全面介紹慢性痛風的臨床表現、治療及合并癥的治療。
慢性痛風 臨床表現 藥物治療 合并癥
痛風是一種嘌呤代謝紊亂所導致的疾病。隨著飲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痛風的發病率明顯上升并呈年輕化趨勢。痛風的表現多以急性發作(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為主,初次發作常可自行緩解,但因疾病本身特點,會再次或反復發作。隨著痛風反復發作和持續的高尿酸血癥狀態,將累及機體多種器官并出現多種合并癥,對機體造成較大的危害。本文就慢性痛風的治療進行綜述。
1 臨床表現
慢性痛風常繼發于急性痛風反復發作或者急性痛風未經治療或治療不當后,部分患者可無明顯的急性痛風癥狀。急性痛風常累及第1跖趾關節、足背、踝、足跟、膝、指、腕和肘關節等處,會因反復發作而演變成多關節炎并進入慢性期。慢性期的關節炎發作將越來越頻繁,間歇期縮短,同時疼痛逐漸加劇,甚至在發作后不能完全緩解。受累關節數也將逐漸增多,嚴重者可累及肩、髖、脊柱、骶髂、胸鎖和下頜等關節及肋軟骨,出現肩背痛、胸痛、肋間神經痛和坐骨神經痛等癥狀,晚期可表現出多關節的腫大、僵硬、畸形和活動受限。
對慢性痛風患者的血液檢查可見其血尿酸水平升高,滑囊液檢查可見尿酸鹽結晶,通過偏振光顯微鏡觀察痛風結節的活組織檢查標本可發現大量的尿酸鹽結晶。X線檢查可見受累關節的關節間隙變窄,軟骨下骨質有不規則或半圓形的穿鑿樣缺損,邊緣銳利,缺損邊緣骨質可有增生反應。同時,因尿酸鹽結晶沉積于關節附近的肌腱、腱鞘和皮膚結締組織,形成大小不一的痛風石,而痛風石沉積處皮膚可出現破潰、形成瘺管,有白色糊狀尿酸鹽結晶析出,并仍可伴有反復的急性痛風發作。因此,慢性痛風的確診常無明顯的時間界限,主要以臨床表現及病程為參考進行確診。
2 治療藥物
慢性痛風治療以降低血尿酸水平為主要目標,同時應對痛風石及可能并發的腎臟疾病等合并癥進行治療,必要時對痛風石進行外科手術處理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對慢性痛風患者的降血尿酸治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012年美國風濕病學學會在其發布的慢性痛風治療指南中提出:所有痛風患者的降血尿酸治療目標是血尿酸水平<6 mg/dl,但對有痛風石者應降至<5 mg/dl。在降血尿酸藥物選擇上,推薦首選旨在抑制尿酸生成的黃嘌呤氧化酶抑制劑別嘌醇和非布司他,以從“源頭”上抑制尿酸生成。此外,在長期服用降血尿酸藥物治療過程中,還應對關節內尿酸鹽結晶快速溶解而誘發的急性痛風進行藥物預防。
2.1 抑制尿酸生成的藥物
2.1.1 別嘌醇
別嘌醇主要通過抑制嘌呤代謝過程中的黃嘌呤氧化酶而抑制尿酸的生成,初始治療劑量不應超過100 mg/d,中、重度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應從更低的劑量(50 mg/d)開始用藥,然后逐漸增加劑量,直至找到適合的維持劑量。維持劑量可以超過300 mg/d,甚至慢性腎臟病患者用藥也可超過此劑量。但對服用劑量大于300 mg/d的患者,應該注意瘙癢、皮疹和肝酶水平升高等現象,以盡早發現嚴重藥疹例。別嘌醇的常見不良反應有皮疹、胃腸道反應、骨髓抑制和肝功能損害等,對長期用藥者需定期檢測血常規和肝功能。目前臨床上還可對患者進行HLA-B*5801快速聚合酶鏈反應檢測,以用來幫助甄別適用別嘌醇的患者人群,因檢測陽性者服用別嘌醇后發生皮疹和肝酶水平升高的幾率較陰性者明顯更高。
2.1.2 非布司他
非布司他的作用機制與別嘌醇相同,但因具有獨特的非嘌呤分子結構,能更特異性地抑制黃嘌呤氧化酶[1]。非布司他的獲準適應證為具有痛風癥狀的高尿酸血癥患者,可用于治療輕、中度腎功能不全的痛風患者,但不推薦用于無癥狀的高尿酸血癥患者。非布司他的推薦初始治療劑量為40 mg/d;2周后,對血尿酸水平仍>6 mg/dl的患者,推薦提高劑量至80 mg/d。非布司他的常見不良反應包括肝功能異常、胃腸道反應、皮疹和心血管系統的不良反應等,但其不良反應較少并可用于輕、中度肝或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未來臨床應用前景良好。
2.1.3 奧昔嘌醇
奧昔嘌醇是Cardiome公司研制的藥物,是別嘌醇的活性代謝物,適用于別嘌醇治療無效的患者。
2.2 促尿酸排泄的藥物
2.2.1 苯溴馬隆
苯溴馬隆能抑制尿酸在腎小管的重吸收、促進尿酸排泄,降血尿酸水平作用較強,對成人的推薦治療劑量為50 ~ 100 mg/d。美國曾發現服用苯溴馬隆后導致肝功能衰竭例,故該藥已被美國FDA禁用。在中國,由于苯溴馬隆引起的嚴重肝功能損害例相對少見,臨床上仍在使用,但應慎用于尿路結石的患者。苯溴馬隆的其他不良反應包括偶有輕度胃腸道反應或過敏性皮炎等。
2.2.2 丙磺舒
丙磺舒能抑制尿酸在腎小管的重吸收、促進尿酸排泄。2012年美國風濕病學學會發布的慢性痛風治療指南推薦,使用單藥促尿酸排泄時首選丙磺舒,但對肌酐清除率<50 ml/min的患者不應單用丙磺舒作為一線藥物,且尿路結石的患者禁用。丙磺舒的初始治療劑量為每天2次、0.25 g/次,1周后增加至每天2次、0.5 ~ 1.0 g/次。丙磺舒的不良反應較大,易發生過敏和惡心、嘔吐等,6-磷酸葡萄糖脫氫酶缺陷患者服用后還可能出現溶血性貧血。
2.2.3 氯沙坦
氯沙坦屬非肽類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常用于高血壓治療。氯沙坦降低血尿酸水平的機制為阻斷尿酸重吸收的陰離子交換途徑,從而降低達40%的尿酸在近曲小管的重吸收、促進尿酸排泄,是一種既能降壓、又能改善和糾正高尿酸血癥的藥物,對伴有高尿酸血癥的高血壓患者治療具有重要價值。
2.2.4 非諾貝特
非諾貝特為第二代苯氧芳酸類藥物,是臨床上常用的調脂藥物,也可通過促進尿酸排泄而降低血尿酸水平[2],可用于伴有高尿酸血癥的高脂血癥患者的治療。Bastow等[3]進行的一項臨床對照研究顯示,非諾貝特降低血尿酸水平的作用主要是由腎臟介導的。非諾貝特的化學結構中有兩個緊密相連的苯環,這可能是其可通過腎臟旁路途徑增加嘌呤及尿酸的清除、從而產生促進尿酸排泄和降低血尿酸水平作用的原因[4]。
2.3 堿化尿液的藥物
碳酸氫鈉、枸櫞酸氫鉀鈉等藥物能堿化尿液的pH至6.5 ~ 6.8,由此提高尿酸和尿酸鹽比值以及尿酸鹽的溶解性,進而減少尿酸鹽結晶形成及有利于尿酸排泄。尤其是在慢性痛風治療過程中,促尿酸排泄藥物的使用會使更多的尿酸從腎臟排出,堿化尿液對提高尿酸的溶解性、防止尿酸鹽結晶在腎臟沉積或者形成結石具有重要的意義。
2.4 尿酸氧化酶類藥物
體內缺乏尿酸氧化酶就不能將嘌呤代謝過程中產生的尿酸氧化分解為極易溶于水的尿囊素而隨尿排出體外。因此,通過補充尿酸氧化酶將體內尿酸分解為尿囊素排出體外即成為高尿酸血癥治療的又一有效策略。目前,尿酸氧化酶類藥物主要有重組黃曲霉菌氧化酶和聚乙二醇化重組尿酸氧化酶,兩藥均有快速、強力的降血尿酸水平作用,主要用于重度高尿酸血癥、難治性痛風或有痛風石并可能逐漸溶解的患者,但易誘發痛風急性發作。此外,這類藥物具有抗原性,易引起超敏反應和耐藥。
Savient制藥公司開發的pegloticase是一種聚乙二醇化重組尿酸氧化酶[5],用于治療既往治療失敗的痛風(即難治性痛風,包括痛風反復發作、慢性痛風性關節炎和進行性痛風石沉積等)患者,可迅速且顯著地降低血尿酸水平、消除痛風石。該藥為靜脈內注射藥物,推薦治療方案為每2周經靜脈注射1次8 mg,最常見的不良反應為輸液反應,可能與用藥者出現藥物相關抗體有關。
2.5 藥用炭
藥用炭是一種微粒化的活性炭,口服后可通過吸附腸道內的非蛋白氮及尿酸、然后從腸道排出。藥用炭不會被吸收入血,對肝、腎無毒性,安全性好,可用于腎功能不全的慢性痛風患者的輔助治療。
3 合并癥的治療
高尿酸血癥的持續存在會使尿酸鹽在體內沉積過多,由此導致一系列的合并癥,常見的有痛風石、痛風性腎病、冠心病、高脂血癥和糖尿病等。
3.1 痛風石
痛風石是痛風的特征性損害,為尿酸鹽反復沉積使局部組織反復發生的慢性異物樣反應,一般在痛風起病10年后出現,提示病程已進入慢性期[6]。
痛風石的典型部位在耳廓,也常見于足趾、手指、腕、踝和肘等關節,少數出現于目眥、脊柱等部位[7-9]。出現皮下結節時,常可通過穿刺或活組織檢查其內容物,在偏振光顯微鏡下觀察,如發現有呈雙折射的棒狀晶體,則為典型的針狀單尿酸鹽結晶[10]。
3.1.1 藥物治療
當血尿酸水平維持在<297.5 μmol/L時,痛風石會逐漸被溶解,進而需要預防關節及腎損害的發生。痛風發作的急性期可使用秋水仙堿、非甾體類抗炎藥物或糖皮質激素治療以控制炎癥和止痛,病情緩解后再進行降血尿酸治療(使用抑制尿酸生成、促尿酸排泄、堿化尿液的藥物或尿酸氧化酶等)。近年來,也有使用秦艽、黃柏、肉桂、金錢草、蒼術等中藥及中成藥治療高尿酸血癥和痛風的報告,但療效和毒、副作用仍待進一步的明確。
3.1.2 手術治療
痛風石手術治療的目的是解除痛風石對關節、組織和神經的壓迫及其可能造成的進一步損害或去除破潰后長期不能愈合的痛風石,適用范圍包括痛風結節破潰、竇道形成、傷口經久不愈或已引起皮膚壞死;骨與軟組織遭嚴重破壞;神經、血管或肌腱受壓;痛風石逐漸增大,影響患者肢體功能和生活質量;嚴重的全身性痛風患者的減負治療;痛風急性發作后使用秋水仙堿治療無效或不能控制的患者;痛風石過大、影響外觀,積極要求手術的患者。手術前必須輔以綜合的內科治療,使患者的血尿酸水平保持在相對低的狀態,因為在痛風石、尿酸鹽結晶被清除的過程中,部分尿酸鹽結晶會溶解并被吸收入血,從而造成術后早期痛風急性發作[10]。
痛風石的手術治療可根據痛風石的大小選用創傷性較小的微創手術,如關節鏡下病變清理術或針刀術等。可根據病變嚴重程度分別采用關節抽吸-沖洗-糖皮質激素注射、關節鏡下病變清理術、痛風病灶清除術、刮除植骨術、Keller手術或關節融合術等治療痛風病灶;也可采用以改良后的針刀術為主[11],輔以刮匙刮除痛風石并用生理鹽水反復沖洗。對體積較大、累及范圍及程度較為嚴重的痛風石,如痛風石在關節囊內,常可采用直視切開清理術治療,盡可能刮除、取凈痛風石,同時盡量保留受侵蝕的肌腱,最后用大量生理鹽水反復沖凈傷口;如痛風石在關節囊外,應盡可能將痛風石包膜完整取出。手術切除痛風石可消除血尿酸的痛風石來源、有效降低血尿酸水平,由此阻斷痛風的病變進程以及預防新痛風石形成,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并改善其關節功能[12]。但患者術后仍須接受包括低嘌呤飲食、戒酒、多飲水、運動和保暖以及降血尿酸、降血壓和降血脂等在內的綜合治療。
3.2 痛風性腎病
痛風性腎病是痛風患者的常見合并癥之一。尿酸鹽長期沉積于腎臟可造成腎實質損害,晚期痛風患者多有痛風性腎病。據歐洲透析移植協會估計,終末期腎功能衰竭由痛風所致者占0.6% ~ 10.0%。此外,有研究者報道,經尸體解剖證實的痛風患者腎臟病變發生率為100%[13]。因此,痛風引起的腎損害已越來越受到臨床醫師的關注。
痛風性腎病的病理基礎為高血尿酸水平,在臨床上可分為急性尿酸性腎病、慢性尿酸性腎病和尿酸性腎結石3種類型。痛風性腎病還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2種類型。急性尿酸性腎病是由于大量尿酸鹽結晶沉積于腎間質及腎小管內、使腎小管腔被尿酸鹽充填和堵塞而引起的少尿型急性腎衰竭,常見于繼發性痛風性腎病患者。慢性尿酸性腎病是由于尿酸鹽結晶沉積在腎髓質引起,常見于原發性痛風性腎病患者。尿酸性腎結石在原發性和繼發性痛風性腎病患者中均可見到。
痛風性腎病治療的關鍵是控制高尿酸血癥,可通過使用抑制尿酸生成、促尿酸排泄和堿化尿液等的藥物治療,防止尿酸鹽沉積、腎間質損害和結石形成。近年來,中醫藥也被用于痛風性腎病治療,但療效及毒、副作用仍有待進一步的明確。
3.3 其他相關疾病
與痛風和高尿酸血癥有關的疾病還有冠心病、2型糖尿病、高血壓和高脂血癥等。血脂水平與血尿酸水平相關,特別是Ⅳ型高脂血癥是痛風發生的危險因素,可能與內分泌紊亂和酮生成過多、尿酸排泄受到抑制有關。高水平的尿酸也可損害胰腺β細胞,誘發糖尿病。
4 痛風的預防用藥
慢性痛風具有反復發作的特點,因此日常預防用藥對減少痛風的反復發作尤為重要。痛風的預防包括在1次急性發作后對再次發作的預防以及對因服用降血尿酸藥物而可能誘發的痛風發作的預防。2012年美國風濕病學學會發布的慢性痛風治療指南推薦,秋水仙堿和小劑量非甾體類抗炎藥物為預防痛風發作的一線藥物。在開始降血尿酸藥物治療時,首選秋水仙堿每天1或2次、0.5 mg/次或者萘普生每天2次、250 mg/次并合用質子泵抑制劑預防痛風的復發。當上述藥物預防無效時,可改用小劑量糖皮質激素如潑尼松≤10 mg/d治療。對于有痛風活動征象的患者,推薦持續用藥6個月。痛風活動征象包括:體檢發現痛風石;近期有急性痛風發作;存在慢性痛風性關節炎或血尿酸水平未達標。對降血尿酸治療患者,通常應持續用藥至其血尿酸水平達標后3個月(無痛風石者)或6個月(有痛風石者)。
白介素(interlukin, IL)-1受體抑制劑是一類新的抗急性痛風藥物。在急性痛風發作過程中,尿酸鹽會誘導關節組織的巨嗜細胞分泌IL-1β,而IL-1β會進一步誘導巨嗜細胞釋放腫瘤壞死因子-α和IL-6等炎性介質,由此產生炎癥反應。IL-1受體抑制劑rilonacept已于2008年獲得美國FDA批準,臨床研究顯示其對痛風急性發作有良好的治療作用[14]。2009年,多克隆的抗IL-1β抗體canakinumab和IL-1受體拮抗劑anakinra又相繼在美國獲準上市,這兩個藥物對急性痛風均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15-17]。IL-1受體抑制劑適用于那些不能耐受傳統抗痛風藥物治療的患者。也有研究將IL-1受體抑制劑用作預防用藥,結果顯示也有很好的療效。但因這些藥物售價昂貴,實際應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5 結語
慢性痛風大多發生在急性痛風反復發作或急性痛風未經系統治療或治療不當之后,隨著體內血尿酸水平持續升高,導致尿酸鹽沉積于組織或關節局部,可引起多種合并癥。慢性痛風的根源是持續的高血尿酸狀態,治療的主要目標是降低血尿酸水平,同時對痛風石及可能并發的腎臟疾病等合并癥進行系統治療,必要時應用外科手術處理痛風石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此外,也應重視痛風發作預防用藥的應用,這可有效減少痛風的發作。總之,慢性痛風治療需要一個長期、持續和綜合的治療過程。
[1] 馬培奇. 降尿酸藥物研究進展[J]. 上海醫藥, 2012, 33(3): 18-20.
[2] 吳靜. 調脂藥物的一枝獨秀——非諾貝特的獨特作用及其臨床應用[J]. 實用糖尿病雜志, 2005, 1(5): 59-61.
[3] Bastow MD, Durrington PN, Ishola M. Hypertriglyceridemia and hyperuricemia: effects of two fibric acid derivatives (bezafibrate and fenofibrate) in 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J]. Metabolism, 1988, 37(3): 217-220.
[4] 劉偉麗, 丁健. 非諾貝特在難治性痛風治療中的療效及安全性觀察[J]. 現代實用醫學, 2013, 8(25): 862-863.
[5] Chohan S, Becker MA. Update on emerging urate-lowering therapies [J]. Curr Opin Rheumatol, 2009, 21(2): 143-149.
[6] 李春先, 張旗, 石顏軍. 風濕病診斷要點指南[M]. 北京: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 2008.
[7] Suk KS, Kim KT, Lee SH, et al. Tophaceous gout of the lumbar spine mimicking phylogenic discitis [J]. Spine J, 2007, 7(1): 94-99.
[8] Hou LC, Hsu AR, Veeravagu A, et al. Spinal gout in a renal transplant patient: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J]. Surg Neurol, 2007, 67(1): 65-73.
[9] 焦根龍, 李志忠, 潘永勤. 腰椎間盤突出合并右側關節突關節痛風石1例報告[J]. 中國脊柱脊髓雜志, 2007, 17(12): 942-943.
[10] 王禮燦, 溫成平, 謝志軍. 痛風石的診療與研究進展[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 2013, 21(13): 1468-1470.
[11] 王德軍, 梁華. 針刀治療痛風石對血尿酸指標影響的臨床研究[J]. 中醫藥學報, 2010, 38(3): 110-111.
[12] 朱迅. 手術治療痛風性關節炎痛風石13例療效觀察[J].中外健康文摘, 2012, 9(16): 112-113.
[13] 袁鷹. 痛風性腎病[J]. 山東醫藥, 2010, 50(43): 109-110.
[14] Schumacher HR, Evans RR, Saag KG, et al. Rilonacept (interleukin-1 trap) for prevention of gout flares during initiation of uric acid-lowering therapy: results from a phase III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onfirmatory efficacy study [J]. Arthritis Care Res, 2012, 64(10): 1462-1470.
[15] So A, Meulemeester MD, Pikhlak A, et al. Canakinumab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flares in difficult-to-treat gouty arthritis: resuits of a multicenter, phase II, dose-ranging study [J]. Arthritis Rheum, 2010, 62(10): 3064-3076.
[16] Singh D, Huston KK. IL-1 inhibition with anakinra in a patient with refractory gout [J]. J Clin Rheumatol, 2009, 15(7): 366.
[17] Schumacher HR, Sundy JS, Terke LR, et al. Placebo controlled study of rilonacept for gout flare prophylaxis during initiation of urate lowering therapy [J]. Arthritis Rheum, 2009, 60(4): 410.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out*
YANG Xue**, XUE Yu, ZOU Hejian***
(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The incidence of gout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Gout is easy to relapse and can gradually become a chronic one, which can affect multiple organs and cause a variety of complications and result in greater harm. Recent reports mainly focused o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out whil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out. Because of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peated flare, the chronic gout needs longtime, continuous and combined treatment. Here, we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rapeutic methods, and the treatment of gout and its complications.
chronic gout;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rapeutic methods; complications
R971.1; R589.7
A
1006-1533(2015)11-0007-0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81373213、81401346);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基礎研究重大項目(項目編號:11DJ1400100);2012年上海市衛生局領軍人才培養計劃
**
楊雪,住院醫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痛風的發病機制和治療、間充質干細胞對自身免疫病的調控作用和機制研究。E-mail: yangxue21@yeah.net
***
鄒和建,主任醫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風濕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E-mail: hjzou@fudan. edu.cn
2014-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