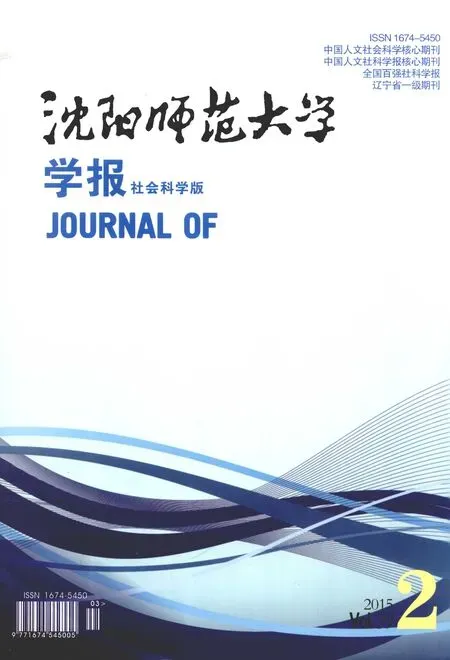《文心雕龍》中的小說理論因子
馬驍英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文學與語言學】
《文心雕龍》中的小說理論因子
馬驍英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由于劉勰獨特的小說地位論和小說觀,《文心雕龍》沒有為小說文體設置專篇專論。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心雕龍》這部體大思精、兼備眾體的文論名著中沒有涉及小說理論。《文心雕龍》中存在著大量的小說理論因子,它們散見于《正緯》、《辨騷》、《諧隱》、《諸子》、《封禪》、《夸飾》等各篇章之中,雖如吉光片羽、零珠碎璣,但卻彌足珍貴,具有非凡的理論深度和不容忽視的肇源意義。《文心雕龍》中的小說理論因子,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概括:尚“奇”的藝術追求、貴“虛”的藝術旨趣、“會俗”的藝術價值取向。
《文心雕龍》劉勰;小說理論因子;小說理論發展史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心雕龍》這部體大思精、成就空前的文學理論名著誕生的時代背景。《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部分,幾乎囊括了這一時期的所有文體,并且對每種文體都進行了高水平的理論闡釋和理論總結。然而,通觀《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的二十篇篇目,不難發現,《文心雕龍》似乎百密一疏地遺漏了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一種文體——小說。《文心雕龍》在其宏大的體系結構中,竟沒有為小說保留一席之地,沒有為小說這種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文體設置專篇專論。
通過對《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的梳理與細讀,我們發現,事實上,《文心雕龍》并未完全忽略小說文體。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小說文體的蓬勃發展、繁榮興盛,使得小說創作的藝術精神、藝術手法,自覺不自覺地、不可避免地浸潤并滲透入了當時其他各種文體的寫作之中,使各種文體都或多或少地、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了小說創作的某些藝術手法,浸染了小說創作的斑斕的藝術色彩。同時,小說文體本身起源的“雜史、雜傳、雜記”形態,與其他各種文體具有著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血緣關系,小說文體的雛形已經初具了兼備眾體的某些特征,小說文體的雛形與其他各種文體已經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渾融局面。因此,《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部分,對其他各種文體的論述與闡釋,無可避免地、自覺不自覺地會論及蘊含在其他各種文體中的小說創作的藝術范疇、藝術手法和藝術精神,這些對其他各種文體中小說因素、小說特征、小說色彩的論述散見于《文心雕龍》二十篇文體論之中,構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小說理論因子的群落,它們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在歷史發展中的最早痕跡,對這些吉光片羽、零璣碎璧的小說理論因子進行梳理和闡釋,對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發展衍變具有重要意義。
一、尚“奇”的藝術追求
尚“奇”,追求“奇”的藝術效果、藝術情節、藝術形象、藝術表達方式,是小說文體的重要特征和鮮明特色。《文心雕龍》中蘊含著大量的關于尚“奇”的小說理論因子,對各種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的“奇”的特征進行了精要而透徹的論述。
《文心雕龍》指出,在眾多文體之中,讖緯文體明顯而突出地具有著尚“奇”的總體特征。我們通過詳細體味《文心雕龍》對讖緯文體的論述,不難發現,讖緯文體的這種“奇”的顯著特征,是讖緯文體中所蘊含的小說性因素所造成的。《文心雕龍·正緯》云:“經正緯奇”[1]30,指出,相比于儒家經書的嚴肅雅正,本應與儒經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讖緯文體卻明顯具有奇詭怪異的特征,與儒家經書風格之正形成尖銳對立,抵觸背迕。后世學者認為,讖緯文體的這種奇詭怪異的總體特征,甚至達到了“顛倒舛謬”的近于“妖妄”的嚴重地步,《隋書·經籍志·六藝緯類序》云:“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圣人之旨。孔安國、毛公、賈逵,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2]這些儒家經學視角之下的“妖妄”“顛倒舛謬”,實際上都是讖緯文體所包蘊的文學意義上的小說性因素所造成的傳奇性的故事性的令人驚心駭耳的藝術效果。劉勰在論述這種藝術效果時,運用了“鳥鳴似語,蟲葉成字”[1]30這兩個在讖緯文體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典故作為例證,來說明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所帶來的“奇”的文體特征。《左傳·襄公三十年》:“鳥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3]《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余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4]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嘻,悲恨之聲。宋有災異,鳥先感之,作聲如言嘻嘻也。”[5]《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昭帝崩,無子,征昌邑王嗣位,狂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4]正是這些陰陽、災異、符命等等在中國古代長期泛濫、風行的文化基因,使讖緯文體的內容具有了強烈的傳奇性和故事性,促成了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的萌發、瘋長,而這些小說性因素的奇詭怪異、“乖道謬典”[1]31的總體特征也成為了讖緯文體的文體特征。那么,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通過乖離正道、竄亂經典而實現的“奇”的文體風格、文體特征,是否有利于讖緯文體的翼輔配合儒家經典的政治功利性的文體功能的達成呢?《文心雕龍·正緯》云:“白魚赤烏之符,黃金(一作銀)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1]31《文心雕龍》又運用兩則例證,加以分析,給出了新穎、完滿、透徹、全面而有說服力的答案。《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6]《尚書中候·洛師謀》:“太子發,以紂有三仁附,即位,不稱王,渡于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謀,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7]399《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黃銀見,紫玉見于深山。”[7]517《文心雕龍》指出,這些本意在于翼輔、配合、解說、詮釋《書經》《禮經》等儒家經典的讖緯文體中包含著大量的以奇詭怪異為特征的小說性因素,這些小說性因素利用乖謬荒悖的符命、兆應、征驗、祥瑞、災異,來實現動人心魄、驚人耳目的傳播效果,這種以“奇”為尚的特征和效果,實質上無益于讖緯文體的詮釋解說儒家經典的本意的達成,無助于讖緯文體的翼輔配合儒家經典的原初政治功利性的文體功能的實現,然而,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所造成的這種以“奇”為尚的文體特征和文體傳播效果,卻在無意之間,給讖緯文體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歷史性的重要意義,這就是超脫于政治功利性之外的純藝術層面的文學性,尚“奇”的小說性因素讓讖緯文體具有了內容豐富、生動曲折、奇異瑰偉、娓娓動聽的故事情節和富麗、豐贍、潤澤的語言辭采,使讖緯文體呈現出“縱橫有義,反覆成章”[8]的藝術風貌,讖緯文體中的尚“奇”的小說性因素雖然無裨益于該文體政治功利性功能的達成,但是卻賦予了該文體超脫出暫時政治功利意義之上的恒久的文學藝術意義和文化影響,讖緯文體中的尚“奇”的小說性因素以其奇妙的構思和表達方式,為當時和后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養料和不絕的藝術靈感,沾溉之澤,至為廣遠,例如,劉勰所引為例證的讖緯文體中的“白魚赤烏”“黃金紫玉”之典,便被后世歷代詩文、小說所廣泛、頻繁地征引、化用,保持著恒久的文化生命力,成為了鮮明的文化符號,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文化影響。
《文心雕龍》進一步指出,尚“奇”的小說性因素也廣泛存在于騷體文學作品之中。《文心雕龍》通過分析騷體文學中的小說性因素,點明騷體文學作品中小說性因素的尚“奇”的藝術風貌在實現手段、表現方式和藝術特色上包含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詭異”。以詭至異,以異至奇;因詭而異,因異而奇。通過虛假詭戾來造就不同于、迥異于傳統舊說的新異之說,以達成“奇”的效果。《文心雕龍·辨騷》云:“至于托云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女,詭異之辭也。”[1]4《6離騷》中隱含的小說性因素,驅遣虛假詭戾、顛覆曲折之思,改造、幻化了傳統舊有的神話傳說定式,賦予舊有神話形象以新的功能,賦予舊有神話內容以新的情節,賦予舊有神話故事以新的意義,打破了舊有神話傳說的模式與界限,溝通、融匯了多重神話的意義空間,創造、構建了多元神話的形象世界,以迥異于傳統舊說的超凡的標新立異之辭,實現了“奇”的藝術效果。《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9]王逸注:“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載云旗者,言己德如云雨,能潤施萬物也。”《離騷》:“吾令豐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王逸注:“豐隆,云師,一曰雷師。宓妃,神女也。”梅慶生《文心雕龍音注》:“宓妃,伏羲氏女,為洛水神也。”《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王逸注:“有,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圣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鴆,一名運日,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言我使鴆鳥為媒,以求簡狄,鴆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離騷》中的小說性因素,絕不滿足于僅僅原封不動地引用舊有神話傳說,而是一反舊有神話傳說的固定形態,大膽地改造、糅合、演繹、重構舊有神話傳說,給舊有神話傳說注入新的血液和精魂。《離騷》中所云的駕馭八龍而載云旗,委托云神豐隆乘彩云去向洛水女神宓妃求婚,憑借鴆鳥去有國向美女簡狄說媒,就是上述的通過改造舊說、標新立異來達到“奇”的藝術效果的典型例證。第二方面是“譎怪”。以譎至怪,以怪至奇;因譎而怪,因怪而奇。通過欺詐譎誑的藝術手段來實現怪誕、荒誕的藝術面貌,進而達成“奇”的藝術效果。《文心雕龍·辨騷》云:“康回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騷體文學中隱含的小說性因素,運用譎詐欺誑的手段,將神話傳說中最荒唐不經的成分突顯出來,并使其荒唐的程度進一步深化,造成最大程度的荒誕、怪誕的藝術面貌,以實現“奇”的藝術效果。《天問》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東南傾。”《天問》云:“羿焉日?烏焉解羽?”王逸注:“《淮南子》言,堯時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宋玉《招魂》云:“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王逸注:“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宋玉《招魂》云:“土伯九約,三目虎首,其身若牛些。”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騷體文學中的小說性因素,極譎誑欺詐之能事,使用最怪誕、荒誕的形象、情節來驚心駭耳、攝人心魄,撞折天柱、斷絕地維、使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的共工,射落九個太陽的夷羿,頂著九顆頭顱的拔樹力士,長著三只眼睛的土地之神,都是這些怪誕、荒誕形象的典型代表,這些荒誕、怪誕的形象,成功地創造了“奇”的藝術效果,并深刻地影響了后世文學的發展,為后世小說創作所廣泛征引、化用。
《文心雕龍》中的小說理論因子,有力地論證了各文體中隱含的小說性因素具有著“詭言遁辭,兼包神怪”的尚“奇”藝術追求,眾多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通過詭譎怪異的手段來避正用奇、避直用曲,吸納、囊括了大量的神怪性元素,實現了以“奇”動人的良好的藝術效果。
二、貴“虛”的藝術旨趣
虛構,是小說創作的最重要的藝術手段之一,是小說作者的想象力與創造力的集中體現,是小說文體區別于其他紀實性文體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文心雕龍》中的小說理論因子,對眾多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的虛構的藝術手段和貴“虛”的藝術旨趣,進行了精彩而深入的論述。
《文心雕龍·正緯》指出,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極善于運用虛構的藝術手段,具有“虛偽浮假,僻謬詭誕”的藝術特色。斯波六郎《文心雕龍札記》云:“‘浮假’者,無根據之意也。”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云:“浮假,謂其虛而不實也。”斯波六郎《文心雕龍札記》云:“‘僻謬’,意為不合于經典之偽語。”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以虛構手段,創造了虛妄偽薄、無中生有、浮虛不實、乖僻悖謬、離經叛道、詭詐荒誕的多重藝術模式,達到了以虛至幻、以幻驚人的藝術效果。歷代學者對讖緯文體中小說性因素的貴“虛”的藝術旨趣,多有論述。《后漢書·桓譚傳》記載了桓譚的觀點,他認為,讖緯文體多通過虛構,造作“奇怪虛誕之事”,讖緯文體的作者基于“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的普遍心理規律,而樂于汪洋恣肆地以虛構創制“異聞”,以收驚聽之效。《后漢書·張衡傳》記載了張衡的觀點,他認為,讖緯文體憑借虛構,“附以妖言”,率皆“虛妄而非圣人之法”。張衡也分析了讖緯文體以“虛”為貴的內在心理規律層面的原因,指出讖緯文體之虛構“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荀悅《申鑒·俗嫌》言簡意賅地指明了讖緯文體貴“虛”旨趣的四大表象:“虛言,浮術,華名,偽事”,認為虛構手段貫穿于讖緯文體所涉及的言、行、名、實各個層面之中。劉師培《讖緯論》認為,貴“虛”的藝術旨趣,使讖緯文體“說鄰荒謬,語類矯誣”,虛構的藝術手段,使讖緯文體“立說誠妄誕不經”。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認為,貴“虛”的藝術旨趣、虛構的藝術手段,使讖緯文體成為了“不可信”的“浮偽之所”。
《文心雕龍·辨騷》借助班固的觀點,指明大量的變幻神奇、光怪陸離的虛構的藝術手段成就了騷體文學中的小說性因素。《文心雕龍·辨騷》云:“班固以為……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班固《離騷序》云:“多稱昆侖懸圃,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經義所載。”騷體文學中充斥漫衍的類似“昆侖懸圃”的虛無縹緲的完全不合于儒家經傳義理的虛構成分,構成了騷體文學中的小說性因素,并使其具有了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離騷》云:“吾道夫昆侖兮,路修遠以周流。”又云:“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王逸注:“懸圃,神山也,在昆侖之上。”《天問》云:“昆侖懸圃,其尻安在?”朱熹注:“昆侖懸圃,高廣之度,諸怪妄說,不可信耳。”騷體文學中小說性因素的貴“虛”旨趣,或由實而生虛,或從無而生有,變幻不拘,手段多樣,例如,《離騷》中“昆侖懸圃”之說,即是由昆侖之實象虛構出懸圃之虛象,帶給讀者充滿無限遐想的藝術空間。
《文心雕龍·辨騷》進一步指出,騷體文學實際上是非小說性因素與小說性因素的混合體,是實與虛的混合體。騷體文學中的非小說性因素,即實的成分,是通過“典誥”風格的藝術形式來實現的。騷體文學中的小說性因素,即虛的成分,是通過“夸誕”風格的藝術形式來實現的。非小說性因素與小說性因素,實與虛,在騷體文學中,既統一,又對立,使騷體文學呈現出“典誥則如彼,夸誕則如此”的復雜的藝術面貌。小說性因素是貴“虛”的藝術旨趣、虛構的藝術手段通過“夸誕”的藝術形式來實現的,這是《文心雕龍》的小說理論因子中的重要觀點。為了充分論述作為貴“虛”藝術旨趣的重要憑藉和支柱的“夸誕”的藝術形式,《文心雕龍》專設《夸飾》一篇,予以詳細闡釋。《文心雕龍·夸飾》云“: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相如憑風,詭濫逾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焦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余波,語瑰奇,則假珍于玉樹,言峻極,則顛墜于鬼神。又子云羽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于朔野。孌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文心雕龍》在這里廣泛引用《詩經·大雅·崧高》《詩經·衛風·河廣》《詩經·大雅·假樂》《詩經·大雅·云漢》《尚書·堯典》、偽古文尚書《武成》、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甘泉賦》《羽獵賦》、張衡《羽獵賦》中的典型例證,論證出小說性因素的貴“虛”的藝術旨趣是依靠“虛用濫形”“詭濫逾甚”的“夸誕”方式實現的,虛構的藝術手段通過夸張、矯飾的“夸誕”途徑完成了對小說性因素的構建,貴“虛”的藝術旨趣經由“夸誕”發展出尚“奇”的藝術效果,實現了由“虛”而“奇”的藝術轉換。
《文心雕龍·諸子》指出,諸子文體中蘊含著大量的小說性因素,這些小說性因素運用虛構的藝術手段,使自己體現出超越方圓、不合規矩的舛謬駁雜、乖離雜亂的“各以其知舛馳,即為怪迂析辯詭辭”的“駁”特征。《文心雕龍·諸子》又進一步使用具體實例,論證了小說性因素的虛構手段所帶給諸子文體的“駁”特征。“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駁之類也。”《文心雕龍》認為,這些廣泛存在于諸子文體中的具有顯著“駁”特征的小說性因素,實為貴“虛”的藝術旨趣與虛構的藝術手段的完美結晶。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云:“‘湯之問棘’,‘棘’,《列子》作‘革’,‘革’、‘棘’古音同。”《列子·湯問》:“殷湯問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觶俞、師曠方夜耳,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莊子·則陽》:“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列子·湯問》:“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子·湯問》:“夏革曰:‘渤海之東,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圣毒之,訴之于帝。帝恐流于四極,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強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沉于大海,仙圣之播遷者巨億計。’”《淮南子·天文》:“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在《文心雕龍》看來,如此眾多地存在于諸子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所帶給我們的令人神迷目眩的藝術世界,實在要歸功于這些小說性因素的貴“虛”的藝術旨趣和虛構的藝術手段。盡管這種務“虛”的旨趣和手段,在思想意義上被《論衡·對作》斥為“浮妄虛偽,沒奪正是”,但是,在純藝術層面上,諸子文體中小說性因素的貴“虛”藝術旨趣和虛構藝術手段,絕對是高超的藝術想象力與創造力的完美體現。《文心雕龍》更為深入地指出,諸子文體中小說性因素的貴“虛”藝術旨趣與虛構藝術手段,在總體面貌上,具有著“混同虛誕”的四大特征。范文瀾注《文心雕龍》的《諸子》篇原文間雙行夾批校語云:“‘混同虛誕’,‘同’一作‘洞’,鈴木云:‘諸本作洞。’”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云:“‘混洞虛誕’,四字平列,而各明一義。‘混’謂其雜,‘洞’謂其空,‘虛’謂其不實,‘誕’謂其不經。”《文心雕龍》告訴我們,諸子文體中小說性因素的貴“虛”藝術旨趣與虛構藝術手段,憑借舛謬駁雜、由無生有、虛幻離奇、荒誕恣肆的四大特征,依靠超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異彩紛呈的極具心靈感染力的宏大藝術空間。
三、“會俗”的藝術價值取向
在《文心雕龍》的小說理論因子之中,有一個組成部分值得特別關注。這就是,對各個文體中小說性因素的區別于廟堂文學典雅之風的通俗風格的格外強調。《文心雕龍》指出,與廟堂文學一味追求雅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各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在藝術價值取向方面,更為貼近社會大眾,更為迎合最廣大受眾的接受心理,更為主動地滿足廣大民眾的審美需求,更為注重采用民眾喜聞樂見的通俗的語言風格和有趣的藝術細節。各個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從而具有了積極適應廣大民眾接受品味的“會俗”的藝術價值取向。
《文心雕龍·諧隱》指出,詼諧文學與小說文體,在地位、語言風格、主要受眾定位、藝術價值取向方面,是完全相同的,“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而且,在《文心雕龍》所根基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詼諧文學中,有一個組成部分本身就是用小說文體寫成的,這就是俳優小說。南朝劉宋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云:“曹植初得邯鄲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正由于小說文體與詼諧文學具有著如此巨大的共性和濃厚的親緣關系,所以,小說文體和詼諧文學之間存在著共有的藝術價值取向和一致的文體風格。小說文體,在藝術價值取向和文體風格方面,與詼諧文學保持一致,追求“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小說文體和詼諧文學一樣,致力于自身能夠被最大多數的受眾所理解、接受、喜愛,追求自身語言文辭的淺顯淺近、通俗平易,努力迎合世俗的趣味,適合大眾的口味,符合民間的品味,通過這些手段,小說文體展現出了與詼諧文學共通的“會俗”的藝術價值取向。
《文心雕龍》進一步廣泛關注了各個文體中小說性因素的“會俗”的藝術價值取向,對它們切合受眾審美心理、滿足民間審美需求的藝術價值取向做出了精當的闡釋。讖緯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文辭淺俗”,多“雷同之俗語”“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以淺近平易包裹神秘內核,俘虜民間受眾心理,從而在民間信仰中占據一席之地,擴大了自身影響,強化了傳播效果,獲得了廣大受眾的迷信和盲從。諸子文體中的小說性因素,采用“綴以街談”的方式,將最淺白通俗的直接來源于民間的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吸納入自身之中,以最大化地增強自身對民間受眾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史傳文學中的小說性因素,基于“俗皆愛奇,莫顧實理”的廣大受眾的普遍獵奇心理,將大量的傳奇性、故事性因素和充滿巧合、虛幻、神異、怪誕等驚人之語的野記傳聞都吸納入自身之中,以充分迎合廣大受眾在閱讀史傳文學時的愛奇、獵奇心理,體現出力求滿足民間審美欲求的“會俗”的藝術價值取向。
結語
《文心雕龍》中的小說理論因子,散見于其《正緯》《辨騷》《諧隱》《諸子》《封禪》《夸飾》等各篇之中,雖非系統的專篇專論,但其理論高度、闡釋深度、覆蓋廣度都達到了令人驚嘆的超凡水平。這種高水平的理論成就,絕非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有著深厚灝瀚的時代文化背景作為其生長土壤的。《文心雕龍》的高水平的小說理論因子所誕生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杰作,它們是《文心雕龍》的小說理論因子能夠取得如此之高的理論成就的堅實的作品基礎和深層的文化根源。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志人小說有:三國魏代邯鄲淳《笑林》、西晉郭頒《魏晉世語》、東晉裴啟《語林》、東晉郭澄之《郭子》、東晉袁宏《名士傳》、東晉葛洪《西京雜記》、東晉孫盛《雜語》、南朝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南朝劉宋虞通之《妒記》、南朝蕭梁劉孝標《俗說》、南朝蕭梁沈約《俗說》、南朝蕭梁殷蕓《小說》、南朝蕭梁謝綽《宋拾遺》、南朝蕭梁裴子野《類林》。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的志怪小說有:三國魏文帝曹丕《列異傳》、西晉王浮《神異記》、西晉陸蔚(或陸夏)《異林》、西晉張華《博物志》、東晉郭璞《玄中記》、東晉干寶《搜神記》、東晉葛洪《神仙傳》、東晉王嘉《拾遺記》、東晉孔約《志怪》、東晉戴祚《甄異傳》、南朝劉宋托名陶潛《搜神后記》、南朝劉宋劉義慶《幽明錄》和《宣驗記》、南朝劉宋劉敬叔《異苑》、南朝劉宋傅亮《應驗記》、南朝劉宋東陽無疑《齊諧記》、南朝蕭齊祖沖之《述異記》、南朝蕭齊蕭子良《冥驗記》、南朝蕭梁任昉《述異記》、南朝蕭梁吳均《續齊諧記》、南朝蕭梁王琰《冥祥記》。在如此浩瀚而厚重的作品基礎的支撐、托舉之上,在如此豐富的文獻素材的滋養之中,《文心雕龍》的小說理論因子,吸飽了充足的養分,破土萌芽,拔節抽穗,乘時而起,應運而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零珠碎璣,流光溢彩。
[1]劉勰.文心雕龍[M].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903.
[3]洪亮吉.春秋左傳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7:126.
[4]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1315.
[5]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20.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111.
[7]安居香山等輯.緯書集成[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399.
[9]蔣驥.山帶閣注楚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36.
【責任編輯楊抱樸】
I206.2
A
1674-5450(2015)02-0108-05
2014-11-03
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K505600418)
馬驍英,男,遼寧海城人,遼寧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