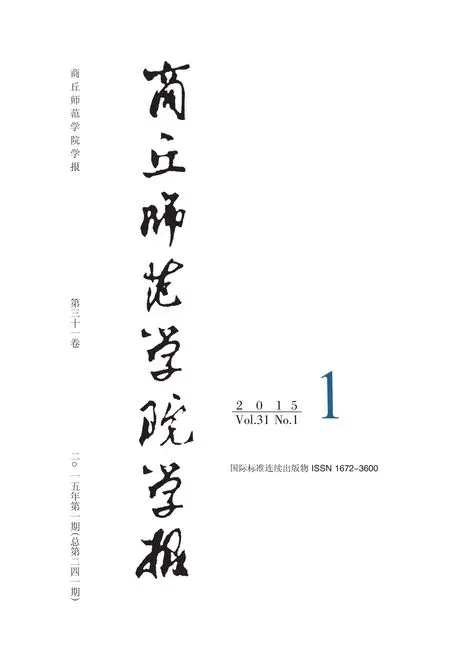阿來漢語小說的雙重文化視角
楊 彬
(中南民族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4)
阿來漢語小說的雙重文化視角
楊 彬
(中南民族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4)
阿來在用漢語寫作藏族小說的過程中,采取藏漢文化的雙重平等視角,穿行在藏漢文化之間,在保持藏族文化的基礎(chǔ)上,用平等視角看待漢族文化,以期探討人類的共同特性。《塵埃落定》中對多民族文化和諧融合狀況的描寫以及采取的平等包容的態(tài)度,可以為我們今天的文化發(fā)展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阿來;藏族漢語小說;雙重文化視角
阿來是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他的作品我們稱為藏族漢語小說。當(dāng)今,少數(shù)民族文化在現(xiàn)代化沖擊下出現(xiàn)碰撞、交融的趨勢。因此,少數(shù)民族漢語小說不能只是以單一地張揚少數(shù)民族意識為己任,而是要探討少數(shù)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交融、和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層次問題。因此很多少數(shù)民族作家不再只是表達(dá)少數(shù)民族文化融于漢族文化、西方文化的努力,而是開始采用雙重視角,在不斷融合的文化中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化。阿來的小說就是采用藏漢雙重視角、在不斷融合的文化趨勢中堅守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典范。
一、在藏漢文化中平等穿行
對包含兩種或者這兩種以上民族文化寫作的作品,有很多界定和定義。有的稱之為“邊緣寫作”,有的稱之作“跨族別寫作”。 “邊緣寫作”的概念是由英國籍印度裔作家薩爾曼·拉什迪首先提出來的,拉什迪具有印度文化、英國文化的多種文化背景,他認(rèn)為兩種文化有大小之分,對于他來說,英國文化是“大”文化,印度文化是“小”文化,“大”文化是主流文化,“小”文化則是自己的母族文化,對于主流文化來說自己總是邊緣文化,但是母族文化又與自己如影隨形,難以割舍。但是,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他文化所不能代替的功能,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因此筆者認(rèn)為,跨越兩種或多種文化的作品不能叫做邊緣寫作,而應(yīng)該稱做雙重文化寫作或者多重文化寫作。多重文化交融過程中,對文化交融的態(tài)度有兩種人:一種自認(rèn)為是小文化的作家,因為對自己的母族文化缺乏自信,總希望融入大文化,母族文化割舍不了,主流文化又?jǐn)D不進(jìn)去,于是自認(rèn)為自己是邊緣人,從而出現(xiàn)焦慮感。 第二種是雖然知道自己母族文化處于弱勢,但卻對自己的文化充滿自信,認(rèn)為文化沒有大小之分,因此站在自己母族文化的基礎(chǔ)上,積極地、寬容地接納外族文化,促使自己母族文化的發(fā)展。阿來就是屬于第二種作家。
阿來在其《阿來:穿行于異質(zhì)文化之間》中說:“我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人。”表明他穿行于藏漢文化之間的狀態(tài)。他對于藏漢文化的交匯、碰撞沒有如批評家所說的那種焦慮癥,因為他認(rèn)為“在我的意識中,文學(xué)傳統(tǒng)從來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條不斷融匯眾多支流,從而不斷開闊深沉的浩大河流。我們從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會包容了上游所有支流中全部因子。我們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創(chuàng)造加入這條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這種眾多聲音的匯聚,最終會相當(dāng)和諧、相當(dāng)壯美地帶著我們心中的詩意,我們不愿沉淪的情感直達(dá)天庭”[1]。阿來的這段話表明他對待藏漢文化的平等、包容的心態(tài),這也是他運用雙重文化視角創(chuàng)作《塵埃落定》的緣由。
《塵埃落定》用漢語對藏族的風(fēng)俗風(fēng)情作了詳細(xì)的展示,對藏族的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作了極力的張揚,采用藏族思維塑造人物、組織情節(jié)、看待萬事萬物。可以說這部作品包含了中國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漢語小說從20世紀(jì)50年代到當(dāng)今所有的創(chuàng)作特色、思想內(nèi)涵和寫作策略。而《塵埃落定》超越以往少數(shù)民族漢語小說的新的特點,也是其獲得讀者和研究者最為稱道的特點,則是阿來在作品中進(jìn)行了有目的的雙重文化寫作。這部作品通過藏族麥琪土司由盛及衰的過程,以麥琪土司二兒子傻子的獨特視角,運用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特殊手法,揭示了既是藏族又是人類的共性的文化內(nèi)涵。同時,在描寫藏漢民族的互相影響時,這部作品將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類文化的普遍性相結(jié)合,將藏族的民族情感和人類的情感相結(jié)合,將藏漢民族的相互影響放在平等的地位來看待,構(gòu)成了這部具有世界性作品的偉大內(nèi)涵。
《塵埃落定》于2000年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xué)獎。獲得茅盾文學(xué)獎的理由包括小說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文化底蘊、運用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手法、語言富有魅力等,這些評論沒有能夠全面概括出《塵埃落定》的所有內(nèi)涵和所有貢獻(xiàn)。起碼對于阿來采用的藏漢文化交融的雙重平等視角沒有提到,因為前面提到的那些特點,其他的藏族小說也具有。阿來獨特之處在于他穿行于藏漢文化之間,用漢語描寫藏族文化,描寫藏漢文化交融中平等的民族意識。
二、藏族文化的主體地位
《塵埃落定》雖然是用漢語寫作,但作品中的藏族意識非常明顯。
首先,阿來有強烈的藏族身份的認(rèn)同。雖然阿來不是純粹的藏族人,他父親是回族,母親是藏族。但他出生在四川阿壩馬爾康縣,從小生活在藏區(qū),在藏區(qū)長大,耳濡目染的都是藏族文化。因此,阿來對藏族有強烈的認(rèn)同。他說:“雖然,我不是一個純粹血統(tǒng)的嘉絨人,因此在一些要保持正統(tǒng)的同胞眼中,從血統(tǒng)上我便是一個異教,但這種排除的眼光,拒絕的眼光并不能稍減我對這片大地由衷的情感,不能稍減我對這個部族的認(rèn)同與整體的熱愛。”[2]273這種對藏族的認(rèn)同和歸屬感,使得阿來浸潤著濃郁的藏族文化,他的視角和感受都是藏族化的,他的思維也是藏族思維。雖然阿來具有混血的身份,也受到藏族文化和漢族文化的多重影響,但是阿來站在自己母族文化的基礎(chǔ)上,對藏族文化充滿自信,因為自信,所以就不焦慮;因為不焦慮,所以就能包容;因此就能平靜地學(xué)習(xí)外族的先進(jìn)的東西。
其次,《塵埃落定》中描寫了藏族獨特風(fēng)俗風(fēng)情和康巴藏區(qū)獨特的土司制度。 作品中雪山、莊園、寺廟構(gòu)成典型的藏族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
漢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陽下面,達(dá)賴?yán)镌谙挛绲奶栂旅妫覀兪窃谥形绲奶栂旅孢€靠東一點的地方。……這個位置是有決定意義的。他決定我們和東邊的漢族皇帝發(fā)生更多的聯(lián)系而不是和我們自己的宗教領(lǐng)袖達(dá)賴?yán)铩3]17
《塵埃落定》的故事發(fā)生在康巴藏區(qū),這是藏族和漢族文化交融的地方。所謂土司,是元代以來中央政府對邊緣少數(shù)民族部落首領(lǐng)的承認(rèn)與加封,是中央集權(quán)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管轄的一種方式。這種土司一般和漢族文化交往較多,因此麥琪土司在打不過汪波土司時,就找出清朝皇帝頒發(fā)的五品官印和一張地圖,到中華民國四川軍政府去告狀,并很快帶回來了漢人黃特派員。這些內(nèi)容很清晰地表述了藏族和漢族的關(guān)系。作品描寫藏族生活、飲食習(xí)俗, 藏族人喜歡喝茶,喜歡騎馬,藏族獨特的喪葬習(xí)俗等等。藏族的喪葬辦法有五種,即塔葬、火葬、天葬、水葬和土葬。一般下層人只用水葬,比如奶娘夭折的兒子就沉入深潭水葬了。而貴族和喇嘛死后才可以火葬,土司的大兒子是貴族,被殺后就實行火葬。作品中描寫了很多歌舞場面,如為了慶祝麥琪土司打敗汪波土司,麥琪土司在官寨里舉行了盛大的歌舞晚會:
大火燒起來了,酒壇也一一打開,人們圍著火堆和酒壇跳起舞來。……我的哥哥,這次戰(zhàn)斗中的英雄卻張開手臂,加入了月光下的環(huán)舞。舞蹈的節(jié)奏越來越快,圈子越來越小,很快就進(jìn)入了高潮。[3]31
藏族習(xí)俗在阿來筆下寫得生動而神奇。阿來極其熟悉藏族的物象,因此作品中大量描寫藏民族特色的事象:寺廟、喇嘛、官寨、經(jīng)堂、酥油茶、哈達(dá)、法器、帳篷等,還大量運用藏族的民族語言和宗教語言,形成了《塵埃落定》鮮明的藏族文化特色。
最后,《塵埃落定》還具有鮮明的宗教特色。藏族的主要宗教是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在藏族人民心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藏傳佛教對藏族來說既是宗教信仰,又是生活方式。“宗教曾是藏族歷史文化的魂靈和主宰。千百年來,從遠(yuǎn)古萬物有靈的神話世界,中間經(jīng)歷苯教的自然崇拜,直到佛教盛行,佛陀的光環(huán)虛影籠罩雪域高原,宗教曾是藏民族社會一體化的意識形態(tài);更有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政教合一’的強化統(tǒng)治,宗教意識深深地浸潤著人們的心靈,乃至使人們用‘神的心’去度人生,在虛無的理想彼岸,享受精神的安慰。”[4]除了藏傳佛教,還有原始苯教,苯教在藏族人心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塵埃落定》中那位在麥其土司家族各種重大事務(wù)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門巴喇嘛,就是一位苯教巫師,他能夠運用詛咒的方式驅(qū)走烏云,引來陽光。作品描寫門巴喇嘛運用法術(shù)給麥琪土司的土地帶來陽光,給敵人汪波土司帶去冰雹,由此戰(zhàn)勝敵人。作品還用很濃重的筆觸描寫了從拉薩來的格魯巴教派喇嘛翁波意西,他是一個佛學(xué)淵博、信仰堅定的喇嘛,雖然麥琪土司不喜歡他,但是他是一個能預(yù)知未來、看透事物本質(zhì)的高僧,即使被割去了舌頭,但依然具有智慧和尊嚴(yán)。
三、藏漢文化的雙重平等視角
《塵埃落定》是藏族作家漢語寫作的典型作品。阿來雖然是回藏血統(tǒng),但是他受到的文化影響卻是藏漢文化影響。他從小在藏區(qū)長大,考上中專后系統(tǒng)地學(xué)習(xí)了漢語,因此藏漢文化都對阿來有很深的影響。阿來說:“‘我’用漢文寫作,可漢文卻不是‘我’的母語,而是‘我’的外語。不過當(dāng)‘我’使用漢文時,卻能比一些漢族作家更能感受到漢文中的美。”在《塵埃落定》中,他站在藏族文化的主體上,描寫傻子這個漢藏混血兒的傻與不傻,從而在漢藏雙重文化之間建立阿來的獨特文化視角。作品圍繞傻子的人生故事展開,他的一生構(gòu)成了作品的主要脈絡(luò),他親歷了藏族土司由盛而衰直至土崩瓦解、塵埃落定的整個過程。
傻子是麥琪土司和漢人太太所生的混血兒,是土司父親酒后生出的傻兒子。因此,傻子天然具有藏漢文化的雙重視角和雙重思維,他不完全擁有藏族父親的思維,也并不完全擁有漢族母親的思維,他夾雜在兩種文化之間,傻子便可以同時擁有兩種不同的眼光、觀點和心態(tài)。因此,傻子不明白為什么可以隨意鞭打家奴,他也不明白土司們都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彼此還是親戚為什么總要打仗?更不明白漢人和紅色漢人為什么能控制土司的命運?這肯定不是藏族土司的思維,因此麥琪土司不喜歡他,叫他傻子。說到傻子,他之所以傻,也是因為他在兩種文化之中穿行,從而具有和純藏族血統(tǒng)的哥哥大不同的思維。夾在漢藏兩種文化視角之間的傻子具有雙重文化的特性,表面看起來是個傻子,實際上他是一個穿行于雙重文化空間,領(lǐng)悟雙重文化優(yōu)點和缺點的聰明人。一方面,他可以在兩種不同的歷史、文化空間自由出入、按照人的本性評價雙方的優(yōu)劣長短;同時因為和土司們的慣常思維不一致,因此顯得不合時宜,傻里傻氣。傻子常常陷入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境地。這個傻子形象的多重內(nèi)涵正好印證了漢藏文化交融的內(nèi)涵。關(guān)于聰明人和傻子的表述,關(guān)于傻子大智若愚的特點,在很多民族的文學(xué)和哲學(xué)中都有描寫。看到《塵埃落定》中的傻子,我們很快就會想到滿族的賈寶玉、漢族的郭靖、藏族的阿古頓巴等人物。可見,傻子這個人物已經(jīng)超越了藏族文化,具有人類的共性。同時作品描寫了麥琪土司莊園里各色人的貪欲、享樂、復(fù)仇、追逐權(quán)利等特點,這也是人類的共性。漢藏文化融合到人類的共同特性中,就形成了文化的和諧美。
傻子這個人物設(shè)置十分巧妙,作品將主人公設(shè)置為傻子具有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 作品描寫傻子二少爺很多不同于常人的傻話和傻事,他每天早上醒來第一句話就是問“我”是誰?“我”在哪里?他總是說出和做出很多讓父親、母親、哥哥以及周圍人看來很傻的話和事。但實際上這些話卻充滿了哲理,說出了事情的真相。比如“哥哥因為我是傻子而愛我,我因為是傻子而愛他”。這句話仔細(xì)分析就包含很多的內(nèi)涵,哥哥因為“我”是傻子而愛“我”,是因為“我”是傻子,傻子不會也沒有能力和哥哥爭奪土司的繼承權(quán),而“我”是傻子,自然不會知道哥哥多么地不希望我聰明,甚至還有殺死“我”的想法,因此“我”還是如一般人愛哥哥一樣地愛他。
傻子這個形象包含了藏族文化也包含著漢族文化,是藏漢文化交融的典范,藏漢優(yōu)秀文化的和諧交融,形成了這個具有人類共性的形象。
首先,傻子形象塑造受到藏族機(jī)智人物阿古頓巴的影響。阿古頓巴是藏族民間故事中的機(jī)智人物。阿來還以這個人物為原型寫過一篇小說《阿古頓巴》。阿古頓巴是個專跟貴族、官員作對的下層人物,他是類似阿凡提的人物,他常用最簡單的方式去對付貴族們最復(fù)雜的心計,并且常常獲勝。這是藏族文化的延伸,藏族文化內(nèi)涵在傻子身上得到充分表現(xiàn)。
其次,傻子具有漢族文化中老莊哲學(xué)的大智若愚的內(nèi)涵 。莊子認(rèn)為,理想的人應(yīng)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傻子在小事情上傻,但在大事情上則充滿智慧 。因此傻子具有大智若愚的特點。說他傻,從世俗、從土司家正統(tǒng)的觀點來看,他與世無爭、不識時務(wù),不熱心權(quán)力,一切順乎天性,不威脅別人,同情下人和奴隸,與他被稱為聰明人的哥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他又不傻,在大事上大智若愚。在麥琪土司種了幾年罌粟獲得大量財富后,其他土司也爭相種植,麥琪土司問是繼續(xù)種罌粟還是改種糧食時,傻子毫不猶豫地選擇種糧食。因而別的土司因種植罌粟導(dǎo)致饑荒時,麥琪土司領(lǐng)地卻獲得極大的豐收,他拿出糧食拯救災(zāi)民,獲得老百姓的愛戴,也為自己獲得尊敬。傻子在叔叔的啟示下,將哥哥修的堡壘變成邊境市場,在藏族土司地區(qū)最先開始了邊境貿(mào)易。以和平方式解決土司之間的矛盾沖突。麥琪土司、土司太太以及大少爺都認(rèn)為二少爺是傻子,但是翁波意西卻一直認(rèn)為傻子不傻,傻子具有超人的智慧,智慧的翁波意西總能和傻子達(dá)成默契。因此翁波意西說:“都說二少爺是傻子,可我要說你是聰明人,因為傻才聰明。” 小說結(jié)尾傻子感嘆:“是的,上天叫我看見,叫我聽見,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讓我看起來像個傻子的。”[3]378這段話準(zhǔn)確地詮釋了傻子大智若愚的特點。傻子的大智若愚還表現(xiàn)在他特別善于中庸之道、會審時度勢、認(rèn)清自己的位置,在紛繁復(fù)雜的關(guān)系中能游刃有余。親人中他最喜歡他叔叔,因為叔叔“他不是什么都要贏的那種人”。實際不是什么都要贏的人就是深諳中庸之道的人, 就是聰明人。雖然傻子沒有說出中庸之道這個概念,但是他所作所為是符合老莊哲學(xué)的內(nèi)涵的,作品通過傻子——這個藏族土司少爺詮釋了老莊哲學(xué)的天命觀。
最后,傻子的形象包含儒家文化的特色。傻子雖然也有暴躁的時候,但善良仁慈是其主要的特點。他對待下人仁慈,對待小廝們寬厚,會為下人挨打而流淚,真心地為翁波意西的不平遭遇傷心。當(dāng)別的土司領(lǐng)地上的人因饑饉快要餓死的時候,他指揮下人用大鍋炒麥子進(jìn)行施舍,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中的“仁義”內(nèi)涵,所謂“仁” 就是具有不忍之心,就是善良之心。傻子就是具有不忍和善良之心的人,這種品質(zhì)是麥琪土司和他的哥哥所沒有的。麥琪土司經(jīng)常告誡傻子要把下人當(dāng)成牲口,大少爺經(jīng)常拿起槍來拿奴隸當(dāng)靶子。和他們比起來,傻子具有更多的仁慈之心,因此他得到了老百姓和下人的愛戴。這里儒家的“仁義” 內(nèi)涵和佛教的慈愛、悲天憫人的內(nèi)涵是一致的。
其實,傻子和《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兩人的生平和命運相似:兩人都是貴族公子,一個是麥琪土司莊園,一個是賈府; 兩人都親歷了自己的家庭由盛及衰的過程;兩人的結(jié)局都很悲慘,一個被仇人殺死,一個出家做和尚。其次,兩人都是大莊園中有“異秉”的人,一個是傻子,一個是癡子,傻子在麥琪土司的官寨里,傻里傻氣,讓他的父親——麥琪土司恨鐵不成鋼;而賈寶玉則討厭功名利祿,討厭讀圣賢書,也讓他的父親賈政惱怒不已。還有這兩人都具有當(dāng)時社會中所缺乏的善良仁慈的特點,尤其是兩人都對女人很好,對女仆和丫鬟好,把他們當(dāng)人看。 賈寶玉對晴雯、襲人的態(tài)度是把他們當(dāng)做自己的姐妹,傻子對女仆卓瑪也是非常仁義。可以說阿來受到《紅樓夢》的影響,也可以說藏族思維、 漢族思維抑或滿族思維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傻子和《射雕英雄傳》中的郭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兩人都是外表笨拙,但內(nèi)心靈秀,都是大智若愚的典型。阿來要表達(dá)的是各個民族具有各自的特點,但是作為人類有很多方面是有共通性的。
從傻子的形象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個具有鮮明藏族文化特色的人物,但又是具有漢族道家文化、 儒家文化特色的人。這些優(yōu)秀的人類文化特色集中在傻子身上,說明人類具有很多共通性。阿來穿行在異質(zhì)文化之間,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基礎(chǔ)上、用平等視角看待各種文化,同時探討人類的共同特性。《塵埃落定》中對多民族文化和諧融合狀況的描寫,可以為我們今天的文化發(fā)展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1]阿來.阿來: 穿行于異質(zhì)文化之間 [N].中國文化報,2001-05-10.
[2]阿來.大地的階梯后記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3]阿來. 塵埃落定 [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8.
[4]朱霞. 當(dāng)代藏族文學(xué)的文化詮釋 [J]. 民族文學(xué)研究,1999(4).
【責(zé)任編輯:郭德民】
2014-10-21
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資助項目:“當(dāng)代少數(shù)民族小說的漢語寫作研究”(編號:12BZW095)。
楊彬(1965-),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與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研究。
I206.7
A
1672-3600(2015)01-00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