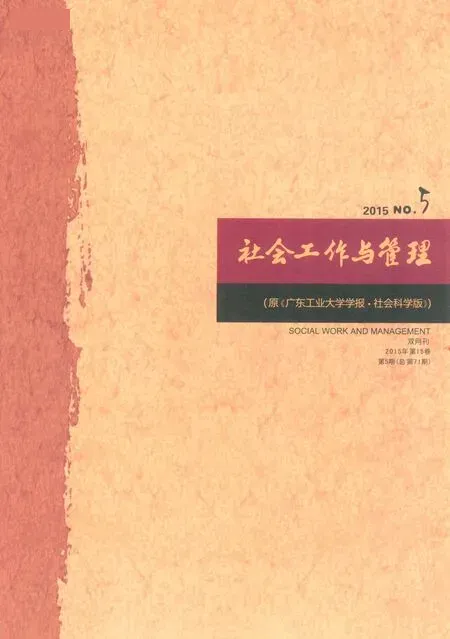美國單身母親與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改革
——社會性別的視角
胡杰容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北京, 100088)
美國單身母親與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改革
——社會性別的視角
胡杰容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北京, 100088)
女性與福利之間的關系是社會政策研究的重要議題。從政策預設、規定與實踐上看,美國的“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AFDC)是一個性別化的社會政策項目,它從既定的性別分工出發,強調滿足現實性別需求,強化了母親和兒童照顧者的傳統性別角色。1962~1996年間,貧困的女主家庭成為AFDC津貼最主要的領取者,并被污名化為“福利皇后”。盡管AFDC及其取而代之的“貧困家庭臨時救助政策”(TANF)強調工作福利,力圖通過工作要求和工作刺激來結束福利依賴,卻導致一些單身母親成為工作窮人,并面臨工作和家庭照顧的雙重重擔。只有從戰略性別需求的角度,改善勞動力市場的性別結構分化,完善公共性兒童服務體系,才能改善單身母親的社會經濟狀況。
單身母親; AFDC; TANF; 現實性別需求; 戰略性別需求
一、婦女與福利國家關系議題
傳統的社會政策研究將福利國家作為一個性別中立的概念,忽視婦女及其婦女運動對社會政策構建的影響,也無視社會政策帶來的性別分層效果。這種性別盲視的傾向在1990年代得到徹底地扭轉,形成了社會政策研究的性別視角。從此,婦女與福利國家的關系議題成為社會政策研究的三大重要版圖之一。它將性別——家庭議題作為影響社會政策議程設置的重要因素,分析婦女的社會政治活動對福利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同時,探討福利國家對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性別角色關系及其不平等、單親家庭的貧困等問題產生的直接效果。[1]換言之,性別視角的社會政策研究將性別作為自變量,考查婦女及其組織化運動對社會政策的推進與社會福利模式的塑造作用,或將性別作為因變量,考查社會政策對性別關系及其角色分工的影響。從美國的實踐來看,社會政策與婦女之間的關系也呈現出這樣緊密且雙向的互動。一方面,婦女關于社會權利議題的斗爭無論失敗還是成功,都對社會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社會政策項目對女性尤其是單身母親的就業狀況、貧困率產生了直接影響。為了清晰地勾勒美國社會政策與婦女之間的關系,本文以其最重要的社會福利制度——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簡稱AFDC)為例,討論這一社會福利項目與貧困單身母親的關系,并分析1990年代中期美國社會福利改革中,以貧困家庭臨時救助政策(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以下簡稱TANF)取代AFDC,對貧困單身母親就業狀況和經濟生活的影響及這一轉變的社會性別意義。
二、AFDC的建立及其社會性別意義
在美國社會政策體系中,AFDC是歷史最悠久的社會福利項目,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母親津貼(Mother Pension)。同時,它也是美國最重要的社會救助項目,對維持貧困家庭的生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建立與實施AFDC是為貧困單身母親撫養未成年子女提供經濟支持,雖然減少不平等(包括性別不平等)是社會福利制度追求的理想目標,但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來看,這一社會政策項目從滿足單身母親被賦予的母親、家庭主婦、兒童照顧者的角色出發,只是對她們照顧未成年子女給予經濟支持,在一定的意義上只是促成她們實現并繼續實現既有性別角色要求,完成傳統角色的生產與再生產。因此,AFDC成為鞏固既定的男女角色模式和擴大現實的男女性別差異的制度性安排與政策模式,具有鮮明的性別化(gendered)特征。
(一)從母親津貼到AFDC
伴隨著現代化的過程,核心家庭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家庭結構類型,而男主外、女主內是其典型形式。對于那些因為戰爭、工傷或其他意外事故導致男性家長死亡或者長期缺席的婦女來說,失去了丈夫就意味著失去了家庭的經濟來源,會直接影響到自身及其子女的生計維持。1909年1月,在白宮第一屆兒童會議上,聯邦政府主張各州制定母親津貼法,以支持喪偶的單身母親撫育其子女。1916年,密蘇里州制定了第一部寡婦年金法。這一法案規定,對喪亡服役人員未再婚的妻子及其未成年子女,由地方政府提供現金補助。在1911—1920年間的“進步運動”中,由于改革者、婦女組織及其政治聯盟的共同推動,全美所有州都推行了寡婦年金制度。1921年11月,作為第一部聯邦政府福利項目,《謝潑德·托納母嬰保護法案》(ShepardTownerInfancyandMaternityProtectionAct)在國會通過,標志著聯邦政府建立了美國最早的社會福利項目——母親津貼。[2]它要求州政府對失去男性養家者的寡婦或者丈夫長期不在家的婦女提供經濟援助,使她們能夠繼續撫育未成年子女。
母親津貼成為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第一個組成部分,為AFDC的創建提供了準備。相對于歐洲大陸先進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來說,美國社會政策的建立不僅嚴重滯后,更重要的是,不同于歐洲大陸的社會保險制度優先保護男性為主的勞動者,美國殘補式的社會福利制度首先考慮保護貧困的單身母親及其兒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達·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認為,1920年代,美國建立了母系主義的社會政策。[3]
保護貧困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不僅是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源頭,也是美國社會福利體制建構和擴張過程的重要內容。1935年,在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下,聯邦政府頒布了《社會保障法案》(SocialSecurityAct),奠定了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在這一法案的Title IV中引入了“兒童救助”項目(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簡稱ADC),授權州政府以現金支付的方式給貧困母親及其子女提供公共援助,它要求聯邦政府給州政府提供資金以幫助貧困單親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聯邦政府根據州政府提交的用款計劃,由議會授權財政部門撥款,最初的撥款需達24 750 000美元。[4]它還規定,由州政府的公共福利部門負責管理貧困家庭及其兒童的社會救濟和福利服務,這標志著對貧困母親及其子女的福利工作從私立志愿性轉向政府公立性。1962年,ADC更名為AFDC,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撥款對因喪偶、離婚、分居、遺棄等原因導致家長長期缺席的貧困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給付經濟援助和福利服務傳遞。
(二)從社會性別視角看AFDC
AFDC 的建立,表明美國政府對婦兒福利領域的干預力度大大增強,家庭領域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私人領域,而是受到政府干預和影響的公共領域。家庭作為兒童社會化最重要的機構和兒童照顧的主體,AFDC體現的政府干預必然影響到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分工和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總體來看,AFDC及其前身是一個具有強烈性別化特征的社會政策項目。從政策預設、文本及其實施上看,它將貧困的單身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作為目標群體,強調這一社會福利項目是資助貧困的單身母親撫養其未成年子女。
首先,在政策預設上,無論是母親津貼,還是AFDC,都假設一個有序的世界。這個世界包括工作的人(主要是男人)和不能工作的人(包括女人尤其是母親、身體殘障者)。假定參與社會性勞動的男性才是有經濟能力的養家糊口者,當一個家庭沒有男性家長時,因為母親無法從事有酬勞動、無力撫養未成年子女,所以政府才扶助她們照顧未成年子女。AFDC理所當然地將母親作為天生的家庭照顧者,強化了女性的照顧者角色。更進一步,無論是母親津貼,還是ADC或AFDC,都不是直接針對單身母親的貧困問題,而是針對貧困的單身母親如何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問題,政策設計的目標和理念是幫助貧困單身母親撫養未成年的子女,使其順利承擔母職。
其次,在政策規定上,AFDC及其前身ADC主要是針對貧困的單親家庭,尤其是女主家庭。《社會保障法案》第406條款將失依兒童(Dependent Children)定義為失去父/母撫養的兒童,包括父/母死亡、長期離家或者身心殘障。除非母親死亡或者殘疾,母親的優先撫養權使得未成年子女多由母親撫養,這預示著ADC及其之后的AFDC目標群體基本是貧困的單身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
第三,在政策實踐中,AFDC及其前身ADC將貧困的雙親家庭排斥在給付范圍之外,并為了控制福利津貼支出,限制受益對象是沒有父親的兒童及其撫養人。[5]作為社會救助項目,所有ADC或AFDC申請者必須通過嚴格的資格審查。1950~1960年代早期,一些州將合適的住所和同居男性作為資格審查的條件,采取半夜突襲的方式檢查申領救助的貧困母親是否有同居男伴,認定無關男性的存在使家庭不適合兒童居住,其經濟需求也不存在。1960年,路易斯安那州以此為借口終結了6 281個個案,涉及23 549名兒童。[6]4-5直到1960年代末期,這些限制性的資格條件才因與侵犯隱私的憲法性條款相沖突而得以廢除。毋庸置疑,這樣的資格條件和甄別機制具有鮮明的標簽化特征和恥辱化效果。
AFDC將未成年子女的撫養責任完全歸于單身母親,將兒童的家庭照顧等同母親照顧。盡管這一政策對緩解單身母親的貧困狀況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主導的價值理念不是幫助婦女實現解放和追求性別平等,不是打破而是強化既定的性別角色分工,不是緩解而是鞏固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既有地位。可見,這一社會政策項目不是性別中立的,而是深深隱含著父權主義假設和男女不平等的性別觀念。
三、AFDC與貧困的單身母親
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隨著婚育模式的變化、婚姻關系的不穩定性和未婚生育率的上升,美國出現了大量女主家庭(female-headed household),其貧困問題也不斷凸現。在撫養未成年子女的貧困家庭中,女主家庭占大部分,她們不得不依賴AFDC津貼維持生活。
(一)美國單身母親的貧困問題
在美國家庭結構形式變遷過程中,女主家庭數量不斷增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1974年,在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單親家庭占17.4%,女主家庭和男主家庭分別占15.7%、1.7%;1996年,單親家庭所占百分比上升到了29.6%,包括24.1%的女主家庭和5.5%的男主家庭。[7]1這意味著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有近四分之一是女主家庭。單親家庭的大增與婚育模式的轉變有關。美國總人口的結婚率從1950年的11‰下降到1996年的8‰,而離婚率則從2.6‰上升到4.6‰。[8]同時,婚外生育大量出現。在1962~1996年間,15~44歲的已婚女性生育率從150.8‰下降到82.3‰,而同一年齡組未婚女性生育率從21.9‰上升到43.8‰。非婚生兒童所占比例也呈明顯增長態勢。1962年,非婚生兒童只占5.9%,而1996年這一比例高達32.4%,這意味著美國近三分之一的兒童是非婚生兒童。[9]概言之,離婚率的上升和非婚生育的蔓延導致單親家庭的數量和比例大大增長,在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近三分之一是單親家庭,而在單親家庭中,近80%是女主家庭。
美國女性的貧困化首先表現為單身母親的貧困。事實上,貧困不是個人特征,而是由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決定的家庭特征。在一定意義上,單身母親的貧困是女主家庭的貧困,它具有兩個重要特征。一是貧困的發生率遠遠高于其他群體。以1996年為例,美國人口普查局“當前人口報告”(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顯示,在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41.9%的女主家庭是貧困家庭,遠遠高于雙親家庭7.5%的貧困率,也高于男主家庭20%的貧困率。在撫養未成年子女的6 131個貧困家庭中,雙親家庭占32.0%,女主家庭占61.3%,男主單親家庭占6.7%。[7]8可見,女主家庭是撫養未成年子女貧困家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二是在1960—1996年期間,女主家庭的貧困率一直高居不下,保持在40%~55%左右的高位[10],而在撫養未成年子女的貧困家庭中,女主家庭所占比例從28%上升到了60%左右[11]。
大量的研究將貧困問題與女主家庭聯系在一起。韋茨曼(Weitzman J.)在《離婚革命》一書指出,離婚后婦女與子女的生活水平平均下降了73%,而丈夫提高了42%。[12]一些研究表明,女性在成為單親后經濟狀況惡化或陷入貧困的概率明顯高于男性;與健康穩定的雙親家庭相比,單親家庭面臨著工作和家庭照顧的雙重壓力,更容易陷入失業困境,在經濟安全、社會與心理支持和兒童照顧上面臨著重重困難,尤其是女主家庭。[13-14]未婚生育的少女媽媽更是面臨著中斷學業和職業培訓的風險,甚至帶來貧困的代際傳遞,成為備受譴責的底層階級。[15]因為很多單身母親的工資收入非常微薄,公共援助成為她們重要的經濟來源,雖然美國還有相對慷慨的遺屬保險,但主要是支付給寡婦。因此,對大多數的女主家庭來說,AFDC及其之后的TANF是她們能夠得到的最主要的政府現金援助。
(二)AFDC最主要的領取者——貧困的女主家庭
為了扶助貧困家庭撫養其未成年子女,政府在AFDC這一社會福利項目上投入了大量資金。根據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DHHS)的統計數據,1962年,聯邦政府對AFDC支出和管理投入7.8億美元,1994年則達到141.92億。在1970—1994財年期間,AFDC津貼總支出從40.82億上升到227.97億。[16]總體上,在1962—1996年間,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AFDC上的支出一直保持明顯的上升趨勢。
AFDC支出的持續上升,不是由于津貼水平的提高,而是因為領取者人數的高速增長。1962年,享受AFDC津貼的家庭數是92.4萬個,領取者總人數達到359.3萬個;而在1994年,受助家庭數上升到504.6萬個;領取者總人數達到1 422.6萬個,撫養未成年子女的貧困女主家庭已然成為AFDC最主要的給付對象。1962—1994年間,單親家庭領取者的數量從87.6萬個上升到468.3萬個。以女主家庭為主的單親家庭一直在AFDC津貼領取家庭中占絕大部分,其占比高達90%以上。[17]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女主家庭一直占AFDC津貼給付對象的大多數,但早期的領取者主要是撫養未成年子女的寡婦家庭,而1960年代以來,因離婚、分居、未婚生育的單身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組成的貧困女主家庭成為AFDC津貼的主要領取者。
(三)AFDC遭到批判
1962—1996年間,雖然政府在AFDC上的支出不斷增長,但單親家庭的貧困率仍然穩步上升。在一定的意義上,AFDC并沒有改善而是滋長了單身母親的貧困狀況。因為AFDC不能給貧困家庭提供充分的經濟支持,這種事后補救型的社會政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雖然AFDC及其前身ADC有利于維持貧困單身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共同生活,但其潛藏的福利意識形態鮮明地體現了對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強化,因為它將母親角色直接定位為兒童照顧者,強化了婦女的傳統性別角色。保守主義者指責AFDC沖擊和破壞了傳統的家庭價值觀,間接鼓勵男性家長放棄養家糊口者的責任,最終導致家庭的解體和功能的弱化,助長了單親問題。[18]
以貧困單親家庭為主的AFDC領取者倍受非議,單身母親更是被打上了恥辱化的烙印,被貼上了雙重標簽:一是不工作,不參加勞動力市場;二是不結婚和不道德的婚育行為。在強調工作倫理和個人獨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和保守主義福利意識形態下,那些領取津貼的單親家庭被視為不勞而獲、不負責任、獨立意識薄弱的福利依賴者,長期領取AFDC津貼的單身母親被稱為懶惰、放蕩的“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動以貧困的單身母親為主的AFDC津貼領取者積極參加勞動力市場、依靠工作收入以脫離福利、實現自立,成為AFDC及其改革的重要取向。
四、AFDC改革——從福利到工作
作為自由主義福利國家范式的典型代表,美國的社會政策強調市場對個人福利的作用,相信市場是個人福利最重要的來源,鼓勵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實現經濟自給自足。因此,美國的勞動力去商品化程度在OECD的18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位。[19]52美國主流的福利意識形態強調新教主義的勞動天職觀和個人主義的獨立精神,而不是集體主義的互助互濟。這些使得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尤其強調工作福利(workfare),并貫徹與體現在AFDC及其改革中。
(一)AFDC中的工作要求與工作刺激
工作要求與工作刺激計劃一直伴隨著AFDC及其轉變,并成為這一福利制度的重要內容。在AFDC的實施過程中,將愿意尋找、接受工作或職業培訓作為待遇給付的前提條件,同時,通過工作激勵方案,推動與維持工作積極性。1962年,聯邦政府要求,AFDC津貼接受者如果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職業登記、職業培訓或職業介紹,就要從福利名單中清退。對于撫養6歲以下學齡前兒童的母親,鼓勵她們自愿參加職業登記并接受職業培訓和其他支持性服務。[20]同時,議會授權撥款支持“社區工作和培訓”項目(Community Work and Training),給AFDC津貼領取者提供免費培訓和就業服務。它規定,所有年滿18周歲的受助對象必須參加這個項目,參加社區勞動也可獲得與同類工作相當的工資。為了維持工作積極性,使福利領取者不因工作帶來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喪失領取津貼的資格,在家庭財產狀況調查計算家庭收入時,扣除與工作相關的支出,如上下班交通費用、工作所得稅等,還扣除為滿足未成年兒童潛在需要的儲蓄,如入托、教育和醫療費用等。
AFDC在給貧困的女主家庭提供必要經濟支持時,也要求和激勵單身母親參加工作,推動她們從依靠福利轉向依靠勞動力市場。歷屆美國政府都將AFDC項目與工作聯系在一起。1968年,議會要求各州政府建立《工作刺激法案》(WorkIncentiveAct,簡稱WIN),由健康、教育與福利部和勞動部通過州政府福利部門和就業服務部門共同管理。一是要求所有的單身母親必須參加《工作刺激法案》規定的就業和培訓登記,只有撫養6歲以下兒童的母親可以豁免。二是加大工作刺激力度,即在家庭財產狀況調查時,工作所得的第一個30美元及其剩余的三分之一都不計入家庭收入內。[6]52這意味著,只要總收入不超過150%AFDC基本津貼,加上30美元,加上150%工作相關支出,就不會喪失領取津貼的資格。
1980年代,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泛起,大力鼓吹市場的作用,批判全民福利摧毀了個人自我照顧能力,助長了依賴性。此間,關于單身母親與福利依賴之間的關系在美國引起了學界和公眾的持續關注。保守主義者甚至顛倒單身母親與福利之間的關系,認為慷慨而寬容的福利抑制了她們的工作動機,甚至誘導她們追求依賴福利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話語背景和削減福利開支的壓力下,里根政府大力推行從福利到工作(welfare-to-work)的工作刺激項目。1981年,議會授權州政府資助津貼領取者找工作,在“社區工作經驗項目”(CommunityWork Experience Programs,簡稱 CWEP)中,為她們提供工作救濟(work relief)和工作補貼(work subsidy)。在家庭財產調查時,頭四個月的工作收入不計入。1988年,《家庭支持法案》(FamilySupportAct)取代《工作刺激法案》,推行“工作機會和技能培訓計劃”(Job Opportunities and Basic Skills Training,簡稱JOBS)。聯邦政府要求各州盡其所能地推動3歲以上兒童的母親參加教育、工作或者培訓,這意味著只有3歲以下兒童的母親可以赦免,這是社會立法第一次要求學齡前兒童的母親必須工作。[20]總體上看,伴隨AFDC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刺激方案,旨在推動包括單身母親在內的津貼領取者積極參加勞動力市場,以最終結束福利依賴,實現經濟自立。
在工作要求的推動和工作刺激的激勵下,申領AFDC津貼的單身母親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有了一定的提高,工作加福利成為她們維持生計的基本模式。1968—1979年間,對女主家庭福利依賴的跟蹤研究表明,領取AFDC津貼母親的長期經濟來源是福利和工作所得,她們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從事兼職工作,每周的工作時間是5.4小時,微薄的工資收入使得她們無力養家,也無法完全退出福利。[21]雖然她們也有工作的意愿,但自身人力資本的缺乏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分化使得她們難以找到足以養家糊口的工作。
(二)工作福利——從AFDC到TANF
1990年代中期,降低福利開支、結束福利依賴成為美國社會政策改革與重組的重要目標。1994年的《福利指標法》(WelfareIndicatorsActof1994,簡稱WIA)明確指出,促進依賴福利轉向依賴收入。1996年8月22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福利改革法》(WelfareReformAct,簡稱WRA),即《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協調法案》(ThePersonalResponsibilityandWorkOpportunityReconciliationActof1996,簡稱PRWORA)。在這個法案下創建的“貧困家庭臨時救助”(TANF)取代了實施60余年的AFDC,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廢除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部分條款的一次。TANF旨在推動職業培訓、就業和婚姻,強調從福利到工作,要求福利接受者積極參加勞動力市場,通過工作收入實現生活自立。
TANF中的工作要求條款對州政府和受助者提出了明確規定。一是州政府必須大力推動津貼領取者參加工作,使其工作參與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具體來說,1997—2000財年間,單親家庭的工作參與率要從25%上升到50%,雙親家庭的工作參與率要從75%上升到90%。二是要求津貼領取者在受助期內必須工作或者尋找工作,否則就減少津貼水平。它規定,雙親家庭每周的工作時間不低于35小時,單親父母每周的工作時間或參加職業培訓的時間不低于20小時,少女媽媽要通過受教育來折抵工作時間;對撫養不滿3歲兒童的單身母親,是否豁免工作要求,或者撫養不滿6歲兒童且無法找到托兒機構的單身母親,是否放寬工作要求,由州政府自行決定。[6]57總體來看,TANF的工作要求更加嚴厲,更強調工作福利。
TANF的工作要求帶來了雙重性的效果。一方面,領取津貼的個案數量大幅下降,成年女性的工作參與率大大提高。2001年,TANF的個案規模比起1996年的AFDC領取者數量降低了56%,比1994年高峰期下降了63.2%;同時,單身母親的就業率從1995年的64%上升到2000年的75.5%,女主家庭的貧困率從42%下降到28.5%,兒童貧困率從22.2%下降到15.6%。[6]59另一方面,工作和家庭照顧的雙重壓力使得一部分單身母親更容易陷入失業或貧困境地。研究表明,將單身母親在TANF前后的經濟狀況進行對比發現,相當規模的女主家庭比起她們依賴福利時生活更加貧困,在退出TANF的女主家庭中,貧困率高達50%以上。因為在TANF嚴格的給付資格和領取條件下,一些單身母親雖然走進勞動力市場,但她們所從事的工作穩定性差、報酬低,實際收入反而比福利津貼低。[22]總之,TANF取代AFDC后,雖然貧困單身母親的就業率有一定上升,但那些無法正式就業或者工資收入低下的單身母親處于一種更加邊緣的地位。
(三)工作與福利——兩難困境中的貧困單身母親
AFDC及其改革后的TANF對美國貧困女主家庭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這是一個具有兩面性和矛盾性的社會政策。第一,推進工作結束福利依賴的政策,假設如果有工作就有收入來源,則能實現經濟獨立,則無需福利支持。這忽視了貧困的單身母親有強烈的工作意愿,不是她們不愿或者不想工作,而是勞動力市場提供的工作機會和就業質量方面有現實的障礙。由于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分化,她們只能參加次級勞動力市場,從事低劣的非正式工作、兼職工作,成為名符其實的“工作窮人”。[21]她們缺乏的不是工作動機,而是缺少足以維持家庭開支的工作機會。第二,政策實踐表明貧困的單身母親面臨工作和家庭照顧的兩難困境。一方面,AFDC及其后的TANF潛在地強化了單身母親承擔兒童照顧者的性別角色;另一方面,又推動單身母親積極參加勞動市場,承擔養家糊口的重任,這意味著要求單身母親兼任母職和父職。她們在家庭生活和勞動力市場中處于母親、兒童照顧者與養家糊口者、勞動者這一雙重角色的矛盾之中,承受著家庭照顧的重任和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壓力。第三,工作福利是以男性為參照標準,以與男性無差異的單一就業形式來判斷單身母親的就業狀態,將女性等同于男性,忽略了男女的差異和性別角色的實際處境的差異。對于貧困的單身母親來說,依靠福利會帶來恥辱標簽,但工作又意味著自己無法全力照顧家庭,由于缺乏普遍性的公立兒童照顧體系,參加工作的單身母親不得不承擔高額的兒童照顧支出。在一定意義上,從AFDC到TANF的改革,片面強調工作福利,試圖將單身母親從福利領取者隊伍驅趕到勞動力市場,忽視了她們在勞動力市場參與和角色承擔上的現實障礙。這無益于單身母親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更不利于推動性別平等。社會政策應該從重構性別角色、推動性別平等的角度入手,切實改善單身母親的社會經濟地位。
五、從社會性別視角看AFDC和TANF
社會性別理論不是片面地強調兩性之間的一致,而是從兩性之間的差異出發,承認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認同兩性的需求、經驗以及實際利益也有不同。莫林諾克斯(Moleyneox,M.)和摩塞·卡羅琳(Moser Caroline)分別提出了性別利益(gender interests)和性別需求(gender needs)概念,并將其區分為現實性和戰略性兩類。前者是從婦女地位的實際條件與現實需求出發,在現存的性別角色分工下,婦女因既有的社會角色,如母親、家庭主婦、兒童照顧者等所產生的實際需求;后者則是從婦女的從屬地位以及作為他者的存在方式來演繹的,基于兩性關系的不平等、社會結構的性別分層和勞動的性別分工而形成的需求。[23]現實性別需求和戰略性別需求的區分為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分析AFDC及其之后的TANF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維度。
福利國家將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男性作為養家糊口者,使得男性往往享有與勞動力市場參與相關的社會保險,而女性則不得不依靠具有恥辱化效果的社會救助和選擇性的社會福利服務。AFDC即是從基于傳統性別分工的現實性別需要出發,旨在協助單身母親順利承擔傳統性別角色——母親和兒童照顧者的職責,使她們有效完成并繼續完成既有性別角色要求。簡言之,滿足現實性別需求的社會政策項目只是強化傳統社會性別角色,不會提高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也不能為她們賦權。因此,1962—1996年間,雖然AFDC津貼支出猛增,但撫養未成年子女單親女主家庭的貧困率及其在貧困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呈現不斷攀升的態勢,而在這一社會政策影響下完成性別角色再生產的單親母親還被標簽化為“福利母親”。
從性別需求的維度來看,社會政策不僅要關注單身母親基于社會性別分工的現實性別需求,還要滿足她們的戰略性別需求。應看到傳統的父權制社會制度和勞動力市場結構對她們造成的影響,努力改變她們在公民身份上遭遇的社會排斥、在勞動力市場上遭到的歧視、在性別關系中遭到的壓迫。概言之,社會政策不僅要滿足單身母親的現實性別需求,更要滿足她們的戰略性別需求。第一,要健全公立性的兒童照顧體系,緩解單身母親遭受的工作與家庭照顧的雙重壓力。事實上,美國政府對這個問題不是無力作為或無所作為。“二戰”期間,美國為了推動婦女在戰爭工廠中工作,為學前兒童提供公共性日托服務。但戰后,聯邦政府停止了對日托服務的財政支持,使得工作母親不得不依靠價格高昂的私立性托兒服務。而在以瑞典為原型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政府通過綜合性的家庭福利將兒童照顧和親職工作的成本社會化,建立龐大的公共部門提供社會服務,不僅為婦女獲得有酬工作給予最主要的機會來源,而且為她們將兒童照顧和有酬工作結合起來提供支持。[19]223-224美國單身母親的經濟狀況遠遠低于德國、瑞典等發達國家的單身母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尚無普遍性的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制度,也沒有普惠型的公共性兒童照顧體系,而是一直片面依賴殘補性的社會救助制度。[24]第二,要改善單身母親的工作機會和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層。對于包括單身母親在內的女性而言,勞動力市場參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工作為她們參與社會生活和實現經濟獨立提供機會和途徑,有助于實現男女平等、擺脫福利依賴;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分化又是性別取向的,職業的性別隔離通過教育不平等和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使得女性在求職時面臨累積的障礙,導致女性被分配到工資低的行業和職業中,形成所謂的“女性職業”,或者在給定的行業和職業中,女性的工資低于男性,即“同工不同酬”。這不利于婦女解放和單身母親社會經濟狀況的改善。TANF取代AFDC盡管提高了單身母親的就業率,但忽視了這一群體的社會人口學特征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分化,使得單身母親陷入嚴重的工作貧困狀態。社會政策要從戰略性別需求的角度,批判與反思現存的性別不平等結構,挑戰勞動力市場的性別隔離,改善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
[1]PIERSON P.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Research[J].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0, 33(6): 791—821.
[2]SKOCPOL T.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Future Possibi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13.
[3]SKOCPOL T.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SA[M].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441—447.
[4]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The Baselin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AFDC Program[EB/OL].[2015-01-20]. http://aspe.hhs.gov/hsp/afdc/baseline/1history.pdf.
[5]GOLDBERG S, COLLINS D. Washington’s New Poor Law: Welfare “Reform” and the Roads Not Taken, 1935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Apex Press, 2001: 32.
[6]CAPUTO K. U.S. Social Policy Reform: Policy Transition from 1981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Springer, 2011.
[7]LAMISON-WHITE L.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6[R].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8]STEVENSON B, WOLFERS J. Marriage and Divorce: Changes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21(2):27—52.
[9]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on-martial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99[J].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2000, 48(16):5.
[10]U S Census Bureau. People and Families in Poverty 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 2001 and 2002[EB/OL].[2015-02-30]. http:/www.census.gov/hhes/poverty/poverty0 2/table2.pdf.
[11]RANK R. One Nation, Underprivileged: Why American Poverty Affects Us Al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6—28.
[12]WEITZMAN J. The Un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American[M].New York: Free Press, 1985:62.
[13]MCLANAHAN S.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over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0(4):873—901.
[14]SANDS G, NUCCIO E. Mother-head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A Feminist Perspective[J].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 1989, 4(3):25—41.
[15]MCLANAHAN S, BOOTH K. Mother-only Families: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tic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89, 51(3):557—580.
[16]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The Baseline. Federal and state expenditures for AFDC[EB/OL].[2015-02-30].http://aspe.hhs.gov/hsp/afdc/baseline/4spending.pdf.
[17]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The Baseline. Trends in the AFDC caseload since 1962[EB/OL].[2015-02-30]. http://aspe.hhs.gov/hsp/afdc/baseline/2caseload.pdf.
[18]MURRY C.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M].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19]ESPING-ANDERSE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20]ROGERS S. Work Test for Welfare Recipients: the Gap between the Goal and the Reality[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981, 1(1):5—17.
[21]HARRIS M. Work and Welfare among Single Mothers in Pover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2):317—352.
[22]CANCIAN M, HAVEMAN H, MEYER R, WOLFE C. Before and After TANF: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Women Leaving Welfare[J].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02, 76(4):603—641.
[23]劉春燕,楊羅觀翠. 對福利政策社會性別分析的評述[J].婦女研究論叢,2010(4):100—104.
[24]WONG,YIN-LING, IRWIN G, MCLANAHAN S. Single Mother Families in Eight Countries: 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Policy[J]. Social Service Review, 1993, 67(2):177—197.
(文字編輯:王香麗 責任校對:徐朝科)
2015-03-06
胡杰容(1976—),女,漢族,社會學博士,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社會福利政策,婦女與兒童福利。
胡杰容.美國單身母親與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政策改革——社會性別的視角[J].社會工作與管理,2015,15(5):66—73.
C916
A
1671-623X(2015)05-006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