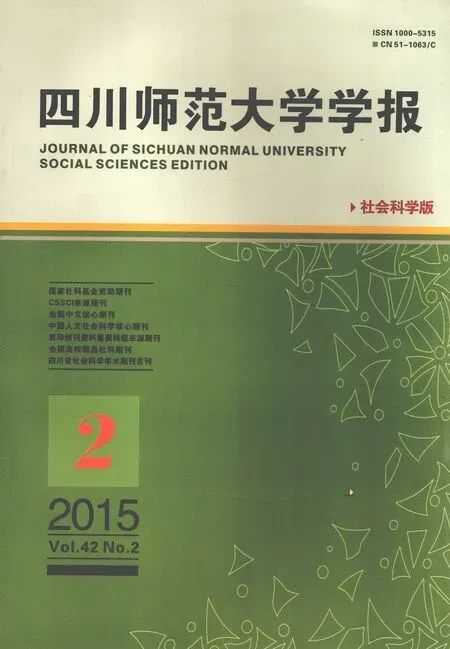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評估與對策
汪 婧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人文學院,廣東深圳518055)
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評估與對策
汪 婧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人文學院,廣東深圳518055)
近年來,基于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考慮,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擔憂與日俱增。根據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評估,美國認為中國可能正利用日益增強的信息技術能力對美發起網絡戰,對此必須加強對中國的網絡防御,尋找網絡安全合作伙伴,構建國際網絡空間秩序,使網絡政策和安全防御一體化,加強網絡威懾或擊敗敵手的能力。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政策充滿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與中國缺乏網絡安全戰略互信,試圖主導網絡空間秩序和確保美國網絡空間霸權,對中美關系與世界和平造成了危害,因此當務之急是中美建立網絡安全戰略互信關系及機制,并積極應對兩國間出現的網絡安全問題。
中國網絡戰能力;美國;評估與對策
隨著網絡空間和信息技術的急速發展,網絡安全問題紛至沓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甚至宣稱“未來戰爭是網絡空間的戰爭”。2011年5月,奧巴馬政府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Prosperity,Security,and Openness in a Networked World),稱如果遭受的網絡攻擊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將盡一切所能予以應對[1]。隨后美國國防部在是年7月發布“網絡空間行動戰略”(Department of Defense Strategy for Operating in Cyberspace),將網絡空間正式列為與陸、海、空并列的第四大行動領域,其戰略目的是“有效阻止敵人利用網絡對美國發起軍事行動”[2]。事實上,自比爾·克林頓總統以來,美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網絡安全戰略及相關政策,并逐步構建起日臻成熟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基于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考慮,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擔憂與日俱增,明確把“假想敵”的矛頭對準中國,在國際輿論中渲染“中國網絡戰威脅論”。本文依據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在2013年4月發布的檔案[3]以及美國政府官方發布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相關文件,細致分析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評估和對策,闡述和分析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政策的性質和特點,總結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對中國的啟示和借鑒。
一 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評估
2009年10月,美國國會成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布“關于中國實施網絡戰和計算機網絡開發利用能力的報告”(Report on the Capabil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Conduct Cyber Warfare and Computer Network Exploitation)。這份報告利用中方發布的權威公開資料,對中國在和平時期和沖突時期執行計算機網絡行動作為戰略情報搜集工具的能力作出綜合性評估,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時計算機網絡行動戰略和整合各種能力的戰略水平;(二)弄清在中國計算機網絡行動中誰是主要機構和個體行為者,以及民用和軍用運營者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三)考察中國在沖突中針對美國進行計算機網絡行動的可能目標;(四)分析中國以美國政府為目標的不間斷的網絡開發利用行動的特點;(五)梳理中國入侵美國政府和工業網絡的大事年表。關于中國的計算機網絡行動戰略,報告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積極發展計算機網絡行動能力,并正在創建戰略方針、工具和專門人員以支持傳統作戰訓練”;“在戰略和作戰水平上,獲得‘制信息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關鍵目標”;“中國已經通過一項名為‘網電一體戰’的正式信息戰戰略”,“這似乎是中國進攻性信息戰的基礎”;“中國可能正在利用其日趨成熟的計算機網絡開發能力,實施一場長期的、復雜的計算機網絡開發行動,用以搜集美國政府和工業情報”[3]。
2012年3月,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再次發布評估報告,題為“占領信息高地:中國計算機網絡行動和網絡間諜能力”(Occupying the Information High Ground:Chinese Capabilities for 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 and Cyber Espionage)。這份報告在2009年評估報告基礎上進行了詳盡的跟蹤和擴充,對六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評估:(一)中國網絡戰戰略的發展態勢;(二)中國用以支持對美國通信網絡進行情報滲透和采集的計算機網絡開發利用能力的新發展;(三)中國網絡攻擊美國系統和基礎設施,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和美國本土軍事力量的潛在影響;(四)中國進行計算機網絡行動和計算機網絡開發的主要行為人;(五)中國最杰出和最有影響力的遠程通信研究機構、公司和財團的活動和研究方向,美國通訊供應鏈的潛在風險和美中信息安全公司之間合作的風險和現實;(六)對當代網絡罪犯和中國政府資助行動的工具和技術進行比較評估[3]。報告認為,隨著中國聯合行動和信息戰能力的增強,中國有能力利用其防御工具或真正的進攻性武器,給美國及其盟國領袖在決定是否干涉中國發起的沖突中提供更為復雜的風險變量;一旦發生沖突,中國計算機網絡行動能力將會給美國的軍事行動帶來真正的風險;支持中國計算機網絡行動的關鍵實體和機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和第四部等,商業IT公司如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等,以及一些開展相關研究的普通高校和軍事院校[3]。報告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尋找占領現代戰爭中“信息高地”的途徑,計算機網絡行動(攻擊、防御和開發利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取初期信息優勢和支持其他行動的基礎;計算機網絡行動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已經超越單純的軍事含義,而是具有戰略意義,并將廣泛用于促進中國國家發展的長期戰略[3]。2012年11月9日,該委員會在給美國國會的年度報告中聲稱,中國已經成為“網絡世界最具威脅性的國家”,美國政府應該深入評估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考慮對從中漁利的中國企業加大處罰力度[4]。
2012年5月,美國陸軍軍事學院(U.S.Army War College)出版專題論文“信息即力量:中國網絡力量和美國國家安全”(Information as Power:China’s Cyber Power an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該論文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為總體網絡戰爭作準備”,包括“進行網絡偵察,打造經濟損害和破壞關鍵基礎設施的能力,準備破壞常規武裝沖突必需的通訊和信息系統,準備實施心理戰以影響美國人的決心”[3]。文章考察了中國網絡力量的發展狀況和網絡能力,以及中國如何利用網絡力量支持國家安全目標,推究中國網絡力量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程度,并為改善美國網絡安全和防御政策提出建議。文章指出,雖然美國必須看到其超級大國地位正遭到中國網絡力量的挑戰,但是并不意味著網絡戰不可避免;對此,美國應該認識到網絡安全和防御是國家安全和防御問題,不斷增強美國的網絡防御,與中國直接建立聯系和互信,確立網絡空間行為準則,還要將北約、印度作為美國的網絡安全合作伙伴,制定國際認可的網絡空間行為規范;與此同時,美國應該努力使網絡政策和安全防御一體化,必須擁有在網絡空間威懾或擊敗其敵手的能力[3]。
2012年10月,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發布題為“對抗中國網絡行動:對美國利益的機遇和挑戰”(Countering Chinese Cyber Operation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Interests)的評估報告。報告認為,由于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和全面信息識別的需要,據稱中國共產黨、中國國家權力機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針對廣泛的國際目標開展一項計算機網絡協同行動,而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對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造成了先進的持續的威脅。報告主要考察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作為計算機網絡開發利用執行機構的基本情況。報告建議,為了應對中國“網絡間諜活動”,美國應該通過深思熟慮的欺騙來減少信息的價值,加強反間諜活動,與臺灣等國際伙伴增進合作,通過有效的威懾來強加成本等[3]。
二 美國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應對策略
通過以上對中國網絡戰能力的幾份評估報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智庫強調中國的計算機網絡行動戰略水平和開發利用能力在不斷提高,針對美國的計算機網絡行動不斷增加,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建議美國政府予以積極應對。據此,美國政府應對中國網絡行動和開發利用能力發展的策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加強對華網絡情報活動
根據2013年6月6日愛德華·斯諾登向《華盛頓郵報》和《衛報》披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棱鏡”項目(PRISM),美國國家安全局與谷歌、蘋果、微軟、臉譜、推特等9家互聯網公司自2007年就已經開始合作,對全球范圍內互聯網數據流進行實時動態監聽。斯諾登公布的資料顯示,“棱鏡”項目主要監控10類信息,包括電郵、即時消息、視頻、照片、存儲數據、語音聊天、文件傳輸、視頻會議、登錄時間和社交網絡資料的細節等[5]。隨后,美國外交政策網站2013年6月10日發文披露稱,一系列機密信息顯示,美國國家安全局設有一個名為“定制入口組織辦公室”(the Office of 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或TAO)的秘密機構,在過去15年時間里,TAO已成功滲透進入中國計算機及電信系統,獲得了有關中國國內所發生的“最好的、最可靠的情報”。據稱TAO是美國國家安全局信息情報理事會最大、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有超過1000名軍隊及民間的計算機黑客、情報分析家、目標定位專家、計算機硬件及軟件設計師、電氣工程師等,黑客們每周7日、每日24小時輪班[6]。2014年3月23日,根據《紐約時報》曝光的機密文件,華為是美國國家安全局代號“狙擊巨人(Shotgiant)”項目的目標,NSA從2007年開始就侵入深圳華為公司的服務器,以查看其是否與中國政府有聯系,同時監控華為高管的通信,并收集華為產品的信息[7]。
(二)增強亞太地區網絡防御合作
1947年,美國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五國達成一項名為“UKUSA”的秘密安全協定,組成后來著名的代號為“梯隊”系統(ECHELON)的全球電子情報監聽網絡(信號情報收集和分析網絡,SIGINT),其中澳大利亞負責中國南部和印度地區,新西蘭負責西太平洋,加拿大負責蘇聯的北極地區,英國則主要負責蘇聯的烏拉爾山以西地區、非洲和歐洲,而美國自己的監控能力覆蓋中國北部、亞洲、蘇聯亞洲部分和拉美[8]。后來美國相繼在德國、日本和韓國建立軍事基地,監控活動也隨之擴大。可見,在亞太地區美國早已同其盟友對中國實行全方位監控。2004年,美國對臺軍售10套衛星監聽截收系統,用于監聽大陸的衛星通訊信號和截收衛星通訊中的聲音、圖像和數字信號,使美國在亞洲建成繼韓國之后第二個擁有“梯隊”系統的中樞網點[9],進一步增強了美國對中國的網絡情報活動能力。
2010年5月,美國國防部宣布成立網絡司令部(Cyber Command),隸屬于美國戰略司令部,以網絡防御戰作為主要任務。2011年7月,美國國防部發布首份“網絡空間行動戰略”,把網絡空間列為與陸、海、空、太空并列的行動領域,使網絡政策和安全防御一體化,加強網絡威懾或擊敗敵手的能力,并提出主動防御以及加強與盟友合作[2]。2011年9月14-16日,美澳兩國定期部長級磋商,據稱在會晤時雙方將網絡空間防御納入《澳新美安全條約》[10]。2013年7月22日,“梯隊”系統澳、加、新、英、美五國國家安全最高官員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舉行會議,集中討論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安全、打擊暴力極端主義以及有關數據交換的倡議[11],從而進一步增強亞太地區網絡防御合作。
(三)確立美國主導的國際網絡空間秩序
2011年5月16日,美國白宮發布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高調表示,美國國際網絡空間政策強調“對基本自由、個人隱私和信息自由流動的核心承諾”,以此為基礎提出支持基本自由、尊重財產權、尊重隱私、預防犯罪、自衛權、全球互通、網絡穩定性、可靠訪問、利益攸關者共同治理、穩妥處置網絡安全等十大網絡空間行為規范。為此,美國將綜合運用外交、國防和發展三項措施,主要在外交上加強伙伴關系;在國防上采取勸阻及威懾策略;發展上尋求建設技術能力、網絡空間能力和政策關系以獲得繁榮與安全。為實現這一愿景,美國政府將在七個領域開展活動:(1)經濟,推動建立國際標準和創新型的開放市場;(2)保護網絡,加強網絡安全性、可靠性和恢復能力;(3)執法,拓展合作與加強法治;(4)軍事,準備應對21世紀的安全挑戰;(5)互聯網管治,推動有效和包容性的管治結構;(6)國際發展,提高能力,確保安全,促進繁榮;(7)互聯網自由,確保基本自由和隱私安全[1]。從這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強調“安全”、“繁榮”、“價值觀”和“主導權”四個戰略目標,其本質是通過一系列戰略部署和行動策略,利用其網絡技術優勢,確立美國主導的國際網絡空間秩序[12]。
三 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政策的幾個缺陷
第一,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政策充滿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和中國在國際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國對華政策變得更加務實。對華定位為利益攸關者,但從美國多方對中國網絡行動能力和開發利用能力的評估報告及其對策建議來看,由于美國情報部門監控到一些對美國政府網絡的“黑客”行為和網絡間諜活動IP地址來源于中國,一些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就想當然地認為是中國政府和軍隊在背后主導和參與了這些攻擊行為。例如早在2010年美國媒體曾僅依據一個發布病毒郵件的IP地址,就宣稱山東藍翔技術學校和上海交大信息安全工程學院是政府背景的中國黑客“大本營”,但事實上該IP地址來自學生寢室的一臺感染木馬病毒的電腦。稍有常識便知,網絡攻擊者總是盡可能地隱藏其真實地址和身份,僅憑IP地址的通聯關系就確定攻擊源來自中國是令人毫無信服的依據的,因此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政策充滿著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美國對于中國防御性軍事戰略的懷疑和對中國崛起意圖的不信任滲透在評估報告之中。但與美蘇爭霸的冷戰時代所不同的是,后冷戰時期的冷戰思維表現出內在的矛盾,美國不可能像對蘇聯一樣遏制中國,而是采取遏制與合作的雙重態度。在2013年6月8日的“習奧會”上,兩國元首同意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即“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13],這一共識具有歷史性意義,也為中美網絡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礎。
第二,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認知誤差較大,與中國缺乏戰略互信。從美國方面披露的各種報告,如曼迪亞特公司和國防部的報告,都多次討論所謂的中國對美國的“網絡間諜活動”和中國對美國“無間斷網絡攻擊威脅”,過分夸大中國的網絡戰能力。2013年2月19日,美國網絡安全公司曼迪亞特(Mandiant)發布了一份長達76頁的安全研究報告,一方面詳細闡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機構設置與智能,另一方面闡述該公司的重要發現與證據,稱其用6年時間追蹤了針對141家美國公司或組織的1905次持續入侵行動,其中追蹤到97%的IP地址來自上海,而且發現被追蹤的入侵使用的是簡體中文計算機操作系統,認定此類黑客行動一定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與這些黑客存在密切聯系[3]。2013年5月6日,美國國防部公布向國會提交的“2013年度涉華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聲稱:“美國政府計算機系統正在遭到中國政府和軍隊的直接入侵”,意即中國正在利用“網絡間諜活動”搜集美國外交、經濟和國防工業基礎等方面情報,并可能很容易利用同樣的手段給美國通信網絡毀滅性打擊[14]。可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誤差較大,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缺乏戰略互信。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6月8日“習奧會”上,中美兩國元首就網絡安全問題達成共識,對構建網絡安全戰略互信具有建設性意義。中方指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網絡安全問題,反對任何形式的黑客和網絡攻擊行為。中國也是網絡攻擊行為的受害者,是網絡安全的堅定維護者。在網絡安全問題上,中美面臨共同挑戰。網絡安全不應成為中美互疑和摩擦的源頭,而應成為兩國合作的新亮點。雙方同意通過已設立的兩國網絡工作組,加強對話、協調與合作,并通過聯合國這一主渠道,推動建立公正、民主、透明的互聯網國際管理機制,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15]。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為中美雙方在網絡安全上建立戰略互信奠定了基礎。
第三,美國試圖主導國際網絡空間秩序,確保網絡空間霸權地位。基于美國在網絡安全領域的能力建設、制度設計和戰略制定無疑有著顯著的優勢,美國政府試圖在國際領域主導網絡空間秩序,確保其網絡空間霸權地位。2006年12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網絡空間作戰國家軍事戰略”強調:“美國必須擁有網絡空間優勢,通過一體化的網絡防御、偵查和攻擊,確保美國的行動自由并阻撓敵方的行動自由。”[16]2011年5月16日,奧巴馬政府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報告,強調“規則”和“秩序”的重要性,聲稱“通過規范尋求穩定”,表示“美國將致力于就可接受的行為達成共識,與那些認為這些規則對于各國自身利益和各國共同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家結成伙伴關系”[1]。該報告是美國在新形勢下針對網絡空間規則和秩序建立的重要政策宣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試圖為網絡空間確立行為規則的同時,強調“要保留自衛的權利、自由行動的權利,發展和保持網絡空間控制能力以及應對潛在危險的應變能力、防護能力、恢復能力和反擊能力”等[1]。顯然,“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的實質是要確立美國在網絡空間秩序方面的主導地位,以及保持美國在網絡空間的絕對優勢。對此,中國應該積極防御,建立健全國家網絡安全政策決策體制機制,加速形成我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將中國對網絡安全的定義、涵蓋的主要領域、遭遇的挑戰與威脅、政府應對措施等問題形成官方的文件,從而建立起新型大國對網絡安全的新認識。
四 美國對華網絡空間安全戰略的評價與啟示
從2013年開始至今,美國對中國頻繁發起網絡安全攻勢,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更要認清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實質,堅持和平發展戰略,建設好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
其一,美國在網絡安全問題上對中國抱有的“冷戰思維”具有誤導性,對中美關系與世界和平造成危害。冷戰思維“過分強調國家間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念的對立,具有‘非敵即友’和必須確定一個頭號敵手的觀念,把前蘇聯當作評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行為的參照物”,冷戰思維是導致“中國威脅論”的重要因素[17]61-62。由于美國對中國仍然抱有冷戰思維,美國政府和智庫對中國的網絡戰能力作出了不確切的評估,過分夸大中國的網絡戰能力,錯誤地認為中國政府和軍隊正在“入侵”美國政府計算機系統,將中國視為“網絡世界最具威脅性的國家”[6]。雖然后冷戰時期的冷戰思維表現出內在的矛盾,美國對中國采取遏制與合作的雙重態度,但美國政府和智庫的冷戰思維仍然具有很強的誤導性,不但影響新時期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中美關系產生消極影響,也會使世界和平與和諧遭受危害。
其二,中美建立網絡安全戰略互信在實踐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正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但是,由于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等方面的差異,中美兩國在政治、軍事、戰略安全等方面都存在很深的猜忌和互疑,影響著雙邊關系向更深層次發展,影響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在網絡安全領域,中美兩國必須增加信息透明度,及時通過各種對話機制進行真誠溝通以增進戰略互信。一方面,增進戰略互信能夠提高雙方信任,減緩緊張情緒,加強國際網絡空間的和平與安全,有助于約束雙方在網絡空間潛在的入侵或破壞行為。另一方面,增進戰略互信也是中美兩個大國自信和負責任的表現,對共同構建網絡空間行為規范具有積極作用,也將促進國際網絡空間的安全與穩定。目前,中美兩國在網絡空間安全領域增進戰略互信已有良好的前提:一是中美關系日益機制化,雙方在各層次、各領域都建立了對話與合作機制,特別是最高層次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二是2013年6月“習奧會”兩國元首就網絡安全問題達成共識,并將通過兩國網絡工作組加強溝通與合作,為中美建立網絡安全戰略互信奠定了基礎。
其三,中國相關部門和行業應該借鑒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并積極應對。首先,重視頂層設計,實現有序管理。以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領導核心,統籌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總政聯絡部、外交部等部門,建立比較健全的國家網絡安全政策決策體制,盡快形成中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取得國際網絡安全的話語權。另外,可以參照美國創建網絡戰司令部,對網絡安全威脅實施動態監控和主動防御,進行網絡攻防對抗演習,提高網絡戰防御水平。其次,加強科技研發,盡快實現技術自主。我國網絡信息領域的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重要信息系統安全存在很多隱患。因此,必須加大對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簡稱“核高基”)的研發和投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各大網絡信息研究所、高等院校、網絡運營商、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等相關機構與行業也應該在加強網絡安全和防御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和技術更新。最后,注重網絡信息技術人才的培養和利用。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等多種途徑,培養出更多高水平的網絡安全工程師隊伍;通過政府和企業的資金支持,網羅海內外網絡安全領域高技術人才;通過政策扶持和資金援助,加強我國網絡安全公司和“白帽”團隊(如中國著名的“白帽”團隊Keen Team)的建設和發展。
[1]The White House.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Prosperity,Security,and Openness in a Networked World[EB/OL].[2014-03-09].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y_for_cyberspace.pdf.
[2]Department of Defense.Strategy for Operating in Cyberspace July 2011[EB/OL].[2014-03-09].http://www.defense.gov/news/d20110714cyber.pdf.
[3]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424[EB/OL].[2014-03-09].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24/.
[4]USCC 2012 Annual Report[EB/OL].[2012-11-09].http://origin.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s/2012-Reportto-Congress.pdf.
[5]PRISM.From Wikipedia[EB/OL].[2014-03-09].http://en.wikipedia.org/wiki/PRISM_%28surveillance_program%29.
[6]Inside the NSA’s Ultra-Secret China Hacking Group:Deep with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an elite,rarely discussed team of hackers and spies is targeting America’s enemies abroad[EB/OL].[2013-06-10].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6/10/inside_the_nsa_s_ultra_secret_china_hacking_group.
[7]美監聽計劃Shotgiant曝光中國業界強烈譴責[EB/OL].[2014-03-23].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23/5983191. shtml.
[8]ECHELON From Wikipedia[EB/OL].[2014-03-09].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ELON.
[9]臺灣軍方加入美國監聽網絡 截收大陸衛星信號[EB/OL].[2004-01-05].http://news.qq.com/a/20040105/000160.htm.
[10]網絡空間成新戰場 美國澳大利亞擬結網絡戰同盟[2011-09-16].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shbt/2011-09-16/content_3795921.html.
[11]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要求安全合作達到新水平[EB/OL].[2013-07-25].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3/07/20130725279491.html#axzz2vxhVtahN.
[12]劉勃然.21世紀初美國網絡安全戰略探析[D].長春:吉林大學,2013.
[13]楊潔篪談習奧會晤成果系中美高層交往之創舉[EB/OL].[2013-06-09].http://news.youth.cn/gn/201306/t20130609_ 3345337_1.htm.
[14]Department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EB/OL].[2013-05-06].http://www.defense.gov/pubs/2013_China_Report_FINAL.pdf.
[15]楊潔篪談習奧會晤成果系中美高層交往之創舉[EB/OL].[2013-06-09].http://news.youth.cn/gn/201306/t20130609_ 3345337_2.htm.
[16]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Operations December 2006[EB/OL].[2014-03-09].http://www.carlisle.army.mil/DIME/documents/National%20Military%20Strategy%20for%20Cyberspace%20Operations.pdf.
[17]張小明.何謂“冷戰思維”[J].世界經濟與政治,1997,(4).
The United States’Assess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to China’s Cyberwarfare Capabilities
WANG J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Shenzhen Polytechnic,Shenzhen,Guangdong 518055,China)
In recent years,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ology,the United States is increasingly concerning about China’s cyberwarfare capabilities.Based on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cyberwarfare capabilities,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China is likely to use the increasing abil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launch cyber warfare to the United States,so it must not only strengthen network defense and look for partners,but also build international network space order,integrate make policy and security defense network as well as to strengthen network ability to deter or beat the enemy.The U.S.cyber security policy toward China is full of ideological bias and cold war thinking in that it lacks strategic mutual trust with China on network security and tries to dominate the network space order to ensure network space supremacy.
China’s cyberwarfare capabilities;the United States;assess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D771.236
A
1000-5315(2015)02-0043-07
[責任編輯:張 卉]
2014-04-03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冷戰及后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隱蔽行動研究(1949-1999)”(14BSS031)的階段性成果。
汪婧(1982—),女,安徽桐城人,歷史學博士,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冷戰史、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