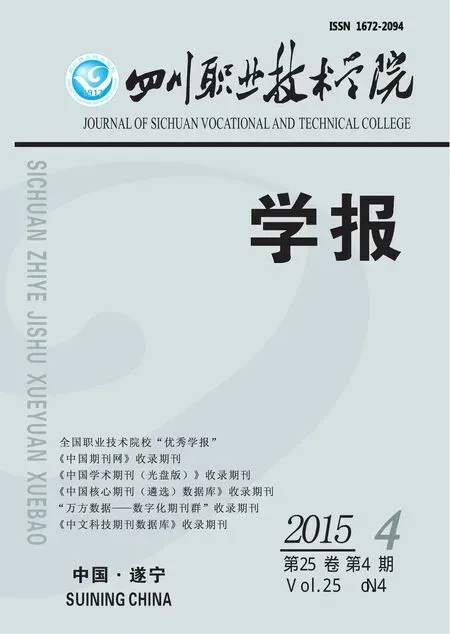論昌耀后期詩歌中的衰老主題
陳曙娟(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期刊社,江蘇 南京 211168)
論昌耀后期詩歌中的衰老主題
陳曙娟
(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期刊社,江蘇南京211168)
昌耀是一位將生命真正融于詩歌創作的踽踽獨行的“荊冠詩人”。昌耀大半生蝸居西部青海,其詩歌是從西部的文化背景中生發出來的,具有拼搏、抗爭、創造、進取的特質。當然,昌耀的詩歌并不局限于西部,而是同時置身于我國悠久的歷史大背景和遼闊的時代大背景之中,隨著大背景的轉換,其藝術風格和主導思想也發生變化。在對困境的反抗中形成的不斷張揚的生命意識,使得昌耀的前期詩歌牢固地建立在昂揚的精神高原之上,然而,其后期詩歌的思想脈絡隨著社會轉型發生了較大變化,衰老主題的出現正是其中一個重要表現。
衰老主題;理想主義者;異化;社會轉型
如果將人生的軌跡比作拋物線,那么昌耀前期詩歌中的主體形象無疑處于上升階段。外部環境為詩人設置下苦難的同時也提供了成長機緣,詩歌正因為具有了掙扎、奮斗和超越的主題而顯得充實和生動。這種樂觀的抗爭式價值理念,賦予詩歌一種崇高價值。然而,求之高、愛之切,難免會導致失落和懷疑。在昌耀的詩歌中,主體形象所向往和追求的超越性存在一旦隱退,生活的最高目標便會缺失。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面對精神的大幅度貶值現象,昌耀痛心疾首,其詩歌創作主題隨著社會轉型而發生嬗變。在目標自我和當下自我之間形成的強烈對照之下,詩人產生了至深的荒誕意識和反省意識,衰老主題便出現在了他的后期創作中。
1 背景
平反復出時的昌耀已年屆中年,但他在詩歌創作中仍努力讓心理年齡和精神氣勢與青年時保持一致。他在《古本尖喬——魯沙爾鎮的民間節日》中寫下氣勢如虹的詩句:“青春不會消寂。/不會隨皮肉的衰老而衰老。/不會隨皮肉的腐朽而腐朽。/青春不會消寂。”“青春之烈焰比閃光的佛焰苞遠為華麗。”正是在如此強盛的精神氣勢中,昌耀迎來了創作的高峰期。他大筆揮就了《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這四首引人注目的紀傳體系列長詩。因為他的詩仍然保持著青春的氣質和戰士的激情,所以有人誤認為詩歌王國冉冉升起了一顆新星[1]。但是,昌耀這種正當青壯年的自我強調和自我激勵并未持續多久,他很快意識到來自暮秋的一種暗示。昌耀的生命意識和精神狀態發生了較大變化,衰老、蒼老等詞語開始在詩中頻繁出現:“大地/每刻落地開花生根的名字/像密林/懸掛的青枝/然后再某一天/同時衰老”(《血路》)“人人都是時光對抗中的敗北者”“我們重又體驗蒼老”(《象界》)……這里的衰老主要指心理上的衰老,主要是由其時代背景造成的。
從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我國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現代商品社會轉型,給人們的物質生活帶來便利,這的確體現著歷史的進步,但是負面影響也接踵而來。物欲橫流、精神貶值、人格異化等逐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昌耀對此感慨頗深,他在《與梅卓小姐一同釋讀<幸運神遠離>》一文中寫道:“人滿為患,金錢肆虐,半個世紀,尤以現今為最。”在商業文化的熏染下,人的存在被明確指歸為物質性存在,很少有人再提及非物質、純精神上的理想,也很少有人能繼續承受信仰之重,曾經占據時代主流的信仰轉眼變為虛無。經濟上的成功成了這個社會獨尊的價值尺度,從“毛澤東時代”走過來的那代理想主義者步入新環境后,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心理上的挫折和失重。昌耀似乎永遠也學不會審時度勢、順應潮流,他不但強調“詩人不是職業”(《唯誰孤寂》),而且把詩歌看成“殉道者的宗教”(《詩的禮贊》)。從《紫紅色絲絨簾幕背景里的頭像》這樣不無戲謔的詩作中,我們可以察覺到他對當下流行的價值觀的抵觸情緒是十分強烈的。在困頓萎靡的精神環境中,昌耀體會到失去信仰時的麻木、空虛和繼續追尋心中的上帝時的艱難、痛苦。
收稿日期:2015-05-10
作者簡介:陳曙娟(1981-),女,江蘇東臺人,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期刊社編輯,碩士。研究方向:編輯學、中國現當代文學。
在這個物質化的年代,當理想戲劇般演化為虛幻的符號時,昌耀成了一個被理想放逐的人。在他的后期詩歌間或也會有一些平凡的世俗生活的描寫,如“前方灶頭/有我的黃銅茶炊”(《在山谷:鄉途》,“我們的婆母還是要腌制過冬的咸菜。/我們的姑娘還是要燙一個流行的發式。”(《劃呀,劃呀,父親們!》這些平實、古樸、溫暖的詩句,讓人油然而生一種可觸可摸的幸福感,但是這畢竟只是碎片式的閃現。昌耀本質上是一位懷有濃厚理想主義情結的詩人,他認為:“世界需要理想,是以世上終究不絕理想主義者。/我們都是哭泣著追求惟一的完美。“(《一天》)昌耀認為在這個精神產生嚴重危機的時代,身為詩人尤其必須堅持以精神探索為己任,他在《宿命授予詩人荊冠》中宣布:“我理解的詩人是‘修辭以誠’的人,必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執著于人生永恒的問知及道德的完善。”正是出于這樣的理想追求,他在名片坐上角印下了與眾不同的如許頭銜:“詩人。男子漢。平頭百姓。托缽苦行僧。”“人文精神的重建與再造”的信念,在他心中是不容動搖的。他認為“制動的主體能力,取決于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與思維狀態,而主要不在于國家是否有發達經濟”(《讀書,以安身立命》)。
理想是燈,照亮腳下的路,而理想的燈火一旦熄滅,原來代表光明的事物便失去一般意義上的象征意味。昌耀后期的詩中出現了一些冰冷怪異的意象:比如燈,變成了“不幸是蛇吻瑟瑟吐吸的劍”(《恓惶》);比如焰,變成了像“硫磺一樣骯臟的冷焰”(《生命的渴意》);比如炭火,變得“好似玻璃球柱涂著冷漠”(《一天》);等等。下面將重點分析太陽這一典型意象的變異。前期作品(如《陽光:火的顏色:溫暖》《陽光下的路》《日出》《晚會》)中的“陽光”像麥草稈兒一樣清香,像火一樣熱烈,像日子一樣溫暖,在陽光的照耀下,一切都顯得明亮和快樂。每日新升起的太陽代表著人們每日新升起的希望,詩人以太陽來表達對新生事物的贊美和樂觀振奮的生活態度。隨著理想的冷卻,火熱的太陽也冷卻下來。在后期作品(如《哈拉庫圖》《冷太陽》《僧人》)中,冷太陽比比皆是,太陽強烈的冷光卻灼痛了詩人的視覺神經和觸覺神經。理想的退場不但引起了燈、焰、炭火、太陽等意象的變異,而且引起了主體精神的變化。隨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因缺乏陽剛之氣變得暮氣沉沉,昌耀筆下很快出現了衰老這一主題。逆流而行的昌耀面對這個喧鬧的世界所發出來的聲音,只能用“微乎其微”(其實正是衰老主題的體現)四個字來形容。
2 內涵
2.1消極內涵
從消極層面上講,衰老意味著消沉的意志以及邊緣化的生存處境。消沉的意志必然引起行動的怠慢和心理的疲倦,而男子漢的怠倦則讓昌耀感覺自己邊緣模糊與物同化漸入逍遙。當詩人將目光轉向那些退出社會舞臺的老人,他體味到一種無法排遣的哀愁。在《詩章》中,“微雨中一場退休者的門球賽”竟組成了一幅悲秋圖:“旌旗森嚴,場地寂寥,前胸后背紅黃對壘。/帽盔下的老人們手持槌棒排立,目光窎遠。/緘默的嘴角線/悲秋勝于競技。”
庸常的精神狀態引發的,只可能是心靈的烘烤感和蒼涼感,昌耀無法適應灰色平庸的生存方式,體驗到一種缺少激情的勞累。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昌耀作為一位大詩人開始得到人們的認可,鮮花和掌聲紛至沓來,他那“灰色的心態”造就的“灰色人生”(《小滿夜夕》)也未能增添一些鮮亮的顏色。在這似乎已成定局的灰色的人生狀態中寫就的詩歌,當然不可避免地被一種揮之不去的生命失敗意緒所籠罩。衰老一詞集中表達了昌耀后期創作思想中愈加強烈的生命悲劇意識:“那頭戴便帽的一代已去往何處?/感覺眼中升起一種憔悴。/我的便帽也驀然衰老了。”(《頭戴便帽從城市到城市的造訪》)
另外,“衰老”還意味著灰暗的未來。昌耀前期的詩是有關理想的詩,有關未來的詩,而在他的后期詩作中,既看不到理想也看不到未來。“我們”是緩緩失蹤、誰也不必察覺的“老去的青年一代”(《一代》),這已然在詩人心中形成一股抑制不住的悲痛,然而更為可悲的是,“衰老”的現象并不僅僅在這一代人身上發生。“孩子確信自己是他的父親樹上長出的瘤子”(《眩惑》),詩人深感到“偷覷”父親的孩子,生來便遺傳了精神貧血病和軟骨病等人類之宿疾。“衰老”的遺傳基因,使新生的生命潛藏著未老先衰的厄運:“厄運之不可擺脫猶如存在于細胞核染色體的遺傳基因,一個新的生命一旦完成,厄運已潛在其中。”(《與梅卓小姐一同釋讀〈幸運神遠離〉》)即便是“渴慕偉力的男子”也只能“撫劍自慚出生就已白頭”(《露天水果市場》)。“衰老”的灰暗色調意味著理想和希望之燈的熄滅,向未來延伸的路也是灰暗一片,因此詩人說:“承認歷史遠比面對未來輕松。/理解今人遠比追悼古人痛楚。”(《在古原騎車旅行》)2.2積極內涵
“生命是悲壯的,這在于它意識到了那一‘悲’的結局之后,仍然要美麗、強壯地去踐約它天然的權利。當昌耀一直那樣頑強地行走在生命之途,當他在這一長途上驀然意識到他生命的壯年時代即將逝去是,這一剎那的警覺,使他一疊聲地驚悸道:‘秋天呵,秋天呵,秋天呵……’,‘高山冰凌閃爍的射角已透出肅殺之氣,竟又是誰在大荒熹微中嗷聲舒嘯抵牾宿命?’其實這一驚悸的發問,已經由昌耀自己作了回答,他說:‘衰亡的只有物質,欲望之火卻仍自熾烈’。”[2]41歲月悄悄在逐漸老去的人們的額頭爬出一道道或深或淺的痕跡,未嘗不可以理解為歲月對人們的一種饋贈。這種饋贈使“衰老”獲得了一種積極的含義:成熟。
在灰色平庸的現代社會,異化(包括心靈的老化)是一種普遍現象,已走上秋之旅的詩人卻關注著那些焦慮、疲憊卻仍然不屈不撓的生命,欲掙脫異化這條粗壯的鎖鏈。心理的跋涉是一種更為艱辛的跋涉,“衰老”的消極含義表明,昌耀遭遇到了生命中一種更加深刻的磨難。“一種受挫的大生命在承受外力的頓挫之后,以生命激情發出的更強大的反作用力。”[2]40正是在這種“更強大的反作用力”的影響下,“衰老”才得以由消極的一面向積極的一面轉化。
“萬物都在趨向衰老”,但“厭恨老境的詩人”警惕著“倦怠”的侵襲,得以“守住蓬勃英年”(《一天》)。由此,詩人對人生的秋景加以了肯定和贊美:“成熟是生命隆重的秋景”(《罹憂的日子》)。他還疾聲呼吁“快些進入秋天”:“我深知從蘆梗唇間吹奏的嗚咽是古已有之的嗚咽。/因此快些進入秋天吧。那時秋之蘆梗將是成熟的了。”“已經飽受生命之苦樂的蘆梗將無懼霜風/而視死如歸。/只有春天的不幸最可哀矜。/因此快些進入秋天吧,對于一切侵凌秋是解毒劑。”(《踏春去來》)
在昌耀的后期詩歌中,盡管父性神話的光輝已經悄然隱退,但并沒有徹底消失,而是存在于詩人的無限追憶之中,存在于詩人“呼喊著的自己另一半的河流”(《呼喊的河流》)之中。因此,出現了兩種“相互對抗于生命中靈魂的掙扎和撐持”[2]40的力量。詩人以一種與“衰老”的灰暗色調相抗衡的力量,對處于矛盾的糾葛和痛苦的煎熬之中的靈魂進行自我表現拯救。在《熱苞谷》一詩中,詩人寫道:“手持熱苞谷的一對小男孩在街頭追戲。/手持的熱苞谷如同奧林匹亞圣火接力的火炬。/一切在加快成熟。”這意味著,未來的希望之火也重新燃燒起來。
3 結論
衰老主題與昌耀精神歸宿的虛無化不無關聯。昌耀曾經無比堅定地相信,西部那遼闊的荒原就是他的精神歸宿,他說:“確實覺著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多么好,我的大地,我的茅屋,我的爐灶,我的把我鍛煉成人的我的時代、命運……而我的誕生并非偶然。我直覺自身與人類命運之相通。我似乎更實在地理解了人類成為命運主宰的那種渴望。”(《我的誕生并非偶然》)然而社會的急遽分化如一陣氣勢洶洶的龍卷風,將西部荒原上那些以理想為原料所剪裁的豪華裝飾全部席卷而去。即使偶爾還殘存些淘金者的欲望和夢想,但是隨著理想的褪色,荒原逐漸現出荒寒、凌亂的面貌,僅剩下“斷簡殘編之美”:“間或,有喋喋的絮語。/還有冰點之下的招降。/還有稀落的鼓點和喇叭的嗚咽/……一些風俗飄零的碎片,/游離于精神恍惚的狀態。”(《西域:斷簡殘編之美》)把靈魂的居所看得遠比吃飯重要的昌耀,突然間失去了精神家園,其內心那巨大的空寂和沉痛的無所歸依感是可想而知的。人在現代社會庸常生活中的異化,觸發了昌耀對于生命的至深的荒誕感。昌耀受到人是否應該擁有某種信念的懷疑的脅迫,同時對這種脅迫進行著頑強的反抗。詩人最終發現生命個體渺如一粒種子飄飄搖搖,失身于宇宙的浩茫,自己原來只不過是人類發展史中微不足道的過客,而衰老在精神空虛的沖擊中加快了到來的步伐。
[1]羅洛.險拔峻峭·質而無華[C].//董生龍.昌耀:陣痛的靈魂.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2]燎原.昌耀:西部大時空中的史記[C].//董生龍.昌耀:陣痛的靈魂.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周哲良
I207.25
A
1672-2094(2015)04-00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