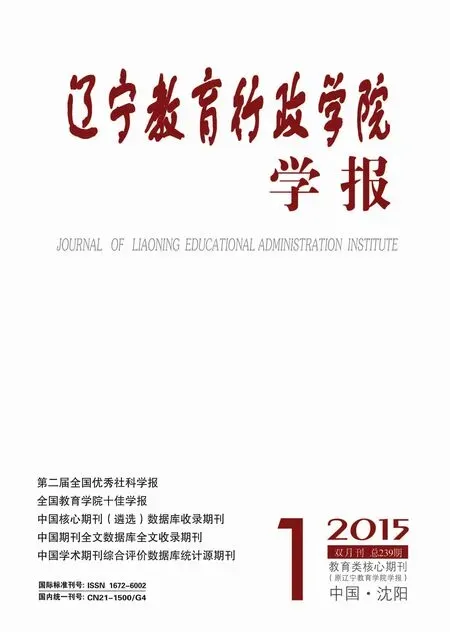巴恩斯通聚焦“聲響”翻譯策略的時代意義研究
姜天翔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巴恩斯通聚焦“聲響”翻譯策略的時代意義研究
姜天翔
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基于詩歌是“詞語打造的機器”這一基本認識,美國譯者托尼·巴恩斯通在其中詩英譯中使用了聚焦“聲響”的翻譯策略,借以在英語語境中再現漢語原詩作為詞語機器的藝術審美功能。此外,聚焦“聲響”的翻譯策略順應了當下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時代需求,與逐步崛起的詩歌“超文本”系統相輔相成。同時,在了解異民族的本質文化內涵以及揭露語言和人的本質方面,聚焦詩歌“聲響”效果的翻譯策略,更能行之有效地規避民族文化偏見,使中國詩歌更好地走向世界。
托尼·巴恩斯通;詞語機器;聲響;超文本;跨文化
一、詞語的機器及其“聲響”效果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曾指出詩歌是“詞語打造的或大或小的機器”。無獨有偶,法國詩人瓦萊里(Paul Valéry)也曾寫道“詩歌實在是一種使用詞語的手段建構詩性意境的機器”。巴恩斯通更是進一步認為,詩歌作為“詞語打造的機器”,必然有其獨特的“功能”來完成某種特定任務,這種“功能”是譯詩需要再現的關鍵所在。在詩歌字面意思的背后,有一種關于如何成就一首詩以及它的各種譯文的靈感,一種轉瞬即逝的智慧。因此相比一首詩說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做了什么。巴恩斯通強調,翻譯之前“必須先找到原詩對你做了什么,以及原詩的機器如何產生其‘功能’,才能在你的新文本再現原詩”。在翻譯中,應該將一首詩歌作為整體來關注其產生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只是拘泥于詩歌的字面意思。根據詩歌的功能不同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才能在譯詩中更好地再現原詩的神韻。
而巴恩斯通自身的翻譯,重點聚焦在原詩的“聲響”(Sound)效果所產生的功能作用。巴恩斯通認為,譯詩“是一臺聲音的機器,意在構建能吟唱出原詩一般美妙音樂的篇章”。在中國詩歌的具體翻譯實踐中,巴恩斯通對詩歌的“聲響”效果極為重視,借此在譯詩中再現源語言中詩歌機器發揮的功能作用。在漢語詩歌中,每個漢字都是表音和表意二者結合的符號,一系列漢字有序組合成的詩歌不僅展現了連亙疊加的“意象”,還構成了一曲綿綿不絕的“聲響”。如何用英語表達中文原詩中“意象”的同時組合出漢語原詩中獨特的“聲響”,是巴恩斯通詩歌譯介中重要的命題。以往中國詩歌的譯者總是捂住耳朵忽略“聲響”效果,卻用電子顯微鏡來觀察詩歌中“意象”上的每一個細節,這種方法帶來的略顯笨拙的譯文在當下已經難以令人滿意。早在80年代翻譯王維的詩歌時,巴恩斯通就提出,譯者的工作過程好比偵探面對一系列謎一般的記錄在案的事件的沉思過程,有時我們會整日整日地在
一首簡單的四行詩上反復琢磨,試圖挖掘出時這首詩中的詞句變得鮮活生動的詩歌機器所發揮的功能作用。而譯介中文詩歌則必須深思熟慮,透過每一個漢字看到漢字背后的“意象”,同時還需要仔細聆聽每一個漢字背后的“聲響”。而譯者的藝術在于呈現詩歌文本在跨越兩種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后展現的可能性,譯者不應該是向讀者獻上一首規整不可改變的詩歌,而應該是向讀者展現一首詩有待挖掘的無限可能。為了在英語譯詩中能聽到中文原詩中的聲音效果,翻譯出源語言中詩歌機器發揮的功能作用,可能需要恪守逐字逐句的精確性,即譯者不得不限制自身的創造力。或者譯者可以干脆激進地背離條條框框的約定直接通往詩歌發源的地方。無論哪種情況,譯者都必須忠實于詩歌能夠滋養激發人類的生命體驗的內在需求。一首詩是一系列“聲響”效果的組合,這些“聲響”的組合同樣是影響讀者的重要因素。如果讀者能夠靜下心來,那么一定能感受到詩歌在我們身上微弱的脈動的聲音。
在唐代詩人王維的《黎拾遺昕裴秀才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的翻譯中,巴恩斯通就貫徹踐行了自己的這一理論。該詩中有一句“促織鳴已急”,字面意思十分簡單,指的是“蟋蟀叫得十分著急”。如果簡單地翻譯為“cricket cry already hurried”,字面意義上沒有任何錯誤,然而詩句讀起來就顯得枯燥乏味,失卻了原詩的藝術審美價值。巴恩斯通不贊同譯者去逐字逐句地意譯,這樣往往會忽略源語言中詩歌機器發揮的功能作用,而應當充分挖掘原詩背后的視覺“意象”、內在蘊涵、文化語境以及整體的詩歌情緒。“促織”在漢語中不僅意義上指代蟋蟀,同時發音上也和蟋蟀的叫聲十分相似,起到擬聲的效果。“促織鳴已急”不僅在概念和“意象”上呈現了蟋蟀急切的鳴叫聲,同時也在“聲響”效果上形成了短促而富有感染力的韻律。在英語中蟋蟀有多種表示方法,例如“cricket”、“grig”和“gryllid”等,而巴恩斯通果斷使用“cricket”來翻譯這句詩。因為“cricket”與“促織”一樣,不僅在概念上指代蟋蟀,同時在詞的發音上有擬聲效果,在英語句子中容易還原漢語原詩中的“聲響”效果。然后配上和“cricket”押韻的“quickens”以及詞組“The urgent whir of”來表示蟋蟀焦急的鳴叫聲,巴恩斯通的譯詩“The urgent whir of crickets quickens”不僅在“意象”上更在“聲響”效果上還原了原詩的神韻,將源語言中詩歌機器發揮的作用在譯文中淋漓盡致地展現,是難得的翻譯佳作。
每一首詩歌都有其獨特的“聲響”效果,在跨語言、跨文化的翻譯中難免有所增損,而聚焦詩歌“聲響”效果的翻譯策略不拘泥于原詩的字面意思,能引導譯者在譯文中更好再現出原詩的神韻。正如巴恩斯通曾坦承的,盡管可以說所有的翻譯都可以說是誤譯,盡管譯者不能用英語真正地百分百地還原中文詩歌,但譯者的責任和樂趣恰恰在于,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拓展了詩歌無限的可能,為英語詩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揭示了一片新的大陸。
二、數字時代下“超文本”系統的需求
巴恩斯通對中國文學的翻譯,強調譯詩本身作為審美實體的自足性,反對為譯詩贅述注釋,而應當由譯詩本身作為一個完整的審美主體去展現原詩中想要表達的神韻。然而,并非所有需要注解的信息,都能完美無瑕地融入到詩歌文本本身中。一時代的中國文學總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不做足夠的注釋會帶來西方讀者閱讀上的困難和文化的隔閡。因此,為了不破壞詩歌本身閱讀的流暢性,并且盡可能地規避在詩歌正文旁添加注釋,同時能夠向西方讀者交代清楚時代背景,巴恩斯通在譯著里加入了盡可能詳細的超文本系統。
法國敘事學家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最先提出“副文本”的概念,他指出“前言(序)、后記(跋)、標題、文獻插圖等一系列中間因素,作為中介者連接起文本和讀者,以展現作品的全貌”。這一概念被廣泛運用在翻譯文學之中,描述副文本因素可以發現不同時代與不同文化中相異的概念或者界定,如翻譯的性質、功能、譯者身份的界定等等,并且有助于讀者了解翻譯文本產生和接受的社會文化語境。在巴恩斯通的譯著中,十分重視“副文本”的使用,序言、索引、傳記等資料詳細完備。甚至在其
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一書中,相關超文本占了整本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而數字化信息時代的當下,巴恩斯通更是在“副文本”的基礎上,利用強大的網絡資源和硬件平臺條件構成一個“超文本”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包括熱奈特所提出的副文本要素選集開頭的序言、時間表、插圖,每篇作品附上的導言、注釋、補充閱讀,整部書后的索引等之外,還有個人網站以及網站上留給讀者的討論區和互動的聯系方式,詩歌改編的音樂、影像等資料。通過互聯網的方式,巴恩斯通提供的遠遠超過了平面文本所能帶給讀者的信息和閱讀體驗,給予了西方讀者更多關于中國文學的引導和解釋,構建出和讀者互動的平臺。
巴恩斯通為其譯詩構建“超文本”系統源于其對文學和科技的關系的敏感性,他尤其注重文學在當前數字時代下的形式特征和變遷。巴恩斯通的博士論文The poetics of the machine age: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sm即從科技角度出發,探討機器時代下的詩學,具體研究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技術化的現代主義問題。此外,巴恩斯通在Technology as Addiction一文中更明顯地表達了科技對文學和詩人的強烈影響。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大大改變了文學創作和傳播的面貌。文中,巴恩斯通援引1996年洛杉磯的一次大范圍停電對整個社會產生的破壞性巨大影響,不禁感慨如今的美國已是怎樣地依賴科技。
巴恩斯通意識到信息技術的進步和互聯網的發展,將促使文學形態的多媒體化。詩歌不再只是簡單的紙質讀物,而將獲得更多機會去發聲。詩歌的數字化將引領人們更多地關注其“聲響”效果。巴恩斯通積極順應這一歷史潮流,主動建立自身詩作的超文本系統。巴恩斯通已經將一組28首商籟體詩變成廣播劇了,其中幾首被Rattle雜志的網站收錄,配上了音樂和音響效果播出。此外,巴恩斯通還積極投身于多媒體項目,除了廣播劇和卡片,巴恩斯通還與藝術家多蘿西·塔內爾合作,把《低俗十四行》改編成連環畫,并與歌手約翰·克林貝爾一起把《戰爭之舌》變成音樂碟,并多次在外校的講座上邀請歌手演唱自己詩歌改編的歌曲。巴恩斯通建立的“超文本”系統是引導讀者閱讀的工具,通過音樂、圖片、影音材料使讀者能更形象深入地了解某一種文學作品背后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使讀者向巴恩斯通心中理想的閱讀效果靠攏。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多媒體化的文本中,詩歌的“聲響”效果愈發成為其重要的美學元素。這樣的詩歌文本將更好地適應當前全球化信息時代需求,而在其跨文化的交流和翻譯中“聲響”效果自然會成為重中之重。
值得一提的是,巴恩斯通之所以重視科技與文學關系,與其被科技“摧毀”而后又被科技“拯救”的親身經歷有密切聯系。科技逐漸使打字機和電腦代替了傳統紙筆的部分功能,增強了書寫效率同時也加大了寫作強度。長時間的打字使巴恩斯通前臂神經受損,逐漸失去使用鍵盤書寫的能力。隨著病情的惡化,巴恩斯通甚至不能用筆書寫。對詩人來說,這是致命的打擊。然而,毀滅了巴恩斯通用手寫作能力的科技,同時又賦予了其用“聲音”寫作的能力。從朋友處獲得了最新的可以用“聲音”寫作的機器,機器可以將巴恩斯通說出的話自動打進電腦形成文字,這使巴恩斯通重獲新生。自然,用嘴代替手來寫作對初嘗試者來說是很別扭的,也是十分疲勞的,因為學會準確發音的技巧和學會準確打字的技巧一樣困難。然而隨著日復一日的練習和“寫作”,巴恩斯通逐漸熟稔而駕輕就熟,能夠自然地用“聲音”寫出幽美的散文和詩句。
巴恩斯通高度重視詩歌中“聲響”效果,這與其自身持續用“聲音”寫作有密切關系。傳統地寫或打字,往往使詩歌沉默化,使詩人和譯者忽略了詩歌的“聲響”效果。而持續用“聲音”寫作的巴恩斯通,則更自然地能夠意識到一首詩的韻律問題和“聲響”效果。巴恩斯通十分青睞十四行詩,個人詩集中多部是十四行詩的合集,還發表了《當代十四行詩宣言》。與自由體詩相比,十四行詩的詩行結構能自動形成模塊化思維,修辭與觀念轉化在結構性的模塊之間發生。巴恩斯通最開始寫的是自由體詩歌,比較怵押韻的問題。隨著對十四行詩特點的認識以及對詩歌形式的偏愛,巴恩斯通開始撰寫
新自由體詩。他倡導“仔細聽句子的節奏,并以形式來創建局部效應。在最近的格律詩里,我將自由體的技巧即興于傳統形式中……白話的聲音,有視野的眼光,意想不到的野生狀態”,來避免自由體詩的音盲、松弛、冗長等問題,同時發揮格律詩和自由體詩各自的長處。此外,巴恩斯通在翻譯時常補充相關邏輯上聯系的字詞,使原詩中離散的意象之間的聯系更為明確,這一習慣與他用“聲音”寫作的機器有關。“聲音”識別機器是根據已有的數據庫和設定好的語法規則來識別新錄入的“聲音”,對離散的、邏輯聯系不強的詞句的識別有很大困難。這難免會使得巴恩斯通傾向于用邏輯聯系更緊密清晰的句子去轉譯,形成巴恩斯通詩作的語義和邏輯比較清晰的特征。
由巴恩斯通自身的例子可見,在當前全球化的數字時代,科技不僅會影響詩歌翻譯和創作的內容,更能在根本上改變詩人的書寫形式,從而影響到詩歌翻譯和創作的側重點和特質。而隨著詩歌的多媒體化以及“超文本”系統成為可能,將促使詩人和譯者更多地聚焦于詩歌的“聲響”效果。而隨著全球化成為勢不可當的趨勢,使用不同語言的民族之間交流溝通的欲望愈發強烈,聚焦“聲響”效果的詩歌翻譯策略,將會很大程度上補充傳統的只是關注詩歌意義內容的翻譯策略的不足,在跨文化的交流上發揮彌足珍貴的作用。
三、聚焦“聲響”的跨文化意義
與追求字面意義準確的科技文獻翻譯不同,文學翻譯在審美上有更高的訴求。隨著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入,拘泥于字面準確性的翻譯法逐漸落伍,越來越多的學者和譯者開始關注譯作本身的審美性。德里達就否認了逐字逐句翻譯的文學意義,提出最準確最好的翻譯“不是只逐字逐句傳達字面意思的翻譯”,而更要關注語言背后的語言鏈。本雅明更指出,“翻譯中個別詞語的‘信’幾乎永遠不能完全再生產原詞的意思。因為這個意思,就其對原文的詩歌意蘊來看,并不局限于所指的意義,而是贏得這樣一種詩歌的意蘊甚至于達到所指的意義受到個別詞語的意指方式制約的程度”。這一追求譯詩審美性和再現原詩神韻的潮流,向譯者訴求一種更能接近語言和藝術本真的翻譯策略。而巴恩斯通在其翻譯實踐中,聚焦詩歌的“聲響”效果,再創造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譯詩,為跨文化的文學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小的借鑒意義。
麥克盧漢的新媒介理論指出“媒介即是信息”,巴恩斯通在此基礎上反思了詩歌文本作為媒介的作用和意義,指出:“一首詩的譯者,在一種語言中消解了意識的機器并在另一種語言中重構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又揭示了關于詩歌機器、意識以及語言本身的東西”。詩歌文本不再是簡單的傳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載體,其形式特征本身即承載了龐大的藝術和文化信息。而文學翻譯本身也擔當了更重大的使命,翻譯成為跳出語言的牢籠思索語言和人的意識本身的途徑。本雅明在《翻譯者的任務》中直言:“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克制想要交流的愿望,克制想要傳達意義的欲望……翻譯者的任務就是要解放他自身語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語言中的純語言,在對作品的再創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語言。”翻譯不是簡單地傳情達意,而是在語言的森林外觀照語言本身,在翻譯和再創造的過程中通過對比走向“真正的語言”的方式。一個人的思維和一個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語言的影響和局限,翻譯在展示語言本質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人的意識和人的本質。“語音”是一種語言最重要的構成因素,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聚焦一種語言的聲音,關注一組詩句的“聲響”效果自然成為最重要的訴求。
值得一提的是,巴恩斯通高度重視詩歌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歷史作用,強調翻譯的功能不止于簡單地再現原詩及其所處的社會語境。巴恩斯通曾翻譯中國當代朦朧詩,借以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80年代特殊的政治與歷史。而同時,美國最高法院正致力于廢除公民權利法案中嫌疑犯的米蘭達權利,將失去對警察暴力行為的約束,極有可能縱容非法搜查、逮捕和審訊的行為。此外,當時美國軍隊正在交戰的格林納達、巴拿馬和伊拉克等地區,也嚴格限制了媒體的獨立介入,并要求媒體妖魔化戰爭對手,以
報道事實為神圣職責的“獨立”媒體就此淪為小部分人群的宣傳工具。巴恩斯通從80年代末中國的動亂中,看到的恰是美國自身類似的黑人歧視法的壓迫,并提出西方讀者不應該以一種沾沾自喜的心態圍觀關于中國審查制度的故事,而應該借此警醒我們自身。巴恩斯通正是希望通過自己的翻譯工作,提供西方讀者一個參照系,由“他者”的鏡像關照自省進步。巴恩斯通愿意相信“世界能夠被詩歌所改變”,詩人和譯者正是這一重任的擔當者。
而在這一歷史使命中,在了解異民族的本質文化內涵以及揭露語言和人的本質方面,聚焦詩歌“聲響”效果更是一種能夠行之有效地規避自身民族文化偏見的翻譯策略。巴恩斯通之前的西方譯者,例如龐德、阿瑟·韋利、王紅公等,總是用英語詩歌中的自由體翻譯中國古典詩歌。這使得中國古典詩歌中特有的韻律在譯文中蕩然無存,閱讀起來就好像美國土生土長的當代詩歌。這種只關注詩歌的內容和意象的翻譯法,不僅會使西方讀者誤解中國詩歌和文化,而且容易使美國人只用自己的眼光打量全世界,滋長美國中心主義的思想。因此,巴恩斯通聚焦漢語詩歌的“聲響”效果,力圖規避自身文化的偏見,在原詩中再現漢語原詩的神韻。可見,巴恩斯通聚焦“聲響”的翻譯策略,不僅能將詩歌機器的獨特“功能”在另一種語言文化中再現,而且是數字時代下詩歌的“超文本”化的內在需求,更是在跨文化的交流以及走向語言和意識的本質時一種有效規避自身民族文化偏見的有效方式,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1]William Carlos Williams,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Volume II 1939-1962, Christopher MacGowan,e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8.
[2]Paul Valéry,The Art of Poetry,Denise Folliot,tr., Jackson Mathews,ed.,Introduction by T.S.Eliot, Vol.7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aul Valéry, Bollingen Series XLV.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3]Barnstone,Tony.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 etry[M].New York:Anchor Books,2005.
[4]Machines Made Out of Words,AWP Magazine& Media/The Writer’s Chronicle,2008 https:// www.awpwriter.org/search?keywords%5B%5D= tony+barnstone
[5]Machines Made Out of Words,AWP Chronicle, 2008.
[6]Barnstone,Tony and Barnstone,Willis.Laughing lost in the mountains:selected poems of Wang Wei[M].Hanover&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1.
[7]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
[8]Genette G.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9]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ume 41,Number 1, January 2000.
[10]“A Manifesto On The Contemporary Sonnet:A Personal Aesthetics”,The Cortland Review, 2006.http://www.cortlandreview.com/features/ 06/december/barnstone_e.html
[11]明迪.訪談:托尼·巴恩斯通[A].http://blog.sina. com.cn/s/blog_6e026c070100pwwp.html.
[12]Jacques Derrida,trans.Lawrence Venuti.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Critical Inquiry, Vol.27,No.2(Winter,2001).
[13]瓦爾特·本雅明,陳永國譯.本雅明文選[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
[14]麥克盧漢,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15]Machines Made Out of Words,AWP Chronicle, 2008.
[16]瓦爾特·本雅明,陳永國譯.本雅明文選[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
[17]Barnstone,Tony.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M].Hanover&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3.
[18]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
(責任編輯:彭 琳)
姜天翔(1989-),男,浙江溫州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現代主義文學研究。
本文系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項目編號12AZD086)階段性成果。
2014-11-12
H1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