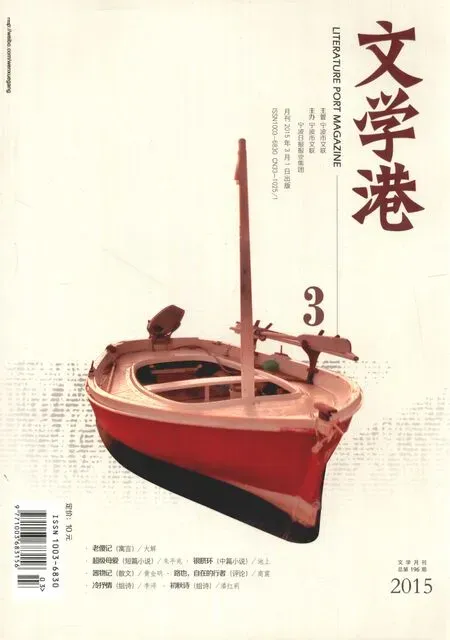師從魯迅的吳耕民
孫群豪
師從魯迅的吳耕民
孫群豪
吳耕民(1896-1991)浙江省慈溪市人。為我國近代園藝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國內外著名的園藝學家、浙江農業大學一級教授、民盟浙江省委顧問。1910年(清宣統二年)陰歷正月,14歲的吳耕民(潤蒼)以優異的成績如愿被紹興府中學堂錄取。紹興府中是浙江省內按照近代教育思想辦學的著名學校之一,其前身是紹郡中西學堂,為徐樹蘭1897年所創。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曾在此任總理,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近代著名革命家徐錫麟曾于1901年在此執教。由于以上原因,當時,紹興府中學堂為紹興各學校之首。
府中校門正對倉橋河岸,門口左右掛有威風凜凜的虎頭牌各一塊,上書“府正堂示:學堂重地,閑人莫入”。虎頭牌上掛著一條黑色的皮鞭,外來者如果沒有經過門衛的同意,私闖校園,就會挨鞭子。府中聘請的教師大多是秀才、舉人之類,還有少數日本留學生。每個學生進校時先得付幾元錢,由校方發給統一的體操服和校服。夏天的校服是蘭竹布或紗布長衫,外罩黑紗馬褂,領子上標有“府中學堂”字樣;冬天的校服是呢馬褂。學生們穿著校服出門上街,人們都會刮目相看,學生們很有些與眾不同的榮耀。
紹興府中的課程設置比較科學,讓學生們頗感興趣,但最讓學生們喜歡的還是上魯迅先生的課。
小潤蒼剛入校時,魯迅先生還沒有來府中任教,到了這年的下半年,即第一學年的第二學期,魯迅先生來了,擔任學監,并教授兩門功課,一門是植物學,另一門是生理衛生。魯迅先生上的植物課生動易懂,各種枯燥的植物知識在他那里都變成了故事般的精彩。由于魯迅先生學過醫,所教授的生理衛生課也十分出彩,學生們非常愿意聽。魯迅的國文功底非常好,他編的講義瑯瑯可誦,他在《越鐸日報》上發表的文章犀利無比,同學們私底下都覺得他非常了得,小潤蒼對此更是無比欽服。對于魯迅先生的課,他百聽不厭,過耳不忘。從這時起,他的心里暗暗地萌生了學農業的愿望。

課外,魯迅先生常帶著學生們遠足或旅行。大家排著隊出發,敲著銅鼓,吹著洋號,先生則走在最前面帶隊。他穿洋服、戴禮帽,裝束別具一格,甚是神氣,同學們著統一校服跟在魯迅先生后面走也覺得很神氣。魯迅先生遠足的時候總是背著一只從日本帶回來的綠色洋鐵小箱子和一把日式的楊桑剪,沿路看到一些感興趣的植物,他就用楊桑剪剪了,放進箱子里。每當別人在討論魯迅先生的洋服和大禮帽的時候,小潤蒼卻盯著那只洋鐵箱子看個不停。不錯,在魯迅先生之前,他們從未見過有人背著這樣的箱子收集植物的,這真是一件太新鮮的事。可能是藥箱吧?因為魯迅先生是學醫的,八成是采了植物做草藥的……小潤蒼一路走,一路想,實在不能明白那玩意兒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索性跑去問魯迅先生,先生很幽默地回答說:“葫蘆里賣藥,小孩子不懂的。告訴你吧,這是采植物標本用的。”小潤蒼方才大悟。
魯迅先生帶學生們出行的次數很多,蘭亭、快閣、宋六陵、柯橋七星巖、禹陵……幾乎跑遍了紹興城四周,蒼潤于是時常能見到那只吸引他的綠色洋鐵標本箱。
在跟著魯迅先生各次出行中,對小潤蒼影響最大的,是到南京參觀“南洋勸業會”。那時的紹興府中雖為紹興學校的翹楚,畢竟因交通不便,無法遠行,所見極少,電燈、電筒、電車、火車、汽車、大輪船、鐵路、公路,甚至連黃包車也未曾見過。一次,同學們聚在一起聊到了一種叫“自來燈”的稀罕物,天黑不用火點就能亮,天亮的時候不用吹就會滅,還不怕風吹雨淋。小潤蒼想來想去,實在想象不出來,覺得這樣的燈肯定與人一樣有知覺,否則怎會天黑能來,天亮能去呢?因為沒有接觸過實物,所以當時老師教物理、化學課講到電的時候,小潤蒼總是聽得莫名其妙。還有一次,老師出了題目——《鐵路國有論》,鐵路這個名倒是聽說過,可鐵路到底是個什么樣的呢?為什么又是什么國有的呢?小蒼潤想來想去,再也無法下筆了。“這路用鐵來造,不僅要花很多錢,而且鐵做的東西冬天太冷,夏天又吸了熱氣會變得很燙,下雨嘛路會打滑,這反倒不如紹興的石板路好呢……”他的思維進入了死胡同,苦苦思索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最后仍然交了白卷。小潤蒼如此,同學們也是如此,憑空胡思亂想,理論脫離實際,即使有了一些基礎知識,畢竟對先進的、現代的東西想不出一個所以然,更談不上融會貫通了。
魯迅先生早就注意到這個情況,“南洋勸業會”在南京舉辦,豈不是一個大好機會?如果能將秋季的學生遠足改為參觀“南洋勸業會”,學生們的眼界必定會開闊,實際知識必定會增長,對于學生的學業進步益處多多。“百聞不如一見”,魯迅先生始終認為懂科學必須接觸實際,非但物理、化學課如此,國文、歷史、地理、圖畫等也須出去看看,接觸實際,才能加深領悟。魯迅先生主意已定,便主動向校方提出這一方案。
校方果然同意了。
“南洋勸業會”是當時國內有識之士倡辦的。清末,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侵略日益加劇,市場上洋貨充斥,價格低廉,我國民間手工業幾乎瀕臨破產,加劇了民生凋敝。國內諸多有識之士認為,縱觀世界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和中國國情,非發展實業不能救亡。于是他們在南京創辦了“南洋勸業會”,借以鼓勵當時的海外僑胞和國內資本家興辦工廠,發展實業。因為當時南洋各地的僑胞很多,有充足的資金和技術來辦工廠,所以將這個博覽會命名為“南洋勸業會”,以吸引各國華僑到國內投資辦廠,興辦實業。
“南洋勸業會”設立了面積很大的展館,并按各省劃分,陳列各地特產,同時也展示諸多進口物品,種類繁多,品種齊全,算得上是一次真正的博覽會。比如在“浙江館”,陳列有傳統絲織品、黃酒、雨傘、紙扇、竹制品等;如“湖北館”,除了湖北土產外,還有“黃岡竹樓”,把地域文化都展示了出來;如“江西館”,集中了大量古色古香、精美華麗的瓷器;又如“廣東館”,除展出當地特色產品之外,還有意識地展出了來自外國的產品。有一張進口的玻璃桌子,小潤蒼和同學們看了都愛不忍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還要用臉貼在桌面上……一切美不勝收,一切讓人震撼,這群孩子猶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東瞧西看,流連忘返,樂此不疲。
除了參觀展覽,小潤蒼和同學們還迷上了夜游,因為在夜間,展館附近燈火齊明,會場正門口彩牌樓的電燈尤其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南洋勸業會”這五個大字竟用電燈排成了一米見方的燈飾,讓這些用慣了油燈的孩子們看了,真是如入夢境:啊,這世界上竟有如此輝煌耀眼的大字!在這里,等到孩子們親眼看過了電燈的開關及裝置,過去對電燈自來自滅的誤解才徹底解除了。
南京之行雖然只有一個星期,但小潤蒼和同學們參觀了展覽,坐了火車、輪船,看到了電燈,增加了不少知識,開闊了眼界,也拓展了思維。對于南京此行,吳耕民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由衷地說:“那次參觀遠至南京,我正如一只井底之蛙,忽然一跳出井,自紹而杭而嘉興,再自嘉興到蘇州,乘車直達南京,都是異鄉異地,未曾到過之處……尤以勸業會集各地和海外物產精華于一地,供我們參觀學習,眼界大開,思想豁然開朗……”他還回憶起此行中的一個細節,并為之沉入思考。他們在火車上看見幾個外國人用刀剖瓜,竟連手都割破了,弄得鮮血直流。他據此“覺得洋人殺雞用牛刀,愚笨之處亦甚多,中國人的智慧何嘗劣于洋人,或反有過之無不及。這點對我自卑感的消除,是大有幫助的”。
童年遇名師,循循得善誘;幼苗獲雨露,茁壯成大材。85歲時,當吳耕民教授回憶起魯迅先生時,他深情地說:“我和先生相處雖短,但惠及一生。追本溯源,之所以選擇農業園藝,是因為先生教授我博物時,讓我十分吸引,使我對生物發生了濃厚興趣,之后又覺得先生以教學為業,誨人不倦,樂在其中,所以我自25歲迄今終身從事教學。甚至,我能延壽至今,身體尚健,亦與先生在生理課教學時,教我們細嚼慢咽,勿貪食,勿吸煙喝酒,勿賭博熬夜,并要我們多做運動有關。因先生學過醫,我對其諄諄教誨,深信不疑,故終身奉行,得益匪淺。”事實上,吳耕民教授一生為學嚴謹,注重實踐,也與求學時深得魯迅先生的言傳身教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