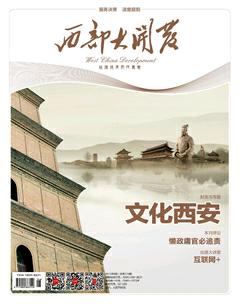轉換增長動力之鑰
——訪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教授
轉換增長動力之鑰
——訪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教授
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未來趨勢及政策選擇,近日我們采訪了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教授。劉偉教授認為,當前要著力推動三項工作:一是下決心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因素;二是加強對消費品供給質量的管理;三是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中國經濟增速尚未探底
西部大開發:回顧上半年,展望下半年,有觀點認為2015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你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你認為,經濟增速探底了嗎?
劉偉:從目前的經濟態勢來看,我個人并不認為2015年是最困難的一年。從橫向上看,中國與全球經濟和新興經濟體相比,7%的增速并不低;從縱向上來說,它也是一個平均速度。我們中長期經濟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GDP總量翻一番,剩下這6年(包含2015年),每年的增長目標平均達到6.73%就可以實現。由此看來,目前的經濟增速還是一個平均速度,談不上探底。
2015年,中國經濟從結構上還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產業結構升級。制造業的升級改造雖然有很大阻力,特別是受困于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的薄弱,但是這方面還是有很大變化。其次,三大產業的結構還是良好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13年開始,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了;從2014年第三次普查數據來看,修正數據之后,這個比例提高了。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的比重占GDP46%多,第三次普查以后的數據顯示是48.2%。三大產業的結構改善為國民經濟帶來很大變化,這主要是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變化,特別是制造業內部去劣質產能取得進展。第三,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有所改善。居民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使得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所提高,去年超過51%,與前些年相比還是在朝著良性方向變化。最后,國際收支結構已經出現再平衡跡象,雖然還是順差,但是順差擴張趨勢得到了遏制。
這一系列變化說明,經過前一個時期,特別是化解經濟危機以后的調整、消化,2015年中國經濟還是在朝著良好結構方向變化。所以,無論是從總量還是從結構演變來看,我并不認為2015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增長動力急需轉換
西部大開發:如今經常聽到這樣的抱怨:政府不作為、經濟疲軟、企業動力不足,等等。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因素或增長動力該如何轉換?
劉偉:實際上,經濟增長的支撐因素首先是需求。大家經常討論的所謂三架馬車中,現在增長的支撐因素發生了一些變化,需要增長動力有所轉換。
第一,投資方面,過去是雙輪驅動,分別是企業和政府。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現在的主要問題還是企業動力不足,受制于制度和技術因素。技術因素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創新一旦有問題,產業結構升級就有問題了。所以,在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再開展大規模的投資,不是很現實。國有大企業投資需求的轉換或者增長,取決于創新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的空間大小。這個空間現在雖然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的速度有點慢,不盡如人意。
企業創新,一是技術創新,二是制度創新,這個動力轉換是非常重要的。盡管民營企業有投資沖動,但銀行等金融機構不信任它們。這種不信任有多種原因,既有民營經濟自身的原因,比如資產質量、管理體制、風險監控、信息不對稱等;也有制度歧視,比如國有銀行構成的金融市場體系對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是有制度障礙的。所以,民營企業的投資沖動,不管是有效的投資還是無效的、盲目的投資,都很難轉成現實的投資需求。這恐怕需要進一步的制度改革和創新,包括市場化特別是要素市場的創新。
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按照五大標準排序,最糟糕或者最滯后的是金融參數的合理性,包括利率、匯率等。金融參數的合理性得不到制度保障,有所扭曲,導致金融市場化中最重要的貨幣資本方面存在問題。因此,要加大這方面的改革,為社會資本投融資提供真正公平有效的市場保障,以活躍民間資本投資。
就影響投資的政府因素而言,現在,地方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發生了變化。過去考核的是地方GDP,現在考核指標有所變化,導致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也發生變化,投資熱有一定程度的降溫。
另外,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約束機制也有變化。比如,中央對地方的債務管理,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擔保等在制度上都有一系列新安排。這樣就使得地方政府本身的債務約束力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投資的沖動。地方政府的行為發生變化,使得投資需求進一步減弱。

工人在北汽集團華北(黃驊)汽車產業基地生產線上工作(3月19日攝)。
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資,特別是財政投資,力度還是很大的。從2010年10月擇機退出之后有所減緩,但是從2012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央投資的刺激力度逐漸提高。今年財政赤字預算是1600多億,占GDP的比重是2.3%,相較去年有所提高。去年政府的財政投資,各級累計大概結余1萬多億。所以,關鍵在于使財政投資的刺激計劃充分實現。就中央政府的投資行為而言,不是簡單地加大所謂財政政策的力度,而是要提高財政政策的效率。
第二,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一大動力就是消費需求。總的來說,消費需求總量還是呈現比較穩定的正增長,因此消費的基本規模是有保障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微觀、宏觀,供給、產品消費的質量、標準等,都有所改變。相信以中國的人口基數,消費增長是一個穩健的因素,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穩定支撐力。
第三,中國進入所謂的新階段之后,進出口對增長的影響恐怕會有一段時間穩定在負作用或者零貢獻水平上。國際經濟復蘇對中國的影響很不確定,因此短期內出口變化不會很大。這幾年實際上就是零或負效應,扭轉這種情況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總體趨勢或低開高走
西部大開發:國家信息中心預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有望止跌企穩,三季度回升向好,如果政策跟進,四季度能夠保持回升平穩向好。你認為呢?
劉偉:我基本同意這個預測,總體趨勢上,可能低開高走。一季度經濟增長7%,投資和消費需求下行態勢比較明顯,但是基本還是在預料中;關鍵是,第一季度在一年四季中占比相對低一點,所以,可以有上述全年向好的判斷。至于季度走勢如何分布,可以再觀察。
目前出現的一些通縮現象,實際上由兩種因素導致,即良性因素和惡性因素,對此要區別采取對策,不宜簡單盲目對待。惡性因素表現在,其導致經濟增速放慢,同時伴隨著就業機會減少;良性因素表現在,供給方面出現有益變化,比如國民經濟生產總成本下降等。
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合理的經濟增長目標要考慮實際需要和可能。需要就是底線,考慮的因素很多,但實際上比較重要的是就業率。今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大概在4.5%以內,要實現這個目標,經濟增長大概要達到6.5%,這就是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可能條件有很多,很重要的約束條件就是承受通貨膨脹的能力。整個社會對通貨膨脹的承受力今年是3%,上下波動也就是在2.5%-3.5%之間。如果把3.5%作為今年通貨膨脹的控制上限,按照目前的經濟條件和結構狀況,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需要達到8%。所以,從所謂的需要和可能來確定經濟增長率的上限和下限,那就是在6.5%-8%之間了。
《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到經濟增長目標時,除了考慮需要和可能,還要考慮和中長期的經濟增長目標相銜接,實現2020年翻一番的增長目標。10年翻一番要求的平均速度是7.16%,過去這4年都高于7.2%,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是7.7%,2014年是7.4%。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經濟增長7%,通脹率3%,城鎮登記失業率4.5%,在預期增長翻番目標時間表不變的情況下,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立即實施三大舉措
西部大開發:針對上半年經濟形勢,你認為當前和今后應采取哪些宏觀調控政策?是否需要繼續微刺激政策?
劉偉:在現有基礎上實施刺激政策,很有必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下定決心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宏觀方面,保證居民收入增速和GDP增速至少要持平。如果居民收入增速長期落后于經濟發展速度,就會使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這恐怕需要一個制度保障,穩定老百姓對未來的預期,包括社會保障制度、離退休制度、醫療衛生制度等,這些都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儲蓄動機,可以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
二是加強對消費品供給質量的管理。現在居民之所以不敢消費,主要是供給不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雖然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終究還是一個總體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家,現在還沒有到供給創造需求的年代。很多產品質量不行,比如不安全、不夠標準,人們不放心,再加上成本高、價格貴,可謂價高質次,難以鼓勵和引導老百姓擴大消費。因此,現階段刺激消費,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應該是改善供給。
三是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這些年還是比較大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3年至2012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分別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收入差距較大帶來的問題就是整個社會消費傾向下降。
中國還可以考慮采取一些特別措施,特別是放松人口控制。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比如雙獨子女放開二胎,但因為成本比較高,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2014年二胎放松,原預期大概能新增嬰兒200多萬,但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這一目標,當年也就增加了100多萬。現在需要徹底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估算,假如中國新增人口能達到四五百萬,大概一年增加1萬多億GDP,意味著將拉動經濟增長1到2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