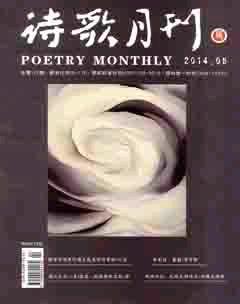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隱喻和宿命

在地球業(yè)已成為一個(gè)村莊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來談詩歌寫作的“地方性”,似乎有些不合時(shí)宜。當(dāng)然,我并非不承認(rèn)詩歌的“地方性”特征,而是說在我們擁有幾乎相近的文化、時(shí)代和閱讀背景的前提下,“地方性”可能會(huì)自然地呈現(xiàn)在各自的詩歌里——如同我們各自不同的表情。
我出生在淮河平原深處,記得我家門口就是一條很寬的河,因?yàn)楹苄【兔刻鞄湍赣H燒飯,夏天就在燒完飯后跳入河水里去游泳,積累下來就生出了麻煩:高燒不退且渾身疼痛,送到鎮(zhèn)上醫(yī)院里住了一個(gè)多月,其中半個(gè)月處于昏迷狀態(tài);后來總算撿了半條命,但風(fēng)濕痛從此像夢(mèng)魘一樣纏上了我,讓我經(jīng)常夢(mèng)到自己不同方式的死亡。我不是宗教信仰者,死亡對(duì)我來說不是天堂,而是活生生的夢(mèng)魘。每次我從夢(mèng)中逃出來,都會(huì)汗水淋漓,半夜睡不著。20歲以前我認(rèn)定自己活不過30歲,非常恐懼。直到今天,“疼”、“痛”和各種各樣的“死亡”場(chǎng)景和記憶仍時(shí)時(shí)刻刻纏著我,它讓我更珍惜人間的小歡樂和小溫暖,每天以笑容示人,而把孤獨(dú)感和宿命的悲傷留給自己,如我在一首詩中所寫:“更多的時(shí)候,我的歡樂大不過一粒米/我就想辦法把它爆成米花,蘸上甜,制成毒藥/送給有緣人,擊鼓相傳。如果這樣的想象失于天真/我就把它寫成詩篇,對(duì)著天空和田野朗誦/這時(shí)候,我的心情蘊(yùn)含著千萬種心情/它是無法比喻和形容的,也是無法描述的,只供奉于/我遼闊而不安的內(nèi)心——”是的,作為中國(guó)詩歌曾經(jīng)的精神家園,作為漢民族文化精神和宗教的鄉(xiāng)村,從長(zhǎng)城內(nèi)外到大江南北,已經(jīng)被被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的狂飆突進(jìn)打得支離破碎,幾千年延續(xù)下來的秩序、倫理和完整性被破壞殆盡,它的不斷消失和死亡,快要把我的詩歌逼到了無處扎根的地步,所以之于我,詩歌寫作的“地方性”除了那片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還有就是這個(gè)無形的疾病了。再進(jìn)一步說,每一個(gè)寫作者的“地方性”其實(shí)就是它的童年和身體本身,它們共同構(gòu)成了寫作者有限的“個(gè)人地域”,我自信。我對(duì)它們持之以恒的書寫,已經(jīng)把我和其他優(yōu)秀的寫作者們區(qū)分開來。
14年前,我從淮河平原來到了北京,攜家在這個(gè)叫通州的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住下來。但我的父母如今還留在老家那個(gè)村子里種田謀生。這真是一個(gè)絕妙隱喻,是一種宿命。我在詩里這樣寫道:“若干年后把住所安置城市的邊緣,說明我心向原野/卻又被名利的藩籬羈絆/你懷疑我虛偽吧,但請(qǐng)不要懷疑我來自那里/最終還將被它一點(diǎn)點(diǎn)收回。”它說明我是清醒的,矛盾的,糾結(jié)的。我是淮河平原的鄉(xiāng)村叛徒,我是首都北京的城市貳臣。我的存在就是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存在,我的無形的尾巴一直藏在衣服里。在現(xiàn)實(shí)里和精神里,我在兩地之間“散步、游走、漫步、奔波”,我是眾生的一個(gè),同時(shí)也非他們中的任何一個(gè),我通過這樣的旁觀和介入,試圖窺破和理解事物和人的精神世界。但即便不寫作,我可能也會(huì)這么做。每一個(gè)人都有窺破他者的欲望。“他者”即世界,詩人就是世界的偷窺者。在我持續(xù)的詩歌寫作里,“父親”一直占據(jù)了非常核心的位置。我在村子里出生并長(zhǎng)到13歲,然后去異地求學(xué)、工作,然后越走越遠(yuǎn)。生產(chǎn)隊(duì)時(shí)代的勞動(dòng)強(qiáng)度其實(shí)并不高,但對(duì)血統(tǒng)的歧視無處不在。我的母親出身三代農(nóng)民,嫁給我父親這個(gè)富裕中農(nóng)的兒子后,受到了不可忍受的人格侮辱,這讓她非常委屈(我倔強(qiáng)的大伯母干脆直接選擇了家門前的老桑樹,用繩子了結(jié)了生命)。我的母親沒有走極端,但性格漸漸變得非常暴戾,尤其對(duì)我這樣野小子,幾乎動(dòng)輒以掌相加,再施以饑餓懲罰。以至于我對(duì)童年最刻骨的記憶就是饑餓和胖揍。在詩《親人們》這樣寫:“四十年前,我還沒有出生,只把母親當(dāng)親人/三十年前,我九歲,把所有的飯當(dāng)親人/二十年前,我十九歲,只把青春當(dāng)親人/十年前,我的父母,妻子,兒子和女兒,是我的親人/踩著四十歲的門檻,所有的敵人和親人,你們都是我的親人/當(dāng)我八十歲,睡在墳?zāi)估?所有的人都視我為親人,但你們已經(jīng)找不見我——//……這一撮新土,這大地最潮濕的部分——”可以這么說,母愛的吝嗇讓我過早體驗(yàn)了人生的孤獨(dú),并反過來造成了我對(duì)母愛的熟視無睹。我生活中的父親是中國(guó)農(nóng)民的典型,他性格隱忍、寬仁、與世無爭(zhēng),向親人和身邊的相鄰釋放著綿綿無盡的愛。“父親”在我的詩歌里其實(shí)早已經(jīng)“溢出”了“個(gè)人”和“血緣”的范疇,從而具有了象征性和寓言性——每個(gè)人遲早都會(huì)回到屋檐下,成為眾多“父親“中的一個(gè)——這就是宿命,它不可逆轉(zhuǎn)。
在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活過14年,我不斷回望記憶里的平原,為它痛心疾首。返身到眼前,我更多關(guān)注和書寫的是那些和我一樣把各自村莊背在背上、在這里那里掙命奔波的人的命運(yùn)。他們每個(gè)人都是一座村莊,都是我詩歌寫作有限而廣大的“地方性”;而童年記憶。憶、身體記憶和“父親”之愛,則是其立足之根本。至于這座生活了14年的地方,“迄今為止,我鄙視這個(gè)城市的/每一片紅磚綠瓦(《問自己》)。
2013-06-23
谷禾詩選
小事件
說到車禍,忍不住心慌起來
早晨經(jīng)過東關(guān)路幾,望見一輛福田皮卡
橫栽在馬路中央,車頭已經(jīng)扭成麻花兒
貨廂里的舊家具散落一地
肇事者和遇難者都已經(jīng)不見蹤影,
這讓留下的大片血跡分外刺眼,也有了更豐富的
想象空間,警察放置了繞行標(biāo)志,
乘客們議論紛紛,有人還把腦袋伸出窗外。
……也是在這個(gè)地方,
大約三個(gè)月前,搞裝修的雷于挺也不幸喪命
我曾請(qǐng)他吃過一次飯,聽他如數(shù)家珍
講述著業(yè)主驗(yàn)工的細(xì)節(jié),他狠抽了口紙煙
突然說他愛上了一個(gè)女孩,“她下月才滿十八歲,
但認(rèn)識(shí)三天就被我搞掉了。”他得意地
笑了,卻馬上又嚴(yán)肅起來,“我要和她白頭偕老?”
他用力揮著拳頭。但三天后,
他獨(dú)自進(jìn)了火葬場(chǎng)燒紅的爐膛。消息傳來,
我去東關(guān)路口站了很久,但終于沒有
碰見他愛上的那個(gè)女孩。
這么多年,我已經(jīng)領(lǐng)教了生命的脆弱
越來越多的死,讓我快麻木了
甚至父親說把我抱大的三爺爺死了.
我也只淡淡地應(yīng)了一句“噢”,就掛了電話
下午帶女兒去看牙醫(yī),順著她手指的方向
突然看見一個(gè)失去雙腿的男孩在借用兩只滑板前行
他的整個(gè)身體都趴在滑板上,兩只灰黑的手
奮力向后,像一條魚在人縫里鉆游。
女兒?jiǎn)枺八麨槭裁床蛔聛砥蛴懩兀俊?/p>
我沒有同答她一一我又一次目睹了死,
形形色色的死,其實(shí)和活著沒任何關(guān)系
譬如人的死,樹的死,田野的死,河流的死
天空的死,愛情的死,性的死。
一個(gè)國(guó)家和民族的死
總有一天,我也會(huì)靜悄悄死去,并且不能選擇其一
西海子公園
它是唯一的,夏天我曾去過,
穿過曲里捌彎的兩條街,在通州劇場(chǎng)后邊,
水面寬闊,渾濁,游艇犁開波浪,獨(dú)不見蓮葉田田。
喝茶的,下棋的,唱戲的,人聲鼎沸,
芭蕉扇揮來舞去,占滿了廊亭,
城市和它游動(dòng)的汽車環(huán)繞著它,暑假或周末
薄暮時(shí)分,這里是孩子的天堂
他們把球踢向空中,自己變成星星,散落進(jìn)樹林,草
叢
直到夜深了,斜月一遍遍催促
但現(xiàn)在是深冬,它的荒涼幾乎等同于歲月,落葉
化成泥土,水而結(jié)了厚冰,
用力踩卜去,卻沒有斷折的聲音傳來,
鑿開冰層,也不見魚兒吐出水泡,
噴水池裸出底部的沙礫,四個(gè)石獅子表情木然
海子角的土山比草叢還矮,從拱橋上,
能望見柵欄外的滿城燈火,但今晚的月光下,
只剩下了我。夏天你和我一起來這里,
但現(xiàn)在,我們天各一方,
公園外匆匆的行人,沒有誰停下來,
給我一杯安慰,或者,陪我坐一會(huì)兒
現(xiàn)在啊,好像有雪落下來了,并且漸漸
彌漫了我的視線,我凍紅的臉
它紛紛揚(yáng)揚(yáng),落在
西海子的冰面上,落在所有的街道、屋頂,
北運(yùn)河兩岸的堤坡,落在向東兩公里外的荊棘叢中
當(dāng)我睡熟,它繼續(xù)輕柔地,
輕柔地,落在所有牛者和死者身上一一
一個(gè)熟睡的老人
一個(gè)熟睡的老人
就像一座空蕩的房子,因?yàn)槟昃檬蓿?/p>
它的內(nèi)部
黑暗,肅穆,荒涼,蛛網(wǎng)密布
如果一陣風(fēng)吹過,
逝去的母親,和母親的母親們回來,和他合而為一
它會(huì)變得
自然,親切,帶著桃樹的端莊和垂柳的慈祥
噢一一,一個(gè)熟睡的老人和空蕩的房子
接著,河流與村莊誕生了
田野,羊群和炊煙,
女人抱著孩子,沿月光走來一一
我想,這不是幻象
從一個(gè)熟睡的老人開始,當(dāng)他和一座空蕩的房子結(jié)合
我被允許經(jīng)常同到屋檐下,成為
眾多父親中的一個(gè)
親人們
四十年前,我還沒有出生,只把母親當(dāng)親人
三十年前,我九歲,把所有的飯當(dāng)親人
二十年前,我十九歲,只把青春當(dāng)親人
十年前,我的父母,妻子,兒子和女兒,是我的親人
踩著四十歲的門檻,所有的敵人和親人,你們都是我
的親人
當(dāng)我八十歲,睡在墳?zāi)估?/p>
所有的人都視我為親人,但你們已經(jīng)找不見我一一
……這一撮新土,這大地最潮濕的部分一一
落院
“從八十歲向一歲活,每個(gè)人都是
如來……”我父親絮絮地念叨,日頭轉(zhuǎn)過
門框,他脖子以下的枯皮和青筋都沒入了
屋檐垂落的陰影。
母親在當(dāng)院里捶棉花,木棒落下
躥起的塵埃在陽光中亂撞。“嘭一一嘭……”
哦,此刻落院的是一對(duì)老人的晚年,激情
恍若隔世,而咳喘的
足音不斷從暗夜涌來,粘稠的云塊
磨損著母親的乳房,也磨損著父親的陰莖
五十年的風(fēng)雨越來越蒼茫、邈遠(yuǎn)……
我從夢(mèng)中驚醒,但接下來會(huì)看見什么
一張隨手翻出的舊照片,
我和妻子之間竟隔著另一個(gè)人
他悄無聲息地死去了,
留下的空曠多年后卻顯影出來
我曾經(jīng)夢(mèng)游穿過田野、村落和許多城鎮(zhèn)
最后又落院回來一一身體里裝載著
我父親和母親的晚境,
還有我半生的風(fēng)濕病,我兒子的旱冰鞋
劃過水泥路面時(shí)打著旋兒的尖叫
原野記
把原野當(dāng)成生命的溫柔地帶,我去它
卻愈加緲遠(yuǎn)。當(dāng)原野上消失了
蓬勃的野草、雜樹、荊棘,而只剩下莊稼
溝坎墳畔的花兒在風(fēng)中加速凋零,請(qǐng)?jiān)试S我
獨(dú)自游過田埂時(shí),心中升起
露水大的傷悲。離開村莊3公里
我一步一回的淚光深處
只捉到了電線上的雀點(diǎn),以及枝頭的半片殘葉
腳下這青綠的麥苗,頭頂著霜露
卻并不見老,偶爾有野兔順著壟溝狂奔去遠(yuǎn)
似乎它要在驚悚中亡命一生
壕溝里流水不復(fù),哪里還有水草魚蝦的蹤跡
藍(lán)天白云凝滯頭頂,壕溝對(duì)岸
高速公路直穿過圍起來的開發(fā)區(qū),不用脫去鞋襪
我也能向著燈紅酒綠飛去。仿佛
原野已不復(fù)為原野,我心已成
齏粉。想起童年時(shí)我也曾在原野上迷路
從連片的馬齒莧、抓地草間摘下一朵牽牛花放在耳邊
隱隱就傳來了暴雨般的蟲鳴,抬起臉來
看見星辰分外密集而明亮,足以照耀古今
讓人平靜地睡去,不再想醒來
不再側(cè)耳搜尋親人的喚歸
若干年后把住所安置城市的邊緣,說明我心向原野
卻又被名利的藩籬羈絆
你懷疑我虛偽吧,但請(qǐng)不要懷疑我來自那里
最終還將被它一點(diǎn)點(diǎn)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