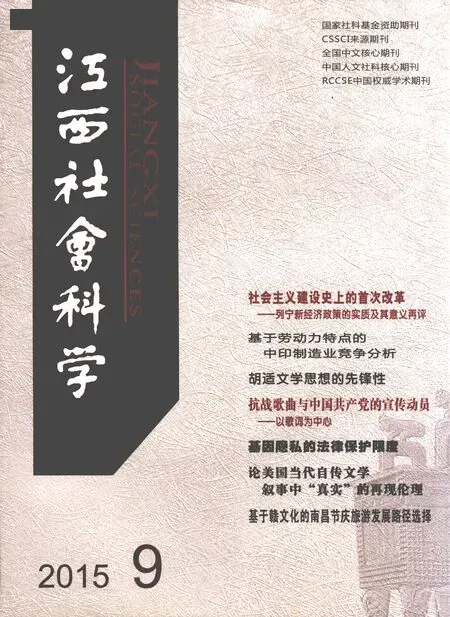以家庭自治為中心的老年人照顧法律研究
■李 欣
以家庭自治為中心的老年人照顧法律研究
■李 欣
孝的傳統、“反哺式”代際互助關系的生命力及對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評價都表明了以家庭自治為中心構建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的必要性。關系契約的特殊性要求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應以“契約”為基礎,尊重制度本身的家庭屬性,以家庭自治為中心,重視家庭成員的充分參與;應當構建分享型老年人人身照顧模式,明確家庭成員的告知義務,根據親緣關系選擇法定老年人人身照顧人,加強家庭成員的照顧監督職責。
家庭自治;老年人照顧;養老保障;家庭法
李 欣,山東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后,安徽工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院副教授。(山東濟南 250100)
人口老齡化尤其是高齡化加劇的背景下,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成為我國轉型期的重要議題。將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從成年人監護體系中獨立出來構建單獨的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已成為學者共識。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屬于養老保障法律體系,但又同傳統的物質與精神贍養法律制度相區別,它更側重于通過實體與程序的規定,保障老年照顧人“替代決定”作出的合理性。區分老年人需求,尊重老年人自主決定權成為老年人照顧法律體系構建的重難點。在尊重老年人“自主決定權”的基礎上,以家庭自治為中心構建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是應然之選。
一、家庭養老照顧的優勢
在社會治理模式中,考慮“平等和自由的彈性安置空間”,合理分配及保護老年人的權利與自由,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在這樣的要求下,提高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和生命質量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指標。總的來看,家庭養老照顧的優勢有以下三點。
第一,孝的傳統和家庭養老的不可替代性。以孝文化為傳統的養老方式,兩千多年來一直由家庭單位直接承擔,這早已根深蒂固于國人的思維中。在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度加深的中國社會,在“社會養老”局限于經濟發展程度的當下,“家庭養老”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人口老齡化和家庭小型化的趨勢導致家庭養老內容分離,形式多元化。學界一直在呼喚家庭養老的社會化,“其實,無論是共居式‘家庭養老’,分居式‘家庭養老’,抑或‘家庭養老’社會化,養老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個人和家庭,即便是‘家庭養老’的社會化情形,表面看來養老職能已經從家庭轉向社會,而這種職能的轉移實際上是以家庭購買養老資源,社會逐步承擔起養老職能的方式實現的,歸根結底仍屬‘家庭養老’”。[1](P76)
無論是從“未富先老”的基本國情來看,還是從老年人同家庭密切的親緣關系看,將養老完全托付給社會都是不可行和不現實的。家庭養老保障是以家庭為主體,根據家庭對老年人的贍養、照顧等功能,為老年人提供身心等全方位保障。社會養老保障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根據法律規定,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對暫時或永久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給予的物質幫助。社會養老保障 “避免社會老年成員因年老勞動能力或失去工作機會導致收入中斷、減少或喪失而影響基本生活”[2](P171)。老年人照顧制度以家庭養老保障為基礎,以社會養老保障為補充。在老年人照顧制度中,家庭和親屬群體是照顧制度的中堅力量,他們在被照顧人因年老、精神衰弱等情況下需要幫助時,自愿或強制性對他們提供人身照顧和財產保障,他們所提供的保障屬于家庭的養老保障功能,并可以稱之為替代性社會保障功能。
第二,“反哺式”代際互助關系的生命力。家庭照顧模式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富生命力和最具有優越性的養老方式。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高度贊譽三代同堂是經歷了千年之久的中國歷史所證明的能維持老年人生命價值的制度。傳統的家庭養老關系是非常親密的代際互助關系,上一代完成對下一代的撫養與教育,等下一代長大成人,再對上一代進行反哺照料。家庭養老是“反饋式”養老,是維系代際之間“哺育”與“反育”的供養關系,促進家庭成員間的和睦融洽,從而直接促進著社會的穩定和諧。大量的個案研究與社會調查表明,老年人在家庭中權威的減弱似乎并未導致中國現代家庭養老方式的重大變化,父母和子女仍然保持著頻繁的交互關系。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表面上這種代際互助關系逐步減弱,且主要反映在城市‘四二一’家庭中”[3](P27),年輕夫妻要在事業、子女、老人間尋求平衡,對于老人的照料難免有所疏忽。調查顯示社會養老方式不能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真正的親情慰藉,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被迫實現社會化也并不能替代家庭成員的照顧監護功能。以家庭自治為中心構建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考慮到家庭成員天然的血緣關系,家庭成員能帶給老年人更多的親切感和歸屬感,家庭成員同老年被照顧人相濡以沫的親密關系也有利于他們揣測與執行老年人的真實意愿,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家庭養老的形式多元化及家庭養老的社會化趨勢并不能弱化家庭的日常照料功能,家庭對成員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使得家庭成員在滿足養老需求的情感上及權益保障上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第三,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評價顯示家庭養老質量更高。敬老院、老年公寓、幸福院等不同方式的養老機構越來越多。不同養老模式下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考量顯示:生活在聯合家庭和直系型家庭中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狀況好于生活在核心家庭及獨身生活的老年人。學者通過對家庭養老、機構養老的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調研數據和不同家庭結構的老年人生命質量自評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家庭養老老年人的生命質量總評分均值70.65,機構養老老年人的生命質量總評分均值59.35,家庭養老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各領域的評分均值比養老機構中的老人高。①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受性別、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身體狀況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但總的看來,通過多因素分析,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后,養老模式及家庭結構仍然是影響老人生命質量的首要因素。機構養老模式,雖然使老人擺脫了家務事的勞作,但為保證老人的安全而可能對老年人的行動有較多限制,老人的社會功能較差,自主決定能力衰退。同時,養老機構中,老人很少得到親人的體貼照顧,精神孤單,情緒低落。在不同的家庭結構中,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評價也存在明顯差異。主干家庭中,由于子女已成家立業,且老年人在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易于得到子女的照料與幫助,盡管生活自由度較夫婦家庭略低,但并未影響他們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價。也即,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生活精神狀況顯然好于不和子女同住的老年人。
二、老年人照顧法律關系的關系契約屬性
“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4](P132)隨著主體自治能力和自我意識的增強,合意的契約已成為慣例。但契約自由的理念是建立在有關人是自由和理性的存在、主體能力完全平等、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等完美假定之上,這些假定存在的缺陷使得從身份到契約的論斷陷入困境,以形式平等掩蓋實質不平等的契約形式導致了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及弱勢群體的不平等保護。“單純的‘契約’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身份’越來越受到關注。”[5](P32)私人間的法律關系不再只是通過自由的契約運動來實現,而是越來越多地通過身份關系來確定,尤其在親屬法律領域,由于契約雙方多為家庭成員,其身份與契約的交織更為顯著。老年人照顧法律關系兼具傳統契約與現代身份雙重屬性,我們認為它更具關系契約屬性,即它必然地在部分意義上是一個關系契約,也就是說,“這個契約不止是一次個別性的交換,而是交涉到種種關系”[6](P159)。
(一)原因
老年人照顧法律關系是關系契約原因有三。
其一,基于被照顧老年人的有限理性。在老年人人身照顧法律制度中,完全行為能力的老年人讓代理人替代決定時,常常不清楚代理人將忠誠、可靠、盡其所能完成義務,還是玩忽職守,而對于限制或無行為能力的老年人來說,他們所獲得的信息更不完善。當照顧事項展開以后,可能會發生照顧人利用他方意思能力弱點而實施的謀利行為。尤其對于意定老年照顧合同,如果不給予當事人設立今后及未來一段可能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照顧的自由,則不能充分完全的實現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如若給予該自由,照顧人如何行使代理事項,才是為了被照顧人最佳利益,這并不是依據傳統的契約理論可以解決的問題。
其二,基于人的利己與利他。傳統的契約理論認為人都是利己主義的,追求自身利益是驅動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但事實上,“我們面臨一種非邏輯性。人既是一個徹頭的自利動物,也是一個徹底的社會動物,除了在極端的情況下,他會在不一致的行為中不斷變換,即這回自私自利,下次自我犧牲”[7](P78)。設立老年人照顧制度正是基于人的利己和利他屬性,沒有一個人能夠大包大攬另一個人的人身事宜,即使被照顧人不能合理地決定自身的事宜。因此,需要一個關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人身照顧事宜相對合理的制度,以最大程度地保護被照顧人的個人自由意志。
其三,非承諾交換的存在。即時同意在傳統契約法理論中非常重要,所有的關系都不應超出同意的范圍,但實質上,其同意充其量只能發揮一種觸發作用。“承諾既不是契約關系中最有效的也不是最主要的交換規劃者,而持續性契約關系未來的交換將會發生,并且通過現存關系的動力以部分可預見的模式發生。”[8](P25)老年人人身照顧的設立前提是承認這類非承諾性交換(包括習俗、身份、習慣和其他為人所內化的東西、等級結構中的命令,以及由包括市場在內的任何現實狀況的動力所創造的期待等因素)的存在。
(二)特征
作為關系契約,老年人照顧制度是以契約為表象,關系為內在,兼具契約與關系雙重屬性的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家庭成員私人關系的嵌入。法定老年人照顧制度因為照顧人與被照顧人的親緣信任關系而具備人身屬性,而在與老年人醫療與健康護理事項相關的可持續性意定照顧合同中,私人關系嵌入性更加明顯。這些照顧合同的代理人或為親屬,或為有信任關系的朋友。在此項照顧關系中,參加者從中得到各種人身的非經濟的滿足,除了進行一個局外的觀察者所謂的經濟交換外,還進行社會性的交換。
二是標的難以測量性。在老年人人身照顧實踐中,由于人身照顧事務不同于財產照顧事務,它的實際履行及合理履行與否,未必具有貨幣估量性,此類照顧關系衍生的責任也具有不可估量性。
三是契約持續時間長。契約交易的一切活動,包括達成協議的過程,達成協議到履行協議之間的時間間隔以及履行協議的時間,都是短暫的。但在老年人照顧制度中,無論是法定照顧還是意定照顧合同,都可能為長期契約,契約的履行和終止都會產生涉及當事人及第三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可能依據約定,也可能依據法理、倫理。
四是照顧人與被照顧人具有 “統一體”意識。在傳統的契約關系中,契約雙方當事人利益對立性較為明顯,此消彼長。但在老年人照顧契約中,當事人具備“統一體”意識。參與人在某種程度上認為他們個人的利益與整個關系的利益范圍一致,感覺到自己照顧的履行要通過實現被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來滿足,在最終的心理學意義上,看不出自己的利益和其他參與人的利益之間的區別。此種關系中的利益并不具備明顯的對抗性,它以信任關系為基石,并不鮮明、自覺地注重個人利益,其對于利益沖突的認識是模糊的。
五是強制保障機制的多元化。“在傳統契約中,契約的內容來源于當事人的承諾,而責任來源于確保承諾實現的外部之神,有關的社會穩定、實施承諾的機制和其他基本需要是由外在之神提供的,在這些嚴格的范圍內,當事人自由地追求最大的個人功利,直到心滿意足。”[9](P14)在老年人人身照顧契約中,契約的內容和責任的淵源也包括關系本身。
無論是以身份為基礎建立的法定老年人人身照顧制度,抑或是以契約為形式基礎建立的意定老年人人身照顧制度,都充分體現了身份與契約的融合。
(三)核心
老年人照顧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家庭自治為中心。基于制度本身的關系契約屬性,在老年人照顧制度中,以“契約”為基礎,②尊重契約本身的家庭屬性,重視家庭成員的充分參與,相信家庭成員是老年人最佳利益的選擇與執行者。
老年人法定照顧制度從傳統的大包大攬轉向細致性保護,老年人意定照顧成為可能。傳統照顧合同基于對被代理人自由意志的保護而要求被照顧人意思能力的持續性健全也發生變化,意思能力日漸衰退的老年人的人身照顧事項可以交由其家庭成員或親朋好友并依據他的意志來決定其意思能力部分或全部喪失后的身體和財產照顧事項。老年人的個人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家庭意志的影響,個人與家庭是密不可分的不可割裂的整體。當然,在家庭和親屬群體缺失或不能的情況下,基于弱勢群體保護,國家需要采取干預政策,設立公職照顧,采取指定照顧等手段,力求以公權手段實現被照顧人利益的平等保障。
總之,在關系契約下,我們看到的契約不只是一個文本,而是一個過程,契約內容不可能全部包含于當初的合意之中,應該從契約背后的社會關系和共同體的規范中去尋求根據,契約中的約定不能成為契約拘束力的一元根據,命令、身份、社會功能、官僚制、宗教義務、習慣,期待都應當成為契約的考慮因素。當事人不必小心翼翼地顧及僵化的契約條款,應當隨情況變化對契約權利和義務進行再協商和調整或對契約內容進行再推測。
三、老年人養老照顧制度的圖景
(一)分享型老年人人身照顧模式
建立分享型老年人照顧模式是考慮到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家庭在養老中的重要性及家庭成員在老年人照顧中的重要地位。我們并不能以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決定權為借口,武斷地忽視被照顧人可能發生變化的自主決定權,也不能割裂老年人本人同家庭成員的密切聯系。分享型健康照顧代理模式要求建立相應的條款幫助老年人作出仔細和深入的思考,維護當事人生命健康安全。醫師、老年人本人與家屬及其親朋密友的探討十分重要。為了防止老年人因為預見到自己的無能力狀態而試圖不增加親人負擔而做出武斷的預立指示,③應當提供防范措施,確保健康護理的代理意見是基于病人的自由意志而非壓力,且經過了與家庭成員的充分溝通。
同時,構建分享型健康照顧的代理模式應當以變化發展的態度對待個人選擇及個人自身的多變性。當老年人已經失去部分意義重大的行為能力而開始適應新的、殘缺的生命狀態時,“他們可能會出現生命價值觀點的逆轉情形。許多被診斷為喪失決定能力的老年人實際上在相當長時間后才會喪失有關復雜醫療行為的決定能力”[10](P78)。而且,在生命質量不高的情形下,多數時候老年人無法回歸當初作出預立指示的具體心境。對“預立指示”的因循守舊并不能保護病人或反映他們的真實愿望。
(二)法定老年人人身照顧人的選擇
法定老年人照顧制度是老年人照顧的傳統模式。對被照顧人的申請進行個案審查,當有事實和證據證明老年人欠缺行為能力,或有可能對自己或者他人造成實質性損害,或客觀上不能處理相關事務的,公權機關應根據該老年人或其他利害相關人的申請或依職權為其設定法定老年人照顧制度。一般來說,基于傳統倫理關系形成的信賴利益,法律強制規定老年人的近親屬為老年人的照顧人。老年人的近親屬或為家庭成員,或受老年人養育,同老年人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此種血緣親緣關系有利于從客觀上保障老年人的最佳利益。法律同時也推定,家庭由于其本身具備的情感特征,它是最了解家庭成員的價值觀以及習慣語言、經常談論的話題、文化娛樂的內容、交友的范圍、個人喜好等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組織,它能夠相對合理的了解老年人的個人意愿,幫助老年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最有利自己和最舒適的選擇,它也是可能最合乎老年被照顧人意愿的照顧人。
在家庭成員擔任照顧人時,要盡量以客觀標準及“功能性行為能力標準”[11](P78)來評估老年人的現狀,避免家庭成員擔任照顧人引起的大包大攬。首先,應當考察被照顧老年人意思能力,針對不同的老年人根據其殘存意思能力選擇適當的照顧類型,盡量以限制照顧、輔助決定替代全權照顧,盡量以臨時照顧替代常規照顧,幫助限制行為能力的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會生活。其次,在選擇家庭成員替代照顧人時,應當最大程度依據老年人的個人意志。老年人本人未對任何可被選任為照顧人的人選提出建議的,在挑選照顧人時,必須考慮與老年人的血統關系或其他個人聯系,特別是父母、子女、配偶的聯系,以及利益沖突的危險。成年子女或與老年人關系密切的家庭成員應當作為第一順位照顧人。配偶是否作為第一順位照顧人,應當酌情考慮配偶年齡與身體狀況。對被照顧老年人提起訴訟或曾提起過訴訟的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血親、正在提起離婚訴訟的被照顧人的配偶不能作為老年人的照顧人履行照顧職責。最后,家庭成員履行照顧職責時,應當給予老年人依照其殘存意思能力進行自治的空間,只有依其個人意思能力不能處理的事項,法律才將其賦予照顧人,即便是涉及老年人人身的重大事項,照顧人也不能私自以其所認定的普遍價值觀為基準代替被照顧人做出決定。
在不同的法定老年人照顧類型中,老年人本人都存有法定的保留性權利。其中,輔助決定人的設立必須經過老年人本人同意。輔助決定人在履行照顧職責時,應當充分尊重本人的意思自治,由老年人本人選擇輔助決定的設立和內容。如老年人沒有明確設定或只進行了概括性設定,則由法院以該老年人的意愿和最佳利益為基礎,確定輔助決定人權利涉及的特定事務。輔助決定人的代理權、同意權、取消權都必須經過本人申請和同意才可設立。無論何種類型的老年人照顧,“家庭成員在履行照顧職責時,必須定期與老年被照顧人進行溝通,以了解老年人變化了的意愿和需求,維持良好的、持續性的、相互間的信任關系”[12](P32)。
(三)家庭成員的告知義務
保障老年人的知情權需要家人與醫生的共同努力,家庭成員與老年人本人的親密關系使得他們能夠更容易根據老年人的意思能力,以老年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運用簡單的語言(肢體語言),向處于平靜心態下的老年人解釋做出接受(或拒絕)某種醫療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以提高他們理解信息的能力。對于老年人來說,由于其意識能力的缺陷,理解能力的局限性,這就要比其他人需要依據更多的信息得出結論。
(四)家庭成員的監督權
照顧監督人是對照顧人的照顧行為負監督職責的自然人、法人或機構。除公職照顧監督人和老年人指定照顧監督人的情形外,如無合適人選,公職機關指定照顧人的配偶、父母、老年子女、其他近親屬擔任照顧監督人。當家庭成員中的一人作為照顧人時,其他家庭成員作為照顧監督人有利于照顧監督人監督職責的行使。照顧監督人應當對照顧人的行為實行檢查和監督,對照顧人不適當履行照顧的行為,督促其糾正并及時向基層組織匯報,甚至以被照顧人的代理人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當涉及重大的照顧決定權時,考慮照顧人實施的控制權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在涉及同被照顧老年人醫療重大事項有關聯時,必須由監督人會同照顧人進行共同決定。
注釋:
①老年人生命質量評分數據表即SF-12量表,是一個12條目的結構式問卷,包括8個領域,分別測定與健康有關的8個維度,即軀體活動功能(PF)、軀體功能對角色功能的影響(RP)、疼痛(BP)、健康總體自評(GH)、活力(VT)、社會功能(SF)、情緒對角色功能的影響(RE)、心理功能(MH),是根據華西醫科大學劉朝杰等人創設的 “36條目簡明量表在中國人群中的適用性研究”而制定。可以較客觀地從各方面反映老年人的生命質量。
②法定老年人照顧也可以視為國家同照顧人簽訂的有關被照顧老年人健康事項的契約。
③預立指示(Advanced directives)是指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事先訂立一份書面文件,告知家人及代理人等,當自己喪失相應決定能力時,有關身體健康照顧的事項交由某一特定人替代決定,或僅僅告知其在處于死亡末期或不可挽回的生命末期時,有關維生治療處置的意愿,通常此意愿為不予治療或撤除無效的維生治療。
[1]李欣.家庭養老保障論——以親屬法之保障為視角[J].民商法學(人大復印資料),2011,(11).
[2]馬長山.國家、市民社會與法治[M].沈景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3]左秀榮.未來的婚姻、家庭與社會[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0.
[4](英)梅因.古代法[M].高敏,瞿慧虹,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5]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美)詹姆斯·M.布坎南.制度契約與自由[M].王金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7](日)內田貴.契約的再生[M].胡寶海,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8]康娜.關系契約視野下的婚姻觀——對傳統婚姻契約觀的反思和突破[J].法律科學,2009,(5).
[9](美)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M].雷喜寧,潘勤,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10]LaurieTarkan,DebatingPatients'CapacitytoDecide,N.Y.TIMES,AwardofOct.2,2001.
[11]Israel Doron,From Guardianship to Long-Term Legal Care:Law and Caring for the Elderly,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Graduate Program in Law Osgoode Hall Law School,at York University,Toronto,2010.
[12]Maura A.Flood,Treatment of the"Vegetative"Patient:The Legacies of Karen Quinlan,Nancy Cruzan and Terri Schiavo,Journal of Health&Biomedical Law,Arb.Int’l,2005,Vol.1,No.2.
【責任編輯:胡 煒】
D923.9
A
1004-518X(2015)09-0179-06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老年人醫療與健康護理代理權制度研究”(2014M551876)、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安徽省老年人照顧制度的法社會學研究”(AHSKQ2014D05)、安徽省教育廳高等學校省級優秀青年人才重點項目“以家庭自治為中心的老年人照顧法律制度研究”(2013SQRW019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