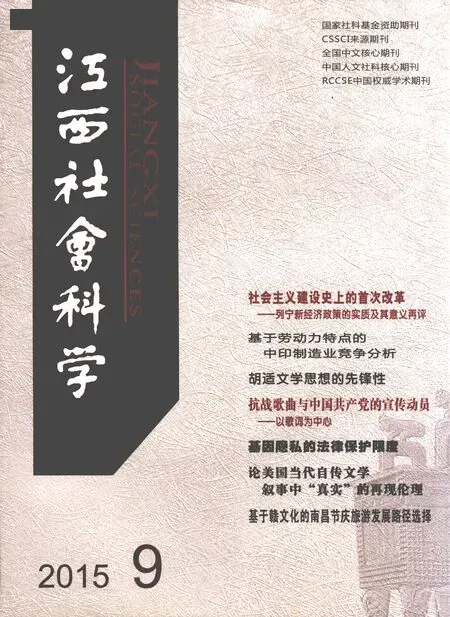脆弱性與農村長期貧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彭新萬 程賢敏
果個體或群體處于貧困狀態的時間達五年以上,則其極可能在生命周期的剩余部分持續貧困狀態。貧困較長的時間持續是長期貧困最重要的特性,貧困的動態變化特性使得在研究長期貧困時對貧困過程的分析顯得更為重要。
近年來,相關領域的研究把長期貧困群體具備的特征概括為以下幾方面:(1)人力資本存量低。相關觀點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存量與長期貧困三者之間存在封閉循環關系。人力資本存量可通過三個層面來提升,分別是傳統教育、后學校職業技能培訓以及群體健康水平。群體教育程度與持續貧困之間存在著逆向關系,普適化學校教育與專業化職業教育及定向培養為現代教育的主要方向,且均與削弱持續貧困水平存在密切關系。同時,人力資本投資的長期化成為研究的要點,減少長期貧困的關鍵在于教育水平或教育時間的持續發展,而且發展較高層次的教育更能有效地防范長期貧困。(2)地理差異。地理差異即長期貧困狀況會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存在差異,長期貧困所展現出的地理差異較之其他貧困類型更為顯著,地理差異在為家庭提供經濟發展的機會方面設置了階梯或者門檻。地理位置差的地區,發生規模性長期貧困的概率大,反之亦然。這種現象在我國表現比較明顯,由地理差異而引起的長期貧困狀況尤為突出,特別是在西部地區或者貧困山區。(3)固定財產存量低。家庭固定財產為突破長期貧困格局提供支持,固定財產存量水平愈低,脫貧實力愈弱。就我國現狀而言,對土地的永久性承包權是家庭固定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固定資產的貧乏,使其不能單靠自己的力量來擺脫貧困。(4)職業特征明顯。通過相關調研發現,可以通過群體的經濟行為來考查長期貧困。例如,長期貧困更容易綁架那些從事自耕的農民群體。(5)長期貧困群體的脆弱性。脆弱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一直是困擾長期貧困群體的重要問題,他們應對疾患、自然災害等沖擊的能力較低。他們除了要面對低收入、低消費、低能力等劣勢外,還要接受其引發的巨大壓力。通過總結大量研究結果發現,長期貧困人群所面臨的巨大問題即疾病和健康。[2]脆弱性在長期貧困形成中的影響十分突出,上述(1)至(4)四項長期貧困的特征也是構成脆弱性的重要元素。
本文把我國當前農村剩余貧困歸于長期貧困進行研究,除了上述特征外,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誘發因素:(1)脫貧者脫貧主要依賴國家的扶貧政策,一旦離開了國家的資金支持,返貧現象極易發生,或者返貧者的脫貧持續期短,貧困期依舊在這個群體的生命周期中占據很長時間;(2)由于更深層次的脫貧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存量,而返貧者的人力資本存量往往較低,無法滿足更進一步的脫貧實力的要求;[3](3)在重大的或突發性的風險因素發生時,缺乏系統性的應對機制,使致貧后難以在短時期內脫貧。
二、我國農村長期貧困形成的本質:社會學層面的脆弱性
(一)脆弱性的概念
所謂脆弱性,世界銀行給出的定義是:包括個人或群體面臨某些風險的可能性,以及因遭受風險致使財富縮水或生活質量降低至某特定水平的可能性。脆弱性包括群體受到沖擊和對抗沖擊的實力兩方面,兩者相比較的結果即脆弱性。在研究過程中,控制其他干擾因素,則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當受到相同的沖擊時,抵御能力和脆弱性之間呈反向關系;當其具有相同的抵御沖擊能力時,受到的沖擊與脆弱性之間呈正向關系。[4]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脆弱性的核心在于個人或家庭在特定條件下應對風險的結果。對其福利水平變動的評價方法主要采用貨幣評價,也可表述為家庭或個人應對風險產生的消費或收入及資本等方面福利的損失。但現實生活中卻不僅于此,對于福利的衡量還需要對其他方面進行評價。因此,具有廣泛概念的脆弱性,除了包含收入、資產、食物安全等脆弱性之外,還涵蓋了與社會排斥、暴力、健康等有關的其他風險。從人類學和社會學角度分析,脆弱性與長期貧困的含義被擴充,同特定環境相結合的收入或消費頻發的狀態是社會學家對貧困的一般描述,他們用來描述貧困狀態的術語通常有實力、謀生、剝奪、排斥等詞匯。參與式也是社會學用來辨別貧困和貧困可能性及貧困程度的方法,個體和家庭及社會面對變化的環境而產生的福利的不穩定,是社會學家對脆弱性的普遍定義。拓展資本的概念是社會學家最大的貢獻之一,他們讓其他人認識到社會資本與物質和經濟資本具有等同的重要性。因此,社會學家發現了“風險-風險響應-結果”這個風險鏈,并且認為社會資本管理在整個風險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5]另外,不少學者從災害管理、生態環境、健康營養等方面對脆弱性進行分析。總之,從宏觀角度講脆弱性,它是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等體系下的整體產物;從微觀角度分析,它綜合了個體人力資本、居住地域、家庭固定財產等因素。
(二)脆弱性與貧困
通常認為脆弱性與貧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但兩者不等同。例如,某個體脆弱但不貧困,或者既脆弱又貧困。[6]脆弱性是事前狀況,它被描述為在未來處于貧困的可能,脆弱性不能被直接觀察到但可以被預測。[7]相反,貧困是事后的可觀察到的狀況,其具有不可預測性。
依據貧困持續時長的差異,本文將長期的和短期的貧困進行區分。長期貧困即某個體或群體在特定時期持續處于貧困線以下,短期貧困為偶爾處于貧困線以下,貧困所具有的動態性體現于此。貧困動態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短期貧困和長期貧困的發生率;貧困的進入與退出。國外學者對長期貧困和短期貧困的發生率進行了深入研究,并且試圖找出其決定因素。Jalan J和Ravalion M指出,無論是長期貧困還是短期貧困,對家庭平均財產擁有量都存在極大依賴,但家庭人口、家庭成員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狀況對長期貧困的影響是巨大的。Radhakrishna R等也指出,長期貧困與工資水平、收入水平、人口壓力、健康水平及其他社會因素密切相關。在分析貧困進入與退出因素的過程中,許多研究者發現,貧困進入和退出過程中不存在穩態,并且人們的貧困持續期越長,脫貧機會就越少,而返貧的風險就越大。[8]
脆弱性具有動態發展的特性。脆弱性是以個人或群體過去為應對各種沖擊而造成的生活質量降低為基礎,結合未來各種沖擊發生的機會和個人或群體在沖擊產生時的承受能力,從整體層面把握個人或群體未來的生活質量的變動,因此脆弱性是一個與時間變量高度相關的具有前瞻性的預測。同時,其地理差異特征表現顯著,受到沖擊的種類和程度會因所處地區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區別,因而對脆弱性的評價也會有較大差異。除此之外,其還存在群體差異,不同的群體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一般而言,在受到糧食危機、政局動蕩等沖擊時,脆弱性表現在婦女和兒童中程度更高。[4]從脆弱性和陷入貧困的可能性層面來分析,長期貧困者更為脆弱,其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更大,脆弱性程度更高,并且自我脫貧的可能性更小,致使貧困持續期甚至覆蓋整個生命周期。因此,解決長期貧困的難度相較于短期貧困更大。[9]
(三)社會排斥、脆弱性與農村長期貧困的形成
如前所述,脆弱性同時是長期貧困的特征與重要誘發因素,實際上,社會排斥也是引發脆弱性的要素之一。社會排斥(或曰政策排斥)具體體現為排斥性政策,即被排斥的社會群體在某些相關政策或法規的作用下被推離社會中心位置的過程。[3]排斥性政策,是指由政府頒布各種政策和規定不能對社會群體進行全覆蓋,總存在部分社會成員被排除在某些特定政策之外,從而無法享受到與其他社會成員等同的社會福利政策。政府頒布特定的政策具有歷史特定性,因而政策的效用性與缺陷共存,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修正。社會排斥這一蘊義與脆弱性含義的界定是一致的,社會排斥的關鍵要素是動態性。因此,想要精確評估社會排斥程度,就不能局限在對當前狀態的考查,對長期貧困的討論同樣不應局限于此。羅伯特·沃克爾曾經指出了這種將貧困和社會排斥概念結合的路徑:“出現長期貧困——貧窮群體脫貧機會少——貧窮群體被更廣泛的社區認同的機會也更少。”在此種狀況中,貧困經歷更加接近于社會排斥經歷。[10]長期以來,在我國多項政策實施的過程中,許多政策對受眾群體進行了劃分,農民群體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處于被束縛的狀態。根據對社會排斥機制的分析,可以發現:有些針對社會保障及就業、干部人事任用、各種基礎資源分配等方面的特定政策導致主要排斥主體的形成,以經營農業生產的農民群體構成了大多數的排斥客體,持續加深對客體不利影響的排斥性政策實施構成了主要的排斥過程,最終導致農民群體脆弱性加劇的排斥結果。[11]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當前農村長期貧困的形成存在“社會排斥——脆弱性——長期貧困”的邏輯機制。總體上,有兩個層面因素致使我國農村長期遭受社會排斥并形成脆弱性貧困。
1.基本政治權益層面的排斥。我國農村農民群體話語權的脆弱與缺失,應歸結于其最基本政治權利(大體包括自由權、平等權、參政權、生存權、自治權等)未得到充分體現,這種現象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尤為顯著。這會導致以下后果:一是農民群體在管理國家或集體事物方面喪失實質性的參與權。在各級政府關于農業發展規劃及方針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決策過程由利益的組織者或管理者主導,沒有真正給農民代表設立席位,發展規劃和政策并不是以農民利益為導向。二是無法形成以農民利益為導向的群眾組織。根據2014年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45.23%,盡管我國農民群體幾乎占據總人口的半壁江山,但沒有群眾組織代表自身利益。因此,在我國,農民利益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侵占的事件時有發生。其實,從更深的層面上來講,這些均反映出當前我國農民組織缺失、地位不高、無相關法律政策支持的客觀事實。顯然,在農民群體無法完全獲得基本政治權利的情況下,我國整體扶貧計劃的實施通常會使扶貧的社會政治經濟目標出現分歧。由于缺乏健全的能夠進行利益訴求和表達、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機制,農民群體實際利益不斷受到挑戰,從而提高了扶貧難度。
2.基本社會權益層面的排斥。我國公民的基本社會權益主要包括受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社會尊重權等,而農民群體的這些權益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策性排斥,致使農民群體人力資本存量降低及農民群體的脆弱性增加。
農民群體人力資本存量水平較低。知識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知識能力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之一,而教育則是人類獲得知識能力的重要渠道,只有知識能力與人力資本存量得到相應提升,才能從本質層面解決農民群體的貧困問題。然而,我國農村農民群體長期以來并沒有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權,特別是在一些老、少、邊、窮地區。現有政策所形成的教育排斥,已經成為大范圍提升我國農民群體素質和知識能力的絆腳石。無論是在義務教育、高等教育還是職業教育等方面,均存在較為明顯的城鄉差距。現行“二元”城鄉戶籍制度對農民群體在享受均等教育機會方面存在較大沖擊,在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分配層面顯得更為明顯。城鄉居民本應享受同等教育權利,但是許多農民群體卻被排斥在各層次水平教育之外,這些“二元”政策嚴重阻礙著農民自身脫貧能力的提升以及代際流動的加速,使得原本存在的弱勢群體深陷代際流動的惡性循環之中。
公共福利權利被忽略。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通過多種福利政策和措施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為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與更為完善的公共基礎服務,卻忽略了農村居民相應的醫療衛生、糧油供應、基本社會保障等制度方面的建設,導致農民應對突發災害能力的下降和物質儲備的不足,農村居民處于公共福利權利長期受到政策性排斥的窘境。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在改革開放初期,占全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群體完全與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無緣,農民群體的分享與貢獻比持續處于較低狀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之后,黨和國家開始重視農村社會保障與福利,農村的社會保障事業建設為部分貧困農村居民擺脫貧困提供了重要途徑。但是,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仍存在較大差距。以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為例,《民政部發布2012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全國城市居民低保補助水平為月人均239.1元,農村居民低保補助水平為月人均104.0元;而《民政部發布2014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全國城市居民低保補助水平為月人均411.0元,農村居民低保補助水平為月人均231.4元。可見,現有政策長期排斥和歧視農民群體本應該享有的公共福利權利。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剝奪和歧視農民的排斥性政策是致使我國農村長期貧困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其中由社會排斥導致的農民的高脆弱性是當前農村長期貧困存在的典型特征。這種高脆弱性表現在:政策上,農民沒有發言權,是被動的接受者;行政上,農民是被管理者;社會保障和福利上,農民無緣分享;公共基礎資源分配上,農村無暇被顧及。因此,對農村長期貧困的消除工作重心應放在消除社會排斥層面。
(一)消除對農村的排斥性政策
消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我國戶籍制度的特殊性在于戶籍權益化,兩種類型戶口背后依附著數十種有區別的權益,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主要代表的是二元權益,戶籍與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權益直接掛鉤,農民群體在分享上述公共社會資源時被嚴重隔離。因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是我國農民受到政策性排斥的源頭。雖然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目前農民群體在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中仍然無法實現與城鎮勞動者平等地位并享受對等的權益,它揭示了我國傳統戶籍制度的缺陷及與其捆綁的相關政策所導致的不公平性。[4]因此,要達到徹底消除農民在教育、醫療和公共福利等方面受到的社會排斥和歧視的目標,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就應放在廢除二元戶籍制度及徹底破解城鄉分治的社會結構。除此之外,還應建立城鄉統籌的戶籍管理制度,實現城鄉無差異化管理,完成城鄉社會保障信息無縫對接,促進社會和諧。
消除教育權益中的排斥。教育權益的政策性排斥具有長期性、隱蔽性、破壞力大、影響程度深等特點,而結構性排斥是我國教育權益的政策性排斥的主要特征,致力于改變現今教育領域內的取向性問題是主要的消除方向。因此,消除教育領域內排斥的措施應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理清城鄉教育整體規劃的側重點,在目前城鄉教育發展差距大的現實背景下,制定合理的、規范的、具有協同性的教育發展計劃;繼續深入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在保障城鄉平等受教育權利的同時,適度向農村傾斜,切實解決農村教育問題;增加農村教育扶持力度,對長期貧困家庭群體進行國家財政補助,啟動教育幫扶基金,對長期貧困兒童入學直補;大力創新農村職業培訓模式,不斷提高貧困人口的智力、知識和技能水平,增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確保農村人力資源的能動性、再生性、增值性和時效性等作用的充分發揮,增強脫貧能力。[12]
消除公共福利中的排斥。消除傳統戶籍制度的二元結構,建立與農村現狀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優化升級社會資源配置,保障農村福利水平穩步提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移支付是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其不僅能提高農民的抗風險能力,也能從體制層面提升農民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消除目前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中的二元結構是有效促進農村地區經濟持續增長,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的有力舉措。
(二)形成或增強有助于降低未來貧困的風險應對機制,提高農民抵御風險沖擊的能力
降低農民的脆弱性和提高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重點是建立城鄉平等的應對風險的機制。當前,自然災害和疾病已經構成了與我國貧困群體最密切的風險。[13]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就一直致力于對自然災害的防范工作,在農業基本設施以及災害易發點農民的安置方面進行了大量投入,這對于減輕無法預測的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及農民正常生活的沖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在災害之后及時提供有效的救助,縮短受災家庭恢復生產生活的時間。但是,在我國農村仍未形成具有長效機制的防災抗災措施,原有措施在應對自然災害時顯得尤為乏力,“因災貧困(或因災返貧)”問題十分突出。在農村受災頻率高于城市的客觀條件下,建立城鄉高效科學的應對自然災害風險的機制,如積極推動農民購買保險、進行家庭儲蓄等,這能夠較好地應對自然災害而避免農民陷入貧困。
疾患風險是農民群體面臨的重大風險之一,雖然我國在農村醫療改革工作中取得了顯著成績,但與嚴峻的農村醫療衛生壓力相比,現有農村醫改規模還遠不充足,未能在防范風險和降低脆弱性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疾患貧困(或疾患返貧)”在農村還非常普遍。因此,應該從事前和事后兩個層面來降低疾患風險與提升抗風險能力。在事前方面,應建立農村快速就診通道,升級基礎醫療條件,保障農民以最快的速度獲取可靠的醫療服務;提高農村衛生水平,降低農村居民患病風險。事后層面的重點在于防范患病后的無資金支持,因此應對目前農村醫療保險制度進行改革,擴大疾病報銷范圍,擴大醫保資金渠道,保障充足的保險資金。
[1]Hulme,D.Conceptualizing Chronic Poverty.World Development,2003,Vol.3.
[2]何曉琦.長期貧困的定義與特征[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4,(6).
[3]彭新萬.當代中國農村貧困:性質、原因及政策選擇——基于社會排斥視角的分析[J]理論與改革,2008,(4).
[4]韓崢.脆弱性與農村貧困[J].農業經濟問題,2004,(10).
[5]黃承偉,.貧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測量方法[J].農業技術經濟,2010,(8).
[6]Gaiha,R.,Katsushi,I.Measuring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Estimates for Rural India.Research Paper No·2008/40·United NationsUniversity,UNU-WIDER,2008.
[7]Ethan,L.,Laura,S.MeasuringVulnerability.The E-conomic Journal,2003,Vol.3.
[8]張清霞.貧困動態性研究[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9]Barrientos,A.,Hulme D.Chronic Poverty and Social Protection:Introduction.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2005,Vol.1.
[10](英)托尼·阿特金森.社會排斥、貧困和失業[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3).
[11]周湘斌.我國社會轉型時期農民群體的社會權利與政策性排斥[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
[12]付志鴻,陳標平.統籌城鄉視閾下的中國農村反貧困戰略轉向[J].求實,2013,(4).
[13]洪秋妹.健康沖擊對農戶貧困影響的分析——兼論健康風險應對策略的作用效果[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