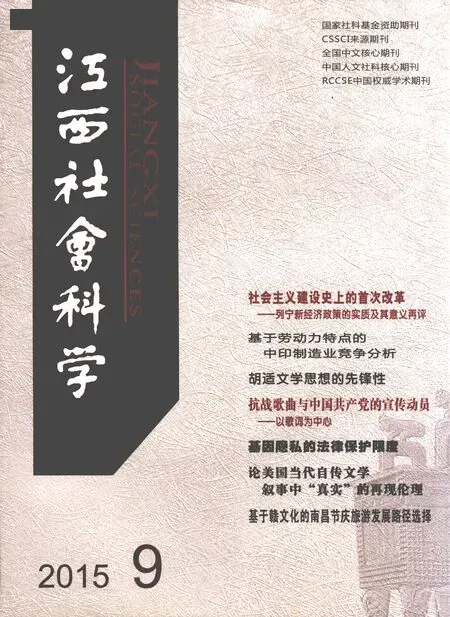論美國當代自傳文學敘事中“真實”的再現倫理
■唐偉勝
論美國當代自傳文學敘事中“真實”的再現倫理
■唐偉勝
自傳文學這一敘事文類既要求“真實”,但又不可避免地帶有“虛構”成分,在“真實”與“虛構”間協調平衡是一個充滿倫理選擇的過程。對《安吉拉的灰燼》《吻》《說謊:一部隱喻式自傳》三部頗具代表性的美國當代自傳文學文本的分析表明:當“主觀真實”比“歷史真實”重要時,即使因各種原因“歷史真實”出現偏差也不違倫理;當自傳主真誠講述時,即使講述的“真實”人生故事不為主流社會規約所容,自傳主的勇氣依然值得贊賞;當自傳主刻意在某一“歷史事實”上語焉不詳,甚至前后矛盾,但他/她以此建構出來的身份也許更加“真實”。與傳統自傳(文學)相比,美國當代自傳文學屢屢突破真實/虛構、主觀/客觀之間的界限,以傳達更加復雜的人生體驗,這使當代自傳文學的倫理問題更加微妙。
真實;虛構;倫理;美國當代自傳文學;敘事
唐偉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云山杰出學者”,教授,文學博士。(廣東廣州 510420)
一、“自傳文學”的倫理本質及倫理層面
顧名思義,“自傳文學”是自傳與文學的結合體。傳統意義上的自傳要求絕對真實,屬于歷史范疇,而文學的本質則是虛構。因此,“自傳文學”既要求“真實”,但又不可避免地帶有“虛構”成分,是在個人真實歷史基礎上的再創造。基于此,我們可以認為,自傳文學是居于自傳與虛構文學之間的一種敘事文類。國外自傳批評家對自傳(文學)的虛構性質已有很多論述。譬如,羅伊·帕斯科認為,“自傳……對一個生命(或部分生命)在其經歷的真實環境中的運動軌跡進行重新建構”,自傳寫作是“對過去進行塑形”,這意味著“給生命套上一個模式,從中建構出一個連貫的故事來”。[1](P9)馬克·弗萊曼認為,書寫自我就是為過去之我尋找一個闡釋框架,然后往其中添加相關信息,這個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虛構的過程,而非一個寫實過程。[2](P30)雷蒙·威廉姆斯把自傳比喻為“雙面間諜”,游走在自我/世界、文學/歷史、真實/虛構、主觀/客觀這些對立之間,卻無力解決這些對立。[3](P7)正是由于難以用“真實/虛構”來定義自傳,勒熱訥提出自傳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一種契約,在這份契約中,自傳主向讀者明確承諾的,“不是忠實于某種不可能企及的歷史精確性,而是真誠(sincere)地努力看待和理解自己的生活”。[4](P12)換句話說,自傳就是自傳主“真誠地”來“講述”“自己的”“生活”,勒熱訥相當于為“autobiography”增加了自傳主“真誠與否”這一標準,試圖以此來取代“真實與否”。
然而,自傳文學又不完全等同于虛構文學。按照德國著名敘事學家多里特·科恩的看法,自傳文學與虛構文學的區別在于:(1)雖然二者都有“故事”和“話語”兩個層面,但自傳文學的“故事”必須有一個外部歷史參照,而不是無跡可尋,也就是說,自傳文學中“發生的事”須指涉外部事實;(2)敘事聚焦方面,虛構文學可以自由使用虛構人物的眼光,而自傳文學則“只能借助永遠處于回顧視角的歷史家 ̄敘事者的眼光”;(3)在敘事聲音方面,自傳文學只能有一個聲音來源,那就是自傳主,而虛構文學則可以有多種選擇。[5](P775-804)這樣看來,自傳文學雖然可以虛構,但這個文類注定要在 “故事”、“聚焦”、“聲音”等各個層面營造真實幻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時,自傳主必須在以上各個層面協調選擇,面臨的倫理兩難更多,因此,對自傳文學進行倫理考量就顯得尤為必要。
按照聶珍釗的定義,倫理結是文學作品中構成倫理困境的矛盾與沖突。[6](P258)基于這一定義,結合以上對自傳文學中真實/虛構關系的討論,我們至少可以劃分自傳文學中三個層面的倫理結:(1)“故事”倫理結,所講之事是否屬于歷史事實?應該選擇講述哪些歷史事實?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修改歷史事實?(2)“話語”倫理結,講述聲音是否“真誠”?講述角度是否客觀?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對講述聲音和角度進行調整?(3)“他者”倫理結,自傳在探索自我及身份的過程中,如何再現與他者的關系?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講述他人的隱私?如何分配自我和他者的倫理責任?比如,雷·吉爾摩強調自傳文學中的“事實”(truth)不是純客觀事實,自傳中的“事實”雖來自傳主的生活,但受制于傳主的寫作意圖,選擇哪些事實進入自傳,如何再現這些事實往往轉化為一個倫理問題。[7](P47)保羅·依金則認為,“我們都生活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因此,書寫自我必定包含一個再現他者的倫理層面。[8](P8-11)
然而,我們該如何考量自傳文學的倫理價值?有人堅持“自傳(傳記)文本的真實性原則”,提出自傳文學的“事實正義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自傳文學都應恪守“事實”。[9](P48-53)但是,如果考察美國當代自傳文學實踐①,我們會發現,這種過于簡單化的唯“事實正義論”也許并不能對他們的倫理價值做出公正的評價。按照聶珍釗的建議,文學倫理學批評分析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在具體的倫理環境中分析文學作品。[6](P9)本文擬以三個著名的自傳文學文本為例,探討如何回到“歷史現場”,解讀美國當代自傳文學中的倫理問題。
二、《安吉拉的灰燼》:“敘事真實”高于“歷史真實”
苦難自傳(Misery Literature,簡稱Mis Lit)是當代美國非常流行的一種傳記文學亞類型,它著重表現主人公童年生活的苦難 (比如受到來自父母、老師或者環境的冤屈或者身體傷害),以及主人公如何戰勝痛苦,最終實現某種心靈凈化、救贖或逃離。代表作包括《名字叫“它”的孩子》(A Child Called “It”,1995)、《野天鵝》(Wild Swans,1992)、《說謊者俱樂部 》(The Liar’s Club,1995) 以及《安吉拉的灰燼》(Angela’s Ashes,1996)等。苦難自傳是當代美國圖書世界里增長最快的領域。雖然苦難型自傳受到讀者的廣泛接受,但批評界對這種類型自傳的評論卻是毀譽參半。支持者認為,這類自傳被廣泛接受表明美國人終于能夠坦然接受諸如困難童年、性侵、大災難這樣的話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反對者則認為,這類苦難自傳常常是作者的編造之物,折射的是人們內心的偷窺欲望,因而產生了很多倫理、甚至法律問題。由于苦難自傳的核心在于再現自傳主的苦難經歷,因此對真實性的評價就成為倫理考量的關鍵所在。
《安吉拉的灰燼》是一部成功的苦難自傳,它曾經連續120周雄踞《紐約時報》最暢銷書籍榜首。該自傳書寫的是作者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苦難,弗蘭克·麥科特(Frank McCourt)文筆清新,富于幽默感,同時具有愛爾蘭背景作家特有的鄉愁意識,這些都使自傳獨具特色。但在筆者看來,《安吉拉的灰燼》中苦難敘述的最大力量源于它給讀者造成的“真實效果”(reality effect)。
和普通自傳一樣,《安吉拉的灰燼》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視角;但和多數自傳不同的是,《安吉拉的灰燼》通篇使用現在時態,而不是慣常的過去時態。也就是說,這部自傳采用的是即時敘述(似乎講述和事件是同時發生的),而不是回顧性敘述(講述發生在事件之后)。在采用“小弗朗克”視角的時候,將其嚴格控制為“旁觀者”,而沒有切換成“敘述者/作家弗蘭克”的視角;同時,“小弗朗克”也沒有被賦予反思的能力。這樣,讀者就只能跟隨“小弗朗克”的視角,去觀察他的童年苦難生活,仿佛事實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這種方法產生的效果是降低了自傳寫作時的“記憶”中介(不讓讀者懷疑自傳主記憶的準確性),從而使自傳顯得很真實和歷史化,為其增加了“逼真感”。
正如杰洛米·布魯納所說:“自傳不僅應該被讀成個人表達,或者表達‘內心變化’的敘事,而且也應該被讀成文化產品。”[10](P38)《安吉拉的灰燼》作為文化產品非常符合美國讀者的心理定位,這也為其增加了“真實效果”。麥科特輕松幽默地敘述自己的苦難童年,傳遞給讀者一種印象,他已經控制了苦難,戰勝了苦難,這一價值觀是美國人(甚至全球所有人)所推崇和贊賞的,無疑為他贏得了很多讀者。另外,麥科特將自傳的開端定位在離開美國,從此開始苦難歷程,然后將自傳的結尾定位在回到美國,暗示新生活重新開始,這種講述結構也頗符合當代很多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看法。此外,詹姆斯·B.米切爾還分析了兩個細節:(1)在自傳中,“小弗朗克”一直是站在母親一邊與酗酒的父親對抗,這一選擇符合當代美國人對 “俄狄浦斯三角”(oedipal triangle)的期待視野;(2)自傳對愛爾蘭宗教、教育和政治的嘲弄也與當代美國人對愛爾蘭的刻板印象相吻合。[11](P607-624)
我們通常要求自傳同時滿足兩類真實,即“歷史的真實”(historical truth)和“敘事的真實”(narrative truth),前者要求自傳內容服從于現實世界,后者要求自傳形式服從于敘事規約。[12](P62)從這個角度看,《安吉拉的灰燼》無疑實現了“敘事的真實”:它有一個穩定的敘事聲音,有一個始終如一的敘事主體,還有一個意義不斷疊加的敘事結構。然而,就“歷史的真實”而言,《安吉拉的灰燼》自出版以來,一直遭遇來自各方的質疑和批評。《安吉拉的灰燼》描寫的是愛爾蘭小鎮萊姆瑞克(Limerick),該鎮居民在書中找出了117處描寫錯誤或不準確的地方[13](P12)。他們稱麥科特是“無賴和騙子”,指責他為了追求文學地位,不惜把自己的母親描寫成妓女,并把她描寫成一個與自己表哥亂倫的窮女人。而按照小鎮居民的見證,麥科特一家絕沒有那么貧窮,他們家有一個不錯的后院,麥科特的母親身材發福,根本不像書中描寫的那樣。此外,麥科特在書中描寫自己14歲時與一位名叫特麗莎的女孩之間的戀愛關系,但實際上當麥科特14歲時,特麗莎身患結核,即將死去。一些居民甚至呼吁抵制麥科特的書和以此書為藍本改編的電影。
面對各種指責,麥科特這樣回應:“我不關心這些東西……我講述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寫的是我自己的境遇,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書中寫的是我的經歷和感受。”[13](P12)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解開被標記為“回憶錄”的《安吉拉的灰燼》的“真實性”倫理結呢?我們知道,無論采取什么語法時態,任何回憶錄、自傳都只能事后敘述,自傳主借此表達自己對生活的主觀看法和理解,這是自傳最重要的寫作目的之一。如此看來,麥科特用自傳來表達“主觀真實”(subjectivetruth)時,對過去的經歷做適當調整和挪用無可厚非。自傳無需、也不可能還原所有 “歷史真實”(historicaltruth)。筆者認為,判斷某個“歷史真實”的調整或挪用(甚至不準確)是否符合倫理的標準在于“歷史真實”和“主觀真實”的重要程度。比如,在《安吉拉的灰燼》中,弗朗克與特麗莎戀愛的細節是否真實(比如,到底是13歲還是14歲)就無關宏旨,因為這一事件本身只是用來表達貧窮給孩子帶來的負面影響:這里的“主觀真實”遠重要于“客觀真實”。但某些至關重要的“歷史真實”,如麥科特家是否真的那么貧窮,他父親是否真的酗酒,他的三個弟妹是否真的夭折,這些事實顯得異常重要,因為麥科特希望表達的主觀真實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這些歷史真實。如果這些事實失去真實性,麥科特就違反了自傳寫作的基本倫理,是在欺騙讀者換取名利。②
三、《吻》:真誠講述超越社會禁忌
懺悔自傳(confessional autobiography)是西方最早的傳記文學文類,可以說正是以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為代表的懺悔自傳開啟了傳記寫作的先河。懺悔自傳一般采用第一人稱敘述,不僅揭示個人的生活,更要揭示自己所犯的過錯。這類自傳的敘事結構通常由 “犯罪—煎熬—懺悔”三部曲組成:主人公犯下逆行,內心為之不安,然后通過懺悔獲得心理平衡。
按照對過失的處理方式,我們可將懺悔自傳分為三類:一類以中國正統文化為代表,回避罪惡,文過飾非;一類以法國懺悔敘事為代表,自哀自憐,玩世不恭;一類以俄羅斯懺悔敘事為代表,直面內心,復活精神。[14](P10-16)前兩類懺悔自傳或逃避,或缺乏真誠,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而以凱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1997年發表的《吻》(The Kiss)為代表的最后一類懺悔自傳才是我們關注的。詹姆斯·奧羅爾克認為,懺悔型自傳中存在兩個敘事,一個是傳主為自己辯護的 “(合法)敘事”(legitimating narrative),另一個是“我”(無意間)傷害他者的“影子敘事”(shadow narrative)。[15](P6)后者的存在使前者的倫理合法性受到質疑。合法敘事和影子敘事相輔相成,充分關注懺悔自傳的合法敘事和影子敘事有助于我們對其進行準確的倫理判斷。
凱瑟琳·哈里森的《吻》講述的是一段父女亂倫的經歷。凱瑟琳的父母17歲時結婚,但他們的婚姻只持續了6個月。凱瑟琳感覺自己被患有憂郁癥的母親拋棄了,開始時事事依著母親,試圖成為她想要的“乖孩子”,然后就開始叛逆。在她整個童年,她的牧師父親僅僅露過幾次面,似乎對她沒有任何興趣。然而當她20歲時,她父親又出現了,而這一次他的眼睛里似乎就只有她了。父親來訪結束后,她開車送他去機場。臨別之際,他吻她,是舌頭伸進嘴里的那種吻。她無力反抗,感覺所有的力量都沉睡了。在他的堅持下,他們的關系演變成了性關系。之后,她的生活一塌糊涂。她退學并與父親及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起,長達4年之久。后來,凱瑟琳的母親因患乳腺癌去世,凱瑟琳也停止了和他父親的不正當關系。在自傳的最后,凱瑟琳寫到“我理解了母親”,意味著“我”不再怨恨她對我的遺棄;“母親也理解了我”,意味著“我”希望母親原諒這段不倫之戀給她帶去的痛苦。從這個角度看,凱瑟琳的自傳完全符合懺悔自傳的“犯罪—煎熬—懺悔”常規結構。
《吻》出版后,在美國文學圈立刻引起了廣泛關注。《紐約時報》贊其為一部“了不起的回憶錄”,體現了驚人的“誠實、力量與美感”,批評者則多從倫理角度提出如下問題:(1)凱瑟琳為什么要和自己的父親保持4年之久的亂倫關系?(2)凱瑟琳為什么要將這段亂倫的主要責任歸于父親?(3)凱瑟琳為什么要講述并發表這樣“有辱世風”的回憶錄?不難看出,前一個問題涉及自傳講述的“合法敘事”,而后兩個問題則涉及自傳的“影子敘事”。
詹姆斯·費倫教授細讀了《吻》中“機場送別”這一關鍵場面后認為,凱瑟琳刻意將自己描寫成了受害者角色:父親在這件事上是主動的,而自己完全是被動的。但在后面的敘述中,凱瑟琳又將這個吻說成是“熱吻”,并渴望父親給自己那樣的吻。因此,費倫認為,凱瑟琳在這個關鍵場面中的敘述是壓制敘述 (restricted narration),也就是說,凱瑟琳在撒謊。哈里森把自己與父親的關系講述出來,其目的是獲得已經死去的母親的諒解,以求心理平衡,但由于她不能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內心,輕易地推卸責任,因此她的講述目的并沒有很好實現,而且對作為當事人的父親來說,也是不公平的。[16](P154)另一位批評家詹姆斯·沃克特的語氣更強硬。他認為,亂倫之始凱瑟琳20歲,已經成人。“引誘這等事,一個巴掌拍不響”,凱瑟琳一方面想通過書寫亂倫來吸引眼球,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擔責任,她是在“欺騙”讀者。[17](P32-36)
然而,在另外一些批評家看來,類似費倫和沃克特的批評之根源在于文化大語境,在這個語境中,無論出于何種目的,亂倫都是令人羞恥的社會禁忌。僅憑這個主流價值觀片面地解讀一部勇于暴露自己 “為人不齒”經歷的女性自傳,而不走進自傳的倫理現場,是有失公允的。比如,在小說家麗莎·艾瑟爾看來,凱瑟琳從小失去父親,在患憂郁癥的母親那里也得不到任何關愛,她一方面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注,一方面又因為得不到母親的關愛而憎恨她。當20歲的凱瑟琳再次遇到父親,在父親全神貫注盯著她看的眼睛里,她仿佛終于找到了存在,而這才是凱瑟琳迷戀父親的最重要原因。[18](P33-34)自傳評論家戴維·帕克持類似觀點,他甚至認為《吻》完全可以用《看》來做標題:要理解凱瑟琳的情感邏輯,就必須認識到“看”的重要性。正是由于這一“看”,才讓凱瑟琳無法自拔,從而進入到一段“為人不齒”的經歷。凱瑟琳極度渴望來自父母的關愛,于是將這充滿性欲的“看”誤認為是來自父母的“看”,并由此迷戀上了這種感覺,即使當他父親終于將“看”發展成為毒蝎般的“性”,她也無法、無力去擺脫。[19](P493-504)
筆者贊同艾瑟爾和帕克的觀點,并認為,凱瑟琳與父親的亂倫還有另一原因:由于多年得不到母親的關愛而生發出的恨,在與父親的亂倫關系中似乎讓她得到某種疏解。于是,在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她與父親的亂倫關系保持了4年之久,直到母親去世,她才從這種痛苦的經歷中走出。凱瑟琳在最后一定已經意識到,正是由于這樣一位母親的存在,她才得以了解自己潛意識中的渴望,以及這種渴望如何讓她走入一段不堪的經歷,而反過來,這段不堪經歷帶來的自我認識又一定會讓她理解到,不被父親“看”的母親無疑也經歷過如自己一般的痛苦掙扎,因此,當她以“我覺得不再渴望做一個不一樣的女兒、有一個不一樣的母親”結束自傳的時候,讀者應該明白,她與母親和自己都達成了和解,從此她對這個世界都不會有仇恨。從這個角度看,她的確并未將亂倫的責任全部推給父親,而是勇于坦白內心,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并在最后原諒了所有人,實現了精神成長。這無疑是一次充滿冒險但令人感動的講述,既可療治創傷,又能給讀者帶來啟迪。
四、《說謊:一部隱喻式回憶錄》:虛構的“真實”身份
借助自傳來表達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回答“我是誰”這一問題,是所有自傳文學的重要旨歸之一:我們通過回憶來組織我們的個人歷史,使用符合敘事規約的方式來講述,讓讀者形成關于我們身份的看法。無論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還是富蘭克林的《我的自傳》,莫不如此。然而,與這些經典自傳不同的是,受精神分析學、解構主義、后解構主義浸潤的當代自傳,對“記憶”、“敘述”、“身份”這些關鍵詞的理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代自傳理論認為,我們的記憶過程往往是一個“故事化”過程,會自動將那些不符合故事框架的材料刪除掉,因此我們對過去的記憶是高度簡化和理想化的,它本身就是一個虛構的烏托邦。[20](P1-8)同時,我們用來講述身份故事的媒介又是高度程式化和規約化的,往往迫使我們削足適履,不知不覺中就修改了自我故事,使之符合敘事連貫的要求。此外,福柯以降的自傳理論均強調身份的建構性和流動性,即,我們不能通過敘述來表達身份,而只能通過敘述來建構身份。羅倫·史蕾特的自傳《說謊:一部隱喻式回憶錄》(以下簡稱《說謊》)就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體現了當代身份自傳的這些思想。
《說謊》第一章只有一句“我夸大其詞”,開宗明義地挑戰讀者對自傳真實性的期待。接著,她又寫道:
我有癲癇癥,或者說,我感覺自己患有癲癇癥,我希望自己患有癲癇癥,這樣我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母親心里,我是那樣臟,那樣蠢,有時候又會那樣發光了。癲癇是一種令人陶醉的疾病,因為一些癲癇病患者是說謊者、大話王、天方夜譚野心勃勃故事的創造者……當我開口說話時,我所有話語都是五顏六色的,而我不知道這究竟是因為我的母親還是因為我的病,或者是像她一樣用虛構來混淆事實。但癲癇病也許并不存在,只是一個確切的隱喻來講述我必須講述的——我的故事。[21](P6)(筆者的譯文,下同。)
史蕾特借此表明了她敘述的那些所謂 “事實”的隱喻性質。這樣,讀者對她接下來描寫的任何事實都會產生懷疑,而史蕾特也從來不希望讀者會相信她的回憶:她不斷講述,然后又提醒我們,她所講的回憶都不準確,甚至是在撒謊。那么她到底是否患了癲癇病?對這一關鍵問題,史蕾特從來就沒有給出絕對的答案。在該書的“后記”部分,史蕾特這樣寫道:
在《說謊》一書中,有些地方是我不能說出真相,有些地方是不愿意說出真相……在了解和講述自我時,重要的不是歷史真實,因為隨著神經退化,歷史真實也會隨之退去;重要的是敘事真實……我更感興趣于創造,以抵達事情的核心,而不是實錄生活真實事件。[21](P238)
不難看出,史蕾特這里所謂的“敘事真實”(narrative truth)指的是生活表面下的“意義”。問題是,所有自傳都在追求真實下面的意義,但同時為讀者制造歷史真實的幻覺,而史蕾特卻是有意打破這個幻覺。她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們是否就此對她的自傳做出負面的倫理判斷呢?
筆者認為,史蕾特到底是否患有癲癇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重要。在她的另一本書《百憂解日記》(Prozac Diary)中,史蕾特曾說:“對我來說,疾病是我的身份賴以存在的一個解釋性模式。”[22](P12)換句話說,疾病可能并不存在,但史蕾特卻可以利用疾病來探索其身份。同樣,在一次采訪中,史蕾特在談及《說謊》時認為:“《說謊》的寫作給我提供了一種方法來重新理解當時我頗感迷惑的事情,同時創造了一種形式,來反思非虛構小說創作的可能性。”[23](P168)由此看來,《說謊》的反傳統手法一方面是史蕾特藝術探索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她借以建構身份的手段。在《說謊》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成長期女孩,試圖利用疾病來喚起自戀型母親對她的注意。更為重要的是,當這個女孩長大成人后,她已經擺脫不了這種假裝的或隱喻的癲癇癥身份,繼續利用癲癇癥病人的特征,寫出了一部充滿了各種幻覺、沖動和夸張的傳記。這似乎表明,通過多年的身份扮演,史蕾特已經接受了自己癲癇癥病人的身份,同時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其實并沒有癲癇癥。
這種介于“有”和“沒有”之間的“第三空間”或許正是她希望為自己建構的身份。在《說謊》“后記”中,史蕾特說她別無選擇,只能用一種“閃爍其詞的、嘲弄式的、頑童般的、令人惱火的”方式來書寫她“像一個問號”的人生,這也清楚地表明了她“第三空間”雙重身份的特征。這種身份對作為心理醫生的史蕾特來說并不陌生:她常常引導她的病人忘記舊身份,建構新身份。因此,當很多人為《說謊》到底是不是回憶錄而爭論時,史蕾特非常堅決地說:“這是我的回憶錄,拜托別爭了。請把它當作非虛構小說來讀。”[21](P239)因為該自傳建構出來的就是史蕾特的“后現代”真實身份狀態:非此非彼,是此是彼。
五、結語
所有自傳文學中都有“真實”和“虛構”的成分,自傳主在此兩極做出的選擇本質上是倫理選擇。但是,對美國當代自傳文學的倫理價值進行判斷時,讀者不能簡單以絕對“真實”為標準,必須回到具體語境。在《安吉拉的灰燼》這部苦難型自傳中,麥科特的敘述制造了高度的真實效果,雖然有些細節可能不符合“歷史真實”,但并不礙于其“主觀真實”的傳達,因此該作品獲得了藝術和市場的雙重成功;在《吻》這部懺悔型自傳中,凱瑟琳講述了一段父女不倫之戀,雖然引起了一些評論家的不滿,但凱瑟琳真誠地剖析自己的內心,并在自傳最后表達出與父母的和解態度,讀者對她的勇氣仍然會作出正面倫理評價;在《說謊:一部隱喻式回憶錄》這部身份型自傳中,史蕾特突破了“歷史真實”,利用癲癇作為隱喻來建構自己的真實身份,讀者同樣不會因為史蕾特的做法而否定這部自傳的倫理價值。
本文分析表明,和傳統自傳文學相比,當代美國自傳文學屢屢突破真實/虛構、主觀/客觀之間的界限,以傳達更加復雜的人生體驗。這既要求我們更加關注當代自傳文學的倫理問題,也要求我們調整倫理判斷標準,以更開放、更細致的方式去辨別這些作品中的倫理價值。
注釋:
①Albert E.Stone 認為,在美國幾乎所有當代自傳文本中均使用了類似的“文學技巧”,seeAlbertE.Stone,“Modern American Autobiography:Texts and Transactions”,in Paul John Eakin ed.,American Autobiography:Retrospect and Prospect,Lond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104.GunnthorunnGudmundsdottir則考察了美國后現代自傳中自傳與虛構在記憶、敘述、性別等方面相互作用的方式,see Gunnthorunn Gudmundsdottir,Borderlines:Autobiography and Fiction in Postmodern Life Writing,New York:Rodopi,2003。
②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92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瑞格博塔·曼秋(Rigoberta Manchu)的自傳《我,瑞格博塔·曼秋的證言》。在該自傳中,曼秋生動地描寫了她父母及哥哥在危地馬拉糟糕的種族壓迫下失去生命。筆者認為,從倫理上講,曼秋這里的“主觀真實”遠比細節的“歷史真實”更重要,我們不能因為這些細節中可能存在的虛構成分而整體否定這部自傳的倫理價值。
[1]RoyPascal.DesignandTruthinAutobiograph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2]Mark Freeman.Rewriting the Self:History,Memory,Narra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3]Laura Marcus.Auto/Biographical Discourses:Theory,Criticism,Practice.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
[4](法)勒熱訥.自傳契約[M].楊國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
[5]Dorrit Cohen.Signposts of Fictionality: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Poetics Today 1999,(4).
[6]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7]Leigh Gilmore.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Trauma and Testim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
[8]Paul Eakin.The Ethics of Life Writing.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9]王成軍.事實正義論:自傳(傳記)文學的敘事倫理[J].外國文學研究,2005,(3).
[10]Jerome Bruner.The Autobiographical Process.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Robert Folkenflik,ed.Stanford:Stanford UP,1993.
[11]James B.Mitchelle.But Enough About Me:Why We Read Other People's Lives.New York:Columbia UP,2002.
[12]ArthurW.Frank.TheWoundedStoryteller:Body,IllnessandEthics.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
[13]Kevin Cullen.Memoir Lashed,and Loved:Angela′s AshesAuthorFindsFoes,FriendsinLimerick.LimerickGlobe,1997,(October29):12.
[14]李建軍.西方現代懺悔倫理與精神復活:論懺悔敘事的幾種模式[J].小說評論,2006,(6).
[15]James O’Rourke.Sex,Lies,and Autobiography:The Ethics of Confession.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6.
[16]James Phelan.Living to Tell about It: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7]James Wolcott.Dating Your Dad.The New Republic,1997,(31 Mar).
[18]Lisa Alther.Blaming the Victim.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1997(14 July).
[19]David Parker.The Self in Moral Space:Life Narrative and the Good.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20]楊正潤.傳記的界限:史學、文學與心理學的考察[J].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11).
[21]Lauren Slater.Lying:A Metaphorical Memoir.New York:Penguin Books,2001.
[22]Lauren Slater.Prozac Diary.New York:Penguin Books,1999.
[23]Alys Culhane.Interview with Lauren Slater.Fourth Genre: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of/on Creative Nonfiction,Robert L.Root,ed.London:Longman,2011.
【責任編輯:倪愛珍】
I106
A
1004-518X(2015)09-02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