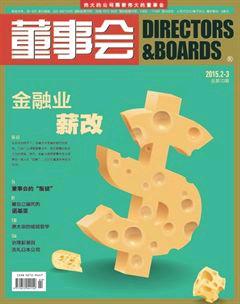王茁PK家化:沒有贏家的紛爭
張曜

企業經營中,總經理等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董事會之間難免出現矛盾、決裂,問題在于,董事會解聘高管是否需要合適妥當的理由,法律該否介入?解聘高管后如何處理與其的經濟關系?高管維權該如何理解、用好《公司法》與《勞動法》的相關規定?王茁被解職引發糾紛可謂提供了一個極具警示意義的案例。
解聘風波
糾紛再起。
2014年12月,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600315)收到證監會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因上海家化對于與滬江日化構成的關聯方以及關聯交易情況均未予以披露,證監會對上海家化、時任董事長葛文耀、時任總經理王茁等給予警告、罰款。上海家化代理律師將上述處罰通知作為證據提供給法庭,讓王茁與上海家化勞動糾紛案更增不確定性。
此前的2014年3月,上海家化的審計師普華永道就公司內部控制事宜出具了《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認為由于公司的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影響了公司控制目標的實現。該報告的否定意見直接導致上海家化的名譽和業績遭受重大損害。5月,上海家化董事會解除王茁總經理的職務,稱“公司總經理作為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及執行事宜的主要責任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故決定解除王茁先生公司總經理的職務并提請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解除王茁先生的公司董事職務”。2014年6月,上海家化股東大會高票通過了解除王茁董事職務的議案。
因不滿董事會的解聘決定,王茁向上海市虹口區勞動仲裁委員會提請勞動仲裁。當年8月7日,仲裁庭作出裁決,支持王茁要求上海家化恢復勞動關系的請求并裁決上海家化支付王茁工資43355.17元。因不服該裁決,上海家化向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上訴,此案至2015年1月初仍未宣判。
法律尷尬
2006年實施的新公司法刪除了原公司法股東會不得無故解除董事職務的規定。即按現行公司法,股東會解除董事職務無需理由。那么,董事會解除王茁總經理職務,法律應該如何處理?事實上,董事會作出罷免公司高管的決議是否有效,應遵循公司自治的原則,法律不宜輕易介入。
現代公司的委托代理關系基于充分的信賴基礎。一旦委托方認為其代理人不再適合繼續任職,則意味著信賴基礎喪失,此時可以通過解除委托代理合同隨時取消對代理人的授權,且這種撤銷行為的作出無須任何理由,股東會解除董事職務、董事會解除高管職務均如此。《公司法》規定了公司經理的職位設立,由董事會決定聘任或解聘。對于2014年5月被解除總經理,王茁一直不認可董事會的決定。上海家化董事長謝文堅則表示,“即使董事會沒有這個理由,也可以讓他下課,我們就認為你作為總經理,你的管理各方面都不合格。這是董事會的權力,董事會沒有任何理由也可以讓你下課,這是公司法賦予董事會的權力”、“本來一個企業管理層的變化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但是現在很遺憾。在中國,尤其在家化這個案子當中,很多就變成了個人的恩怨”。
從資本市場的外部制約和法院介入的局限性來看,董事會罷免高管的行為也應當得到充分尊重。
首先,公司相比于流動商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幾乎所有公司都致力于維護與其交易方的長期合作關系,這種重復交易的期待促使高管妥善地從事經營活動,因為如果公司的表現差強人意,不僅公司在日后的融資活動中將付出高昂的成本,被解雇的高管因為不良的公司經營口碑亦難以在勞動力市場謀求到等價的職位。這種資本市場的事后懲罰機制足以創造出適當的激勵,使高管們不敢怠慢于經營,法律責任規則的介入顯得畫蛇添足。
其次,高管必須頻繁地投資個人時間和資源以獲取特定公司的投資機會、人力資源、行為和組織結構的相關知識。這種因為在特定公司中浸潤日深而獲取的“專業知識”反過來使得管理層對該特定的公司而言更具價值,而這種特定的專業知識對其他公司而言或許毫無出彩之處。這就好比,即使最出色的乒乓球單打選手在參加雙打比賽之前,也要和其搭檔進行長時間的配合訓練,雖然同樣是乒乓球比賽,但這名球員在單打訓練中獲取的經驗和技術并不一定能在雙打比賽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對公司而言,撤換高管不僅意味著該價值不菲的特定知識在別的公司的價值將大為減損,也意味著公司必須為新上任的高管付出重復的培訓成本。因此,雙方都試圖避免產生這些成本。一旦公司作出撤換高管的決定,一定是基于全方面的利益考量,法律無須過問。
最后,法院介入存在很大的局限:缺乏對董事會會議查明并糾正錯誤的能力,而且成本高昂。如解職理由,上海家化的代理律師稱,王茁在擔任總經理期間涉嫌違法關聯交易、私設并私分小金庫,對公司內控管理上存在重大缺陷負有責任,故與其解除勞動關系于法有據;王茁的律師稱,擔任總經理期間執行的是董事會的決議,上海家化因內控原因被出具否定性的審計報告,不是其個人原因造成的,上海家化的內控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法院要查明真相無疑難度大、成本高。
維權路徑
需要指出的是,為何王茁可以申請勞動仲裁?對于公司管理人員,勞動法從總體上將其歸入了勞動者行列。如《勞動合同法》第24條特別規定了高級管理人員的競業禁止義務。同時,依照1994年勞動部《關于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的通知》,企業廠長、經理和有關經營管理人員,應根據《公司法》有關規定,與董事會簽訂勞動合同。因此,在高管與公司之間,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合同關系:即股東和高管之間的委托代理合同,以及董事會和高管之間的勞動合同。據此,衍生出了兩種不同的高管解聘模式,高管維權各有不同。
其一,董事會可以做出決議,解聘高管的管理職務(即解除股東與高管之間的委托代理合同),此時高管雖然不能繼續履行管理職權,但仍然可根據其與董事會之間的勞動合同主張繼續支付勞務報酬,且董事會不得以其不再履職為理由拒絕給付。2014年8月,仲裁庭的裁決支持王茁要求上海家化恢復勞動關系的請求并裁決上海家化支付相應工資。
其二,董事會在剝奪高管職權的同時終止與其簽訂的勞動合同,此時即意味著公司對高管的違約,高管可以依據《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主張違約賠償金或補償金,但不能要求繼續履職。以王茁為例,其不能要求繼續履職總經理。
當然,如果高管被證明存在《勞動法》第25條規定的過失或失職行為時,用人單位可以直接解除與高管的勞動關系,并且無須支付經濟補償,亦無須進行任何形式的事前通知,這體現了《勞動法》對于勞動者的敬業要求。
法律和市場對公司高管的監督和制約很重要,同時,高管在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時也應當注重自身的權益保護,而董事會在解聘高管職務時或許可以通過轉換職務但維持薪水的事前合同約定減少勞動爭議的發生。畢竟,司法和仲裁的介入意味著在勞動紛爭中沒有贏家:上海家化與王茁的勞動糾紛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