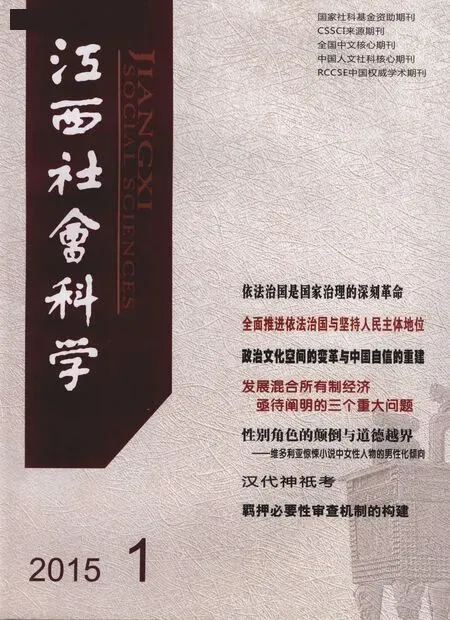在場(chǎng)與失聲:浪漫主義時(shí)期英國(guó)女性創(chuàng)作的雙重困境
■李 琳
18世紀(jì)末19世紀(jì)初,英國(guó)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指征是以“想象力”和“自然性”為特點(diǎn)的浪漫主義的蓬勃發(fā)展,其年限是指1780—1830年這段時(shí)間。提起燦若繁星的英國(guó)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代表作家,讀者馬上會(huì)聯(lián)想到六位著名詩(shī)人:布萊克、華茲華斯、科勒律治、雪萊、濟(jì)慈和拜倫。因?yàn)樗麄兘艹龅脑?shī)歌創(chuàng)作,浪漫主義文學(xué)也被定義為詩(shī)學(xué)創(chuàng)作時(shí)代,且是以男性作家為主的時(shí)代。值得注意的是,這個(gè)時(shí)期的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也開(kāi)始展露文壇,盡管這個(gè)時(shí)期中的女性作家無(wú)論從文學(xué)地位還是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上都無(wú)法與男性作家相提并論,但依然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女性作家在進(jìn)行創(chuàng)作,至少在數(shù)量上是可觀的。然而,更令人驚異的是,文壇明明有女性作家的存在,但卻沒(méi)有她們的聲音,女性作家似乎集體失聲了。于是,文壇便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詭譎現(xiàn)象,即女性作家身份的“在場(chǎng)”和話語(yǔ)的“失聲”,最終使得女性作家成了“在場(chǎng)的不在場(chǎng)”者。所謂“在場(chǎng)”是指:女性作家身份與女性作家作品在文壇上的出現(xiàn);所謂“不在場(chǎng)”是指:依據(jù)男權(quán)對(duì)女性身份的宰制與女性作品風(fēng)格的藐視。本文擬論述浪漫主義時(shí)期英國(guó)女性作品在“在場(chǎng)”與“失聲”之間的基本表現(xiàn),繼而略論女性作品走向真正“在場(chǎng)”而發(fā)聲的可能。
一、公眾視野中女性的在場(chǎng)與文學(xué)女性的失聲
從歷史角度分析,浪漫主義時(shí)期英國(guó)文學(xué)女性的“失聲”存在以下原因:18世紀(jì)的職業(yè)作家主要為男性,因?yàn)榕栽谶@一期間還沒(méi)有獨(dú)立的經(jīng)濟(jì)地位。當(dāng)時(shí)的已婚婦女沒(méi)有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即使是對(duì)她們自己的工資也沒(méi)所有權(quán);法律規(guī)定只有父母雙亡的單身女性和寡婦才具有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除了法律規(guī)定,社會(huì)習(xí)俗也把女性局限為妻子和母親的角色。想要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女性絕大多數(shù)非常富裕并且具有良好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因?yàn)樵谀莻€(gè)時(shí)代文學(xué)作品的出版和發(fā)行需要自己提供經(jīng)濟(jì)贊助。18世紀(jì)中期以后,男性作家一統(tǒng)天下的情況有所改觀。1750—1760年一批女性作家在倫敦成立了文學(xué)沙龍,她們學(xué)習(xí)希臘語(yǔ)和拉丁語(yǔ) (男性的專屬教育)以及其他歐洲國(guó)家語(yǔ)言,聚集在一起探討道德問(wèn)題、翻譯經(jīng)典名著、進(jìn)行文學(xué)批評(píng)——這些原本被視為男性知識(shí)分子才從事的工作。1795年,年僅27歲的Maria Edgeworth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shuō) Lettersfor literary Ladies。作品翻譯完成行將出版時(shí)卻受到了Maria父親摯友Day的阻撓。Day認(rèn)為瑪麗父親的這種教育培養(yǎng)方式不是正常培養(yǎng)模式,“文學(xué)女性”不適合做一個(gè)賢妻良母。瑪麗的這部小說(shuō)著力講述了兩位紳士之間的爭(zhēng)論,對(duì)于如何培養(yǎng)女孩雙方持有不同的觀點(diǎn),瑪麗也借作品表達(dá)了她本人的看法。這部作品中的“文學(xué)女性”除了指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女性,也包括那些閱讀文學(xué)作品的女性。[1](P8)即便是對(duì)文學(xué)女性持有異議的人也不得不承認(rèn)在18世紀(jì)末涌現(xiàn)了一定數(shù)量的女性作家和女性讀者。現(xiàn)代學(xué)者Janet Todd認(rèn)為:18世紀(jì)末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女性達(dá)到了三四百人。Stuart Curran也指出數(shù)百位女性詩(shī)人在浪漫主義文學(xué)時(shí)期出版了她們的詩(shī)作,并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女作家天才的優(yōu)美的文字使得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評(píng)論家為她們的作品而震驚、嘆服。這一時(shí)期著名的女詩(shī)人有Anna Seward、Charlotte Smith和 Anna Barbauld。[2](P62)
盡管有客觀證據(jù)表明,這一時(shí)期女性作家無(wú)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在文學(xué)影響力上都較之先前有所提高,但女作家和女讀者的社會(huì)地位從總體上來(lái)說(shuō)仍然不樂(lè)觀。Lonsdale認(rèn)為一個(gè)突出的證據(jù)就是在浪漫主義文學(xué)期間幾乎沒(méi)有女詩(shī)人的作品被收錄到當(dāng)時(shí)有影響力的詩(shī)歌選集中。Alexander Dyce則指出“女作家的作品被小心謹(jǐn)慎地排除在外了”[3](P103)。其次,這一時(shí)期的女作家和女讀者承受著男性作家和男性讀者所沒(méi)有的種種壓力和焦慮。世俗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有學(xué)識(shí)的女性不適合做一個(gè)賢妻良母。具有文學(xué)想象力的女性讀者往往會(huì)沉溺于小說(shuō)、詩(shī)歌所營(yíng)造的浪漫愛(ài)情,不能自拔,這將帶來(lái)危險(xiǎn)的后果。而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在內(nèi)容上往往局限于瑣碎的家庭生活,表達(dá)往往過(guò)于直白和膚淺,這將會(huì)降低大眾的品位。另外,這期間對(duì)女性的行為進(jìn)行教化的書(shū)籍十分流行,保守的倫理學(xué)家認(rèn)為對(duì)粗制濫造的女性文學(xué)作品沒(méi)有嚴(yán)格的審查制度將會(huì)導(dǎo)致文學(xué)的低俗化。面對(duì)種種歧視,即便是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非常成功的女作家Fanny Burney和Mary Shelley也非常清醒地意識(shí)到了來(lái)自外界的壓力,不約而同地在其作品的前言中表達(dá)了對(duì)作品面世后的焦慮和矛盾的心態(tài)。
18世紀(jì)末19世紀(jì)初,隨著工業(yè)革命的蓬勃發(fā)展,英國(guó)資本主義城市文明進(jìn)一步繁榮。社會(huì)中的富裕中產(chǎn)階級(jí)家庭中的女性有財(cái)力出版自己作品。這一時(shí)期同時(shí)也是英法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英國(guó)面臨著與拿破侖領(lǐng)導(dǎo)下的自詡為歐洲文化的領(lǐng)導(dǎo)者法國(guó)的激烈競(jìng)爭(zhēng),英國(guó)在軍事上和文化上都決心與法國(guó)一決高下。傳統(tǒng)而古板的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呼吁這個(gè)時(shí)代應(yīng)誕生“偉大的作品”,那種能夠展現(xiàn)廣闊的歷史背景,反映時(shí)代主旋律的驚世杰作。之所以做出這種呼吁,其中一個(gè)原因是女性文學(xué)創(chuàng)作隊(duì)伍的不斷壯大讓很多文學(xué)評(píng)論家驚懼不安。時(shí)任英國(guó)皇家學(xué)院主席的Henry Fuseli的觀點(diǎn)很有代表性:“女性文學(xué)反映家庭生活的文學(xué)作品占據(jù)了一席之地,這些作品逐漸改變大眾的文學(xué)審美品位,高雅藝術(shù)漸漸墮落為靡靡之音……這些作品缺乏雄心壯志、沒(méi)有開(kāi)拓精神,不能展現(xiàn)宏大的社會(huì)活動(dòng)。總之,乏善可陳。”[4](P47)讓Henry Fuseli尤其擔(dān)心的是,在一個(gè)女氣十足的時(shí)代中女性主導(dǎo)大眾審美品位的能力將會(huì)使社會(huì)中的男性具有陰柔氣質(zhì)。Henry Fuseli的觀點(diǎn)在現(xiàn)在來(lái)看未免極端,但是聯(lián)系其社會(huì)背景,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個(gè)時(shí)期中女性普遍被認(rèn)為應(yīng)該是屬于男性的私有財(cái)產(chǎn),家庭就是她們的唯一生活場(chǎng)所,通過(guò)其他途徑進(jìn)入公眾視野都被認(rèn)為是離經(jīng)叛道的行為。
其實(shí),除了男性文學(xué)評(píng)論家對(duì)女性文學(xué)作品措辭激烈外,女性評(píng)論家本身也并非完全認(rèn)同這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著名倫理學(xué)家Hannah More將女性比作藝術(shù)館中的肖像畫(huà),認(rèn)為女性除了容貌和身材可以外露,精神和思想不應(yīng)當(dāng)在大眾跟前展示。倘若精神和思想外露,就像藝術(shù)館中的肖像畫(huà),不會(huì)固定屬于一個(gè)家庭,而是會(huì)不斷轉(zhuǎn)讓。[4](P58)Fuseli和More對(duì)女性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存在驚懼和擔(dān)心,但本質(zhì)不同。Fuseli擔(dān)心的是女性的狹窄視野會(huì)左右大眾的審美能力,而More擔(dān)心的則是女性進(jìn)入公眾視野將會(huì)引起社會(huì)的亂倫。盡管本質(zhì)不同,但我們不難看出女性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面臨的重重阻力。文學(xué)女性是作為“第二性”而存在的,作為政治權(quán)威下的衍生物與弱者而存在,女性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以各種客體的形態(tài)“在場(chǎng)”,但作為具有女性意識(shí)的主體卻是“失聲”的。這種“在場(chǎng)”的話語(yǔ)建構(gòu)的是男權(quán)話語(yǔ)對(duì)女性的種種欲望和苛求,“女性意識(shí)”在女性的“在場(chǎng)”中“失聲”,“女性意識(shí)”在這種矛盾狀態(tài)中被屏蔽,女性話語(yǔ)的表達(dá)陷入一種困境。這種話語(yǔ)形態(tài)僅僅是一種男權(quán)文化所表達(dá)的消費(fèi)話語(yǔ)、規(guī)訓(xùn)話語(yǔ),女性話語(yǔ)則徹底陷入了一種失聲癥中。正如《為女權(quán)而辯護(hù)》的作者M(jìn)ary Wollstonecraft所指出的:“我從政治和公民權(quán)的角度把女性稱之為奴隸,她們間接地獲得了一些權(quán)利(表達(dá)思想的權(quán)利),但是她們努力去行使這些權(quán)利卻又被認(rèn)定為是不合常理的,并因而受到貶斥……”[5](P293)社會(huì)有了這些對(duì)女性身份的認(rèn)知與共識(shí),則女性作品失聲豈不是理有必至?!具體說(shuō)來(lái),就是重視剛健德行使得女性文學(xué)成為“在場(chǎng)”的“失聲”者,同時(shí),重視文學(xué)教化也使得女性文學(xué)成為“在場(chǎng)”的“失聲”者。
二、脆弱情感的在場(chǎng)與剛健德行的失聲
恣意張揚(yáng)的情感表達(dá)是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典型特征之一。情感話題隨著18世紀(jì)研究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哲學(xué)思想的產(chǎn)生而進(jìn)一步深化。到了18世紀(jì)的70年代,這個(gè)話題的研究達(dá)到了高潮,研究的重點(diǎn)在于對(duì)他人遭受的不幸而產(chǎn)生的同情和憐憫之心。繼而,關(guān)于情感的表述也就成為所有的浪漫主義文學(xué)作品的共性。女性文學(xué)之于情感表達(dá)尤為擅長(zhǎng),正因?yàn)槿绱耍晕膶W(xué)也由此備受貶斥,因?yàn)樵谠u(píng)論家看來(lái),女性文學(xué)就意味著“文以載道”傳統(tǒng)的消失。
1774年,Goethe的小說(shuō) The Sorrow of Young Werther出版,這部作品被認(rèn)為是英國(guó)浪漫主義文學(xué)的代表作之一,在18世紀(jì)末19世紀(jì)初具有廣泛的社會(huì)影響力。小說(shuō)作者用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了一個(gè)悲劇愛(ài)情故事:年輕男子Werther愛(ài)上了已與別人訂婚的女孩Lotte,陷入一場(chǎng)無(wú)望的愛(ài)中不能自拔。作者對(duì)于理想愛(ài)人Lotte的描寫(xiě)頗能代表這個(gè)時(shí)期男性對(duì)理想中的女性的評(píng)價(jià)。Lotte被描寫(xiě)成一個(gè)無(wú)微不至地照顧弟妹、充滿母性的年輕女子。而作品中男主人公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種種憂郁情緒有別于當(dāng)時(shí)的其他文學(xué)作品,因?yàn)樵?8世紀(jì)90年代之前,占主流文化的詩(shī)學(xué)都試圖擺脫帶有女性特質(zhì)的情感表達(dá)。一些作家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應(yīng)該摒棄情感表達(dá),而另外一些作家雖在自己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借用了情感表達(dá)的價(jià)值和傳統(tǒng)卻又試圖給它打上“陽(yáng)剛氣”的標(biāo)簽。Wordsworth的很多詩(shī)歌就包含著情感表達(dá)的內(nèi)容,譬如為在路邊遇到一位老人而感傷,或者聽(tīng)到了年輕女人的不幸遭遇而產(chǎn)生同情心。Wordsworth認(rèn)為這種情感的宣泄有別于女性的多愁善感,他進(jìn)而認(rèn)定自己詩(shī)作的讀者應(yīng)該是具有深刻的思考力和敏銳的觀察力的男性讀者,這樣的男性讀者都有悲天憫人的情懷,會(huì)主動(dòng)向那些遭受不幸的人提供幫助、進(jìn)行施舍。18世紀(jì)90年代,Blake在其詩(shī)作 The Book of Urizen中塑造了一位叫Pity的女性,從消極的方面記敘了世間第一位女性——夏娃的誕生,與John Milton的 Paradise Lost中原罪的產(chǎn)生情節(jié)正好吻合。在Blake看來(lái),女性是情感的動(dòng)物,情感即虛弱、無(wú)能的女性特質(zhì)。也就是說(shuō),女性文學(xué)豐富而脆弱的情感不能表達(dá)剛健而正大的社會(huì)內(nèi)容。關(guān)于情感宣泄與女性文學(xué)的關(guān)系,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女性們所持有的觀點(diǎn)也不盡相同。Helen Maria Williams和Wollstonecraft的觀點(diǎn)就很有代表性:Williams認(rèn)為情感表達(dá)是女性文學(xué)的特質(zhì);Wollstonecraft除了肯定Williams的觀點(diǎn)外,更深刻地指出,將情感表達(dá)與女性文學(xué)畫(huà)等號(hào)其實(shí)是當(dāng)時(shí)特定時(shí)期對(duì)女性的一種錯(cuò)誤看法。但是,Blake的觀點(diǎn)依然是主流,女性文學(xué)就意味著:脆弱情感的在場(chǎng)與剛健德行的失聲。[6](P43)
這種關(guān)于女性文學(xué)的價(jià)值評(píng)判也體現(xiàn)在基于文學(xué)作品的女性話語(yǔ)范疇的特征歸納上:女性的話語(yǔ)常常被認(rèn)為是饒舌的、散漫的、平庸乏味的、沖動(dòng)的,而男性話語(yǔ)則是果斷的、理性的、富于幽默的、簡(jiǎn)潔有力的。威廉斯曾在《功能詞》一書(shū)中列舉出155個(gè)詞,他認(rèn)為這些詞在形成人們對(duì)“文化經(jīng)驗(yàn)”的觀察和討論的方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考慮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語(yǔ)詞變化之后,威廉斯還列舉了數(shù)百個(gè)對(duì)詞義的形成變化及再形成過(guò)程具有最大影響力的人物,其中絕少女性,如Jane Austen、Lady Bradshaw等女性僅僅被列入“敏感性”一項(xiàng)中。
在主流價(jià)值觀念中,女性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團(tuán)隊(duì)中的“在場(chǎng)”并不意味著女性意識(shí)在文本敘事中擁有話語(yǔ)權(quán)。女性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表現(xiàn)形式呈現(xiàn)出一種類型化的趨勢(shì),這意味著男性采用一種隱蔽的方式拒絕女性意識(shí)的“在場(chǎng)”,女性文學(xué)作品雖然存在,但女性意識(shí)是游離的,實(shí)際上是一種“在場(chǎng)”的“失聲”。
三、教化文學(xué)讀本的在場(chǎng)與女性文學(xué)的失聲
18世紀(jì)末19世紀(jì)初,行為教化文學(xué)讀本的出版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程度。正是這些教化文學(xué)讀本的存在,使得女性文學(xué)失去了其在場(chǎng)性,集體失聲了。
所謂的行為教化讀本是指用刊印文學(xué)作品的方式教導(dǎo)女性如何做適應(yīng)社會(huì)的賢良淑女。18世紀(jì)前已有出版行為教化文學(xué)讀本的傳統(tǒng),但是到了18世紀(jì)80年代左右讀本的數(shù)量和流行程度達(dá)到了一個(gè)頂峰,這種現(xiàn)象正好與風(fēng)起云涌的法國(guó)革命密不可分。譬如法國(guó)革命引發(fā)了關(guān)于女性在英國(guó)社會(huì)中的權(quán)利的討論,行為教化讀本也就成為表達(dá)各方不同意見(jiàn)的一個(gè)載體。此類文學(xué)讀物所關(guān)注的一個(gè)核心問(wèn)題就是女性應(yīng)該選擇什么樣的書(shū)去閱讀。當(dāng)時(shí)最流行的是James Fordyce的 Sermonsto Young Women(1765)。在這部書(shū)中,作者措辭激烈地表明閱讀小說(shuō)將給女性帶來(lái)無(wú)窮的貽害,作者認(rèn)為小說(shuō)的故事情節(jié)與現(xiàn)實(shí)生活相距甚遠(yuǎn),小說(shuō)中對(duì)兩性關(guān)系的描述毫無(wú)節(jié)制,愛(ài)情小說(shuō)中的男女主人公要么都是些瘋子,要么就是些虛偽造作之人。James Fordyce認(rèn)為適合女性去閱讀的是歷史、地理和散文書(shū)籍;女性應(yīng)該按照社會(huì)規(guī)定的角色生活,有很多的職業(yè)都是不適合女性的,比如商業(yè)、政治、深?yuàn)W的哲學(xué)和科學(xué)研究都是男性才能涉足的領(lǐng)域。[7](P149)盡管James Fordyce的書(shū)在當(dāng)時(shí)非常流行,但從其偏激的觀點(diǎn)我們不難猜測(cè),即便是那些家中藏有他著作的女性也不一定會(huì)非常認(rèn)同書(shū)中的觀點(diǎn)。Jane Austen在小說(shuō) Prideand Prejudice中的一個(gè)故事情節(jié)很能反映當(dāng)時(shí)女性對(duì)這部書(shū)的態(tài)度:Collins先生為Bennett家的幾姊妹朗讀Fordyce的作品而受到了這幾個(gè)女孩子的揶揄。Jane Austen的小說(shuō)反映出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實(shí)際情況:對(duì)于女性而言,閱讀是一種公眾行為。關(guān)于書(shū)籍,個(gè)人并不具備選擇權(quán)。[2](P4)
通過(guò)教化文本傳播的男權(quán)文化漸漸內(nèi)化為一種大眾的社會(huì)期待,不但男性樂(lè)于接受這種性別權(quán)利關(guān)系,女性的認(rèn)知心理也被這種性別意識(shí)所左右,她們會(huì)自覺(jué)地認(rèn)同男性話語(yǔ)為其所設(shè)定的女性特質(zhì),從而將這一文化約束力內(nèi)化到個(gè)人內(nèi)部。男權(quán)社會(huì)中與社會(huì)預(yù)設(shè)角色相背離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都極易碰壁,這使女性從最初就輕而易舉地接受了既定的工具角色和從屬地位。對(duì)女性而言,其唯一的主體性在于如何把“女性”這一角色扮演好,從而得到男性鑒定者的肯定。不難發(fā)現(xiàn),教化文本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文化中發(fā)揮了多重功效:維護(hù)了既有的性別秩序,掩蓋了兩性的不平等關(guān)系,麻痹了女性的文化批判的能力,使得男性為中心的文化和社會(huì)統(tǒng)治更為堅(jiān)固和合理。從影響來(lái)看,這種合理性每增加一分,則對(duì)女性主義文學(xué)的殲滅就必定加深一步。
四、女性文學(xué):需要理解與寬容
曾有研究證明,盡管女性作家所處的地理位置、歷史時(shí)期和心理狀態(tài)各不相同,但她們使用的題材和意象卻很相似。雖然女作家們無(wú)法跳出父權(quán)制和男性創(chuàng)造的文類,但她們可以像Emily Dickinson所指出的那樣,“講真理,但用傾斜的方式來(lái)講”。[8](P7)18世紀(jì)的女性作家陸續(xù)在一些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進(jìn)行耕耘,譬如小說(shuō)、詩(shī)歌、新聞和兒童文學(xué)領(lǐng)域。一些描寫(xiě)溫馨家庭生活的小說(shuō)膾炙人口,通過(guò)塑造種種合乎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的淑女賢妻式的女性形象,文學(xué)女性試圖用這種看似合理的方式進(jìn)入公眾視野。到18世紀(jì)末,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已經(jīng)成為女性作家選擇最多的寫(xiě)作體裁,而她們?cè)谛≌f(shuō)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也遠(yuǎn)遠(yuǎn)超出她們?cè)谄渌膶W(xué)體裁上的創(chuàng)作。Wollstonecraft這位女權(quán)主義的代表在自己的小說(shuō)中極力擺脫女性小說(shuō)的特點(diǎn),即對(duì)于日常生活的細(xì)致入微的記錄、人物情感和心理活動(dòng)的深刻體驗(yàn)的特點(diǎn),因?yàn)樵谒磥?lái)女性主義不可避免地會(huì)受到精神習(xí)慣的束縛,女性與男性相比由于缺乏高層次的教育、生活圈子狹窄而缺少理性,缺少抽象思維、歸納總結(jié)的能力。[5](P92)Austen的看法則與Wollstonecraft相反,她認(rèn)為對(duì)周圍真實(shí)生活的觀察能力是女性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優(yōu)勢(shì),更堅(jiān)持小說(shuō)能夠反映思考的能力,流行小說(shuō)并不只是提供一時(shí)歡愉庸俗的消遣品,而格調(diào)輕松幽默、注重遣詞造句的女性小說(shuō)更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高級(jí)形式。[9](P21)
隨著女性主義批評(píng)的發(fā)展,女性主義者開(kāi)始對(duì)語(yǔ)言的用法及其權(quán)力產(chǎn)生懷疑。因?yàn)檎Z(yǔ)言是社會(huì)約定俗成的產(chǎn)物,性別的歧視早以浸入其中。現(xiàn)代語(yǔ)言學(xué)與心理分析都表明:從深層意義上觀察,不是人類操縱語(yǔ)言,而是語(yǔ)言操縱人類;“女性”是寫(xiě)作的結(jié)果,卻不是寫(xiě)作的源泉。面對(duì)帶有性別的語(yǔ)言,女性作家的明智選擇是接受有缺陷的語(yǔ)言,同時(shí)對(duì)語(yǔ)言進(jìn)行改造,但純粹的“女性話”與“女性文本”是難以存在的。因此,女性的作品應(yīng)該是兩種聲音的描述,即體現(xiàn)“緘默者”和“統(tǒng)治者”兩個(gè)方面:它既不包括在男性傳統(tǒng)之中,也不游離于統(tǒng)治傳統(tǒng)之外,而是存在于兩個(gè)傳統(tǒng)之間。同樣,女性作家在表述自己時(shí),不是對(duì)語(yǔ)言本身的拒絕,也不是回到女性專有的語(yǔ)言領(lǐng)域 (因?yàn)槟菢又荒鼙砻髋允軌浩取⑹軌阂值牡匚?,而是應(yīng)該使用一種活動(dòng)在語(yǔ)言之內(nèi)、跨越界限的獨(dú)特話語(yǔ),并嘗試建立一種將語(yǔ)言、主體、社會(huì)組織和權(quán)力聯(lián)合起來(lái)的獨(dú)特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模式。
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浪漫主義文學(xué)時(shí)期女性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迄今沒(méi)有統(tǒng)一的看法。但是顯而易見(jiàn)的是:漫長(zhǎng)的男權(quán)社會(huì)傳統(tǒng)文化建構(gòu)了女性“在場(chǎng)的消失”。浪漫主義時(shí)期英國(guó)文學(xué)女性所處的他者地位讓我們更好更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男權(quán)統(tǒng)治和男女二元對(duì)立的弊端。在全球化發(fā)展的今天,女性不應(yīng)該成為他者,只有男性和女性的和諧一致,彼此交融,相互包容,才能達(dá)到人類的共在和融洽境界,才能促進(jìn)人類整體的和諧與進(jìn)步。這需要對(duì)女性及其特質(zhì),乃至女性文學(xué)予以足夠的尊重、理解與包容,這樣,才能使女性文學(xué)真正“在場(chǎng)”,進(jìn)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使人類真切地聆聽(tīng)到人類另一半的傾訴與呼喚。
[1]Edgeworth, Letters for Literary Ladies,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 Co.,1993.
[2]Todd,J.,The Sign of Angellica:Women, Writing and Fiction,1660—1800,London:Virago,1989.
[3]Stephen B., Romantic Writings,Oxford:Routledge,1996.
[4]Kelly,G.,English Fiction of the Romantic Period 1788—1830,London:Longman,1989.
[5]Todd,Janet and Marilyn Butler,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9.
[6]Kelly,G.,Women, Writing and Revolution 1790—1827,Oxford:Clareden Press,1993.
[7]Turner,C.,Living by the Pen:Women Wri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Routledge,1992.
[8]張京媛.當(dāng)代女性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1.
[9]Austen, Northanger Abbey,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td.,1992.
- 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積極心理導(dǎo)向的心理健康教育——基于99 名大學(xué)生的實(shí)驗(yàn)研究
- 城市社區(qū)傳播系統(tǒng)與居民歸屬感的營(yíng)造——以江西南昌為例
- 中國(guó)式家庭農(nóng)場(chǎng)發(fā)展:戰(zhàn)略意圖、實(shí)際偏差與矯正路徑——對(duì)中部地區(qū)某縣的調(diào)查分析
- 旅游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對(duì)員工績(jī)效的影響——以關(guān)系質(zhì)量和工作投入為中介作用
- 高校學(xué)生輟學(xué)的現(xiàn)狀、影響因素及建議——基于江西普通高校的調(diào)查
- 江湖世界:武俠小說(shuō)中虛構(gòu)的可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