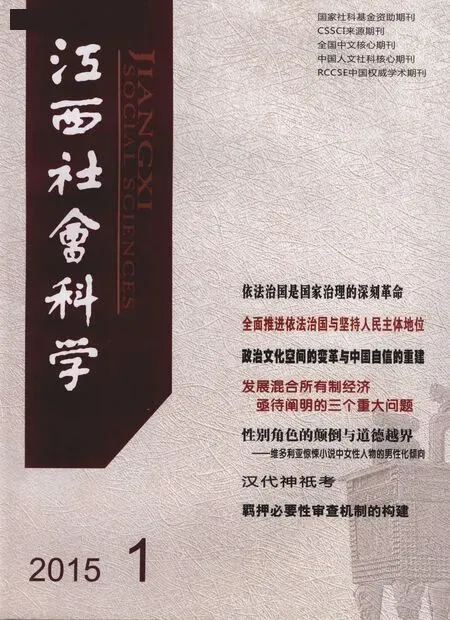依附與超越:中國古代審美的兩個維度
■陳 莉
審美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行為方式,人類睜開朦朧的雙眼,就開始了審美活動。審美活動是人超越于實用性、功利性之上,為了愉悅身心所進行的各種活動。審美活動作為主體的一種特殊的活動,在根本意義上體現了人對于精神價值的自覺追求。因此,審美文化是人類擺脫動物界,不斷建構自身,從而實現人的自由自覺的類本質的文化現象,是人類文化發展的一種高級形式。審美文化既包括人追尋美、創造美、鑒賞美的行為,也包括為了美飾和精神需求所創造的審美產物。屬于審美文化范疇的審美產物,既包括藝術品,也包括具有藝術性的實用器物。從史前彩陶到清代鼻煙壺,從在人跡罕至的懸崖上畫畫,到優雅地坐在書齋中品茗賞畫,中國審美文化走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縱觀中國審美文化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依附與超越是中國審美文化發展的兩個維度,也是中國古代藝術發展的兩個維度。本文力求對中國審美文化存在和發展的這兩個維度進行闡釋,以期從這一角度對中國古典美學有更深入地領悟。
一
審美和藝術具有超實用性和非功利性的屬性,但是在獨立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意識產生之前,審美卻與功利目的相伴而生,美依附在實用器物的邊緣而存在。可以說,審美以實用性和功用性為發源地。
中國古代審美文化首先是依附于宗教活動而產生和發展的。如史前的彩陶、玉器,雖不是獨立的藝術形式,但隱含著史前人類的審美觀念。甚至史前人類脖頸、手腕和腳腕上所戴的貝殼、石珠、牛骨串成的裝飾品也都顯示出人類朦朧的審美情趣。在這些具有審美價值的器物上,普遍籠罩著一層神秘的氣息。如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人面魚紋盆、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豬龍、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琮等。它們究竟訴說著怎樣的情懷,我們不能十分清楚地解讀,但從出土的地點來看,這些器物大多與神靈祭祀有著一定的關系。這意味著審美與宗教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此外,我國史前時期的巖畫也很能說明處于萌芽狀態的繪畫藝術與宗教神秘文化之間的關系。史前巖畫多被畫于形勢險峻、人跡罕至的深山之中,其內容也多與神靈祭拜及巫術觀念的表達有關。如陰山巖畫中的拜日圖,描繪了一個雙手相合舉過頭頂的人正在向一輪太陽虔誠地叩拜,表現了當時人祭拜太陽神的場景。廣西壯族自治區左江兩岸峭壁上的巖畫,人物造型體態相似,均為兩腳叉開、兩手上舉的蛙形舞蹈動作,似乎表現的是宗教儀式中人與自然神靈溝通的情景。這些巖畫雖不是為審美目的而創作的,但也隱含著當時人朦朧的審美情懷。商周時期,審美對宗教觀念的依附程度有增無減。青銅器上大量出現的饕餮形象巨口、獠牙、突目,充滿恐怖色彩,能夠在充滿宗教意識的人心靈中激起強烈的恐怖之感和敬畏之情,同時,這樣的形象也隱含著當時人對獰厲之美的認識。
中國早期審美文化中的這種神秘色彩,在文獻中多有反映。如《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塤篪鼗椎鐘,帝嚳乃令人,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1](P125)當帝嚳命人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之時,苓、篪、磬等素樸的樂器發出熱烈的樂音,鳳鳥、天翟紛紛飛來,翩翩起舞。《尚書·堯典》中也指出古樂具有使鳳凰來儀、鳥獸嗆嗆、神靈現身的作用。可見,在中國古代人的觀念中,音樂審美文化具有通神的作用。
藝術就是這樣依附于神靈祭拜和巫術活動而展現出它的雛形,在之后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藝術總也擺脫不了對宗教的依附關系。清虛的道教音樂、佛像的神秘微笑都是藝術的絕佳形式,也是審美依附于宗教而存在和發展的明證。
中國審美文化的依附性還表現為藝術對政治的依附關系。發展到周代,中國審美文化中的神秘色彩有所減弱,審美文化更多地被統治者所利用,成為傳達政治意識形態的載體和彰顯身份的標志。如周代的玉器雖然還是祭神的禮器,但周代貴族將佩戴玉器當成尊貴身份的象征。《禮記·曲禮下》記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2](P124)意思是在沒有喪葬禮儀的情況下,君子一定會佩戴著玉器。周代社會有著較為嚴格的等級制,佩玉的色彩也與貴族身份和等級相一致。天子佩白色的玉,用天青色的絲帶;諸侯佩山青色的玉,配朱紅色的絲帶;大夫佩水蒼色的玉,配黑色絲帶;士佩美麗的石頭,用赤黃色的絲帶。在這里,溫潤的玉再配以不同色彩的絲帶,既是貴族身份和等級的標志,同時也是周代貴族審美趣味的體現,只是周代貴族對玉的色彩和質地的審美感受與佩玉的等級制融為一體。在三門峽虢國國君墓地出土的七璜玉組佩,由一組七件白色玉璜與紅瑪瑙相間組成,是非常美麗的藝術品,也是審美與意識形態完美結合的典范形態。在政治與藝術的完美聯姻中頗值得一提的還有周代的音樂審美文化。周代音樂大都是廟堂之樂,用在祭祀和燕飲等各種儀式之中,是社會上層統治理念的載體。如周代貴族的燕飲中首先是瑟工在堂上演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三首樂曲,然后是笙工在堂下吹奏《南陔》《白華》《華黍》等三首樂曲,接著是堂上彈瑟歌唱與堂下笙樂吹奏交替進行,最后是堂上和堂下一起演奏。貴族的燕飲禮儀在這些舒緩、典雅的樂曲中展開,這是美的享受,但這些禮樂的最終目的是強化等級理念、傳達溫柔敦厚的處世之道。
西周末年,禮樂文化就開始衰微了,藝術與政治的依附關系也漸漸松弛,但從周代開始奠定的審美意識形態模式在之后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中并沒有完全中斷,作為統治階級總是力求在方方面面滲透權力意志。如歷朝歷代官服的色彩和形制都是統治者對審美觀念的權力化控制,官服上的補子,文官繡鳥,武官繡獸,各品的紋樣均有規定,充分體現了藝術對政治的依附關系。
中國藝術的依附性還突出表現在藝術對實用器物的依附關系方面。從繪畫的角度看,可以說最早是沒有獨立自足的繪畫觀念的,繪畫基本上都是依附于實用器物邊緣的紋飾。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就出土有大量具有審美價值的生活用品。如在一個橢圓形盤的盤沿上裝飾著連續的樹葉紋圖案;在一塊陶片上刻畫著五片肥大的植物葉子,呈現出蓬勃生長的態勢;在一個陶盆上還裝飾著成熟的稻谷紋樣。在仰韶陶器上廣泛出現了與當時人們生活關系密切的動植物形象,如鳥、蛙、魚、鹿、枝葉、花朵等。這些圖案雖然稚拙,但都能捕捉住對象的形態特征,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如陜西臨潼姜寨出土的一件魚蛙紋彩陶盆,兩只魚蛙正沿著盆壁蹣跚爬行,形象逼真可愛。陜西華縣出土的一件彩陶盆的腹部外側畫著一只鳥兒,展翅欲飛,頗為生動傳神,顯示了原始先民觀察和模仿生活的能力。從這些被美化的生活用品中,可以看到史前時代的審美主要依附于具有實用性的器物而存在,但同時也可以看出在實用器物上美已展示出它非實用性、非功利性的特性。一個陶盆沒有任何裝飾,但并不影響其使用價值。正如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所說的:“埃斯基摩人用石鹼石所做的燈,如果單單為了適合發光和發熱的目的,就不需要做得那么整齊和光滑。翡及安人的籃子如果編織得不那么整齊,也不見得會減低它的用途。”[3](P89)但是在使用價值之外,史前先民卻刻繪上如此富有審美氣息的裝飾圖案,這意味著他們已經能夠在功利性和目的性之外,營造出詩意的天空。
如果說史前時期審美與實用的結合還帶有偶然為之的性質,那么之后人類就開始有意地將藝術和實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藝術和審美在實用器物的邊緣處潛滋暗長,長久地發展下去。如宋代磁州窯燒造的白地黑花孩兒垂釣紋枕,枕面上繪有童子垂釣的繪畫,整個畫面簡潔明了,具有空靈的藝術意境,是實用性與藝術性完美的結合。
二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審美與宗教、政治、實用器物等有著密切的關系,可以說審美依附于宗教、政治和實用器物而存在,審美和藝術并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反過來看,宗教、政治、實用器物既是審美文化的緣起,同時也是審美文化發展的巨大束縛。因而,超越這些外在約束是審美和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幾千年的審美文化發展歷程其實就是一個審美和藝術努力超越宗教附庸地位、超越政治附庸地位、超越實用器物附屬地位的過程。
中國審美文化的超越精神較早集中于審美對宗教約束的超越方面。當審美文化超越了宗教的約束時,才會關注人的現世存在,才能帶給人愉悅和審美享受。面對廣袤的大地,面對日月輪回,人類感到自己是渺小的,感到無所適從,他們需要一個更為強大的無形力量的牽引。這時出現了神靈的觀念。有了神靈,人獲得了心靈的慰藉,人將自己的精神寄托在神靈那里。但是當神靈被統治者利用之后,神靈成為人存在的桎梏。這時,人們反而要努力擺脫不自由的狀態。人類擺脫宗教桎梏的過程漫長,有幾千年。比如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天神觀念逐漸弱化,這一時期的器物全面擺脫宗教的束縛,獲得了自由發展的空間。河北平山中山國王陵出土的十五連盞銅燈被塑造成樹枝的造型,樹干上一條螭龍正奮力向上攀爬,枝頭上有鳥兒正在歡快地歌唱,有小猴在樹枝間玩耍嬉戲。這盞銅燈不再有商周青銅的厚重感和壓抑感,而是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再如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宴樂射獵攻戰紋銅壺上描繪了比射、采桑、燕飲、作戰等場面,這些具有現世生活情趣的畫面,突出了人的形象,體現了擺脫宗教束縛后,人的價值的提升和審美風格的輕松化趨勢。還有戰國時期秦國、齊國的瓦當,其圖案多為太陽紋、樹紋、鹿紋等,紋飾輕松、靈動。春秋戰國時期的審美文化之所以顯得清新可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擺脫了商周以來濃厚的宗教氛圍和政治附庸地位。可以說,審美發展的動力就是力求擺脫當下的不自由狀態,擺脫外在的約束,尋求自由發展的空間。
中國審美文化的發展經過了多次身陷神靈桎梏以及努力擺脫神靈束縛的反復。如神靈觀念在商周時期較為濃厚,到春秋戰國時期有所弱化,審美文化趨于簡潔明了,這種美學風格一直延續到西漢前期。但到漢武帝時期,為了建立大一統的政權,為了給統治合法性找到先驗合法性,漢代統治階層再次關注神靈問題,他們將天神觀念與陰陽五行思想以及民間種種神秘觀念結合起來,使“不語怪力亂神”的原始儒家成為董仲舒以天神觀念立論根據的儒家,神化了統治的合法性和威懾力,因而漢代審美文化中有著濃厚的神秘色彩。但是當神秘文化成為無所不在的魔咒滲透在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時,這種思想本身也就走向了窮途末路,加之依賴神靈觀念來構建政治統治合法性的把戲在后世統治者那里表演得并不高明,因而在漢之后的審美文化中,富有神性色彩的審美文化現象基本都局限于官方祭祀典禮等很小的圈子里,或作為民間小傳統而存在,不能成為中國審美文化的主流。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審美文化的超越精神更為突出地表現在審美對政治的超越方面,而超越政治束縛的主體往往是歷朝歷代的文人士大夫。在中國大一統集權政治模式中,政治統治全面控制著文人,使他們基本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但中國審美和藝術精神很大程度上正來自于文人與官方控制之間的張力關系。對于中國文人士大夫而言,所謂的審美化生存,就是主動或被動擺脫外在政治功利誘惑獲得恬靜審美心態的努力。
中國審美文化的發展歷程也是一個文人與官方權力相抗爭贏得詩意化生存的歷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面臨著極端的政治斗爭,被拋到風口浪尖上,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們努力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于青山綠水中開始了玄虛的哲學思考,創造了竹林之下的風流。到了宋代,文人雖有較高的政治地位,但朝廷里黨派斗爭激烈,各種不同政見相互交鋒,政治風云瞬息萬變,文人士大夫動輒被彈劾、被貶官。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宋代文人大都能夠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努力營造遠離政治的生活環境和心境。如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迫離職后來到洛陽,購買了獨樂園。獨樂園的主體建筑是藏書五千卷的讀書堂,此外還有弄水軒、釣魚庵、種竹宅、采藥圃、澆花亭等。司馬光在這里主持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著作之余,還在這里種菜植竹,挖渠灌花,暫時遠離了政治紛擾。還有蘇舜欽被罷職后來到蘇州,購買了滄浪亭,在這里過著登舟容與、舉觴舒嘯的退隱生活。滄浪亭前竹后水,草木茂盛,在滄浪亭可以看到“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的景象。宋代文人的居住環境未必富麗堂皇,但遠離政治紛擾的深深庭院成為他們的精神歸宿。隔著窗欞,可見庭院中疏籬花徑,榴花明艷,這靜謐的氛圍中成就了宋代文人的詩意生存模式。元代文人無緣接近政治,他們處于流浪狀態,因而他們也獲得了較為自由的生存狀態和藝術創作狀態,但是由于這種狀態不是積極主動選擇的結果,因而元代藝術中總有一些幽怨的氣息。明代統治者推行文化專制政策,提倡程朱理學,以八股取士。在專制統治的影響下,明代文人紛紛遠離政治,追求隱逸、閑雅的園林生活,寫出具有閑淡氣息的小品文。清代文人歷經改朝換代的陣痛、科舉失意帶來的痛苦和文字獄造成的高壓,他們中有表現出抗爭精神的,有成為貳臣的,同樣還有李漁、袁枚等很多文人遠離政治,在市井民間延續著詩意化生活方式,尋找著生命的平衡點。
縱觀中國文人的詩意棲居之途,可以看到中國審美文化發展的歷程中充滿了政治斗爭的血雨腥風,也洋溢著超越于政治功利之外獲得有限審美空間的快樂。中國文人無論窮達都有著淡泊名利的努力,都力求與政治功名保持一定的距離。正是這種超越精神使中國古代文人能夠與政治功用保持一種張力狀態,擁有相對獨立的人格和審美的自由。為此,文人承受了很多痛苦和煎熬,但也許正因為超越精神和張力的存在,中國審美文化之花在政治高壓的夾縫中開得格外地璀璨。
至于中國審美文化的另一維度:審美與實用器物的關系,在漫長的審美文化發展歷程中,其矛盾和沖突并不尖銳。可以說,隨著獨立審美觀念的產生和發展,以及社會生活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藝術形式”與實用器物自然分離,成為一種較為純粹的藝術品。比如當史前人類使用的石斧不再作為實用性的工具時,就演化為一種儀仗器,進而成為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觀賞器物。漢代墓葬中大量存在的陶樓、宅院、豬圈、糧倉、陶井等建筑明器,與死者生前使用的實物有著相似性,反映了漢代莊園畜牧業的發展狀況,是漢代民間生活的立體畫卷,但這些明器僅僅具有模型的性質,尺寸比實用器物小得多,顯然不具有實用價值。進一步講,正是對實用價值的超越使這些建筑明器具有小巧精致的特點,成為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品。而宋元時期的文人畫和宋明清時期的瓷器,則是某些藝術形式擺脫實用性成為純粹意義上的觀賞品的最為典型的形態。如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定窯白釉刻花牡丹紋梅瓶,造型簡潔優美,色彩和紋飾恬淡寧靜、柔和,幾乎是一個不具有實用性的純粹觀賞性器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純粹藝術品的產生有賴于一種超越精神——超越宗教、政治、實用器物的束縛才能獲得獨立自足的審美價值。而超越功利,彰顯純粹鑒賞性,可能是美的最高境界。中國審美文化的發展歷程較為清晰地展現出中國古人將審美從不自由不自覺的狀態推向自由自覺、獨立自足狀態的過程。
三
人類總是力求超越功利和實用,詩意地棲居在這大地上。審美和藝術總是力求擺脫政治和宗教的附庸地位,成為不帶目的性的純粹美。“在自己的判斷中把這目的抽掉,才會是純粹的。”[4](P67)這也是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著力論述的觀點,但康德僅限于指出純粹美是美的最高境界,并沒有認識到,這種境界只能是人類審美文化發展的一個平衡點、一個制高點。一旦這個平衡點達到了,美的發展就會出現僵化狀態。可以說,當美完全擺脫任何外在的約束時,往往會走向極端,陷入失去生命活力的蒼白狀態。
從審美文化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審美和藝術極度自由的存在狀態,總是要導致審美和藝術的最后崩潰。這種狀況在器物藝術中得到充分體現。中國古人對物的關注,一是因為物常常是祭神的禮器,如青銅器、玉器等都與神靈祭祀有關,因而人們對物保持著一種敬畏意識;二是因為統治者對物的享受權力進行了等級劃分,器物的審美享受權力被納入等級體制之中,成為意識形態觀念的載體。此外,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對物質的享受歷來都抱有一種警惕心理。《尚書》中記載,西旅獻給周朝一種被稱為獒的大狗,太保召公奭擔心武王沉迷于對這種狗的玩賞之中,勸勉武王要奮勉慎德,不要“玩物喪志”。從此不玩物喪志就成為國人對于物的一種基本態度。但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人們就追求擺脫物質中的意識形態內容,追求僭越等級享有審美權力。物也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各種外在因素,成為較為單純的享樂對象。如出土于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蟠虺紋銅尊盤,運用失蠟法鑄造出極為復雜的三層鏤空紋飾,表現出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藝,但極端繁復和炫耀技術水平的尊盤既缺乏宗教的底蘊,也失去了實用價值,成為一個缺乏深層內涵的純粹觀賞器物。可見藝術和審美發展的動力是擺脫外在約束,但當藝術完全擺脫了宗教、政治和實用器物附屬地位時卻常常流于形式。
人的審美追求也常常因為完全超越了外在束縛而變得非常空洞。如前所述,文人在中國文化中總是處于不自由狀態,但當文人獲得了巨大的自由時,往往會走向空虛和無聊,文人藝術會失去了應有的厚度和深層內涵。如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得到發展,文人們擺脫了“致君堯舜”的理想,但也失掉了其他精神向度的引領,因而將審美的自由發展成墮落和放縱。明代后期社會生活淫逸,商人和市民追求享樂,士人則將飲食男女、聲色犬馬、賭博等一切滿足感官享受的娛樂作為人性解放的內容,使淫俗之風泛濫。袁宏道在致龔惟長的書信中毫不掩飾地說人生在世的五種快活是:極盡世間耳目聲色之美;賓客滿席,男女交舄;與妓妾數人,載歌泛舟;蕩盡家產,托缽妓院,恬不知恥。[5](P205)這些赤裸裸的世俗享樂宣言,是人性自由的表現,但也是人性墮落和放縱的體現。明代審美文化中充斥著淫穢的末世氣息。
在中國審美文化史上,利用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將審美和藝術推向制高點的帝王大有人在。但也正是在他們那里,審美由于失去必要的約束而變得空洞。如西蜀、南唐帝王頗具審美情懷,能超越功利打算之外追求詩意化的生活,但當他們將審美的特權發揮到極致時,也使審美和藝術走上了淫俗之途。西蜀文化的代表花間詞主要寫男歡女愛、離情別緒、春愁秋怨以及上層貴婦美人的裝飾容貌等,具有純審美的價值,但花間詞大多華艷柔媚、溫馨熱烈、濃艷綺麗,有著淫靡流蕩的傾向,內容上顯得空洞、蒼白。南唐上層統治者生活奢華,沒有社稷之憂,南唐的審美和藝術也表現出一定的自足性,但這種缺乏政治情懷和社會關懷的審美文化現象只能如玉樹后庭花般不能長久。明清時代的王侯享有至高的審美享樂權力,但正是這些可以沒有外在約束的帝王往往將審美推上窒息的境地。如明代的熹宗皇帝喜歡做木匠活,常親自制作漆器、硯床、梳匣等,用五彩裝飾,工巧妙麗,有時還讓太監帶到宮外賣錢。熹宗皇帝的“藝術創造”因為脫離實用而成為沒有價值的“玩意”,它們折射出帝王生活的枯燥和無聊。再如清代宮廷中那些看起來具有純審美價值的指甲套、鼻煙壺與有閑階層衣食無憂的生活聯系在一起,高貴無比,卻令人窒息,因為它們失去了任何外在的約束,在幾乎完全自由的狀態下,美麗但也空洞。
四
審美力求自由,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藝術的獨立自足。審美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功利目的和實用價值的藝術是異常美麗的,但只能是審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平衡的瞬間。當人類獲得了沒有外在約束的審美自由時,當藝術成為不受外在因素“牽絆”的純粹藝術時,審美活動和藝術要么走向空虛無聊,要么走向淫俗。因此,審美的最終目標是無功利、無目的,但審美卻應與功利之間保持一種抗爭的態勢,呈現出一種張力狀態。也許只有受到各種力量牽制的藝術才能呈現出一定的生機和活力,因為各種事物只有處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影響中才有動態的平衡和健康的發展。正如恩格斯在致約·布洛赫道的信中所闡明的:“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6](P697)恩格斯在這里說的是社會發展的力的平行四邊形原理,這個原理同樣適用于對于審美發展規律的認識。審美和藝術發展力求獨立,但審美和藝術只有在各種相互交織和牽制的力量之中才能獲得健康的發展。
回首中國審美文化發展的歷程就會發現,也許正是因為受到了來自宗教、政治、社會輿論等各個方面的限制,審美和藝術呈現出一種抗爭態勢,但這種抗爭態勢卻是最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狀態。如面對茹毛飲血的生存困境,史前人類竟然能夠創作出精美的彩陶。換句話說,史前人類的生活條件那樣艱苦,他們卻能夠超越于口腹之欲和實用目的,美化自己的生活用具,創造出如此美麗的藝術品。在彩陶這一藝術形式中凝結著史前人類對生存困境的超越,凝結著一種藝術追求與生活現實之間的張力,因而彩陶的美才如此讓我們驚異。再如中國歷史上那些有著藝術愛好的王侯將相,他們的審美追求大都受到一定的約束,但正因為受到一定的限制,對美的追求才彌足珍貴。《國語·周語下》記載,為了滿足個人的聽覺欲求,周景王打算鑄造一個合于“無射”音律的樂器,建成一套八枚以上,具有八度以上音域的編鐘。但周景王的這個不靠譜的鑄鐘設想遭到了大臣們的反對。大臣單穆公說:“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7](P108)單穆公的意思是先王制樂都有一定的規范,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這個規范還是應當繼續遵循的。此外,音樂如果超過了一定的限度,聽著刺耳,看著刺眼,就不是審美享受了。也許只有受到適度的約束,藝術和娛樂應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才能保持良好發展的態勢。相反失去約束和壓力的審美將是曇花一現。如宋代的徽宗皇帝幾乎沒有外在的功利計算,可以說是一個絕對詩意化的帝王,在他的影響下,宋代的青瓷呈現出淡雅、脫俗的藝術氣質,宋代畫院的小品畫尺幅之間顯出無限空靈的藝術意境,但當超脫的宋代帝王成為階下囚時,帶有濃郁憂傷氣質的宋代審美情調就變成了京華煙云,只能隨風而去。
中國古代文人一路走來都無法擺脫出仕和歸隱的矛盾和沖突,總是在矛盾和沖突中尋找平衡點,尋找詩意的棲居方式和表達方式。這種矛盾狀態使中國文人深陷痛苦之中。中國文人的藝術觀念也一直在“文以載道”與“為藝術而藝術”兩個極點之間徘徊。但正如“文章憎命達”的矛盾一樣,當文人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時,當文人完全超越了家國之憂時,文人以“妓鞋行酒”為樂,藝術境界卻非常狹窄。所以說只有處于一種抗爭態勢之下,中國文人才有深沉的思索,中國文人藝術才表現出特有的生命力。
一定程度的約束不是審美和藝術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審美和藝術得到健康、茁壯發展的有利條件。沒有任何約束,審美會失去張力變得蒼白。審美和藝術應與官方意志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與宗教處于若即若離的狀態。所以藝術是功利性與審美性相互交織的產物。富有生命活力的藝術境界當在純粹藝術與實用功利之間。正如叔本華所說,人生實如鐘擺,在痛苦與倦怠之間擺動。其實,這種“鐘擺理論”有更廣泛的適用范圍。可以說,審美永恒地在功利目的和絕對自由的審美狀態之間做鐘擺式的運動,審美總是在過程之中,人總是在尋求審美的平衡點,這才是審美得以發展和富有活力的狀態。平衡只能是一個瞬間,而且人類總是要為平衡付出巨大的代價。也許明白了審美發展的這種內在規律,我們才能坦然面對生命的不自由狀態,才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態去追尋純粹美,追求美的平衡點。然而審美最富有活力的狀態是“在途中”、在不平衡的狀態下,并不等于說,人類就應當放棄對審美自由和獨立的追求。一旦放棄對審美無功利性和獨立性的追求,審美同樣會失去發展的動力,同樣會僵化。審美應當在依附和自由兩個終點之間做鐘擺運動,超越精神是使審美的鐘擺運動的內在動力,沒有不斷地超越,沒有不斷地力求回歸審美最初的實用性出發點,審美的發展將是不充分的。從中國審美文化發展的歷程也可以看出,審美總是在發展到幾乎完全脫離實用功利的狀態時,又走上了回歸實用、回歸依附狀態的軌道。比如明代的小品文美到了極致,失去了對社會人生的關懷,到清代必然會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重倡藝術的社會關懷。但擺脫外在目的和約束又是審美和藝術得以發展的必由之路。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審美文化處于依附地位是藝術和審美不獨立的表現,但宗教、政治、實用性卻是藝術發展的源頭,也是藝術得以茁壯成長的沃土。藝術的發展就是要努力擺脫這些外在約束,但當藝術完全脫離社會、人生,藝術有可能變得蒼白和缺乏深度。第二,審美文化的發展永遠在途中,或者說在純審美與實用性兩個端點之間做鐘擺式的運動,這才是審美富有活力的存在狀態。藝術超越對其他因素的依附地位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可能相當漫長,但當藝術和審美達到了獨立的極端,藝術完全與生活、社會相脫離時,即藝術達到完滿自足狀態,這必然是藝術的下一步發展應當努力超越的一種狀態。依附于政治、宗教和實用器物而產生和發展,又要努力超越這些外在因素的束縛,這是我們從幾千年中國審美文化發展歷史中提煉出來的普遍規律。有了對這一內在規律的認識,我們就能夠深刻認識未來藝術發展的趨勢,更理性地引導藝術的發展,更理性地認識審美和藝術的存在狀態。
[2](清)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3](德)格羅塞.藝術的起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4](德)康德.判斷力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明)袁宏道.袁宏道集校箋[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徐元誥.國語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