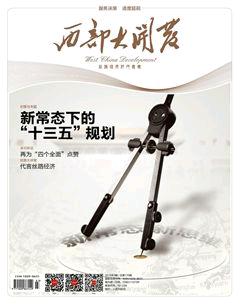天山南北經濟走廊
天山南北經濟走廊是漢代以來開辟的相互聯系但方向不同的貿易兩條北線主絲路,從天山北走廊可以西去哈薩克干草原和南俄草原,穿越漢代史書所記載的烏孫、奄蔡與阿聊蘭故地,是亞洲游牧民族通向歐洲的一望無際的草原之路,也是17世紀土爾扈特蒙古萬里長征回歸故國的道路。歸國的土爾扈特蒙古后代,一部在巴彥郭楞蒙古自治州,一部在居延海的額濟納旗。天山南經濟走廊由巴彥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庫爾勒、鐵門關西去庫車、喀什。或者經由帕米爾十二帕(山谷)眾多的山口與口岸與吉爾吉斯、塔吉克連接,或者經由瓦罕走廊走向阿富汗,這里是漢代古大夏、古月氏和古安息所在的方向和盛極一時的貴霜王朝的腹地。通過著名的紅其拉甫口岸走向中巴經濟走廊等印度河上中游地區,是古絲路大南道的最重要路線,也是歷史上中國與西亞和南亞諸國的文化與貿易交流最為密集的地區,是東方文化、希臘文化、伊斯蘭文化交會之地。佛教東傳和西方古代宗教東來也循著這條道路。
天山南北經濟走廊也是面向中亞、南亞和西亞的姊妹廊道,無疑是今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最重要的核心區域。天山南北經濟走廊也有跨越天山南北的“微絲路”,一條是伊犁、昭蘇至阿克蘇,一條是伊犁經由著名高山草原景區那拉提和巴音布魯克“天鵝湖”到庫車的天山之路。由此構成了天山南北經濟走廊的內部循環。天山北經濟走廊建設發展,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建設發展的啟動力首先來自新疆建設兵團,也來自當地各民族居民和支援新疆建設的內地項目和企業。建設進程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一是中央政府沿襲從漢代就開始的歷經2000年的屯墾戍邊傳統,成立新疆建設兵團,篳路藍縷以啟荒漠,一步一步地改變了新疆經濟發展的停滯狀態,使北疆地區較早脫離了原始的“轉場游牧”和小規模農業生產的單一經濟形態。1962年,在伊犁、博爾塔拉、塔城、阿勒泰、哈密地區建立長達2000公里的邊境團場發展帶,為日后的沿邊開放奠定了發展基礎。1966年底,新疆建設兵團團場達到158個,屯墾人口148.54萬。截至2013年,建設兵團擁有14個師176個團場,耕地面積1244.77千公頃,人口270.14萬,占全疆人口11.9%,其中包括37個少數民族聚居團場的少數民族人口37.54萬人。這37個少數民族聚居團場發展得更迅速,2012年總產值實現111億元。建設兵團不僅在戈壁荒漠開荒造田,也初步建設起涵蓋食品加工、輕工紡織、鋼鐵、煤炭、建材、電力、機械、化工等基礎工業體系。二是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烏魯木齊從一座邊城變成了包括中亞五國在內所有城市中規模最大市場最活躍的國際城市。新疆包括天山南北經濟走廊的發展水平進一步提升,綠洲經濟模式的城鎮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除了哈密、吐魯番、伊犁、喀什、和田、庫車、庫爾勒等傳統節點城市和克拉瑪依、奎屯等新興工業城市持續發展,更多的綠洲新城鎮出現了,與此同時,建設兵團依照“師市合一、團鎮合一”的規劃思路,前后建立阿拉爾、鐵門關、石河子、雙河、北屯、五家渠、圖木舒克等七個市和五個建制鎮。石河子市在2000年被聯合國評為人類居住環境改善良好范例城市。兵團的城鎮化建設是新疆新型城鎮化的縮影。三是推動天山北經濟走廊發生脫胎換骨的根本性變化的西部大開發階段。在這個階段里,鐵路建設、公路建設、天然氣管道建設、電網建設、生態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聯動,為天山南北經濟走廊建設的現代化作出了居功至偉的貢獻,也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合作建設拉開了大幕。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際物流、能源供給,國際旅游的發展大格局形成,生態環境也在改善。尤其是阿拉山口與霍爾果斯的國際鐵路、公路口岸的前后開通,使它們成為新的絲路貿易重鎮。在西部大開發的推動下,天山南經濟走廊也在加快發展,那里有西部的第一大淡水湖博斯騰湖,有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相對豐沛的水資源,有古老的龜茲文化和喀什的大巴扎,在南疆鐵路系統加快完善之后,將會迎來絲路西去的又一條超級經濟走廊。天山南北經濟發展帶是“微絲路”,也是主絲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經濟戰略核心區域,內涵能量無限。
當然,在關注天山南北經濟走廊的同時,誰也不會忘卻古絲路的大南道。在漢代,首先開通的是古絲路的大南道,這條大南道在隋唐時代依然暢行無阻,甚至在草原絲綢之路大行其道的元代,同樣是重要的國際貿易通道。馬可·波羅與其父叔三人從威尼斯到元上都與元大都,走的就是大南道。他們從地中海西岸登陸,沿波斯灣南下到霍爾木茲海峽再次登陸,經過古安息國所在的呼羅珊地區,到達今阿富汗的巴達克商也即臨近瓦罕走廊的地區,休整一時,翻越了空氣稀薄的“大勃律”、“小勃律”,也即中國史料中的另一稱呼“大頭疼”、“小頭疼”地區,到達于闐。然后穿越羅布沙漠和哈密,進入古沙洲敦煌和甘州張掖,經由今天蘭州北部的景泰地區,沿著騰格里沙漠的東緣北去,他們跨越了烏蘭布和沙漠,從陰山北麓一路東行到達上都(內蒙古藍旗),覲見忽必烈汗之后,再到大都北京。馬可·波羅的旅程線是精確無誤的,這本身也說明《馬可·波羅游記》的真實性。也許,那時的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生態環境要比后來好,但即使目前人們看到的是尼雅遺址一類的滿目滄桑,并不意味著南大道已經消失。沙漠化并非不可逆,關鍵在于持之以恒地去抗爭去改變。漢武時期張騫前后兩次出使西域,南道和北道都走過,但回程多選大南道,選擇路線主要參考因素是規避匈奴游騎,但他終究還是沒有躲過去,兩次被擄后逃脫,輾轉回到長安。500多年后的法顯、玄奘走的是同一條大南道,說明生態環境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法顯記錄了路途中的白骨,這其實在干旱的沙漠中是尋常可見的,如果你到過已經成為游人如織的居延海黑城景點,在殘存的城墻下,同樣可以發現500多年前戰死者的許多白骨,你可以發幽古之思情,但不會有恐怖之感,何況在地處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緣的大南道上。大南道的東入口,就是著名的樓蘭古國遺址,一路向西就是若羌和且末、尼雅(今民豐)、于闐(和田)等古代絲路重鎮,古樓蘭就是南北道的分路點。對樓蘭這條大南道絲路,若羌人并沒有釋懷,他們雖然并非樓蘭的后人,但樓蘭是他們的地理文化遺產,他們要打造樓蘭文化、若羌紅棗、黃色和田玉三張名片,還想為自己的產品爭取保稅政策,再現古樓蘭的風貌。這里有515、218兩條國道,支線機場也正在修建。換個視角看若羌,離敦煌與青海柴達木盆地也就是600多公里距離,在青藏鐵路和蘭西新高鐵開通的時代,這點距離算不了什么。樓蘭不遙遠,若羌不遙遠,和田同樣不遙遠。若羌這個古色古香的地名,會讓你聯想起大月氏西遷,小月氏余部留居“南山”的歷史記載,小月氏余部與古羌人融合,若羌而非羌,這是若羌的來歷。絕世獨立的樓蘭古跡、米蘭古城、小河墓地遺址、野駱駝保護區和阿爾金山“動植物王國”,至少構成一條旅游經濟長廊的全部要素。有規劃從成都向西修建格爾木到若羌和庫爾勒的鐵路,絲路南大道的再次通暢,同樣不會令人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