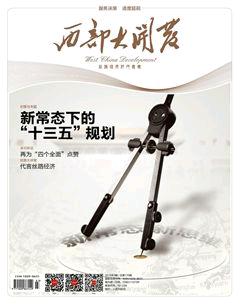黃河“金三角”與甘南隴南道

在西部的東半部地區,還有沿黃河北上南下東西相望的兩條地理交通走廊,這是兩個著名的“黃河曲”。一個上文已經講到,是劉家峽里已被確認的絲路故道,一個是隋唐前后繁榮一時的北上三晉的蒲州風陵渡,由風陵渡東去,便是三門峽,這里都有鐵路連通。從行政區位上看,它們都是“雞鳴三省”或兩省的地方,但位勢重要,市場流通發達,現在都成為經濟發展的“金三角”。其實,在黃河“金三角”的市場景深里,往往有著來自絲路走向絲路的大背景。風陵渡交通孔道的延長線就是中亞綠洲絲綢之路與北方草原絲綢之路的一條南北連接線。風陵渡與三門峽一渡一峽連三省,河西有司馬遷韓城故里、西岳華山,河東有眾多的春秋戰國遺存甚至是考古學家正在苦苦追尋的夏王朝的故地。水聲驚天的壺口瀑布則是他們共同的旅游資源。現在,陜、晉、豫三省的四個城市即渭南、臨汾、運城、三門峽和韓城打破了行政分割,聯合建立“黃河金三角經濟區”,主打特色農業全加工產業鏈、國內黃河旅游鏈和黃河金三角物流產業鏈。這個“金三角”歷史含金量高,現代經濟發展的含金量也高。隋唐以前,這里就是關中與華北、中原的交通要津,甚至是華夏先民遷徙開拓的主要通道,華夏文明形成的舞臺。就連那部不可考《穆天子傳》中穆天子巡游西域,都要經由此道北上輾轉入西,同樣難以考定的黃帝如何縱橫在后來的兩條絲路之間,從晉陜到冀豫,相關記載雖可姑妄聽之,但不可姑妄棄之,那至少披露史前年代人們的地理認知和“黃河金三角”的交通價值。
這個“黃河金三角經濟區”的內陸物流港建設項目建成,貨運交易量可達2000萬噸,年交易額500億元。“黃河金三角”是蘋果種植區,種植面積和產量分別占全國的20%與30%,每年果汁加工能力90萬噸,這個“黃河金三角”是經濟產業跨省融合沿絲路經濟發展的范例。無獨有偶,在黃河大河曲中與此適成對角線的內蒙古烏海市、鄂爾多斯市與阿拉善盟,也聯合建立了一個“黃河金三角經濟區”,這個“金三角”的前生是“煤三角”,含碳量高,持續發展的含金量并不高。現在以高新技術產業和農畜加工為主產業,對重化工產業實行低碳化改造,沿黃建設了22個產業集中區,“煤三角”開始向“金三角”轉變。但這個“金三角”應當是“金四角”,與烏海市、鄂爾多斯市與阿拉善盟隔河相望的寧夏石嘴山市也是一座大型的煤城,同處一個產業經濟帶上,跨區域經濟融合與聯合,既要打破縣與縣、市與市的行政界限,也要打破省區的行政界限。特別是跨省區的三角區域,往往也是“微絲路”的關節區域,道路通,物流通,市場通,才能打破產業的同質競爭。
九曲黃河中最大的一曲,一個更大的“黃河金三角”,其實是包括陜甘寧老區和鄂爾多斯草原在內的“大河套”地區。在這個“大河套”地區,潛在的跨省區并同絲路干線密切相關的“金三角”至少還有三個,一個是晉陜內蒙古交界的河曲地區,一個是寧陜蒙晉,一個是延安、慶陽、平涼或寧夏固原一線。第一個“三角”擁有包括榆林市和鄂爾多斯、包頭市、呼和浩特市、集寧市、大同市等眾多地區核心城市,是草原絲路經濟帶的重要支撐區域,需要建立緊密型的經濟合作關系。第二個“金三角”是由銀青高速公路和新開通的銀川、延安到太原的鐵路連接,是中亞綠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輻射區、支撐區 。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這條橫向鐵路上,東來的列車可以轉由銀川、中衛、武威的沙漠鐵路直達河西走廊,與“第二座大陸橋” 緊密相關,也可以視之為草原絲路的必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寧夏黃河東岸的靈武與陜北“三邊”、橫山一線同樣是能源富集區,低硫、低灰煤探明儲量近千億噸,與神府煤田堪稱“大河套”雙璧,石油天然氣蘊藏豐富,湖鹽和巖鹽儲量大,擁有風速每秒52米的風能和太陽能光熱發電的巨大資源,是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同步發展的不可多得的獨立單元,而不僅僅是一個能源接續地區。第三個“金三角”則是陜北與甘肅隴東、平涼、寧夏固原與蘭州之間的經濟協作的地緣聯系。就陜西彬縣、長武與甘肅平涼地區來講,歷史上就是秦隴交通要沖,絲路必經之地,優質化石能源資源豐富,是“關天經濟走廊”之外的另一條重要經濟走廊。特別是平涼,綰三省、連六地,是蘭州以東絲路古道西進甘新北上寧蒙的重鎮,目前有寶中鐵路、天平鐵路、西平鐵路和銀武高速相連,是新絲路建設中的重要樞紐。從隴東慶陽和寧夏的固原市來看,同樣是能源與農業資源富集地區。慶陽市是《禹貢》所記載的雍州之地,歷史悠久。在擁有“天下第一塬”之稱的“董志塬”的周邊還有環縣、華池等,是長慶油田的主產區和接續區。使人感到遺憾的是,延安與慶陽、固原之間的省際道路尚未進一步提速,這是一個大的制約因素。延安南部的洛川、富縣原本就是陜北的“五路咽喉”,境內有洛河與葫蘆河水系,道路連通是延安連接并融入“大陜甘寧金三角”進而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也是延安老區走上新絲路建設的重要思路。
在絲路經濟的大棋局里,黃河“大河套”和九曲黃河的多個“金三角”,并非是陪襯與配角,“大河套”里不僅僅是黃土高坡,是一塊西連中亞綠洲絲路北去草原絲路的重要的經濟戰略高地。在人們為長江黃金水道規劃興奮不已的時候,也應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九曲黃河。
相比之下,甘南隴南走廊更有其特殊的經濟戰略意義。這里是中國西北與西南的分界線,也是南方與北方的經濟劃線,白龍江就是經濟界河,美麗的九寨溝是他們的公共花園。甘南、隴南走廊歷史上就是中國西北向西南的民族移民大通道,與中原向東南方向的客家移民通道齊名,甚至影響更遠更大,超過了國界。甘南隴南應當是西南絲路的北源。為什么四川話屬于中國北方方言區,為什么在古代東越部落部族曲折迂回向西南遷徙的同時,有許多羌、氐部落和部族來到西南,沿著橫斷山脈一路走向了高黎貢山?為什么在甘南隴南與四川省交界處至今還有“白馬羌”、“黨項羌”以及已經在族屬認定消失了的氐族的后裔?在羌族集聚的汶川、北川,有著關于大禹出生地的傳說,在離黃河大夏河、洮河交匯的“三河口”地區有大禹活動的傳說,就連那令人不知其源的“三星堆”文化,似乎也需要從更早的絲路交通里尋找新的答案。
漢張騫在西域千里之外發現了西南的“蜀布邛杖”,判斷中國西南還有一條商路,那些商品毫無疑問是四川制造。遠在長安的人們知道“蜀布邛杖”,并據以推測西南商道的存在,可見甘南隴南早已是連接北方商業中心與南方四川商業中心的重要經濟通道。在隴南與甘南交界處的素有旱碼頭之稱的岷縣,自古就是“西控青海,南通巴蜀,東去三秦”的咽喉之地,秦漢以前,蘭州地區還是西域之一部。岷縣離蘭州不遠,最早的秦長城就在臨洮岷縣一線。離岷縣北邊幾十公里的漳縣與武山就坐落在中亞綠洲絲綢之路的大路口上。這條西去的大路,東接天水地區,西到渭源、臨洮,一直通向劉家峽水庫邊的永靖,這里不僅是黃河上游的中國第一條“梯級水電走廊”,又被稱為“黃河三峽”。“黃河三峽”包括了傳說中大禹導河積石在內的眾多丹霞地貌峽谷,被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列入“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世界遺產名錄。在炳靈寺石窟附近,至今還有西秦符堅時代架設的“天下第一橋”遺址。文成公主、張騫、法顯、玄奘、弘化公主、金城公主以及《水經注》作者酈道元都從橋上走過。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推論:這個離蘭州只有幾十公里的地方,確乎是中亞綠洲絲路與雪域高原絲路和西南絲路的無可替代的交會點。
成都經甘南、合作,臨夏、永靖到蘭州的鐵路正在分段施工,蘭州向甘南的沿黃河公路也在日夜兼程地“趕路”,而與甘南通道并列的隴南鐵路通道,即通向嘉陵江長江水系的蘭渝鐵路也正在秦巴山脈的隧道里穿越。已經可以看得清楚,這里不再是古老馬幫穿行的山間小道,將是現代鐵路動脈。如果加上還要遲早到來的“泛亞鐵路”有極大可能從這里向中國西北延伸,在這里對接,甘南、隴南走廊的絲路新角色也就在意料之中。
中國的著名記者范長江在抗戰初期考察西北,走的就是從甘南通道與隴南通道,由此進入蘭州,進入西北的旅行路線。他由他的家鄉四川內江出發到成都,進入那時還不是一級行政單元的九寨溝地區,輾轉宕昌、岷縣、臨夏、永靖、蘭州一線,在河西走廊、西寧湟水、大通河流域、寧夏黃河峽谷、隴東地區和西安關中地區穿插采訪。他關心時局更關注民生與經濟,他是近代中國西部區域經濟開發研究的第一人。他從成都進西北,不能完全歸因于家鄉在四川,在抗戰初期,“國府”遷都重慶已幾成定論,中國西北部與西南部如何形成犄角之勢同赴抗戰,必是一個重要的思考切入。那么,在絲路復興的今天,如何接續這種思考,不僅是交通對接和民俗旅游的發展,需要更多地思考甘南與隴南經濟走廊的發育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非同一般的關系。
實在說,蜀道的西支“金牛道”原本從甘南隴南走廊擦過,有時干脆就是前者的一部分或者替代線。從這里可以由廣元沿嘉陵江直下閬中古城到達重慶,也可以隨魏將鄧艾“偷渡陰平”,直下劍門關。在成都與重慶,成昆與渝滇鐵路和公路干線,或者按照秦代開鑿的“五尺道”南去,或者伴隨“蜀布邛杖”流轉的 “博南道”一路南行,形成了西南絲路的基本架構。成昆與渝滇鐵路都是上世紀50年代修筑的,但在抗戰初期,當時的國民政府已經開始了滇緬鐵路項目工程建設,1938年4月成立“滇緬鐵路工程處”,由主持過浙贛鐵路、湘桂鐵路的著名鐵路專家杜鎮遠領銜,動用了數十萬民工,修建由臨滄、耿馬出境的鐵路,與緬甸境內臘戍的鐵路相接。但路基方成,日寇攻入滇西,鐵路工程被迫停工。現在,計劃中長達860公里的“滇緬鐵路”已經路基難尋,但另一條沿瀾滄江到萬象的鐵路也即“泛亞鐵路”中段已經開始進入程序,一旦“泛亞鐵路”建成,從四川成都和重慶北顧甘南、隴南經濟走廊,甘南、隴南經濟走廊的地緣經濟價值也就凸顯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