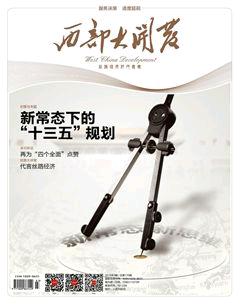“塞上江南”的絲路地位

從蘭州在絲路發展中的核心區位,也引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原來被認為是既不靠邊又不靠海的內陸省份,特別是西部地區的腹地省區,在“一帶一路”的發展格局中又會是怎樣的狀況?換言之,中部六省的位勢是明確的,四川與重慶和陜西的西安,其發展水平也如上文所說的是“西部的東部”,有自身明顯的經濟優勢,但西北地區的一些腹地省區如青、寧和西南地區的貴州,卻有被絲路相對“邊緣化”的擔憂。即便是在四川盆地和陜西關中地區,真正發展快的是較大的都市,四川的川西、川南、川北,陜西的陜北、陜南,甘肅的定西和隴東以及重慶的石彭酉秀地區,依然處于不發達狀態和經濟輻射的末梢。解決他們的問題,同樣需要仰仗“微絲路”的發展。
寧夏其實不算是“微絲路”,是絲路主干道的一個分支。寧夏地處黃河中游,是自古流傳的“黃河百害唯利一套”說法中最大的“一套”,銀川平原所在被稱為“前套”,內蒙古西部的黃河回水灣是“后套”。銀川平原在唐代就有“塞上江南”的盛名。“安史之亂”之后,唐肅宗在臨武即位,說明這里不是等閑之地。北宋時黨項羌族的李元昊在此建立西夏皇朝,也不是僅僅因為這里農業資源雄厚,主要是因為銀川平原在絲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這里四圍多沙漠的自然地理形態,對于以駝隊運輸方式的陸上絲路貿易,是長項而非短項。這樣一種絲路優勢也給彼時西夏立國帶來可攻可守的戰略優勢。西夏最盛時,北到居延,西到敦煌,東臨中原,川西則是其先祖曾經居住的故鄉。風傳中川西丹巴“美人谷”是西夏與成吉思汗戰前安頓后宮人等的地方,恐怕也非空穴來風。西夏的滅亡,與控制絲路貿易有著密切的關系,至少是成吉思汗進攻西夏的真正的原因。當時的西夏確乎掌控了通向中亞綠洲絲路和北方草原絲路所有的重要道路。
近代以來,寧夏的行政區劃一度屬甘肅,也有絲路地理的某種考量。1958年寧夏建區,成為以回族為主體民族的重要自治區。從一般行政地理的角度看,寧夏似乎是一個與絲路干線相鄰的省區,并非核心區域。但從絲綢之路發達的系統和寧夏獨特的經濟通道功能來看,不僅不會被絲路經濟“邊緣化”,相反地使絲路交通具有了更多的選擇。第一,寧夏連接著北方草原絲路,同時也連接著中亞綠洲絲路。第二,寧夏與臨近甘南走廊的臨夏的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的天然聯系是一種無可替代的人文資源,這種人文資源使寧夏與中亞、西亞的阿拉伯國家的市場聯系與產業聯系極為契合,與東南亞、南亞的一些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也有著必然的經濟文化溝通。馬來西亞是世界穆斯林食品用品認證轉口中心,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寬展性與互聯互通的網絡便利性,給出寧夏發展絲路經濟的巨大回旋空間和獨特的優勢。第三,寧夏的銀川在鐵路運輸上頗具有蘭州物流副中心的潛能,不僅是距離近,還因為擁有直接進入“河西走廊”的獨立鐵路系統,就是由騰格里沙漠南緣直向“古涼州”武威的沙漠鐵路。這條鐵路提高運能,緩解蘭州的物流壓力,也使武威重新找回自己在絲路經濟中的地位。也因此,包蘭線的高鐵化和沙漠鐵路的高鐵化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寧夏區位的這種潛在優勢也說明,盡管區位資源有絕對性,但絲路的網狀結構也給出了一種相對中的絕對。2014年,寧夏銀川至山西太原的鐵路貫通,也使寧夏多了一個優勢,可以直通東部與中部地區,與蘭州出現了合理的物流分工。
寧夏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潛在優勢,也給出了一個重要的“微絲路”的考察點,那就是原來被認為是幾不靠的內陸省份,特別是西部地區的腹地省區,在“一帶一路”的發展格局中同樣重要。事實上,從北方草原絲路和中亞綠洲絲路的區位互動關系看,猶如中國的“四橫四縱”的道路格局一樣,它們之間有著明顯的歷史形成的東西南的經濟連接線。它們都具有“微絲路”的形態,都與橫向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有著高度關聯。
貴州在西南的位勢與寧夏在西北的位勢相近,貴州是云貴高原的一部分,處于貴西南絲路帶通向內地的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說,沒有貴州就沒有七彩云南的開發與發展。戰國后期的莊嶠入滇以及漢代的漢使出使夜郎,前者由長江水系的沅江、清江一線進入,后者由川入黔,這是古代西南絲路上歷史形成的湘黔經濟帶的延伸與輾轉。這些古老的“微絲路”現在依然活躍。連接兩廣的西江經濟帶輻射到黔東南,雖然略有末梢之感,但從陸路連接了黔東南商業重鎮都勻,都勻南面的獨山成為日軍由桂向北侵入中國的最后“通道”,而日軍的最早受降儀式在此舉行。貴州的地理特點是“地無三尺平”,道路連通是貴州沿絲路發展的關鍵。目前,時速可達380公里的廣貴高鐵開始貫通,與連接兩廣與云南的高速并稱“兩高”以及“兩高經濟帶”,加上貴州西部“貴安新區”的建設,不僅使古老絲路多民族的人文與自然旅游資源得到有效盤活,也使貴州直接融入西南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中。貴州還處于渝黔高鐵經濟帶上,北上可以通過高鐵輾轉通向蘭州,是同時面向西南絲路與西北絲路的重要支撐扇面。貴州還有風景如畫的烏江旅游經濟走廊,融合了重慶與貴州旅游經濟互補的天然優勢。貴州與云南更是一對弟兄,人文相連,物流相連,滇北的發展要靠貴州的經濟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