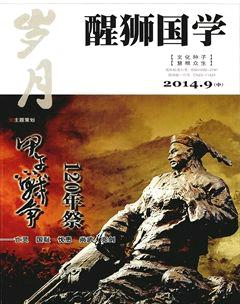唐太宗“道治天下”
編者按:韓異教授認(rèn)為,中國歷史上有好幾個“千古一帝”,但只有唐太宗同時做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這兩件事。他曾是個豪邁的軍人,登基之時讀書識字還有困難;他接手了隋朝留下的“爛攤子”,以區(qū)區(qū)2000萬人口起步;他面對的是五胡十六國以來復(fù)雜的民族形勢和多元文化的碰撞。唐太宗是怎么做的呢?
三個轉(zhuǎn)型奠定大唐盛世基礎(chǔ)
唐太宗完成的三個轉(zhuǎn)型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礎(chǔ):領(lǐng)袖自身的轉(zhuǎn)型、“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轉(zhuǎn)型、朝廷治國理念的轉(zhuǎn)型。
唐太宗16歲參軍,2年后他父親李淵起兵反隋,他以18歲的年紀(jì)率軍打仗,24歲就掃平群雄、統(tǒng)一中國。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這樣的人。毛澤東說他是第一號軍事天才,無人能比。從24歲到29歲,他又挑戰(zhàn)既定的政治秩序,在和哥哥的政治斗爭中勝利,通過玄武門之變當(dāng)上了皇帝,從此政治上也沒有了對手。他可以繼續(xù)玩下去,但他選擇以道治國,不搞權(quán)術(shù)。
我們認(rèn)為唐太宗是文冶的典范,但往往忽略了他在登基時是個純粹的軍人。他晚年回憶,年輕時曾有很多文字看不懂,于是請老師讀書給他聽,每天從下午讀到深夜。從“打天下”到“治天下”,他認(rèn)為“治國先治君”,轉(zhuǎn)型從自己做起,推動治國理念的轉(zhuǎn)變。孟子說:“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國就是政權(quán),可以通過爭奪贏來;天下是老百姓,不可能用不仁的手段獲得老百姓,所以“打天下”不是政權(quán)合法性的來源,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他要“逆取順守”。這樣,從上到下、從政治制度到社會文化,唐太宗推動了國家的一系列轉(zhuǎn)型,所謂“馬上得天下,下馬治天下”。
朱元璋也打天下,但他沒有及時轉(zhuǎn)型,治國手法和理念和打天下的時候沒什么區(qū)別。康熙皇帝則不是打天下的皇帝。從這個標(biāo)準(zhǔn)來看,開國皇帝中能完成轉(zhuǎn)型并實(shí)現(xiàn)天下大治的皇帝只有唐太宗。
從隋朝的滅亡中吸取教訓(xùn)
唐太宗如何接手隋朝的“爛攤子”?唐太宗請魏征主持修纂《隋書》,以史為鑒。
隋亡的原因是與民爭利——38年間征調(diào)了3000萬勞動力,隋朝統(tǒng)一時人口只有2000萬,這意味著每一個壯丁一生要被國家無償征調(diào)數(shù)次。唐太宗接手隋朝的“爛攤子”時,登記在冊的人口數(shù)已從(隋)頂峰時期的5000萬掉到了2000萬。冷兵器時代,僅僅幾年的動亂,不可能殺掉3000萬人,這些人口只是從國家的戶籍登記中“逃”走了——這意味著國家收不到稅。古代繳納的都是人頭稅,國家和老百姓之間的博弈就在于人千方百計地掙脫戶口以逃避稅收。唐太宗沒有像隋初時那樣徹查戶口、追繳稅收,而是“藏富于民”。如果說人口5000萬,在戶口登記中只有2000萬,意味著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二的稅是讓給了老百姓。
唐朝就從這2000萬登記在冊的人口起步,直到150年后的唐玄宗時期,人口才恢復(fù)到6000多萬。而隋朝登記在冊的人口從2000萬人增加到4000萬人,只用了一年——當(dāng)然不是生出來的,是查出來的。再從這4000萬升到5000多萬人,則用了十幾年時間。同樣的人口增長,唐朝花了150年,隋朝只用了20年。人口數(shù)的緩慢增長背后,是政府在減稅和讓利。
隋朝為加稅還用了各種手段,比如“析戶”,即分家。國家規(guī)定孩子成年必須結(jié)婚,婚后即分家,戶數(shù)增加了,賦稅就有了。然而這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孩子另立門戶以后孤寡老人沒人贍養(yǎng),子女的教育也做不好。中國古代實(shí)行大家庭制度自有其道理,但這樣一來道德的社會基礎(chǔ)、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就被擊穿了。唐太宗接班以后,唐律規(guī)定,只要父母在,孩子不分家。如果分家,孩子要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對國家來說,這就是犧牲了賦稅收入,為社會秩序和維持道德買單。
關(guān)于文化開放政策的爭論
唐朝之所以是盛世,根源在其開放、多元。尤其是文化方面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舉個例子,唐太宗曾經(jīng)為制定音律組織過一次討論。
中國音樂的正統(tǒng)是廟堂音樂,追求莊嚴(yán)肅穆,輕松歡快的小曲則被視為“靡靡之音”。五胡十六國時期,少數(shù)民族進(jìn)入中原,帶來了中亞音樂。例如琵琶就來自波斯,早期是橫著彈的,因?yàn)橛文撩褡宥简T在馬上彈奏樂器。千年以后的今天,我們稱琵琶為“民族樂器”,事實(shí)上這些來自中亞的樂器、音樂融入中原的過程伴隨著艱難的斗爭。
中國古樂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分別有對應(yīng)之物:“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隋朝統(tǒng)一以后曾重新定音律,希望吸收中亞音樂,遭到了政治力量的反對,認(rèn)為不能轉(zhuǎn)調(diào),否則“君”變了“臣”,豈不天下大亂?隋文帝是一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他拍板決定維持原有的音律、秩序,不吸收這些“靡靡之音”,恢復(fù)到漢朝以前緩慢莊嚴(yán)的音律上去。這事實(shí)上要抹殺五胡十六國以來三百多年的音樂成就。
隋朝短命,數(shù)十年就滅亡了,唐太宗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如何定音律?同樣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力量在老調(diào)重彈:“陳將亡也,為《玉樹后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舊唐書·音樂志》)”唐太宗則反駁這種看法,認(rèn)為悲歡在于人心,而非音樂,“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他甚至要為這些大臣演奏“靡靡之音”:“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dāng)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舊唐書·音樂志》)”唐太宗選擇了開放的政策以應(yīng)對多元的文化,才有了大唐盛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