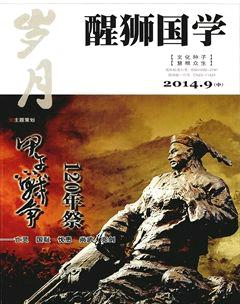甲午戰爭的文化沉思
王毅
中日榮辱觀差異決定戰爭勝敗
武士道精神是大和民族之魂,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重榮譽而知恥,以流血為榮,以流淚為恥。對于武士而言,他們視武士榮譽重于生命,倘若他們認為自己有辱領主的榮譽,就會自殺以謝罪。一言以蔽之,武士道就是為了榮譽看透死亡,而且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亳不猶豫地死。要成為真正的武士,都得接受魔鬼般的訓練,甚至野蠻的考驗,磨煉出他們冷酷、忍耐、冒險的鮮明性格,這也成為日本的民族性格。他們只崇敬強者,從不憐憫弱者,這種“重榮譽而知恥”的精神已經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血脈,影響著日本一代又一代人。
明治維新以來,西方先進的軍事思想和武器裝備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使日本軍隊成為世界近代史上最野蠻強悍的軍隊。正是憑借這支軍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橫行肆虐,“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讓對手無不瞠目結舌,也讓一些對手精神崩塌,放棄抵抗。
培根曾言:“任何國家之所以偉大,主要在于是否有尚武的人種。”戰國尚武,但自秦朝統一中國后,統治階層極力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思想文化,桎梏國民思想,國民重“內修文德”,輕“外治武功”,多講明哲保身,莫談國家政治,無一不頹損人之雄心,消磨人之豪氣,使國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如馴羊。梁啟超說:“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蔡鍔則說:“中國之教育,在摧殘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奴隸之資格。”
甲午戰爭之前,《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實際情況是“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水師最高指揮者丁汝昌,在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船有半”。
甲午平壤之戰結束后,日軍在清理清軍遺棄物品時,發現衛汝貴妻子給其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于財,宜自頤養。且年事已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此信后來被日本作為敗軍亡國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國人。
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羅豐祿也好不到哪兒去。生活在環境幽雅的天津紫竹林,沒有在籌劃戰事上勞思費神,卻利用自己在北洋水師統帥層的特殊地位,通過關系把侄子調離硝煙彌漫的前線。在戰事緊要階段給妻妾的信中,羅豐祿關心的幾件事是:一旦撤換北洋大臣李鴻章,自己在官場上將失去后臺;戰爭最好早日結束,中日最好早日議和;一旦和議成功,就會接妻妾子女回天津團聚。家比國大,只能看到家里那點蠅頭小利,哪能有國家和民族擔當?哪里又會有什么精神可言?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武士道“受命忘家忘親”的精神。甲午戰爭期間,在中國腐朽的統治者仍在貪圖享樂籌擺宴會之時,明治天皇在大本營親自領導作戰。牙山戰后,天皇親自譜寫歌詞:“我勇猛之兵士,踏過彼我之尸體,奮勇前進,那是牙山之本營。前進、再前進,凱歌三唱。”黃海海戰后,天皇敕令嘉獎有功官兵,親自為犧牲官兵舉行祭奠儀式,還再次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時至今日,日本人仍不喜歡《紅樓夢》,他們認為《紅樓夢》過于家長里短,兒女情長,纏纏綿綿,不符合大和民風,而酷愛《三國演義》和關云長,能使他們陶醉于豪情壯志之中。
清軍多阱明哲保身,與身家性命相比,氣節輕如毫毛。中日甲午之戰,從豐島海戰、成歡、牙山之戰、平壤之戰、黃海之戰,到威海之戰,清軍少有與日軍血戰到底的氣概,反而屢屢出現將帥先逃、士兵潰散之事。成歡、牙山之戰,葉志超主力狂奔五百里逃過鴨綠江。黃海海戰,“廣甲”號管帶吳敬榮臨陣脫逃。旅順保衛戰,衛汝成、龔照玙、趙懷業、黃仕林率先逃跑不戰自潰。最后至威海衛保衛戰時,發展到一些人集體投降以圖保一命。營務處道員牛昶炳請降;劉公島炮臺守將張文宣請降……面對全軍崩潰的局面,丁汝昌命令沉船,無人奉命,再命令艦船突圍,也無人奉命。最后軍士抽刀脅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自殺。丁汝昌自殺前給李鴻章發了份電報:“縱有艦沉人亡而后已的決心,但現今眾心潰亂,已不能有所作為。”
旅順大屠殺過后,日占領區內的民眾,固然有舍生取義者,卻極少,“更多人竟然以能在日軍中找一份牽騾馬差事為榮”。在甲午戰爭結束十多年后,女革命家秋瑾仍在喟嘆:“忍看眼底無馀子(男兒),大好河山少主人。”日本占領東北期間,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這樣像樣的個人反抗,卻沒有中國人進行過。
實際上,這種奇怪的現象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1931年,日軍策劃“九一八”事變。日本兵力不足2萬,中國東北軍達20多萬,結果3個月丟掉東三省。在日本人扶持的偽滿政府中,偽滿高級官員東北人有35人,占被統計人數的71%,奉系背景占82%。投降日軍充當偽軍頭目的國民黨將級軍官,至1943年時即達58人之多。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人,并成了南京偽國民政府的基礎。在抗日戰爭中,偽軍人數達到118萬之眾,與侵華日軍數量基本相等。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聞。
反觀日本軍人,一向以投降為恥,投降回去也要“謝罪”,名字不能列入靖國神社,家人享受不到撫恤,子孫幾代人都會蒙羞。甲午戰爭平壤之戰前,面對戰場上的不利形勢,日本樞密院院長兼出征軍司令官山縣有朋對軍官們訓示:“萬一戰局極端困難,也絕不為敵人所生擒,寧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兒之氣節,保全日本男兒之名譽。”此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爭中,日軍寧死不屈者眾,而投降人數極少。
平型關之戰是林彪的得意之作,戰前他反復給部隊交代要抓些俘虜。戰斗結束后,八里長的狹溝尸橫累累,1000多目軍戰死,居然無一被俘。為了抓到俘虜,八路軍付出慘重的代價。有一位營長背起一個半死不活的日本傷兵,準備送往急救站。半路上傷兵稍稍緩過勁來,一口咬掉了營長的耳朵。電影《太行山上》有個鏡頭,一位女戰士發現躺著個日本傷兵,受了重傷,還在呻吟。女戰士掏出紗布準備為他裹傷,那傷兵卻揚手將刀刺進了女戰士的胸口。戰斗中的確有這樣的真實事例。這么大的伏擊戰沒有抓到一個俘虜,在我軍戰史上尚無先例,也讓林彪驚詫。而這1000多日本兵都是些什么兵呢?這是一個輜重部隊及其護衛部隊。日本的后勤兵尚且如此,何況其主力。endprint
中國知恥而后勇實現大變革
1894年的中國是一盤散沙,甲午一役讓一部分優秀兒女知恥而后勇,在中國大地上拉開了最為劇烈、最為急促的大變革。啟蒙、自強與救亡,匯聚成時代主旋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黨成立、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些歷史鴻篇巨制次第展開。其中,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相繼走上歷史舞臺,都以不同形式回答了甲午之恥。
孫中山知恥。1894年6月,時年28歲的孫中山,將八千余言的《上李傅相書》轉呈李鴻章,直指器物層進不足以勝西洋。結果不被采納。3個月后,黃海海戰失敗,孫中山憤然長嘆:“知清政府積弊重重,無可救藥,非徹底改造不足以救亡。”當年底,孫中山赴美成立興中會,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1911年,他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古老的中國告別專制,走上共和之路。
毛澤東知恥。上世紀60年代,他談到中印領土爭端時斬釘截鐵地說:“不能做李鴻章。”這個出生在甲午戰爭前一年的湖南人,從參加“少年中國學會”這一“甲午產兒”組織開始,帶領中國人民走上精神崛起之路,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最終實現民族獨立與階級解放。究其一生,毛澤東從來不曾忘記甲午。年輪轉過一甲子,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場。毛澤東以“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的膽魄,敢于同世界最強國交鋒,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生生從鴨綠江畔趕回“三八線”。毛澤東知恥而后勇,洗刷了中華民族百年屈辱,抗美援朝打出的精神高地讓世人景仰,讓對手從此害怕“毛澤東化”。這是毛澤東給中華民族留下的精神遺產,至今仍讓我們享用。
鄧小平知恥。在事關民族榮辱的原則問題上,從來不讓步。1982年,面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不愿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鄧小平斷然作答:“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中國人窮是窮了點,但打起仗來不怕死!”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甲午戰爭帶給中國人的恥辱!
在人類歷史上,窮兵黷武的民族一個接一個冒出來,但基本上是曇花一現,要么沒落消亡,要么回歸正途、涅槃重生。似乎,日本在二戰中的慘敗使武士道精神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千年形成的基因怎么可能輕易變種!看看今天日本政要和國民對靖國神社的頂禮膜拜,就知道武士道精神仍未消亡,也沒有改邪歸正,隨時可能掀起西太平洋的驚濤駭浪。
中華民族的崛起是精神的崛起。今天,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夢,武士道精神是我們繞不過去的一道坎。武士道,服力而不服理,借用別人的力量戰勝它,它仍然是心腹之患;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徹底戰勝它,才能真正臣服于你。怎么應對武士道?還是電視劇《亮劍》中李云龍那句話長中國人志氣:“什么他娘的精銳,老子打的就是精銳;什么武士道,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就是要有點李云龍這種“亮劍”精神。
今天,中國人有些健忘,當年日本人殺中國人如羊,現在中國人以用日本貨為榮。再健忘,有個反復出現的歷史規律總得記住:每當中國經濟繁榮,就引來日本的貪婪,這種貪婪從來沒有因為中國忍讓而適可而止、見好就收。武士道精神從來沒有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這個傳統。而今,日本海上自衛隊兵不滿6萬,敢言“3小時結束下一場中日海戰”。面對狂人狂言,精神懈怠的危險早在我們眼前,“太平官”“庸官”“昏官”“貪官”為數不少,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見怪不怪,這是當今中國自己的敵人。回首百年甲午,君可知恥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