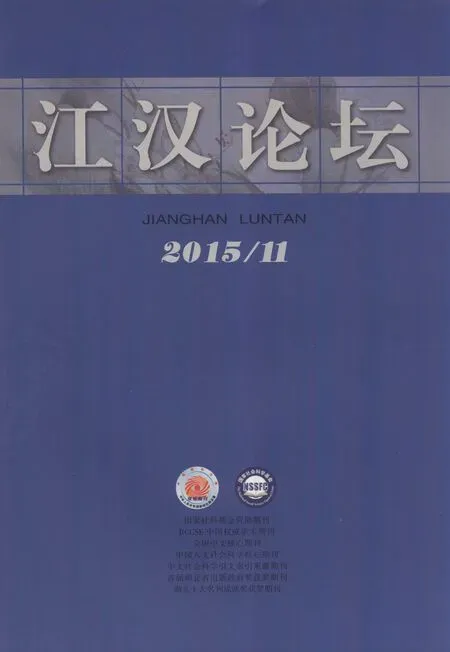論作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
彭繼紅 任書東
所有的文明都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但是,與漁獵文明、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不同,生態(tài)文明是在人類較為充分地認識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關系的基礎上自覺創(chuàng)造的。人類特有的能動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在此得到集中體現。為此,東西方學者都在極力探尋并建構這種生態(tài)文明的理論基礎。西方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在回應和批評西方綠色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時,把目光投向了歷史唯物主義。但歷史唯物主義在他們那里是碎片化的鏡像,為他們建立技術 “分散化”、生產決策 “非官僚化”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服務。而國內一些學者梳理出的所謂 “馬克思主義的生態(tài)理論”又僅僅專注于馬克思恩格斯人與自然的思想,不能很好地反映人與環(huán)境特別是生態(tài)環(huán)境關系的復雜性。有感于此,我們試圖把從馬克思恩格斯到普列漢洛夫、從前蘇聯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經驗到今天中國的探索等方面的思想資源融合成更為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使之成為引領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理論指南。
一、從生態(tài)文明建設視域剖析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
生態(tài)文明是人類通過對自己與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進行反思而設計出的一種復合型的新型文明形態(tài)。它高于過去以某一種單純的生產勞動類型命名的文明形態(tài),但又包含它們的全部內容;它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對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的征服“理性”和制度安排,但又離不開以人為本的同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和諧相處的主題;它既是集人類未來生存理想、價值追求和美好愿望為一體的遠大目標,又是人們必須嚴肅認真應對的現實。具體說來,就新文明思想領域而言,它實現了自然觀和歷史觀的統(tǒng)一;就新文明前進的動力而言,它實現了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規(guī)律的統(tǒng)一;就新文明發(fā)展歷史過程而言,它實現了自然史與社會史的統(tǒng)一;就新文明主體而言,它實現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統(tǒng)一;就新文明的價值體系而言,它實現了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統(tǒng)一。要建設這樣一種新型的文明顯然需要一種全新的思維、全新的理論基礎。
西方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者籠統(tǒng)地把這種新理論指稱為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科學的生態(tài)文明理論應該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和指導。這種觀點,比起西方綠色思潮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同技術決定論、人類中心主義一類的理論而斷定歷史唯物主義不能作為建設生態(tài)文明理論基礎的觀點來說,無疑更趨近真理,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歷史唯物主義畢竟是揭示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適應于一切社會當然也適用于一切文明。所以,它對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指導意義表現為普遍性而缺少特殊性,并且這種普遍性更注重社會結構、社會發(fā)展的動力分析,容易遮蔽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環(huán)境特別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系。而國內把人與自然關系為核心的 “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理論”當作生態(tài)文明建設理論基礎的觀點之所以顯得 “狹隘”,是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本身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部分并貫穿其始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應有之義。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是認識人與社會關系的前提條件。生態(tài)文明是一個高級的綜合文明,需要復雜性理論指導,僅僅一個理論前提無法承擔如此重任。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里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既有分析也有綜合;其地理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的概念本質上既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又反映了人與社會的關系;而且,還以生產力發(fā)展的狀況、水平為中心合理地解決了地理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人與 “兩個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從而使自己具備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持的基本功能。
任何一種全新的理論都不是憑空掉下來的,都必須在梳理繼承前人的思想資源之后發(fā)展起來。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就是在吸取了地理學派,特別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等觀點的合理思想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發(fā)展而來。一百多年來它經過幾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創(chuàng)新與傳承,已經形成了包涵如下要點的系統(tǒng)理論:一是人的地理環(huán)境論,著重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人的社會環(huán)境論,著重解決人與社會的關系;三是在人的活動影響下的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關系論,著重解決自在自為的自然與人化了的自然和創(chuàng)造出的 “自然”之間的關系;四是自然—人—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論,著重解決人所處的環(huán)境良性循環(huán)、活性運轉的問題。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在這個方面超越了前人,為我們構建建設生態(tài)文明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優(yōu)質的思想資源。
過去,在教科書中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常被簡化為在生產力發(fā)展狀況和水平主導下的地理環(huán)境社會作用的論述,實際涉及的僅僅只是地理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討論的只是地理環(huán)境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狀況和水平不同而表現出來的不同的社會功能。這對批判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揭露其錯誤實質是管用的,但作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理論基礎就顯得單薄了。現在,豐富和發(fā)展這種理論已經具備了兩個現實條件:一是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實踐的需要。這種需要比幾十所大學更能推動理論建設。二是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學術視野對以上四個方面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梳理,思想資源已挖掘得比較全面,理論脈絡也逐漸清晰,為全面綜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首先,從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視域看,人的地理環(huán)境論是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的理論基石之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對于人具有先在性,人依賴于自然。這是舊唯物主義就有的觀點,并于18世紀形成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馬克思的過人之處在于他在承認人是自然一部分、自然的先在性的同時,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屬人的自然、人化的自然。自然被理解成 “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被理解成 “人的無機的身體”①。這樣他不僅把人作為自然的存在物來把握,而且把自然作為人化的東西來把握。遺憾的是像這樣辯證論述人與自然關系的天才思想并沒有為后輩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理論學者所重視,從而造成這一基礎性缺位。
其次,從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視域看,人的社會環(huán)境論是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的邏輯鋪墊。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大談 “環(huán)境”創(chuàng)造人,所謂的 “環(huán)境”多指社會環(huán)境,當然也有自然環(huán)境因素,因為社會本身就是自然長期發(fā)展的產物。而馬克思恩格斯則認為舊唯物主義只看到環(huán)境創(chuàng)造人,沒有看到“同時人也改變環(huán)境”,人既是歷史舞臺的演員又是觀眾。這些人與社會雙向互動、連為一體的思想,是在對人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肯定的基礎上對人的社會關系的進一步完善,是對人的自然本質和社會本質的全面說明。如果這樣的思想還游離在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之外,對于我們生態(tài)文明建設將是非常不利的。
再次,從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視域看,在人的活動影響下的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關系論是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的理論框架。在這個問題上,剛剛站在工業(yè)文明大門口主張 “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學者只能總結出漁獵文明和農業(yè)文明時代自然環(huán)境對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社會制度決定性的一面;而在工業(yè)文明深度發(fā)達時代,以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前蘇聯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者雖然涉及到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看到了社會環(huán)境的不可或缺性,但基本上還是屬于有條件的地理環(huán)境作用論。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狀況和水平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量”。近年來崛起的西方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過多地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把一切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危機都歸罪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其實,早在1950年前蘇聯學者伊凡諾夫·歐姆斯基就討論了 “資本主義社會對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和 “社會主義社會中對地理環(huán)境的改造和利用”②。現在看來對二者關系的認識總是停留在兩個極端,對于生態(tài)文明建設無疑是有害的。
第四,從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視域看,自然—人—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論是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的理論核心。這三者的相互作用是由兩個相互聯系的 “變換”系統(tǒng)完成的:一是通過生產實踐實現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二是通過交往實踐實現的人與社會之間的物質與非物質的變換。馬克思指出: “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chuàng)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③而按 《資本論》的邏輯,通過交往實踐實現人與社會的物質和非物質變換則創(chuàng)造價值。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形成人類一切文明類型的最基本最關鍵的要素。由于包括工業(yè)文明在內的以前的文明都是自發(fā)地積淀而成的,所以,人們基本上沒有從這兩個 “變換”的統(tǒng)一的角度來推動文明發(fā)展和享受文明成果。而生態(tài)文明建設必須糾正過去習慣上的偏頗,抓住三者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理論內核,開拓出兩個 “變換”整體推進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新思路。
二、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呼喚新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
國外生態(tài)學馬克思主義學者從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吸取理論依據并試圖用生態(tài)社會主義來解決生態(tài)危機、建立生態(tài)文明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如日本的巖佐茂就認識到, “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并不是僵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動態(tài)關系。因此我們不能在只有人才是能動的、自然是受動的那種人對自然的單方面作用關系中,而應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中來理解這一關系”④。但他們用對資本主義社會生態(tài)危機現實的批判代替理論的批判與創(chuàng)新,用對生態(tài)社會主義的虛幻代替實實在在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進程是與指導具體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實踐有一定距離的。而現有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中的地理環(huán)境觀點的內容又太狹窄了,難以擔當指導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任,因此必須對其內容進行大幅度的改造和發(fā)展,重建符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
首先,從文明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同發(fā)達國家比較有以下不同:一是中國正處于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過渡時期,人的綜合素質和社會制度體系的完善程度還遠遠趕不上工業(yè)文明成熟的國家。中國一邊要補好工業(yè)文明拉下來的課程,一邊必須加強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頂層設計。二是這種頂層設計沒有經驗可循,沒有榜樣可以學習。我們不可能走西方工業(yè)文明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如何建設生態(tài)文明西方發(fā)達國家雖然實踐上走在我們的前面,但是他們也沒有總結出系統(tǒng)的經驗。即使在實際操作層面,他們那種把有損于環(huán)境的產業(yè)都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的 “環(huán)境殖民主義”做法,我們也是不能學的。三是我國幅員遼闊地理環(huán)境復雜,再加上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不平衡,有些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破壞嚴重,有些地區(qū)則地理環(huán)境保護良好,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政策方針不能一刀切。
其次,從現有的相關理論結構指導實際的張力來看,中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呼喚理論創(chuàng)新。我國現有的指導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相關理論,最為重要的當然是科學發(fā)展觀。科學發(fā)展觀是在反思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發(fā)展的舊路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fā)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在指出了生態(tài)文明建設方向的同時也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和標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生態(tài)文明建設上的理論自覺。在這一理論框架里,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如何處理好人與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如何深度把握自然—人—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內在規(guī)律等等問題都需要予以說明。所以指導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理論,結構上必須體現層次性:頂層設計和具體策略相結合;內容上必須體現完整性和復雜性: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相關思想相結合、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探索成果相結合;價值方面必須體現未來性:要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建設人類新型文明的光榮使命結合起來。
再次,從生態(tài)文明建設實踐活動的需要來看,只有綜合化系統(tǒng)化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才能解決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實際問題。生態(tài)文明就是人類在自然—人—社會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過程中實現三者的和諧相處共生共榮的生存狀態(tài)。作為人類迄今為止最高的文明形態(tài),它既有一般性的要求,也有個別性的表現,這是它與工業(yè)文明的不同之處。工業(yè)文明的資本、市場、生產線甚至包括城市建筑等等都有全球化的相似之處。而生態(tài)文明則不然,它的內容具有普遍性,形式卻具有個性特征,是共性和個性的統(tǒng)一。工業(yè)文明的產生是遵循以一般模式向世界擴展,一般規(guī)律引領個性發(fā)展的路子實現其存在的;而生態(tài)文明應該是遵循相反的路徑:從個別到一般的生成模式。這就要求中國的建設者在建設過程中,一方面內容上必須按生態(tài)文明的一般要求建設,使生態(tài)文明具有國際化水準;另一方面又必須依據中國的地理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和人的素質情況,把中國特有的自然—人—社會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作為統(tǒng)一的工作對象,找到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可行之路。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能夠在建設實踐中為這種特殊性提供解釋的模型和建設的依據。
綜上所述,我們把作為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概括為如下幾點:一是以科學發(fā)展觀的思想、價值和制度設計等方面為統(tǒng)領,彰顯出建設新的生態(tài)文明高度的理論自覺;二是以統(tǒng)籌兼顧自然地理環(huán)境、社會人文環(huán)境為兩翼,因地制宜,凸顯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多樣性共生共榮;三是以促進自然—人—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為核心動力,打造生態(tài)—經濟—制度的良性循環(huán)圈,以促進區(qū)域實際生態(tài)—經濟—制度的良性小循環(huán)帶動大循環(huán),從而讓整個社會生態(tài)文明建設有序運轉起來。總之,作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是關于科學發(fā)展觀統(tǒng)領下的人與自然關系理論、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論和人的活動影響下的自然與社會關系理論的概括和總結;是關于自然—人—社會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不斷推動生態(tài)—經濟—制度進步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系統(tǒng)理論。
三、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引領中國特色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三個維度
生態(tài)文明是人類嶄新的文明形態(tài),也是當代人們追求的理想境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tài)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huán)境污染嚴重、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tài)文明理念;把生態(tài)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為此必須在三個重點方向著力:一是改變舊觀念,創(chuàng)造新的理念;二是以堅持節(jié)約資源和保護環(huán)境為基礎著力推進綠色經濟、循環(huán)經濟、低碳經濟的社會良性發(fā)展;三是加強生態(tài)文明的制度建設。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可以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維度引領人們建立新的觀念體系;可以從把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兩個物質 “變換”的必然性和自然—人—社會相互作用規(guī)律的維度探討生態(tài)文明發(fā)展的深層動力體系;可以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相互關系的維度中找到生態(tài)文明制度建設的鑰匙,使“用制度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規(guī)劃得以實現。
首先,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中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是引領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形成人與自然關系新觀點、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西方有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tài)中心論的對立;中國有 “天人合一”和“人定勝天”的兩極,并由這兩種對立的觀念演化出人類與自然一系列對立的行為:人類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遭到了恩格斯早就斷言過的 “自然界的報復”。這種報復不僅制約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甚至直接威脅人類自身的存在。而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統(tǒng)一;是建立在價值標準上的自然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統(tǒng)一;是建立在操作層面的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統(tǒng)一。這些思想不僅遠遠地超出了 “兩極對立”的形而上學思維,超出了舊唯物主義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學說,而且其理論深度和廣度也是現代西方生態(tài)學研究者無法企及的。但是這種立足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設計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閃光思想不可能被資本主義社會的管理者所重視和運用,以致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災難性的環(huán)境污染。而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把這三個統(tǒng)一好好地運用起來,重新審視與建構人與自然的關系。
其次,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中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兩個物質 “變換”的必然性和自然—人—社會相互作用規(guī)律的理論是我們建設綠色經濟、循環(huán)經濟、低碳經濟良性發(fā)展的資源節(jié)約型和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的精神動力。為此,必須在實踐中注意如下關鍵環(huán)節(jié):一是要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當成是自然循環(huán)的一環(huán)來把握,在尊重其自然過程的同時,注重其社會性。要以自身的活動為中介對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進行 “合理的調節(jié)”、 “共同控制”, “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⑤。二是要在認識人與社會之間、物質與精神之間的變換過程的社會性同時,注重其自然性,注重生產和消費中的自然過程。人把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和在消費生活中產生的廢棄物排放給了自然界,但卻沒有考慮自然過程本身的物質變換的能力,從而造成物質變換的斷裂。馬克思早就看到了這一問題: “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yōu)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⑥也就是說,兩種 “物質變換”過程中,既包含有社會的必然性,又充滿著自然必然性,是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規(guī)律的辯證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表現在自然—人—社會三者的相互作用的物質變換中是多樣性、復雜性和無限的可能性。過去,我們的認識受歷史條件制約,只看到其中單一的自然規(guī)律或社會規(guī)律,并據此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造成兩種 “物質變換”的相互脫節(jié),從而造成了整個自然—人—社會三者相互作用過程的斷裂。現在,新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要求我們運用復雜性思維把握兩種 “物質變換”中自然性與社會性、自然規(guī)律與社會規(guī)律的滲透原理,并從這種滲透中找到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具體說來,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我們不能僅僅只按自然規(guī)律辦事,要同時考慮社會規(guī)律;同樣在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時也不能僅僅只看到社會規(guī)律,而要同時考慮自然規(guī)律。只有這樣,才能系統(tǒng)地把握自然—人—社會相互作用的動力生成機制,構成生機勃勃的自然—人—社會大循環(huán)圈,才能奠定循環(huán)經濟、循環(huán)發(fā)展的基礎。馬克思主義早已預見了這種統(tǒng)一。經典作家寫到: “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⑦
再次,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中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相互關系的理論是引導我們進行生態(tài)文明制度建設頂層設計的理論原則。制度作為個體社會行為的規(guī)范或運作模式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人們有目的地建構的存在物。由于廣泛滲透到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之中,制度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尺之一。在生態(tài)文明誕生以前,文明所擁有的一切制度都是以處理、調節(jié)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為目的的,在認識社會必然性和利用社會規(guī)律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指出:建設生態(tài)文明,必須建立系統(tǒng)完整的生態(tài)文明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huán)境治理和生態(tài)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顯然,這里的制度建設已經超出了過去僅僅只考慮到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層面,而上升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的相互關系的層面來解決問題。例如,建立空間規(guī)劃體系,劃定生產、生活、生態(tài)空間開發(fā)管制界限;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終身追究責任;實行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tài)補償制度等等,都是在認識到兩個 “物質變換”過程中兩個相互滲透的必然性的基礎上做出的正確的頂層設計。這些頂層設計說明,我們的決策層在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導下對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論的整體內容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理論自覺。但是,從這種高層決策的理論自覺到具體的制度,從頂層設計的理想藍圖到實踐主體的行動指南,還有一段很長的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要走。這也是本文討論的內容雖然已經遠遠超過了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地理環(huán)境理論本身而我們仍然用它命名的原因。
注釋:
① 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頁。
② 詳見伊凡諾夫·歐姆斯基: 《歷史唯物主義論地理環(huán)境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馮維靜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40頁。
③⑥ 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9頁。
④ [日]巖佐茂: 《環(huán)境的思想》,韓立新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頁。
⑤ 馬克思: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7—928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