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鄒市明
◎ 雷曉宇
采訪鄒市明
◎ 雷曉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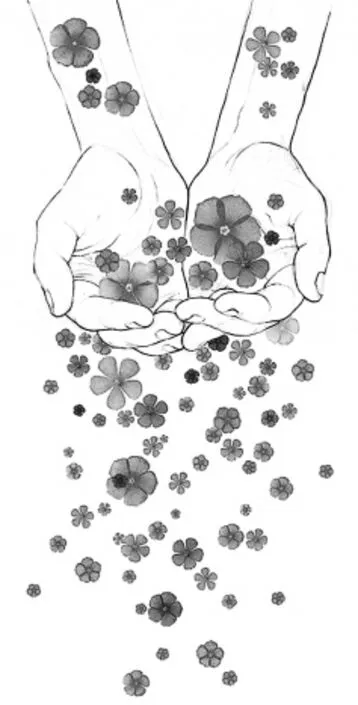
前一陣子,我帶了一本《李小龍傳》去見鄒市明。你知道鄒市明吧?他是唯一一個拿過奧運金牌的中國拳擊手,今年34歲,住在美國,指望抓住最后的機會在那里打出一片天地。
我把這本書送給他,其實是想問:“李小龍能得到美國人的認同,不只因為他能打。他在華盛頓大學上過哲學課,懂得怎么把東方哲學和西式搏擊結合起來——他有他的武術哲學,你有你的拳擊哲學嗎?”
鄒市明一愣。他可能沒想到會有人問他這么不著邊際的問題。最后,他給我講了兩個故事。
在他還沒出名的時候,有一次上臺打拳,打一個南美人。那是業余拳賽,以點數的多少計算勝負。上臺之后,兩人相互試探,誰也不肯第一個出招。偶爾虛晃一槍,淺嘗輒止,你不出手,我也樂意繞圈子。對方比鄒市明年輕,熬到比賽快結束的時候終于忍耐不住了。鄒市明瞅準機會,一拳打中他的肋骨。其實,這一拳并不重,只要對手繼續閃避便沒事。但血氣方剛的南美人豈能受辱,第一個反應就是還擊。
“打拳要有城府。人家用招數逗你,刺激你,你要是連這點氣都沉不住,立刻就還手,這就等于把自己的弱點敞開給對方看。”
最后,南美人輸了。
另外一次事情是最近發生的。鄒市明每天都在洛杉磯的一家拳館進行訓練。他的陪練是一位前職業冠軍,曾拿過兩條金腰帶。現在這位陪練已經40歲,狀態下滑,又剛剛有了孩子,生活負擔很重。沒有比賽,就沒有收入,他只好靠當陪練來補貼家用。
有一天上午,鄒市明和他做對抗練習時被打到左眼,舊患復發。在鄒市明的職業生涯中,這樣的情形曾經發生過無數次。每一次只要他閉一會兒眼,緩一緩,再睜開眼睛的時候,畫面就能恢復正常。可是這一次,陪練下手確實狠了點,鄒市明好幾次閉眼和睜眼后,眼前還是一片模模糊糊。
鄒市明慌了,一個人退到拳臺角落,背對著所有人。
“那一刻,我不知道臉上是汗還是淚。我已經是這個歲數,曾經無數次想過在哪個時刻退役。我想,如果這就是我退役的那一刻,我會怎么樣?”
幾秒鐘之后,他轉身繼續練習。
“那天打完之后,沒人知道發生了什么。我還是跟他一起換衣服,一起說笑話。拳手之間沒有恩怨。如果他不夠狠,下次在臺上被打的可能就是我。”
鄒市明非常努力地想要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如果說拳擊有哲學,那我的哲學就是拳擊是一項紳士運動。什么叫紳士?有城府,無恩怨。”
我們沒辦法把拳擊和紳士聯系在一起。不過,拳擊手確實是個有詩意和悲劇色彩的職業。一個男人,赤裸著上身站在臺上被人圍觀,和另外一種生活搏斗。他看起來很可憐,但又是個斗士,要靠肉身贏回尊嚴。肉身就是武人的家。哪有什么關山萬里,哪有什么四海為家,身體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倘若有一天身體沒了,那么家就沒了。
我問他看沒看過徐皓峰,他說沒聽過。其實我很想告訴他,一拳被人把家打沒了的感覺,徐皓峰曾經寫過。形意門傳人李尊吾學成下山,入世爭名,頭一個就要拿高手祭旗。高手倒下,被家人用一床藍印花棉被裹上抬回家,兩個月之后就死了。他記得藍印花棉被的味道,那是一股舊棉花的霉味。一舉成名,行走江湖,一想起這股子老棉花的霉味,李尊吾就會一陣陣惡心。
鄒市明是個粗人,他不懂得其中的況味。他只記得那天回家時眼前還是流動的雙影。他老婆遞給他一杯水,他伸手去拿,杯子在左,手在右。他摸索半天,才默默喝下一口。他老婆不知道她的男人這一天經歷了什么。萬言不值一杯水。
(摘自《中國企業家》2015年第4期 圖/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