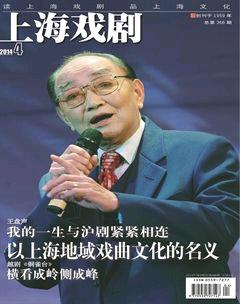愁煞風雪夜歸人
阿彬
如果沒有十六年前的《風雪漁樵》作對比,那新版越劇《風雪漁樵記》確實算得一部不錯的作品,它具備編劇吳兆芬“翻案文章”的一貫優點——以故事和人物體現女性意識,而非對男權社會的單純泄憤,自然且有說服力。然則看過舊版便知,該劇的深度和新意均輸于舊版,新版那些貌似不明顯的改動并未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反而從量變到質變,把一部95分的作品改到了80分。
貧賤夫妻百事哀已在以昆曲《爛柯山》為代表的傳統朱買臣故事中描繪得淋漓盡致。翻案文章并不是要否認這種現象,只是提供另一種可能,使人相信人性中畢竟還存在一些格調更高的東西。所以在越劇中,朱妻劉玉仙的逼休是出于激將法,朱買臣在最終真相大白后追妻悔錯。新版保留了這一故事框架,除了刪去見證者之一的楊孝天一角,主要在朱氏夫婦的人物性格上作修改,但這卻帶來了立意的降低,并導致節奏的散亂和層次的粗糙。
舊版的朱買臣在真相大白前有著較為明顯的局限性,雖然這正是塑造成功之處,但人物形象也因此不甚討喜;劉玉仙形象飽滿,但有過于拔高之嫌。新版便著意提升朱買臣,并使劉玉仙走下神壇。于是,朱買臣借酒麻痹、借山水逃避的苦悶頹唐形象,變成借酒澆愁、寄情山水,甚至有了點山中高士的意味。從開頭便感激妻子“寬容秀才成樵子”,仿佛是個明白人,“馬前潑水”之前有憐惜妻子、感念患難之恩的心理活動,潑水之后也覺“雖然十分解恨,心中卻又添一道傷痕”。單獨拿出來看,這可算是對朱買臣形象的改良,但放到全劇中看,卻十分生硬和混亂。既懂妻子的寬容,何以心安理得混吃等死?既念舊恩,何以極盡羞辱毫不留情?既毫不留情,何以會在氣頭上生出一絲愧意?如果說舊版朱買臣所為,皆是因認識不足而產生的無心之過,那么新版的有心之過恐怕更加過分。再說劉玉仙,本來逼休是為了丈夫“從今立恒志”,“不中也盼早回門”,如今考中功名成了終極目標。兩版“癡夢”同樣因朱買臣的高中而喜悅,不同的是,舊版是出于對丈夫終成“有志男兒”的欣慰,新版是出于對烏紗帽的渴望;夢境的破碎,在舊版是夢到朱買臣又酗酒喪志,新版則是朱買臣竟然沒考中。兩廂對比,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要是劉玉仙的形象悉數改成舍己為功名也就罷了,偏偏還保留了舊版的崇高成分,見朱買臣榮歸,驚呼:“你真是朱買臣?我不是在做夢吧!”隨即歡天喜地地跪下,簡直就是討封的王寶釧,轉身又說朱買臣能有今日,正是自己日思夜想、苦心促成的結果,別說朱買臣聽了不信,劉玉仙你自己信嗎?
人物性格的矛盾,主要因為舊版的渾然一體,絲絲入扣。新版僅在局部做些加減法,便牽一發而動全身,連統一連貫都做不到了,更影響合理性和真實性。為了表現人物的新屬性,全劇在節奏層次上也相應調整,這或許是觀劇體驗不佳的直接原因。
開場風雪尋夫,劉玉仙頂著老父病重、被逼分手和生計艱難的三重壓力,丈夫在關鍵時刻毫無用處,重在一個“愁”字;朱買臣則油鹽不進,不以為意,重在一個“頹”字。一個在火里,一個在水里,構成了強烈的戲劇沖突,也讓觀眾為之著急。而新版中,劉玉仙簡直要順著朱買臣一起遐想餐風飲露的神仙生活了。友鄰王安道也不是幫忙尋找去請郎中而一去不回的朱買臣,而是嘻嘻哈哈地給劉父送魚(送魚不往家里送,冰天雪地送上山?)、約朱買臣喝酒。于是我簡直要忘了劉父病重這件事。隨后劉父就不受重視地死了。劉玉仙決心逼休也是經過了一波三折的心理斗爭,舊版中病榻前(猶豫:是否真的非分不可?轉折:朱真的無藥可救)和靈堂上(猶豫:本來鐵了心,見朱求饒又心軟;轉折:為鞭策必須分)猶豫及轉折的點是不一樣的,而新版中劉在靈堂上猶豫的內容很大程度是病榻前的重復,甚至擔心起冷被孤衾難耐寂寞來,不禁再次感嘆劉父真是死得毫無存在感。好不容易逼休一通羞辱激出了朱買臣的血性,緊接而來的山廟戒酒又把繃緊的情緒松了下來。
作為一個正常的男人,遭遇奇恥大辱,必然憋足一口氣要重新證明自己,又怎會再思酗酒?如果逼休這樣的強刺激都不足以使朱買臣徹底戒酒,那廟中已趨平靜的情境又怎能下定決心?看似增加了心理活動的層次,實則打破了劇情的連貫性。也許因這一折占據了較長時間,隨后的層次都被簡單化,到了癡夢一折,則進一步上升為邏輯問題。劉玉仙做夢在先,見證者王安道之死在后,在一切逐漸好轉的情況下,劉沒有做噩夢的理由。不像舊版中,希望因王安道之死破滅,劉在大起大落中夢到了大喜大悲。
“馬前潑水”也是節奏散亂明顯之處。原本是個逐漸積聚勢能的過程,羞辱劉玉仙導致情感第一次爆發,劉父遺書真相大白導致情感第二次爆發。而新版中朱買臣性格的兩個改良點,恰是情感節奏的兩個泄壓點,雖不似山廟戒酒的干擾那么大,對沖擊力的減少也很可觀了。此外,新版《風雪》還吸收了昆曲中朱買臣瑟縮滑稽的丑態,據說是為了調節氣氛以免觀眾太累。可見主創對新編戲“累”的理解失之片面。累,主要在于必須忍受劇情的無病呻吟和故作高深,如果劇情的痛苦能打動觀眾,這種“累”的體驗實則是一種享受。可以昆曲為奶娘但不宜生搬硬套,移植前應先搞清人物定位,人物已改過自新尚且油滑,叫觀眾如何認真得起來?
近年來,戲曲界進入了“人性化”的怪圈,仿佛不體現弱點和被動就不算人性化。其結果便是人物面目模糊、性格趨同。愚以為,體現人物的獨特性并使之豐滿、深化,才是人性化之要義。
最后說說配角。刪除楊孝天是本劇改編最成功的地方。本來朱劉嫌隙的核心就是對朱個人價值的否定,緋聞只是催化劑,未必要有具體對象。而且揭示真相的作用已由王安道遺孀間接完成,且頗巧妙,減少旁線人物有利于劇情緊湊。然而,王安道遺孀形象的改良,伴隨著水妹形象的改惡。本來水妹為首的眾鄉親本質還是善良淳樸的,只是由于眼光有限,所以在他們的認知范圍內出于正義而反對劉玉仙。而新版則有主觀惡意,甚至做出戳窗紙的狗仔行為,朱買臣再夸她是“俠義剛強漁家女”就沒有了說服力。
也許,我觀看此劇的一切落差在于沒分清重排和復排的區別。如今戲曲界原創能力薄弱,紛紛轉向對傳統戲和早期新編戲的改編。改編則必尋求突破,原作者不滿足于原地踏步,新參與者(尤其是權威)要體現自己的存在感,但往往又找不到好的切入點,為不同而不同。這使我想起俄國畫家列賓的一個故事——列賓晚年修復了一幅年輕時的名作,結果色彩嚴重偏差,效果反不如前。原因是他眼睛色素沉著導致的辨色失誤。戲曲創作人員從業年久,也難免因“身在此山中”而產生眼光上的色素沉著,輕易否定前期的優秀作品。當創新已成為一種新的窠臼,也許更好的回顧才能指引更好的前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