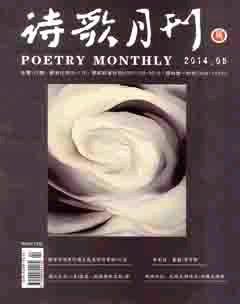“至誠”、 “真美”與“摩羅詩力”
劉康凱
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文化史上地位崇高,無出其右。但即便如此,魯迅依然受到嚴(yán)重的忽視和誤讀,這突出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相對于他的小說,他的詩歌(主要是《野草》)受到嚴(yán)重忽視和誤讀;二是相對于他晚期帶有左翼色彩的零散的文論,魯迅早期的系統(tǒng)性的詩學(xué)受到嚴(yán)重忽視和誤讀。在看似熱鬧的魯研界,其實是冷熱不均的,作為啟蒙小說家、左翼作家和文論家的魯迅受到過多的關(guān)注,而作為詩人、詩學(xué)理論家以及作為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和詩學(xué)奠基者的魯迅則被邊緣化了。雖然新世紀(jì)以來這種失衡狀況有所改觀,但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
早在1907、1908年,青年魯迅以其慧心精思,先后寫下《科學(xué)史教篇》、《文化偏至論》、《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詩》、《破惡聲論》等諸篇思想文本。這些文本高屋建瓴、體大慮周,以當(dāng)時最具現(xiàn)代性、國際性的視角,觀照人類文化史特別是中國文化史的興衰變化,對種族、國家、科學(xué)、宗教、人文、詩歌等諸多議題提出振聾發(fā)聵的見解。雖然這些文本的論題各異,卻有共同的題旨貫穿其中,可以一言以蔽之,日“根柢是人……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w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認(rèn)為,與那些輇才小慧之徒或干祿求利之輩所掇拾的“枝葉”相比,這才是抓住了“根柢”。那么何以立人?首先在立“心”,在魯迅看來,中國的危機(jī)在根本上是“心”的危機(jī),因此魯迅的啟蒙訴求也就成為對“心”的訴求。那么何謂“心”?魯迅并沒有為此下一個定義,總觀五篇思想文本, “神思”、“圣覺”、“內(nèi)曜”、“心聲”、“性靈”、“意力”、 “精神”等等表示心靈的概念貫串其中,大體上是在一種較寬泛的意義上指示真實無偽的情感、自由無礙的心智,獨(dú)立無依的人格和充沛強(qiáng)健的生命力。鑒于“心”的概念的核心地位,由此,我們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把魯迅早期詩學(xué)稱之為“心論詩學(xué)”。
魯迅極其重“心”,認(rèn)為“內(nèi)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發(fā)于孟春,而百卉為之萌動,曙色東作,深夜逝矣”。雖然人和世間萬物一樣,都可能受到外界影響而改變自己情狀,但只有人能夠做到“天時人事,胥無足易其心,誠于中而有言”,這樣,“聲發(fā)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這里的邏輯是,人有“心”才“有己”,人“有己”才能夠強(qiáng)大;“人各有己”,則整個社會才有覺醒的可能與走向強(qiáng)大的希望。維新從“心”開始,這正是魯迅的維新和啟蒙思想異于當(dāng)時那些急功近利的新學(xué)之士的獨(dú)特處,也是他的深刻處。
在魯迅的觀念中,民族與文化的興衰俱與“心”的得失存亡息息相關(guān):“蓋人文之留遺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秘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其聲度時劫而入人心,不與緘口同絕;且益曼衍,視其種人。遞文事式微,則種人之運(yùn)命亦盡,群生輟響,榮華收光;讀史者蕭條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記,亦漸臨末頁矣。”“心”之發(fā)即為“心聲”,發(fā)于語言文字即為詩歌(文學(xué))。作為“心聲“的詩歌是一個民族人文昌旺的表征,也是遺留后世的最寶貴遺產(chǎn)。因此;詩歌(文學(xué))的盛衰也就與民族的盛衰相表里。魯迅例舉印度、以色列、伊朗、埃及等文明古國,這些國家在古代均文化發(fā)達(dá),民族昌盛,在詩歌(文學(xué))方面或有瑰麗幽復(fù)的史詩、或有美妙絕倫的抒情詩篇、或有幽邃莊嚴(yán)的文章,然而一旦“人種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聲,漸不生于彼國民之靈府” “燦爛于古,蕭瑟于今”。
因此,絕不能沉醉于祖先所創(chuàng)造的過去的輝煌中,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而“欲揚(yáng)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fā),每響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非然者,口舌一結(jié),眾語俱淪,沉默之來,倍于前此。蓋魂意方夢,何能有言?即震于外緣,強(qiáng)自揚(yáng)厲,不惟不大,徒增欷耳”。通過“審己”、“識人”、“比較”,在世界文明的高度來反觀自己的處境,從而在自我心靈中激發(fā)出“自覺”意識(隱曜),也即一種主體精神。以這種主體精神為支撐而發(fā)出的“自覺之聲”,就是一種真實無偽、強(qiáng)健有力的“心聲”,這種“心聲”能夠動人心魄,能夠喚起沉睡的國民之魂,促使他們走上向上之路,從而把“沙聚之國”變?yōu)椤叭藝薄R浴靶穆暋睘榧~帶,魯迅就把民族與詩歌(文學(xué))的命運(yùn)聯(lián)結(jié)在一起。
在魯迅看來,能夠發(fā)出這種“力足以振人”的“心聲”的詩人,無疑不是那種媚俗附勢、哀樂不從己出,或淺吟低唱、愛好“平和”之音的詩人,而是那種“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的詩人,這些詩人“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wù)吲d起,爭天拒俗,而精神復(fù)深感后世人心,綿延至于無已”。雖然那些“平和之民”會對他們的聲音感到恐懼,但那些“生活兩間,居天然之掌握,輾轉(zhuǎn)而未得脫者,則使之聞之,固聲之最雄桀偉美者矣”。魯迅把這類詩人稱之為“摩羅詩人”。“摩羅”即魔鬼,撒但。魯迅以此命名這派詩人,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詩人獨(dú)立不倚、我行我素的行為方式常遭受權(quán)力的壓制和流俗的忌恨,從而把這些詩人目為撒但,比如拜倫;而這些詩人也常在撒但形象上尋找身份認(rèn)同,作品常歌頌撒但。另一方面,撒但形象非常準(zhǔn)確地表征了摩羅詩人的矛盾處境: “上則以力抗天帝,下則以力制眾生,行之背馳,莫甚于此”。魯迅正從這一矛盾中論證了摩羅詩人行為的崇高性:“顧其制眾生也,即以抗故。倘其眾生同抗,更何制之云?”。撒但對神權(quán)的反抗不是為了代替神權(quán),而是為了眾生的自由與人道;對眾生的抗拒則是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摩羅詩人正與撒但同:“故既揄揚(yáng)威力,頌美強(qiáng)者矣,復(fù)日,吾愛亞美利加,此自由之區(qū),神之綠野,不被壓制之地也。……壓制反抗,兼以一人矣。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通過這樣的論證,不但摩羅詩人作為道義英雄的形象被揭示出來,而表現(xiàn)為“揄揚(yáng)威力,頌美強(qiáng)者”的“摩羅詩力”也被賦予了道德的和美學(xué)的合法性。“摩羅詩力”不但是發(fā)于“內(nèi)曜”的至誠無偽的“心聲”,而且是充滿道義力量的心聲,比起那些只關(guān)乎一己悲歡的“心聲”,具有更強(qiáng)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價值。
由此,魯迅提出了一個文化和詩歌(文學(xué))的評價標(biāo)準(zhǔn):攖人心。真正的詩人,正是“攖人心者也”。因為“凡人之心,無不有詩,如詩人作詩,詩不為詩人獨(dú)有,凡一讀其詩,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無之何以能夠?惟有而未能言,詩人為之語,則握撥一彈,心弦立應(yīng),其聲激于靈府,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qiáng)力高尚發(fā)揚(yáng),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魯迅展開了對中國文化衰落的反思,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在總體上都是“不攖”,首先是道家:“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于太平”。但這顯然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幻想,因為“進(jìn)化如飛矢,非墮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飛而歸弦,為理勢所無有”。其次以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治者和庶民,其理想也在“不攖”:“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 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jìn)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這種“不攖”的文化傳統(tǒng)心須對詩歌“設(shè)范以囚之”:
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后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qiáng)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繇于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輾轉(zhuǎn)不逾此界。其頌祝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yīng)蟲鳥,情感林泉,發(fā)為韻語,亦多拘于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
一方面要求詩歌志從己出,另一方面要求詩歌持人性情,數(shù)千年來,中國正統(tǒng)詩學(xué)就一直在儒家人倫真理的牢籠內(nèi)打轉(zhuǎn),騰挪閃躲,左沖右突,卻從來沒有實現(xiàn)真正的突破;盡管這個牢籠的內(nèi)部空間有時會放大些,但它所許可的自由度幾乎從來沒能讓心靈真正酣暢淋漓地表達(dá)過。詩學(xué)觀念上的這個牢籠已經(jīng)內(nèi)化化詩人的自我規(guī)訓(xùn),在無形中規(guī)范著詩人的寫作。甚至當(dāng)他們避開政治和社會題材而寄情于自然山水時,這個規(guī)訓(xùn)依然在起作用,讓他們不能發(fā)出真正發(fā)乎本心的吟唱。至于違反常俗的聲音就更不可能出現(xiàn)了。
魯迅敏銳地抓住了中國傳統(tǒng)詩學(xué)觀念的內(nèi)在癥候。概括地說,這個癥候就是對“心”長時期的羈勒,導(dǎo)致詩人無力發(fā)出自己至誠無偽的“心聲”;即使發(fā)出的,也是孱弱無力的聲音,不能夠展現(xiàn)生活的“真美”,也無以攖國民之心。同時,這個癥候也是整個民族機(jī)體的癥候,詩歌觀念上的功利與粗暴及其導(dǎo)致的詩歌實踐的卑弱無力,使國家和社會失了精神上的黃鐘大呂,國民心靈充斥實利,喪失樸素?zé)嵴\和血性,變得一盤散沙。由此國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與孱弱。魯迅論詩不像王國維那樣,主要從詩歌內(nèi)部著眼,而是把詩歌與國家、民族的命運(yùn)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時時不忘其啟蒙使命。他觀念中的詩歌往往是廣義的,是真誠無偽、剛健雄大的生命精神的象征;詩人也往往是精神界戰(zhàn)士的代名詞。
但魯迅也并非像此前的梁啟超那樣,簡單而直接地把文學(xué)視為政治變革與思想啟蒙的工具,而是充分認(rèn)識到文學(xué)的本質(zhì)特征以及審美與功利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他首先指出“美術(shù)”(藝術(shù))的本質(zhì)在于使人“興感怡悅”,“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yè)之券”。但“其為用決不次于衣食,宮室,宗教,道德”,人的生活有了“文章”(文學(xué))才會具足圓滿,何以故?因為“文章”能夠“涵養(yǎng)人之神思”,也即灌溉人的心靈,這正是一種“不用之用”。其次魯迅指出文學(xué)還有一特殊作用,即“啟人生之秘機(jī),而直語其事實法則,為科學(xué)所不能言者”, “所謂秘機(jī),即人生之誠理是已。此為誠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學(xué)子”。“誠理”也即真理,但人生的真理與自然界的真理不同,更為復(fù)雜玄妙,非科學(xué)的方法所能揭示。而文學(xué)“雖縷判條分,理密不如學(xué)術(shù),而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文學(xué)不是通過推理的、說教的方式,而是通過感性、直觀的方式揭示真理,魯迅的這一認(rèn)識正觸及到文藝的本質(zhì)特征。
根據(jù)這一認(rèn)識,魯迅對“據(jù)群學(xué)見地以觀詩者”的觀點(diǎn)作了分析。這種觀點(diǎn)的主旨是文章與道德相關(guān),認(rèn)為詩的主要因素是所謂“觀念之誠”,“誠”即是“詩人之思想感情,與人類普遍觀念之一致”,獲得“誠”的方式就是掌握廣泛的經(jīng)驗,所據(jù)經(jīng)驗經(jīng)驗愈廣,則詩的意義愈廣。而“所謂道德,不外人類普遍觀念所形成。故詩與道德之相關(guān),緣蓋出于造化。詩與道德合,即為觀念之誠,生命在是,不朽在是。非如是者,必與群法僢馳。以背群法故,必反人類之普遍觀念;以反普遍觀念故,必不得觀念之誠。觀念之誠失,其詩宜亡。故詩之亡也,恒以反道德故。然詩有反道德而竟存者奈何?則日,暫耳”。這種詩學(xué)觀念把外在于主體的道德視作詩歌核心因素,詩的價值即在于傳達(dá)道德。道德的形成本來有極其復(fù)雜的原因,經(jīng)濟(jì)、政治、民族、文化、性別等各種因素?fù)诫s其中,并非單純的人類普遍經(jīng)驗的結(jié)晶。先驗地把道德本體普遍化,使之上升到真理的地位,往往是為某種權(quán)力做推手。把詩歌的價值定位于傳達(dá)外在道德,其目的往往是為了限制詩歌“攖人心”的危險力量,以維護(hù)某種權(quán)力的穩(wěn)定;同時也是企圖對詩歌加以改造,以服務(wù)于某種權(quán)力。魯迅認(rèn)為,中國正統(tǒng)儒家的“無邪之說,實與此契”。雖然魯迅沒有對這種觀點(diǎn)加以具體的理論批駁,但通過對這種觀點(diǎn)內(nèi)涵的概括,將其邏輯上的悖謬展示得一目了然。
魯迅早期的心論詩學(xué)并非一般所認(rèn)為的,是魯迅思想發(fā)展歷程中的“不成熟”階段的產(chǎn)物,而是體現(xiàn)了極為深刻的文化和文學(xué)智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概括地說,首先,魯迅早期詩學(xué)是中國文化、文學(xué)(詩歌)現(xiàn)代化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體現(xiàn)了這一進(jìn)程的質(zhì)的飛躍。雖然魯迅的這些早期文本是用古奧的文言寫成,所用概念也多借自于中國古典文化和詩學(xué),比如“心聲”、“神思”、“至誠”、“真美”等,但其表達(dá)的思想內(nèi)涵卻是全新的,基本上突破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詩學(xué)的古典形態(tài)。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魯迅的這些早期思想文本標(biāo)志著中國現(xiàn)代詩學(xué)的真正的起點(diǎn)。可惜直到今天還很少有人認(rèn)識到這一點(diǎn)。其次,魯迅具有強(qiáng)烈的理論主體意識,對于一切思想資源都采取“拿來主義”、“六經(jīng)注我”的方式,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是如此,對西方思想也是如此;當(dāng)中西理論和概念不敷其用時,他就采取自造的方式,比如“摩羅詩力”一語就出自他的獨(dú)創(chuàng),以這一概念為中心,他建構(gòu)起全新的詩學(xué)觀念體系。因此他的詩學(xué)觀念不是某種思想或理論的注腳,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和全然現(xiàn)代性的,這是其古奧的文言所遮掩不了的。魯迅的這一理論姿態(tài)直到今天都非常具有啟示意義。自1980年代以來,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到西方理論話語的魔沼當(dāng)中,幾乎成了后者的奴隸,基本上喪失了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重溫魯迅的早期思想文本,或許能夠使們對今天的理論話語困境有著更清醒的認(rèn)識,并激發(fā)我們的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最后,魯迅早期詩學(xué)以“心”為核心范疇,通過“心”溝通了文學(xué)(詩歌)與人生,審美與功利,在它們之間做出恰當(dāng)?shù)钠胶狻t斞敢环矫姹袕?qiáng)烈的國家、民族與社會關(guān)注,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認(rèn)同那種以道德為詩之價值核心的觀念。他沒有像同時代的諸多論者那樣淺薄而偏頗地純粹以功利價值來衡量文學(xué),但也沒有簡單地否定詩歌的功利性。他指出詩歌具有“無用之用”的特點(diǎn),也即詩歌必須排除直接的功利目的,以“直語”的方式去“攖人心”,去涵養(yǎng)人的神思,開啟人的靈明,使人成為“自由”與“人道”的真正的人。“自由”與“人道”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形態(tài),既符合于人生理想,又符合于審美規(guī)律,因此,能夠把文學(xué)與人生、審美與功利恰到好處地聯(lián)結(jié)起來。魯迅的這一“心學(xué)”觀充分汲取了中西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美學(xué)與詩學(xué)理論資源,并加以融匯貫通,建構(gòu)起一個既具有深刻的哲學(xué)基礎(chǔ)、又具有極強(qiáng)的現(xiàn)實針對性的詩學(xué)體系,不但極富詩學(xué)思想史的意義,對當(dāng)代的詩學(xué)理論和詩歌實踐也極具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