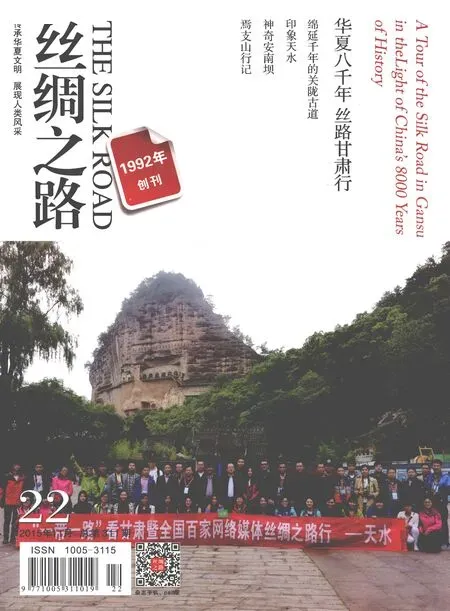綿延千年的關隴古道
文圖/ 張振宇
1000多年前,玄奘大師跟隨秦州僧人孝達,沿著古老的關隴古道,翻越隴山,抵達秦州。至此,大師西行求法的萬里行程邁出了最為關鍵的一步。
隴山,萬里絲路上的第一座山脈。而翻越隴山的道路則為關隴古道,這是一條讓后人終身銘記,并留下了無數難忘詩篇的古道。
今天,再次踏上關隴古道,我們不僅有了新發現,而且對絲綢之路產生了更為深刻的感受。
秦人走廊
夏秋時節的關山是最美麗的。山山岔岔綠得耀眼,紅得似火,黃得璀璨。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季節,我們再訪關山,尋覓古道的蛛絲馬跡。
2015年9月,由中國甘肅網承辦、《絲綢之路》雜志社協辦的“一帶一路看甘肅暨2015全國百家網媒絲綢之路行”采訪團一行60多人走進天水,就當地人文歷史、旅游名勝等進行了深入采訪,從而對鮮為人知的關隴古道有了更深的了解。
今天,人們將2100年前張騫鑿空西域視為絲綢之路開通的標志。其實不然,張騫出使西域只能算是正式開通絲綢之路。實際上,至少早在幾千年前,絲綢之路就已經開通。上海交通大學葉舒憲教授認為,絲綢之路的前身為玉石之路,玉石的對外貿易歷史比絲綢更為悠久。他結合對甘肅玉礦的考察提出了“玉出二馬崗”之說,認為西周生產大量玉禮器的原料產地就是馬銜山、馬鬃山地區。并且,他把絲綢之路即有文字以來的傳統視為“小傳統”,把先于和外于文字記錄的傳統視為“大傳統”,即玉石之路。這說明,有著2000年歷史的絲綢之路是由4000年之久的玉石之路發展演變而來的。
絲綢之路始于長安,往西沿涇河、渭河而行,后在涇川和天水兩地之間擇其一繼續西行。其中,走天水要翻越隴山,然后經蘭州,穿過河西走廊,進入西域。
隴山是聳立于關中平原西部,甘、陜、寧交界處的一座山脈,實與六盤山為同一條山脈,其首伏寧夏,尾落甘陜,自北向東南逶迤而下。北隴山即六盤山,也就是涇河的發源地;南隴山即關山,位于張家川境內,是一條長約200公里、寬五六十公里的山嶺。古人將兩座山統稱為隴山、隴坂、隴坻或關山。隴山的南邊是渭河峽谷和高峻的秦嶺,交通極為不便,因此來往的商人都必須翻越隴山。它是古絲綢之路西出長安過漢中之后的第一道屏障,只有翻越了它,才能到達更遙遠的河西走廊。
天水境內的古道,至少在8000年前的大地灣文化時期就已經開通。5000年前,天水境內古道已和江南的古道連通,原產自江南的水稻被傳到天水渭水流域。后來,以隴南為根基的秦人,出于政治軍事的需要,對隴山古道進行了大規模修整,最終形成了可通大車的大道。
可以說,不論是秦人的西來,還是東出,都與隴山古道密不可分。秦人不論是翻越關山走關隴古道,還是穿行渭水河谷過秦人走廊,都是關隴古道早期的使用者之一。
渭河曾養育了遠古先民,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了眾多古遺址,有村落,也有墓葬。聞名遐邇的大地灣遺址就坐落在渭河支流的葫蘆河邊,而渭河上游所流經的地域,也就是上古時期人們所說的成紀地區,曾經的部落首領伏羲就生活在這個區域。
距今3000年左右,周武王率眾討伐殷紂王,并把殷紂王的兒子武庚分封在山東曲阜一帶。誰知武庚卻策動管叔和他一起造反,就造成了西周初年的“武庚之亂”。這次戰亂平定后,一部分造反者被西遷到了甘谷渭水河邊的朱圉山邊。之后,秦人就在融合中不斷發展壯大,最后席卷天下。
當時,秦人東進西來的通道大體有三條。第一條是在張家川一帶翻越關山的關隴古道。秦人是非子之后,非子由于為周人養馬有功,從而獲得獨立于大宗的資格,后來他們翻越隴山在今天張家川的馬家塬、秦家源一帶繁衍生息。第二條是秦人走廊,這條通道沿渭水的南北兩側而行,進出關隴,通道沿渭水河谷延伸,比較單一,兩側是高山,中間是河流,其早期的使用開發者主要是秦人。2014年底,長期致力于絲綢之路和西北史地研究的著名文化學者王文元首次將這條古道稱為“秦人走廊”。第三條古道是連通張家川馬家塬秦人活動地和禮縣大堡子山秦人中心的南北向通道,這條古道至今不為人所關注。
我們應該感謝秦人,他們不僅為關隴古道的最初開通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艱辛勞動,也使這條數千年來生生不息的古道至今仍散發著強大的生命力。

關隴古道示意圖
古道遺跡
自周秦至漢唐再至明代,在此間長達近3000年的歷史歲月中,關隴古道一直是關中通往西域的交通紐帶,隴山也成為防守關中的第一道屏障。因而,人們將隴山視為隴右要沖、關中屏障、軍防重地。從軍事戰略上說,守長安必守隴右,守隴右則必須掌控河西走廊,阻斷青藏高原與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相互聯系。要守住河西走廊,就要看護好西域。大唐晚期,河西、隴右失守,吐蕃逼近隴山一線,游牧民族的騎兵距離長安只有200里,導致大唐王朝一蹶不振。
按照學術界對絲綢之路東段北、中、南三線的劃分,關隴道屬于東段中線,也被人們稱為隴西段。漢武帝元鼎三年(前109)在平襄縣(今通渭)設天水郡,出于政治、軍事的需要,隴山古道被再次進行整修,路線大體如下:從長安到隴縣,出大震關翻越隴山,在張家川馬鹿南折經清水,過天水(古秦州),沿渭河西行經甘谷(冀縣,東漢漢陽郡治)、武山、隴西(古襄武)、渭源、臨洮(古隴西,又稱狄道),此后分為兩路,一路可走金城,一路渡洮河,再經臨夏(古河州、枹罕),在永靖渡黃河出積石山經樂都至青海西寧,然后經大斗拔谷(扁都口)到張掖。這條路的隴山段開通于漢,盛于隋、唐,修建標準較高,石板路至今尚存。
絲綢之路中線是漢代重要的軍事運輸線和商道,即便在北有匈奴、南有羌氐侵擾之時,這條路也是最安全的。它是到達蘭州的捷徑,唐初玄奘大師就是在秦州僧人孝達的陪同下走這條路線的。
據考察,張家川一帶的關隴古道大體有兩條線路:一條是通過固關,翻越隴山,到達分水驛(位于今張家川縣馬鹿鄉東北10公里的老爺嶺),沿馬鹿、閆家店、弓門寨、張川鎮、龍山鎮、秦安隴城西行經秦安縣到達天水;另一條是繼續沿弓門寨(今恭門鎮)、樊河,經清水縣城再到天水。在張家川縣與陜西隴縣之間長約200里的路程中,現遺存有依稀可辨寬3米的原始古道。這條道路在晚唐時為抵御吐蕃人曾遭受了大規模破壞,或道中植樹,或巨石塞路,不復往日勝景。
隨著中央王朝向西開拓步伐的加快,隴上古道沿線的設施逐漸完善。據記載,漢武帝時期,隴山古道沿線“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寨”,建立了嚴密、完善的驛置體系和軍事防御通訊系統。隋朝時期,由于隋煬帝西巡的關系,關隴道又一次得到大規模拓建,達到了能夠通過御駕的標準。
元初,在關隴道的基礎上又開通了咸宜關,商貿更加繁榮。如元泰定二年(1325)一月至七月,通過關隴道的使臣多達185人,平均每天通過一隊,用馬840匹,由此可見當時盛況。明清兩代是關隴古道的曲折發展和衰落時期,由于海路大開,北路暢通,關隴道逐漸被冷落。
至今,這條古道沿線仍有大量遺跡。行走在關隴道上,一件件古拙的石雕、一個個殘破的條石、一條條車轍壓痕、一座座關隘舊址、一個個別有風韻的古鎮,見證了曾經的輝煌,也成為數千年絲路文明的最好注解。
出陜西隴縣不久就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關隘大震關,這是翻越隴坂的一個重要關口。關于大震關之名的來歷,有這樣一個傳說:漢武帝劉徹在鳳翔祭祀五帝后,準備繼續西行,誰知卻在翻越隴山時發生了意外,天氣突變,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此關口因而被稱為“大震關”。大震關后來被安戎關代替。安戎關原名定戎關,是唐宣宗大中六年(852)由隴州防亂御使薛逵移筑,而修建該關的目的是防御吐蕃人進攻。
絲綢之路上,名叫張棉驛的地方有好幾處,我們這里要說的是張家川縣北部的張棉驛。張棉據說是張騫的兒子。張騫出使西域,為匈奴所扣,匈奴單于見其一表人才、有膽有識,便將公主許配于他。后來,匈奴發生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翻越隴山時,為保全妻兒,便將公主和孩子安置在張家川一帶。漢武帝召見張騫后,見其萬里出使,不失持節,便封為博望侯,并賜予張騫長子張棉亭驛官職,建立驛站。
離張棉驛不遠的長寧驛也有其來歷。從張家川縣城出發,過恭門鎮,走城子村,再翻越一座大山——小嶺子梁,就是馬鹿鎮了,長寧驛距馬鹿鎮約有10公里。長寧驛是元、明、清時期關隴道上的重要站點,從這里向西南可達清水,向東翻越隴山,過南寨鋪,則能經咸宜關入關中,古有“隴山第一驛”之稱。而如今,它寂寂無名,如同一只貓靜悄悄地躲在隴上一隅安度歲月。
眾多遺跡見證了古人翻山越嶺堅韌不屈的開拓精神,也演變為今天我們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關隴古道遺存至今的“沙發石”
詩意古道
歷史文化名城天水,誕生了人文始祖伏羲及女媧,大地灣文化、秦早期文化、三國文化、石窟文化等更是在此交相輝映。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和延展,天水很快成為絲綢之路上千古不變的必經通道和中西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橋梁。
關隴古道,連接著關內八百里秦川和天水,曾經車流陣陣,人聲鼎沸,異常輝煌。幾千年來,在這條古道上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秦人的東進,西漢張騫開拓西域,東漢劉秀滅隗囂,諸葛亮留下空城計,唐玄奘西天取經有傳奇。到了唐代,關隴古道更為興盛,成為一座散發著詩意的山脈、流淌著詩歌的古道。
隴山是秦人東進中必須翻越的大山,最早的隴山詩歌有《詩經·秦風》中的篇章,其中《車鄰》、《小戎》、《蒹葭》、《駟驖》四篇是秦人崛起西垂的見證。隋唐時,隴山詩歌大放異彩,李白、王維、岑參、高適……他們如繁星般的創作讓人為之驚嘆。唐以后,隴山逐漸沉寂下來,詩歌也漸漸遠去。
“隴板滿目皆千仞,唯有關山以秀媚”、“西上隴坂,羊腸九回”、“銜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隴頭征戍客,寒多不識春”、“塞外飛蓬征,隴頭流水鳴”、“隴水不可聽,鳴咽令人愁”、“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如今,這些詩句依舊讓我們惆悵不已。
《元和志·秦州》載:
隴坂九回,不知高幾里,每山東人西役,到此瞻望,莫不悲思。
無數文人墨客在這里留下了詩篇,王維雖沒有到過隴山,但也寫下了《隴頭吟》。杜甫《秦州雜詩》第一首嘆: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遲回渡隴怯,浩蕩及關愁。
水落魚龍夜,山空烏鼠秋。
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此外,還有白居易的“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
據考證,以前隴山頂有古建筑遺址,疑為隴頭或分水驛。據說古代關東人從此登隴山,東望秦川如帶,西望隴坂九回,頓生離家去國之感。北朝民歌《隴頭歌辭》其三這樣寫道:
隴頭流水,嗚聲幽咽。
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這首詩為后人留下著名詩歌題目“隴頭水”、“龍水吟”,并最終奠定了隴頭詩歌悲涼、凄慘、愁苦、思鄉的風格。
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岑參在翻越關山時就為宇文判官寫過一首名為《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詩。從詩的首句“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可以看出,唐代的關山古道不但有關隘,而且還設有不少驛站。
關隴古道已成為遠去的記憶,只能供人們追尋歷史的腳印。如今,“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關(中) 天(水) 經濟開發區的建設和現代交通的快速發展,大大縮短了關隴兩地間的距離,這為天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