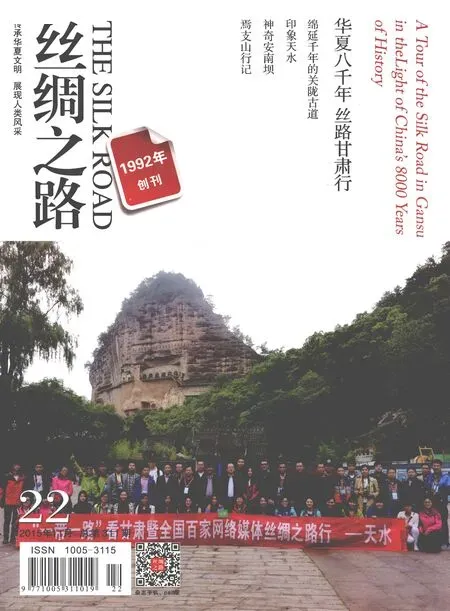敦煌,千年前也許我已來過
文圖/ 王惠芳
漫漫黃沙,無法遮掩她夢幻般的倩影;迢迢旅途,阻擋不住人們向往的腳步。心心念念、魂牽夢縈的是敦煌,是那些柔美的線條、濃烈的色彩,是那份虔誠的信仰、慈悲的情懷,是那座藝術的寶庫、文化的殿堂。陽關、玉門關在這里孤獨守望,莫高窟在這里綻放魅力,雅丹地貌鬼斧神工,鳴沙山、月牙泉靜靜訴說著美麗的過往。
敦煌之美,足以震顫每個人的靈魂。
自20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后,一支支駝隊來來往往,踏過歷史的煙塵,一度給敦煌帶來繁華似錦的景象。難以想象,如今滿目荒涼的戈壁,曾經歌舞升平、燈火輝煌。作為絲綢之路必經之道的敦煌,在唐代達到了鼎盛階段。曾幾何時,布匹、鐵器、藥材、金銀器等各種商品琳瑯滿目,陽關甚至可以同時容納上萬人居住、停留。
而今,玉門關也只留下斷壁殘垣,讓人空嘆“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蒼涼。陽關城外那起伏的沙丘,似乎還在吟唱“陽關三疊唱無休,一句離歌一度愁”的眷眷離愁。
公元366年,游僧樂僔受到佛光的感悟,在鳴沙山斷崖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閉關修行,從此便開啟了莫高窟夢幻佛宮的大門。在其后1000多年的時間里,歷經十六國時期的北涼、南北朝時期的北魏、西魏和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和元等近十個朝代,叮叮當當的開鑿聲響徹敦煌,身著炫麗衣飾的佛菩薩彩塑、曼妙靈動的壁畫人物、不可思議的佛國世界在能工巧匠的手下逐漸誕生。
微閉的雙目、慈祥的淺笑、莊嚴的姿態慰藉了多少商賈、游乞、達官顯貴;數以萬計的經卷、包羅萬象的壁畫、延續千年的歷史吸引了多少學者、專家、學子、民眾;建筑、雕塑、考古、繪畫,多少學科在這里汲取營養,孕育新生。
然而,在這里,朝代的更迭、時光的變遷所留下的印記如此令人唏噓。在莫高窟的壁畫上,本應呈肉粉色的佛像面部,有些已經變黑,我們只能去想象舊時那栩栩如生的姿容。脫落的金箔、毀壞的塑像、風化的前殿門廊、殘缺的壁畫,無不透露著時光的殘酷,更不用說藏經洞了。數萬卷經書遺落在世界各處,我們該痛恨曾看守洞窟的愚昧道士王圓箓,還是該痛恨那些掠走經書的西方探險家?其實最恨的,也許還是當時政府的無能和冷漠。如果可以,我寧愿藏經洞從未打開過,至少,敦煌的珍寶可以留多一些給子孫后代。
所幸,身處大漠深處的莫高窟,竟然在“文革”的浩劫中躲過了一難,否則,我們哪里還尋得到瘦骨清像的北魏遺韻、流光溢彩的盛唐氣象,哪里還看得到1000余年的民情風俗、建筑服飾。莫高窟被譽為“沙漠中的美術館”和“墻壁上的博物館”,能走進它,踏過秦磚漢瓦,仰望大唐佛像,感受光陰變幻,體驗輝煌藝術,何其幸哉!
今天,當我們在莫高窟漫游巡禮,面對傳承了1600多年的2000多身塑像、4.5萬多平方米壁畫時,任七尺男兒的心也會變得柔軟,縱橫捭闔的野心家也會變得靜默,驕傲任性的公主也會變得謙卑。
如莫高窟第254窟《薩埵太子舍身飼虎圖》,描繪了薩埵王子為了拯救快要死去的母虎和幼虎,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身飼虎的故事。畫中,薩埵王子見餓虎連啖食的力氣都沒有,便爬上山崗,用竹子刺破自己的喉管,又跳下山崖,將自己的肉體摔碎以便餓虎食用。
再如莫高窟第220窟《西方凈土變》,畫中寶蓋旋轉,彩云繚繞,亭臺樓閣,隨意自在。綠波浩渺的七寶池,盛放的各色蓮花,不奏自鳴的天樂,莊嚴慈祥的阿彌陀佛、觀音、大勢至菩薩,展現出極樂世界無比美妙的圖景。莊嚴、清凈、平等、慈悲的佛教文化感染著每一位來此瞻仰的遠方來客,漂泊的靈魂在這里找到了歸宿,人性的善良、智慧之根再一次被熏陶、澆灌。
敦煌,千年前也許我已來過。
那時候,我也許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三步一叩,九步一拜,全身匍匐在粗糙的地面,心中的敦煌承載著我全部的期望和熱情。我變賣了所有的家當,只為在敦煌為佛像貼上金箔,為菩薩描摹色彩,為佛殿點一盞油燈,添一縷檀香。
那時候,我也許是駝隊的一名商人,在陽關換取通關文牒,將中原燦爛的文明傳播到塞外,多少次風沙迷了眼睛,多少次饑渴難耐陷入絕境,多少次踏過野獸和游商的尸骸,行走在這條希望與絕望交織的漫漫長路上,念著佛號壯膽前行。
那時候,我也許是月牙泉的一滴泉水,在細細的沙子下緩緩流淌,隨時可能化作煙塵了無蹤跡。當月夜的鳴沙山灑滿清輝,孤獨的駝鈴一聲聲傳來,我用自己的生命潤濕著旅人的疲憊身軀,留給世人撫慰和詩意。
但終究,我也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如同敦煌那曾經的熱鬧繁盛。而敦煌是不會寂寞的,至少現在,她充盈著我們的生命,活在贊嘆和艷羨的目光里,哪怕在千秋萬代之后被黃沙掩埋,也遮蔽不了她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