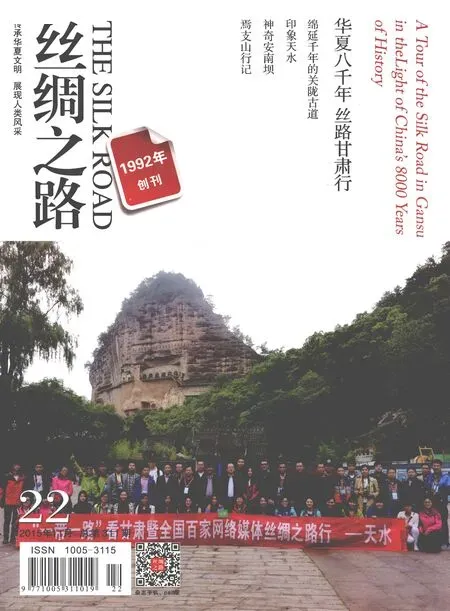印象天水
文圖/ 張光明
應(yīng)“一帶一路看甘肅暨2015全國百家網(wǎng)媒絲綢之路行”活動主辦方中國甘肅網(wǎng)的邀請,我作為長城網(wǎng)的代表,于9月下旬來到甘肅。
作為一個從未到過西北的人,甘肅留給我的最初印象是干旱,甚至黃沙漫漫。到了天水之后,我徹底顛覆了這種印象,因為這里的天青藍澄澈,水甘甜清冽,自然風光秀美多姿。在這里,我們拜謁了“華夏第一廟”,即莊嚴肅穆且為全國規(guī)模最大的伏羲建筑群的伏羲廟;在這里,我們登臨南郭寺,即詩圣杜甫吟出“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的地方;在這里,我們瞻仰了中國四大石窟之一,有“東方雕塑藝術(shù)館”美譽的麥積山。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樣的人文水土孕育了中華人文的始祖伏羲,從而開啟了中華民族文明的曙光?在天水的采訪使我眼界洞開。天水,位于隴東南,陜、甘、川三省交界處,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渭河支流籍河橫穿境內(nèi),兼具北國風光的雄渾和江南水鄉(xiāng)的婉約。8000年前,伏羲始祖及其部落生活在比現(xiàn)在更為溫暖的環(huán)境中,周邊水草豐美,林深地沃,節(jié)令分明。于是,他觀象于天,察法于地,取火種,正婚姻,教漁獵,用陰陽八卦來解釋天地萬物的演化規(guī)律和人倫秩序。正是天水這一寶地,孕育了生生不息的華夏文明,其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也使文明的種子得以茁壯成長。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不必說西戎的馬蹄聲碎,不細說秦人的勵精圖治,轉(zhuǎn)眼到了秦末漢初,這方沃土有了現(xiàn)在的名字——天水。關(guān)于天水的得名還有一個傳說。相傳,一天夜里,狂風大作,電閃雷鳴,地上裂開一條縫,天上的水傾盆而下,注入裂縫形成“天水湖”。天水湖的水甘冽醇厚,造福了一方百姓。后來,這個傳說被漢武帝聽到,遂將湖旁新設(shè)的這個郡命名為天水郡。
往事越千年,不細說難封的飛將軍李廣,更無奈壯志未酬的姜維,天水得名800年后的唐朝,一位流浪詩人來到此地,城郭之南,白云腳下有一古剎,是他心向往處,此地名為南郭寺。寺內(nèi)“蒼柏翠槐蔥蘢成蔭,殿宇禪院交相輝映”,西院有老柏,鐵干銅枝,壯偉瑰奇,杜甫因此寫下了“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詩人哪里知道,千百年后,他的詩句依舊被人傳誦,他也已被尊為“詩圣”,而詩中提到的老樹歷經(jīng)2500年,依然形如虬龍,不動聲色地生長著。樹本無言,但也披紅掛彩,作為文明的傳承象征被頂禮膜拜。面對老柏,當時的杜甫也只能是小杜,南郭夜色曾映小杜,今日倚樹憶老杜,憑吊懷古,不由感嘆人生如蜉蝣,渺如滄海一粟,只有文明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提到天水印象,麥積石窟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因形似麥垛而得名。麥積山海拔不到1742米,站在山下,看著懸崖峭壁和造型各異的佛像,不由心生敬畏。麥積山石窟開鑿于公元4世紀的后秦時期,這里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佛教自西域東傳至此,并在這里生根、茁壯成長。后麥積山經(jīng)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各個朝代的不斷開鑿、重修,石窟造像也體現(xiàn)出了各朝代的特征。如北魏時期,以瘦為美,造型秀骨清像;隋唐時期,造像則豐滿圓潤。佛、菩薩、弟子、力士等塑像或在崖閣,或在走廊,不同朝代塑像同處一室卻毫無違和感,反而更凸顯出一種藝術(shù)之美,無論是巨像還是如拳頭大的小像,均神態(tài)莊嚴可敬,顏色華美不俗。
天水,是一個很難用簡單的詞匯來表述其魅力的地方。我試圖用一種文化脈絡(luò)來梳理它的歷史和山川:豐饒的天水滋養(yǎng)了人文始祖伏羲及其部落,四通八達的地理因素也促進了各族群的融合與發(fā)展,各種文明在這里交流、提升,共同孕育了深厚、開放、親切的文化底蘊。麥積山石窟便是天水文化開放交融、兼收并蓄的典型代表。
在整個的考察采訪活動中,除了秀美的景致,我們更能清晰地感覺到天水人民的熱情好客及其濃烈的家鄉(xiāng)自豪感。無論是伏羲廟的講解員劉復興,還是天水市的宣傳干部胡江,抑或是街頭巷尾擺攤的小販,提起自己的家鄉(xiāng)都是幸福滿滿,且不遺余力地向外界推介。我覺得這不是偶然,相由心生,天水的文化魅力可想而知。
昨天的天水,悠揚的駝鈴依然縈繞于耳;今天的天水,“花牛”蘋果的栽培種植已享譽海內(nèi)外。我相信,明天的天水依舊會延續(xù)“天河注水”的傳說,鐘靈毓秀,璀璨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