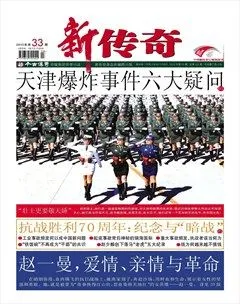底層少年“幫派化”背后的農村江湖
底層少年的幫派問題,不可能只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單元,更有著農村社會大環境和秩序的影響。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網站上發布《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為1.38億,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數已分別達2075.42萬和1294.73萬。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總數已占到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為未來中國脊梁的底層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筆者深入到中國西部一個偏遠村落——四川芥縣雍村所在的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中展開了為期兩個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觀揭秘鄉村底層孩子們所不為外知的日常“江湖”。
寄宿制學校如何成為少年幫派的土壤
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是一所寄宿制學校,全校200名學生來自云鄉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鄧老師兼任生活教師,負責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學關系來統一編宿。鄧老師認為,這種基于同班同學正式組織關系上的編宿,有利于舍友間形成群體內更為牢固的信任關系,并防止宿舍內打架、盜竊等惡性校園事件的發生。
事實上,被編于同一宿舍或相鄰宿舍中的學生們確實能夠因為同班同學關系而顯著降低在學校內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夠減少宿舍內群體間發生暴力沖突與財物丟失等事件。但鄧老師將這種“同班同學型”的編宿方式效果想象得過于完美。
很快鄧老師就發現不良后果:該編宿方式更容易發生團伙內部的共同違紀行為,例如熄燈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學相互間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話題,可以長時間聊天、打牌、喝酒、翻圍墻出校游泳或打游戲等等;也更容易發生團隊之間的相互違紀行為,例如高年級學生經常欺負低年級的學生,如強迫低年級學生給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強迫低年級學生夏天在生活老師沒在身邊時到自己宿舍給自己扇風,冬天則將低年級學生的被子強行搶來自己蓋,而低年級學生只能兩人甚至三人擠到一個床上彼此取暖睡覺等。
為了抵御高年級學生的欺負,低年級學生則施展各種“弱者的武器”以示對抗。其中一項就是建立所謂的“小幫派”,在小范圍內集體抗拒個體化的高年級學生,但“小幫派”很快也進一步刺激高年級學生組成“大幫派”來予以集體鎮壓。鎮壓的結果是進一步固化了“小幫派”內部緊密型的共同體關系,從而使“小幫派”逐漸突破宿舍和班級的組織邊界而匯合為反高年級學生欺負的“巨型幫派”。
“兄弟幫”:從被人欺負到欺負別人
“兄弟幫”的創始人之一、九年級男生李元元說,“兄弟幫”是他在讀七年級時成立的,起因是當時班上同學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和九年級的“霸王團”因為搶熱水打過群架,和八年級的“流氓會”因為晚上打呼嚕和講話也打過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級的同學模仿高年級的同學,建了一個“兄弟幫”。最開始是一個比較封閉松散的群體,成員都是自己班的同學,主要是防止同學被欺負。之后宿舍重新編排,“兄弟幫”就又陸續加入一些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的低年級同學。
李元元介紹,現在“兄弟幫”的規模大約維持在35人,其中九年級全班38個同學中就有24人,其他11人則分別來自八年級(7人)和六年級(4人),再低年級的就全部被清除了。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級同學所控制的“兄弟幫”事實上已經成為新的“欺負者”和“鎮壓者”。
李元元和同學們建立了一個QQ群,群名就叫做“行俠仗義——兄弟幫”,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50多人,其他低年級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幫”沒有明確的入幫或者退幫規則。李元元說,最開始大家都經常在一起玩鬧,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級同學說,我們有個“兄弟幫”,你加進來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平時誰要是挨欺負,“兄弟幫”其他成員都是要幫忙的,如果誰見死不救,就會被清出QQ群,就算退幫了。
另一位九年級“兄弟幫”骨干成員楊柳說,幫里的成員都要服從幫里的“大計”安排——必須每天都要有幫員出來違規與犯錯,以此不斷挑戰班主任老師。比如,今天我們就準備把垃圾桶直接丟到學校外邊去不拿回來了,昨天我們是故意打壞了后門上邊的那塊玻璃,前天是把粉筆全部折斷丟垃圾桶了……因為班主任老師對我們管的實在太苛刻了,把我們當“機器”一樣,我們要反抗!
這學期開學時選班長,在“兄弟幫”的推舉下,老大齊磊當選。班主任老師雖然很不爽,但是沒有辦法。楊柳為此很自豪:這就是我們“兄弟幫”的力量,齊磊就敢和老師對著干!
“兄弟幫”的組織功能在不斷地擴張,從最初僅僅對抗同輩群體,到后來逐漸對抗班主任老師,甚至于后來對抗學校制度。他們始終在強者與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轉換,而這種相互轉換使他們悄悄地完成了個體的社會化。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幫”欺負的其他“兄弟幫”則在隱匿中如春筍般不斷創生,他們大多數為學校管理者所不可見,但卻真實存在于像云鄉學校這樣的底層寄宿制學校中。在日常學習生活中運轉更為常規的非正式群體是:師徒制、親戚制和情侶制。
需要呼喚起人們對底層的更多關注與幫扶
學生“拉幫結派打架斗毆”,其實在每個人的“學生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像這一田野調查報告所反映的大面積出現的狀況,卻極其少見。
特別是較之于其他的“調皮”方式,拉幫結派的流行更具有某種象征意味。它往往可以追溯到一種心理安全感的缺乏,因為拉幫結派本質就是尋求一個共同體,免于外部傷害的過程。在過去,這種幫助的功能多由家庭、學校來完成。但在今天,隨著鄉村留守現象的普遍化與農村教育的弱勢,一些孩子不得不去尋求一種外在的保護體系和歸屬感,比如所謂的師徒制、親戚制、情侶制,并從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從常識和經驗看,底層少年的幫派問題,不可能只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單元,更有著農村社會大環境和秩序的影響。現代鄉村多被夾雜在轉型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傳統的公共生活和鄉土社會倫理都處于失序狀態,而新的秩序卻遠未生成。包括底層少年問題在內的鄉村問題都可以從鄉村的凋敝中找到答案。所以尋求解決之道,還需要從鄉村治理的角度入手。
此項田野調查的樣本學校,有75%的學生屬于留守兒童,而據保守統計顯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總數已占到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人數的四分之一。可見,解決留守的問題將有效緩解鄉村底層孩子的成長問題。留守問題之所以得以產生,社會其實已經不缺乏共識,如城鄉二元制下的社會福利政策割裂,兒童隨父母進城的渠道缺失等等。
因此,這方面的改革,應該加速推進,瞄準目標不放松。同時在教育資源的下沉和扶貧工作的落實上,應該創新思路,改掉大水漫灌的方式,實施精準化的扶貧,將幫扶落實到“人”的身上。
在城鄉二元結構短期內無法改變的背景下,如何確保底層少年的成長盡量不受到鄉村頹勢的影響,靠政府的單方面介入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具體到寄宿制學校的建設上,它原本是為了免除留守兒童受到外部傷害的一種應對之策,但從田野調查來看,外部傷害似乎被阻隔,而內部引發的幫派問題又隨之而起。這種條件下,社會組織的加入是一種必要的選擇。
然而,此前有調查顯示,在幫助鄉村留守兒童的活動中,社會組織總體來說沒有發揮專長,也沒有持續性、長期性活動。且社會各界對鄉村兒童的幫扶重點是救貧濟困,鮮有涉及心理或情感上的支持。
這些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說明社會組織力量的自我成長還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或許與社會各方對社會組織的態度也不無關系。一些社會公益組織在支援鄉村建設的過程中,仍舊受到不少觀念上的誤解和制度上的阻力,這些既拖延了社會組織對鄉村社會的關照進程,也阻礙了社會組織本身的發展。
鄉村底層少年的幫派化,其實是鄉村在傳統秩序瓦解后而呈現出原子化社會特征的一個縮影,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農村社會對于組織的需要。家庭功能雖然不能完全被其他的社會組織所代替,但在當前情況下,健全的社會組織將能夠有效規避農村家庭功能缺失可能帶來的弊端。
(《中國青年報》2015.8.10、《新華每日電訊》 ?2015.8.11)